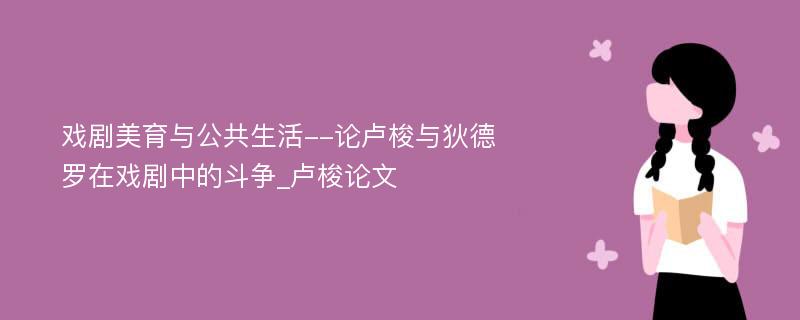
戏剧美育与公共生活——论卢梭与狄德罗的戏剧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戏剧论文,狄德罗论文,美育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2)06-0067-07
“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的这个重要观点对后世美育学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受其启发,绝大多数的美育理论都把人格的健全与完善视为艺术教育的核心目标。席勒及其追随者的基本预设是,当每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完善之时,由个体构成的社会也将随之走向道德与正义。然而,这一预设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另有一些美育思想认为应把对人的教育与公民的教育区别开来,为了社会正义和公共生活的完善,需要某种非人格化的审美教育(戏剧教育)。在席勒之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深入理解他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对完善和发展当代美育理论不无积极意义。
一、引论:一场有关戏剧的论战
175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Letter to D'Alembert on the Theatre”)的论文,公开了他与启蒙阵营的分歧。在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看来,“那是卢梭最柏拉图主义、最日内瓦调调和最吊诡的作品”[1]320。这篇论文表面上是在与达朗贝尔就日内瓦是否建造剧场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实质则暴露了他与整个启蒙阵营之间的深刻裂痕。
事件缘起于达朗贝尔准备为《百科全书》撰写关于“日内瓦”的条目,伏尔泰劝他在其中插入一个段落建议日内瓦应该有一个剧场,以达到敦风化俗、开启民智的效果。达朗贝尔在该词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解释:
戏剧在日内瓦不被容忍。这不是他们不支持戏剧本身,而是他们担心演员在青年人当中扩散浮夸、浪费及放荡的趣味。然而,难道没有可能用严厉的,演员必须遵守的准则来补救这些困难吗?以这种方式,日内瓦既有剧院,又有风尚,并能享有两者的优点。剧院演出将培养公民的趣味以及教导良好的举止、微妙的感情,这些没有演剧的帮助是难以达到的;在没有放纵(的情况下),文学将是有益的,并且,日内瓦将斯巴达的审慎与雅典的文雅结合起来。[2]4
达朗贝尔的这一提议代表了整个启蒙阵营绝大多数文人的看法,他们都把艺术看作是推进这项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因为艺术在破解宗教迷信,反抗政治权威以及推进世俗幸福与人生快乐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梭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达朗贝尔的词条激起了他的愤怒,他极力反对在日内瓦建造剧院的提议,认为此举将有害于城邦的良好风尚。卢梭的这封信延续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科学和艺术无助于道德和风尚的改善。
卢梭的这封信不仅质疑了达朗贝尔,挑战了伏尔泰,而且还终结了他与狄德罗的友谊。尽管这次决裂有很多私人方面的因素,但两人在思想方面渐行渐远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单就对待戏剧教育的问题,两人的看法就大相径庭:狄德罗对戏剧教育持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优秀戏剧带来的道德效果毋庸置疑:“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可能犯过的恶行感到不安,会对自己曾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产生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种品性的人表示气愤”,当那个坏人走出包厢后,他就“已经比较不那么倾向于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有效得多”。而在卢梭看来,人们根本不会因为看了戏之后变得善良,“费赫的那位暴君在剧院里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看戏,因为他怕被人家看到他同安德洛马克和普立安一起抽泣,而他对每天被他下令处死的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的哀号却充耳不闻,无动于衷”。[2]25
由此可见,卢梭和狄德罗都对当时戏剧的美育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分歧背后似乎体现了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关于戏剧美育的不同看法。因此,重要的并不在于在卢梭与狄德罗之间作出抉择,而在于探讨这种表面分歧背后的深层政治社会因素与人性理念。卢梭与狄德罗有关戏剧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特定社会因素和政治理念造成了这种分歧?如何理解这种分歧对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的美育问题又将提供怎样的启示?
在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有关狄德罗和卢梭戏剧美学已有不少成果,但由于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局限,并没有把启蒙时代的美学放到更为开阔的政治社会理论视野下给予观照。①卢梭、狄德罗都不单单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家,而是对人类命运充满忧虑的思想家,因此视野上的局限很可能遮蔽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政治思考与人性关怀。为此,本文尝试在学科交叉的视野中呈现两位思想家戏剧论争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社会与人生问题。
二、表演与异化:卢梭对戏剧的抵制
借着与达朗贝尔论战的机会,卢梭系统阐述了他的戏剧观。他不但从一般的意义上指出了戏剧绝无改善风尚的可能性,而且也在日内瓦的特定角度上论证了戏剧将对这一城邦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不仅从经济、道德、文化与政治层面对剧院的影响力做出了评估,而且还从剧本、演员、观众等多个角度抨击了戏剧之害。尽管他自己也曾创作戏剧并成就不菲,尽管他也曾提出过诸如戏剧“对好人是有益的,而对坏人却是有害的”这样的观点,但就整部作品而言,戏剧带来的危险与罪恶依然成为他论述的重点,借此来反驳他的启蒙运动的同行们有关戏剧的乐观看法。
有不少论者认为,这篇关于戏剧的论文几乎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的改写,无非是重复了古典主义的道德批判,似乎并无新意。[3]258不过尽管他在言说上极力向古人看齐,但在西方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语境中,卢梭的用意恐怕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牵涉到柏拉图式的“灵魂正义”,而且还更多牵涉到“社会正义”的问题。正如阿兰·布鲁姆所言:“《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就成了一部全面的理论著作,它从一个最具有激发性的角度来看待公民社会,即公民社会同心灵的作品之关系。”[3]255思考卢梭的戏剧美学背后所牵涉的公共政治问题,无疑将是准确把握其美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卢梭看到,剧场的引入所带来的东西将对政治共同体起到腐蚀与破坏的作用,而卢梭之所以将政治共同体看得如此重要,则在于他认可国家对个体的教育功能,因为正义的城邦有利于培养富有德性的公民。在一个风尚良好的城邦之内,戏剧并不能在道德的巩固和提升上起到丝毫的功效,它反倒可能迎合民众中存在的不良趣味,妨碍国家对公民的正常教育。这当中,卢梭提出的戏剧表演的问题是颇为引人瞩目的。他这样写道:
演员的才能是什么?就是装扮自己的艺术,模仿别人的性格而非自己的,不照自己的真面目表现给人看,貌似激情万丈实则冷血无情,如此自然地口是心非,好像他真的这样想,最后,完全忘却自己的地位而去占据别人的。演员的职业又是什么?这是桩交易,为钱财而表演。……演员的职业灌输给演员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呢?下贱、欺骗、荒谬的自命不凡和可怜的逆来顺受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使他适于扮演各种角色,就是不能扮演其中最崇高的人的角色,因为他们放弃了。[2]79-80
演员是怎样一种人呢?在卢梭看来,他是一种放弃自己而去表演他人的人。在舞台上,他过的是别人而非自己的生活。他善于通过有效的技巧和富于煽动性的动作与台词模仿他人的情感,他们通过这种“虚情假意”的演出还赢得了丰厚的回报。这种人为别人而活着,以扮演角色的方式活着。他们没有本真的自我,他们是伪善者,他们也因丧失本真而变得“异化”。卢梭是最早对现代文明条件下人性异化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卢梭的启发。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信息。”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传达信息的手段。在不少情形下,它本身就是信息。在信息的传播与交换过程中,交流媒介本身也会对整个文化精神的重心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4]10尼尔·波兹曼接受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4]12由此可见,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虽然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悄无声息、潜移默化。从钟表、书面文字,到电报、显微镜以及电视,不同的媒介对每个时代的风尚都具有不为人知的潜在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戏剧同样如此。在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戏剧其实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回看历史,18世纪是个戏剧的时代。这不单是指戏剧是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公共世界中最重要的艺术,同时也涉及戏剧作为一种媒介对时代环境的深远影响。翻看当时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人生如戏”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就曾这样写道:“世界经常被用来和戏院进行比较……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深入人心,某些戏剧用语起初只是通过引申比喻才能被应用于世界,但如今它们已经能够被毫无差别地直接应用于两者:因而当我们在谈论日常生活时,常常会熟极而流地使用舞台、布景之类的词汇,仿佛我们所谈论的是戏剧表演……”[5]136-137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戏剧,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的生活,也逐渐呈现出戏剧化的特征。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如戏剧舞台上表演的演员。
可以看到,卢梭的戏剧观基于他的整个教育理念。他看到戏剧表演的威胁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伤风败俗,而且更在于戏剧表演的形式造就了整个社会的舞台化和面具化。人通过戏剧学会了扮演他人,而且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状况之下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在一个人人都戴着面具的社会里,他们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卢梭痛恨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腐化了的人,不再具有自然天性。他们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却从来不愿意真诚地袒露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卢梭的《忏悔录》体现的是一种与戏剧美学相对抗的自传美学;因为只有在自传中,作者才能摆脱虚伪的面具,显露真诚的灵魂。
关于教育,卢梭曾刻意将人的教育与公民的教育区分开来:人的教育追求保持人的自然天性,而公民的教育则把目标设定在政治义务的履行。但这两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卢梭的教育理念可被理解为两个层次,与之相反,人格与政治理应保持高度的统一。“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卢梭把政治的正义建立在人格的基础上,无论他是自然人还是城邦的公民,只要他是真诚的(或按斯塔罗宾斯基的说法,是“透明的”),而不是伪善的,布尔乔亚式的,那么建立在真诚人格上的政治也将是正义的。
基于这样的理由,卢梭对戏剧的批判存在着理论上的合理性。因为戏剧的表演形式正在剥夺人的真诚,而这种真诚正是卢梭式政治正义的基础。但卢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个体生活与公共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理所当然的统一性。真诚的人格并不一定促进政治的正义,而为了促进政治正义,似乎需要一种更为特殊的公民教育来区别于这种人格教育。在这个问题上,狄德罗显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三、表演与接受:狄德罗的戏剧情结
与卢梭的反社会的孤僻个性不同,狄德罗更能适应城市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因此他对戏剧也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他1769年撰写的《论演员的悖论》(“Paradoxe sur le comdeien”)中,他将社会比作剧院中的舞台:“舞台好比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了整体和全局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某些权利。”[6]293除了创作大量戏剧作品之外(如《私生子》《一家之主》以及《订亲的姑娘》等),狄德罗还长期不懈地致力于戏剧理论研究,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莱辛曾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从没有一个哲学家心灵像他(狄德罗)那样关切戏剧。”[1]312
在对戏剧美学的诸多理论贡献中,狄德罗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以及在理论上创立“市民剧”,无疑是多数狄德罗美学思想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本文对此不做过多的讨论,而是把重点聚焦于狄德罗有关戏剧表演的看法,正是在关于戏剧美育对于公共生活的这一重要问题上,他得出与卢梭截然相反的结论。
狄德罗在戏剧这一艺术类型中发现了在艺术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界限:“只有自然而没有艺术,怎么能造就伟大的演员呢?因为在舞台上情节的发展并非恰如在自然中那样,而戏剧作品都是按照某种原则体系写成的。”[6]279在《论演员的悖论》这部作品中狄德罗的核心看法是,一个演员若要演出成功,若要有效地表现出剧中人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必须保持冷静与克制,而不能过于激动。因为:
那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演员必须具备的根本品性。我要求伟大的演员有很高的判断力,对我来说他必须是一个冷静的、安定的旁观者,因此我要求他有洞察力,不动感情,掌握模仿一切的艺术,或者换个说法,表演各种性格和各种角色莫不应付裕如。[6]280-281
反过来说,一个缺乏训练,容易动感情的演员往往不会获得成功:
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你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一致性;他们的表演忽强忽弱,忽冷忽热,忽而平庸,忽而卓越。今天演的好的地方明天再演就会失败,昨天失败的地方今天再演却又很成功。[6]281
在狄德罗的演员辞典里,一个好的演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判断力”、“精细的处理事物的机智”以及“准确的鉴赏力”,当然还有一点,“他们是世上最不易动感情的人”。在他看来,“演员的哭泣好比一个不信上帝的神甫在宣讲耶稣受难。又好比好色之徒为引诱一个女人,虽不爱她却对她下跪;还能比做一个乞丐在街上或者在教堂口辱骂你,因为他无望打动你的怜悯心;或者比做一个娼妓,她晕倒在你的怀抱里,其实毫无真情实感”[6]287-288。演员在舞台上是靠演技来征服人,而不是靠真情来打动人。
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卢梭无法同意的。这样公然地为演员辩护,这样公然地容忍并赞扬虚情假意的演出,也是后者所不能理解的。在狄德罗看来,在正式的戏剧表演中“真诚”是不合时宜的,表演不是真情流露,而是制造真情的幻象:“演员的眼泪从他的头脑中往下流;易动感情的人的眼泪从他的心头往上涌。”[6]287真正优秀的演员为了达到好的表演效果,需要凭借他对人性的钻研,凭借他对人类的观察,以及每一次表演的比较和揣摩。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研究过程中,演员的表演水平才能达到很高的造诣。莱辛也认可这个看法,虽然演员在表演中似乎是无动于衷的,但在舞台上却远比那种感情激烈的表演要好。[7]单从戏剧理论的角度看,狄德罗的贡献极大。他“为知性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和艺术的自主性提出了有力的辩护”[1]346(彼得·盖伊),他也是“第一个认为表演本身是一种和表演内容没有关系的艺术形式的人”[5]139(理查德·桑内特)。
那么,狄德罗为什么认为不动感情才是表演的真谛呢?是怎样的问题视角让他作出这番思考呢?这就牵涉到狄德罗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狄德罗较之卢梭更为清醒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以演员的方式活着。随着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人与人的关系交往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正是在当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到一种被称为“社会”的事物,在“社会”这个空间里,存在着大量的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探寻人际交往的方式。戏剧表演在那个时代恰恰为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指引与导向。
剧场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将情感传达给台下的观众,这种传达的有效性靠的不是满腔赤诚,而是技巧。在陌生的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和互动,依托的也是这种非人格的技巧,“在舞台上和在社交界一样,感情冲动只会带来危害”。狄德罗认为,一个演员在台上真情流露,未必能造成台下观众的共鸣,反过来,台上的演员刻意制造的感情,却能更有效地激发观众的情绪。“倘若你把自己亲切的语气,朴实的表达方法,日常的姿态,自然的举止照搬到舞台上去,你会看到你将变得贫弱可怜。你的眼泪流得再多也是徒劳,你变得可笑,而别人则会笑话你。”[6]288因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只有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节制情感扮演角色,才能达到人际间良好的互动。正如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两个个体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需要交流人的经历、烦恼和秘密,那么都市生活对我们来说就会变成难以忍受的折磨。”[8]40狄德罗洞察到了那个“作为演员的人”对于公共生活的重要价值,为此理查德·桑内特才坦言,“狄德罗是第一个将表演当作世俗活动的伟大理论家”。[5]139
四、从人到公民:美育的公共维度
由此可见,狄德罗对戏剧美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人格教育的层面,他更多看到的是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在表演提供人际交往原则和塑造公共生活秩序方面所彰显的价值。正如日本学者山崎正和所言,在社交场合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私人生活。在社交场合,人们需要像在戏剧中那样扮演角色。在社交场合最大的忌讳就是“弄错场合,不能直觉地把握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这样的人就会被排除在戏剧的幕外”[9]18。礼仪就相当于社会舞台上的表演规则,它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言行举止的合宜准则。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详尽地描绘了礼仪在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发展,并认为它是对人类天性的调节和控制。正是这种对情感的控制,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狄德罗看到,戏剧艺术教会人学会如何扮演,学会如何控制自我的感情,学会如何有意识地制造人为的情感,这种情感将有助于交流对象的有效接受。戏剧艺术确实能够充当一位生活的教师,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导了人们公共空间中的相处之道。
卢梭的信徒们必然会对此表示质疑:人为什么需要社交,难道社交不是人性的某种异化?在此,大致有两种理由可以来回应这种质疑。其一,有不少论者认为,社交同样是人的本性,并不存在着异化的问题。相传是法国作家乔治·桑的祖母的回忆,18世纪的人们都相信活在人世间与人相会是人生的最大目的。[9]7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则认为:“社交不只是消磨时间或铺张浪费,而是人们为了人性化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活动。”[9]34桑塔耶纳甚至认为这种社会化的人格更为真实:“凭借我们公开声明的信条和誓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隐匿我们的情绪与品行之间所有的不一致,这并不是伪善,因为我们审慎蓄意扮演的角色是比我们不由自主的飘然梦幻更为真实的自我。”[8]46无论从史学还是社会学层面,我们似乎都难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社交是人性的异化”这样的看法。
其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社交的“非人格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极为必要,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开辟和捍卫政治的公共领域。由剧院模式所引导的人际社交,会把人们从自恋式的自我中带离出来,并把他们引向多元和差异的公共空间中。它有效地阻止人们以一种情绪化、人格化的态度去看待政治人物和社会事件。它将成为一道屏障有效地阻止社会向极权主义下滑,它也将成为一股力量,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②
与之相反,痛恨社交的卢梭从一开始就认定了“非人格”社会的罪恶,这种社会对“透明”的人格造成了“阻隔”(obstacle)。他一生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揭去这些掩盖自然和天性的面纱(veil)的事业中。作为自我,他可以在《忏悔录》中揭去自己的面纱,来凸显人格;但又如何揭去他人的面纱,如何揭去政治的面纱,实现这所有一切的真诚化与人格化呢?桑内特指出,卢梭在这点上终究是反动的,他竟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只有将一种政治的专制强加于人类身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拥有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对立面——真诚的关系。在此后的法国革命中,卢梭式的“真诚”终究演变成一出出血腥的恐怖。革命之所以不断杀人,就在于人们随时随地都会找出不真诚的人。[10]由于看不到道德与政治的区别,看不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这使得他的思想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五、结语
卢梭与狄德罗有关戏剧表演的争论,的确是个争讼已久的话题。在今天的戏剧院校以及表演艺术界,也依然维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过在考察这两位法国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单单是一种审美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其实更是一种政治社会认识上的偏差。启蒙思想家的美学不可能是后来所谓的“纯”美学,一定是与整个现代文明的转型以及新兴的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卢梭与狄德罗的戏剧美育之争,根源在于个体的人格教育与社会的公民教育之间的区分。在卢梭的意义上,他想用个体性真诚性的政治来取代公共性模仿性的政治;而在狄德罗的意义上,个体性是个体性,公共性是公共性,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卢梭的思想批判旨在抹平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因为正是两种生活领域的隔离导致了现代人格的异化。人在私人生活中如何生活,那么在公共生活中也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人的自然的真实的生活。为此他反对一切扮演,反对一切模仿,他希望一切社会都能建立在自然人格不受扭曲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狄德罗则鲜明地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彻底割裂开来。他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设置了完全不同的行事原则,并将自然与艺术截然对立起来。在私人生活中他也倡导自然,但在公共生活中,恰恰是不自然的行为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得以可能。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在狄德罗与卢梭之间作出取舍。狄德罗对公共生活的敏锐洞察和卢梭对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尖锐批评都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代,戏剧表演也早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媒体王国的兴起。一方面,人们在面对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介的过程中愈来愈远离公共世界而陷入自恋之中;另一方面,当真诚成为这个时代唯一道德标准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热爱这种价值。因此在今天,我们依然能通过狄德罗的大脑来深刻洞察人类公共生活的本质,也依然能通过卢梭的心灵来感受这个时代的腐化与堕落,由他们的精神所灌注的那个戏剧时代,终究留给人们无限的思考与怀恋。
收稿日期:2012-09-11
注释:
①现有的对两人戏剧美学思想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狄德罗用“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市民剧来代替17世纪主要为封建宫廷服务的新古典主义戏剧,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武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54页。
②关于这点可参见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以及理查德·桑内特的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