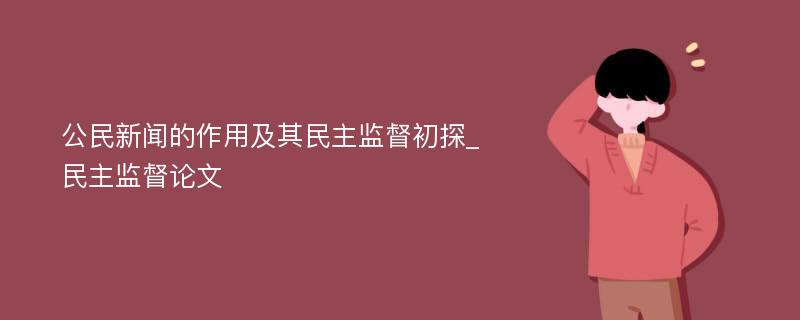
公民新闻及其民主监督作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民主论文,作用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新闻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概念之一。“公民”一词从古希腊直至当代的含义演变,不仅体现了公民新闻的特异之处,亦表明了它在当代政治及社会运作中会起到重要的民主监督作用。
一、何谓公民新闻
关于公民新闻的概念和内涵,在学术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将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等同于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此观念起源于学者对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①,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也可以称为公民新闻运动(Civic Journalism Movement)。其实从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过程看,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存在不小差异。郑一卉(2012:27-30)认为,公共新闻是该运动的首倡者杰伊·罗森和戴维斯·梅里特率先使用,获得大部分公共新闻研究者的认同。公民新闻乃是公共新闻运动的重要资金支持者皮尤新闻中心成立之后选用的术语。在皮尤新闻中心的专家看来,“公共新闻”这一概念过于政治化,而“公民新闻”的政治色彩则较淡;“公共新闻”中核心的概念“公众”过于模糊不清,而“公民”一词则指涉明确;此外,“公共新闻”开始于对政治选举报道的关注,内容狭窄,而“公民新闻”的议题显然要宽广很多。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迥异于公共新闻(Public/Civic Journalism)。此处所谓的公民新闻,与第一种观念中的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邵培仁、章东轶(2004)将Citizen Journalism译作“市民新闻学”,认为市民新闻是指“市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和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两位作者在探讨“市民新闻”这一新闻现象时,特别强调了新传播技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以韩国新闻网站OhmyNews为例给予阐发,并未将其与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共新闻”联系起来。这与公共新闻理念中将新闻记者和传统新闻媒体看作新闻活动的主体,显然迥然有别。余建清(2008)对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的差异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兴于1980年代的新闻改革运动,后者始于2000年韩国OhmyNews新闻网站的成立;二者的实践主体也有差异。杨保军(2008a;2008b;2008c)为了区分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特意将民众或社会大众自主传播、不经过新闻组织编辑、过滤的新闻定义为民间新闻,目的是将其与公共新闻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公共新闻又被称作公民新闻,二者易于混淆)。
第三种观点认为,凡是有公民参与新闻生产的新闻活动,均可称作公民新闻。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专业新闻与公民新闻的融合。范东升(2006)虽然认为公共新闻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那场公共新闻运动,但他也更强调公民新闻是公民依托互联网传播技术介入新闻生产流程的活动。吴乐珺(2007)认为新闻生产的“重包”模式催生出一种专业余新闻(Pro-am Journalism,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的新闻)。这其中既包括公民自主完成的新闻传播活动,也包括公民与传统新闻组织共同进行新闻生产。斯蒂夫·奥汀(2008)则认为,公民新闻存在着11种潜在变体,其中很多是传统媒体与公民新闻的融合。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公民新闻是一种与公共新闻不同的新闻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二者区别,那就是公共新闻是以公民为对象的新闻,公民新闻是以公民为主体的新闻。前者的新闻活动主体是传统新闻组织内部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目标虽好,但却有些一厢情愿,单纯依赖基金、项目等外力支持,未能常态化,成效也较为有限;后者新闻活动的主体及服务对象都是公民或者公民群体,他们知道自身最希望传播和接收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这真正激发了公民(生)产、消(费)新闻的热情。从新闻活动的载体来看,公共新闻依然以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为主,且大多是地方性、社区型小型媒体;公民新闻的活动载体则是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兴传播工具。
以上对公民新闻的分析是从源流与形式上给予的界定。笔者认为,认识公民新闻,厘清其来源与形式固然必要,但“公民新闻”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概念在于“公民”二字,只有厘清“公民”的内涵,才能对公民新闻有一个透彻清晰的认识,也才能真正理解公民新闻是在何种意义上起到了民主监督作用,进而又如何促进了监督式民主的发展。
二、公民是谁:公民新闻的公民观
在Public Journalism、Civic Journalism、Citizen Journalism三个新闻概念中,Citizen Journalism一词出现最晚②。在public、civic、citizen三个词中,根据《美国传统英语词典》,public有“与共同体和人民相关的”、“人民或共同体所主张的”等含义,又可以指“人民或共同体自身”、“分享共同利益的群体”,带有明显的“公共性”色彩;civic则有“公民的或者公民身份的”之意,可以说与citizen指拥有选举等诸权利的“一国之公民”或“一城之居民”意思非常相近,二者都强调公民自身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citizen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又常常被翻译为“市民”,citizen journalism也因此被有些学者译为“市民新闻学”,其实此“市民”恰恰就是彼“公民”。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对于公民资格有严格规定,外邦之人、奴隶、妇女、儿童都不在公民之列,而实际上能够参与公民大会,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通常而言,只有那些拥有一定资产,有财力又有闲暇参与城邦管理的少数人,才是真正意义上既有公民资格实际上又可参与城邦事务的人,而这些人又大都是脱离农业生产(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即对农民极为蔑视)的市镇居民,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公民”与“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群体。从现代意义上讲,公民的概念早已突破了古希腊“市民”的范围,扩展为一国之民,所以citizen journalism译为“公民新闻”应更为恰切。
在原初的意义上,公民概念中即有“公”、“私”之分。在汉娜·阿伦特(2009:33)看来,作为一种社会或者政治的动物,人既在家庭中生活,又身处城邦之中。家庭对应于公民之私人生活,城邦对应于公民之公共生活。相比家庭生活的权威专制,城邦生活是自由的、协商的、说服的、高尚的,它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聚合的公共领域:“我们的现实感完全依赖于呈现,从而依赖于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在那里,事物走出被遮蔽的存在之黑暗并一展其貌,因此即使是照亮了我们私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微光,也最终来源于公共领域更耀眼的光芒”。这大抵是从公民的活动领域出发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对象所做的区分。在那里,公民之“公”,主要指公民承担的是“一个融入城邦共同体的公共性角色”(张凤阳,2006:134)。
古希腊以后,积极公民的角色逐渐被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销蚀,直到经历启蒙运动之后,启蒙思想的传播带来人本主义的高扬,现代公民逐渐诞生。现代社会的积极公民,在社会行动中,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一是私人性质的活动;二是公共性质的活动。杜威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处于共存状态,人与人之间亦处于共存状态。当一个人的行为结果只涉及和影响直接参与活动者的时候,这种活动即是私人性的;当一项活动的结果对未直接参加活动的人产生了“广泛、持久、重要的间接影响”,这种活动就是公共性的(转引自威斯布鲁克,2010:319)。杜威的划分着眼于社会行动,但其突破了古代公民家庭与城邦的空间二元对立,论述的对象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着眼的是公民行动的结果及其影响,虽也是“公”与“私”的二元划分,但杜威意义上的私人性质的活动因现代公民所具有的平等、自由等广泛的权利,远远超出了阿伦特所谓的古代公民的家庭式私人生活。
杜威对公民行动的两种划分方法,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公民新闻极有启发价值。公民新闻中的公民是现代社会中集权利、义务于一体,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其从事的新闻活动依性质划分,亦可分为两类:一是私人性的公民新闻,二是公共性的公民新闻。私人性的公民新闻,是立足于自身,将公民个人生活中的变动信息以文字或者影像等符号形式向外界发布并进行传播的活动,其特点是与己相关、与他人无涉。在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私人性的公民新闻已成为新闻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斥于博客、播客、微博、BBS等空间。此类公民新闻的兴起当然有赖于技术条件,更为重要的,它与内在于人自身的游戏精神紧密相连——西美尔认为人类去除了生存迫切性而进行的活动乃是一种“社会游戏”;赫伊津哈则把人类在特定时空中进行的非强制性的自愿活动称为“游戏”,认为人本身就是游戏的人,游戏本身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而杜威更是干脆将人称之为“嬉戏的动物”,具有诉诸感觉、实践与玩乐的本性。(约翰·德拉姆·彼得斯,2009:105;山崎正和,2008:30-32;约翰·赫伊津哈,2007:31)私人性的公民新闻正是体现了公民游戏性的一面,所传播的信息极具个性化和个人色彩。公共性的公民新闻,是公民发布的对其他公民、社群乃至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一己之利、一己之乐,带有很强的公共性。在杜威看来,公众就是那些“所有受到活动的间接结果影响的人”,作为个体的公民既影响他人,亦受他人影响。从公民的这个属性看,公共性的公民新闻以其显著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公民新闻区分来开。更重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传统的组织性新闻媒体同样甚至是更有效的传播权力,对政治运作和社会公共事务起到至关重要的民主监督作用。
三、以监督为核心:公民新闻的民主监督作用
民主理论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认为,民主自诞生之后,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公民大会民主(Assembly Democracy)阶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10世纪;第二阶段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阶段,从10世纪直到今天,且已成为当今民主的主流;第三阶段是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阶段,1945年至今,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基恩认为:“民主的价值观及相关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民主的含义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在监督式民主阶段,“无论人们为何种国籍,宗教和文明信仰是什么,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对民主的话语、观念以及制度已颇为熟悉”,民主既是“全球化的”,又是“普适的价值观”,“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Keane,2009:xv,xxiii)。
在基恩看来,太平洋两岸的民主理论家,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约翰·邓恩(John Donne)、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人,以代议制为描述对象的精英民主理念仅仅是围绕议会政治展开讨论,而1945年以后议会之外的权力机制风起云涌,对全球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上述民主理论家的观念已经与现实脱节,尤其对于当代新技术不断涌现,公民通过新技术手段在各个层次参与民主进程的现状失去了解释力。而监督式民主呼应社会发展,它“是‘后议会’政治的一种变体,由迅速发展的许多不同类型的议会外权力审查机制所界定,是民主的新的历史形态”(Keane,2009:688)。与以往的民主形式相比,监督式民主有显著的优势:第一,为公民提供有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多样化的信息和观点,使其置于公民的审查之下;第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通过普通大众运作;第三,与民主的“大众权力”、“大众监督”、“防止不正当决策”的本意相契合;第四,强化了多元化和参与性;第五,是一种对权力最为敏感的动态民主。(基恩,2011:204)与监督式民主塑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网络”相似,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公民成为随时随地的新闻发布者,构造了一个遍布社会诸领域的新闻发布网(同时也是权力监督网)。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讲,公民新闻的主体亦是民主监督的主体,同时因其社会分布的广泛性,公民新闻又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监督对象宽广的特点。在新闻业以往的鼓吹模式、市场模式和委托模式下,普通公民在新闻活动中都是边缘角色,只有被动接受信息的权利,而无主动参与信息传播的机会。行使民主“看门狗”职责的是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而不是公民自身。当新闻传媒成为一种巨大的利益集团的时候,为了自身利益,新闻业极有可能将民主看门狗的角色弃置一边,对此,公众仅有批评指责的权力,而很难改变现状。换句话说,传统新闻业提供给社会公众的新闻往往是模式化的,对于社会议题往往根据自身需要精心设计报道议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新闻活动“自发”地屏蔽了许多信息,这些信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众急于了解和渴望了解的。更重要的,不同媒体之间,会互设议程,这也导致新闻的趋同化,多元的信息难以面世。公民新闻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每一个公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摆脱了传媒中介,公民成为新闻生产和民主监督的主体。与组织化的新闻传播活动相比,公民新闻活动参与主体以个体为主,更具独立性,不为私利左右,更具公益性。2010年,维基百科解密了美国有关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的数万份机密文件。全世界的读者包括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有了全面的了解,此举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政府进行阿富汗战争的持续不断地抗议。值得一提的是,维基百科的这次“解密行动”并非一时兴起,在此之前和之后,它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所谓秘而不宣的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经事件,乃至于非洲国家的政府腐败等给予了多元化的、透彻的“报道”,开拓了传统媒体没有能力进行报道的题材和领域,为公众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新闻资讯,取得了传统媒体难以望其项背的民主监督作用。更为重要的,维基百科的“解密新闻”并非广受瞩目的朱利安·阿桑奇一人所为,在世界各地,有数以千计的“阿桑奇”在致力于公民新闻的发现与发布,维基百科及“维基人”无疑是这个时代公民新闻的代表,他们关注着这个世界各个领域不易觉察的一举一动,以执著专业的精神,为世人发掘出传统媒体难以操作的新闻,构造了遍布全球的监督之网。
公共性公民新闻具有很强的民间色彩,对公权力运作的民主监督常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且常常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公权力的行使是政府官员代表国家对某些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从源头上讲,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是共同体成员为了实现公共善,让渡部分私权利由国家代为行使。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让渡了部分权利的公民,为了共同善的实现,防止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做出有损于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必要的监督。20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乃是一种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精英民主形式。之所以依然是民主的,是因为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是经由人民投票产生经历优胜劣汰的民主竞争程序。在精英民主模式下,对权力的监督往往求诸于制度,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是其典型的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机制。在这种模式下,民主的有效运转,依然仰赖于各分权领域内的少数精英分子。自治是民主的本质含义,在精英民主模式下,除了程序性民主之外,自治的理想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参与式民主的出现为公民实现自治创造了条件,而建立在新的传播技术基础之上的公民新闻无疑大大拓宽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治的可能性。在异常情况下,公民新闻常常成为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并凭借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能力聚集起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而动员不同阶层的公民参与到社会运动和公民新闻扩散的队伍中来。历史上,新闻媒介就曾经为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查尔斯·蒂利(2009:116-117)就认为:
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布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指的是社会运动中的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奉献——commitment。——引者注)展示发生转型。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虚拟动员和现实运动的结合,二是新媒体上的虚拟串联。2007年,当PX项目即将上马的消息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厦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行动吧!参加万人游行,时间6月1日上午8点起由所在地向市政府进发!手绑黄色丝带!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张晓娟,2007)这既是一条动员信息,也是一条关于当地民众反对PX项目运动最新进展的公民新闻。这条新闻随后通过手机和互联网迅速流传,厦门社会各界乃至于全国各地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这场监督公权力使用、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环境的运动中,他们实时跟踪事态进展,及时利用网络、手机、BBS等新媒体技术更新和传播新消息,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普通大众自发的自上而下汇集起来,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我们也看到了媒介化时代公民新闻的力量。
公共性公民新闻对权力极为敏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民主监督机制,具有自发性、偶然性等特点,而正是庞大的公民群体的广泛参与,同时使得公民新闻真正做到了民主监督的动态化、常态化。在实际运作中,此类公民新闻参与主体具有明显的集群效应——一则公民新闻的发布,引发更多公民的参与,新的信息不断加入,新的观点不断呈现,直至出现舆论放大效果,最终使公民新闻的民主监督机制真正生效。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公民新闻的影响并不是由单一的个体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来决定的。”(彭兰,2010)此外,公民新闻还深受“自组织”规律的影响。童兵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活动是“以传播者为核心的自组织系统,它的组织化过程,是不断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自组织系统的运作过程,不受组织系统以外的力量的干预,而是系统内部事物或者变量自动引起和维系的。(童兵,2012)应该说,相比较传统的组织化新闻活动而言,公民新闻的“自组织”色彩更加突出,它深受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尤其在公权力监督方面,公民多是出于维护个人权利或秉持社会正义,自发地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民主监督,少有功利色彩。公民新闻的“自组织化”和“集群效应”使它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同时由于监督主体的公民具有分布广泛(超越一国一地,真正是跨时空的)、及时敏锐等特点,更增加了民主监督的有效性。自发性、偶然性的公民新闻促成了传播共同体的出现,这些共同体不一定长久存在,也不会保持规模不变,但是其成员却可以通过发布公民新闻共同致力于对民主监督。虽然詹姆斯·凯瑞推崇“社会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的观点,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认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凯瑞,2005:3,16,10)。但是参与仪式的人在何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与他们共享“参与仪式”的感受?在传统媒体环境中,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一定不能解决,但是实现起来确实非常不易。可以说,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出现,真正使凯瑞所提的“传播仪式”有了现实意义。人们通过公民新闻,不仅可以共享意义,而且可以分享参与的感受,可以为了共同的兴趣、目标和所遇到的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极为便利地与五湖四海的“同好”结为共同体,协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引发围观的“天价烟”、“表哥”、“红十字会”捐赠账目、“房叔”、“房姐”诸事件中,我们均可以看到公民新闻发布者们那紧盯权力的敏锐目光,正是因为有了前赴后继、聚沙成塔的诸多公民新闻对权力的持续追踪和报道,我们看到了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民主监督新机制,也为社会的民主化增添了更多希望和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性的公民新闻因其只关心一己之事,对公民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有一定的消解作用。私人性的公民新闻在实现新闻自由、新闻民主方面自有其价值。但是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讲,私人性的公民新闻是建立在“嬉戏性”、“游戏性”基础之上的,传布的信息,多是为了自娱,不会对社会及其他公民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共性色彩极为淡薄。此外,即使是少量以“公共性”为指向的公民新闻,由于受到公民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融合了大量评论,以观点代替事实,毫无客观性可言,更有甚至可能会为了某种目标而传播虚假信息,貌似负责任,实际上已突破了新闻真实性的最低界限,背离了新闻的本质③。(郑一卉,2012:144-145)如果在新媒体上充斥着此类公民新闻,公共性的公民新闻因此而被冲淡、淹没,其民主监督的作用可能因此而无从发挥。
四、结语
在人类的诸种传播活动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特别看重口头传播的价值与作用,在他看来,口语传播是最不容易控制和不易产生垄断的传播方式,而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并非如今的数字媒体)是最易产生垄断的,而垄断的结果,就是传媒只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服务,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公民新闻再一次将易于受到控制的新闻自由解放出来,重新交还给公民自己,它使公民在真正拥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切实担负起了民主监督的作用。它对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起到多大作用,又会走向何方?也许,正如基恩认为对监督式民主还有待观察的看法一样,我们对公民新闻的发展及其与民主的互动关系的全面认识也尚需时日。
注释:
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吴惠连(2002)就认为:“在重新贴近读者的尝试中,从新闻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新闻运动,有时也称为公众新闻运动。”蔡雯(2004)认为:“公共新闻,在美国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②以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看,在2000年以前,研究者一般将公共新闻称之为“Public Journalism”,而2000年以后,则使用“Citizen Journalism”更为普遍,也有少数学者偶尔会使用“Civic Journalism”一词。
③郑一卉认为,公民新闻缺乏客观性、原创性内容很少、对普通民众没有吸引力,而且很多公民新闻的记者本身就是传统的新闻组织的从业人员,因此公民新闻根本不能对传统的组织化新闻活动构成威胁,相反,公民新闻的出路在于职业化,而职业化就意味着公民新闻的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