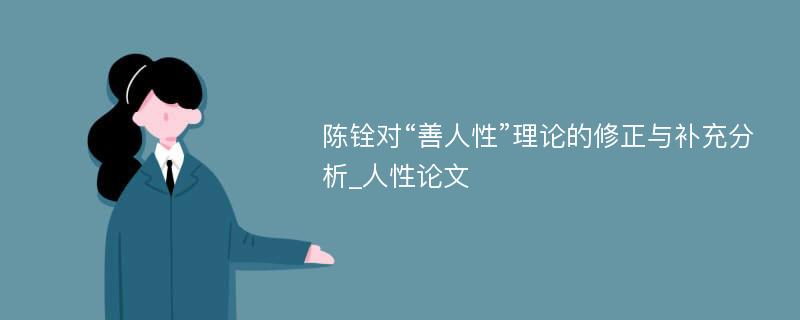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理论论文,试析陈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确是我国明清之际的一位思想家,在当时思想界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潮流中,他占有一定的位置。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其思想的研究却比较缺乏。本文试就其对我国传统“人性善”命题的修正和补充谈点粗浅的看法。
“人性善”命题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提出,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如孟子、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说明和论证。陈确在以人性一元论批判程朱人性二元论的过程中,作为重要的理论根据沿用了这一传统命题,并在对“人性善”学说给以发挥的同时,对其传统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
一
中国传统性善论中,最早有孟子的“四端说”。他认为,人先天具有善的萌芽、趋向,即“善端”,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之心是人生而具有的,故人性善。若能将此“四端”之心扩而充之,人们就具有了仁、义、礼、智的德性。后来,王阳明和陈确之师刘宗周以“良知”规定性善的内涵,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良知”,比如“是非之心”。通过扩充善念、克除恶念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功夫,就可以保持良知。他们都把性善与“致良知”的修养功夫结合了起来。到了黄宗羲又回到了孟子,甚至比孟轲还要彻底,认为仁、义、礼、智之性现成地存在于“人心”里,无待扩充。陈确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学说。
陈确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孟子。在孟子性善说中,有“浩然之气”之说,它体现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同时,孟子还谈到“才”,它似与“性”是同等的概念,具有天生“材质”的意思,是就人性本善说的。另外,在孟子那里还有“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注:杨伯峻:《孟子导读》,第190页,巴蜀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是其人之情也哉”(注:杨伯峻:《孟子导读》,第190页,巴蜀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使用。他所谓的情具有“本来的样子”、“实际状态”的意思,也是指人性本善而说的。陈确继承并发挥孟子的思想,认为人性不存在程朱理学所谓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分别,不存在所谓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人性是针对现实存在的人而言的,是与现实人生融合为一的,指人的气、情、才。如陈确语:“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注:《陈确集》第45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由性之流露而言谓之情,由性之运用而言谓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谓之气。”(注:《陈确集》第451~45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 )“气情才而云非性,则所谓性,意是何物?非老之所谓无,即佛之所谓空矣。”(注:《陈确集》第454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就是说,在陈确看来,气情才即人之性,是人性的表现和具体、现实的形态。性本身是不可见的,它通过气情才表现出来。他进一步解释说:“今夫心之有思,耳目之有视听者,气也;思之能睿、视听之胡聪者,才也。”(注:《陈确集》第453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欲’字兼才情言。”在陈确看来,气情才指现实人的形态所具有的各方面素质或特性的综合,是与人的生命密切联系的,其中,“情”大概指人的各种需要的自然流露;“才”指人本身所固有的能力;“气”则指人的形体的自然存在状态及其特性。陈确所谓人性善,即气情才善。他说:“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论自此大定,学者可不复语性矣”。“子曰性相近,本从善边说”(注:《陈确集》第447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性之善,不可见,分见于气情才”(注:《陈确集》第45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情才气有不善,则性之有不善不待言矣”(注:《陈确集》第45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人性有善而无恶,故气情才有善而无恶”(注:《陈确集》第45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性皆善,人性善等同于气情才善。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他将气情才看做人之性。他认为,《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明性之善,都是就气、情、才而说的。
陈确进一步认为,气、情、才之善在于他们都是性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孟子说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注:杨伯峻:《孟子导读》,第217页,巴蜀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表示人天生所固有的知善为善能力。陈确认为,气、情、才是人先天所具有的善性,是知善为善,固人性善。用他的话讲“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无不善也”(注:《陈确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不为,非不能也”(注:《陈确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以人具有“为善”的能力规定性之“无不善”,这使陈确哲学出现了漏洞:人不仅具有为善的能力,同时也具有为恶的能力。也就是说,善与恶就人的能力和倾向性而言,是机会均等的。何以以性为善而非恶呢?这一点,陈确的同门学友黄宗羲已经有所察觉并给以揭露:“老兄虽言‘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无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为不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善反得半而失半矣。”(注:《陈确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为了弥补这种理论上的缺陷,陈确提出了“习”的概念。
二
“习”在陈确那里是相对于生而具有的“性”而言的,指后天对人的影响,是人有善恶之别的原因。按他的观点,既然性是善的,是社会上善的现象的来源,那么恶的现象就必然要归结于后天的影响,归结于“习”。在他看来,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素质和属性,是纯善,“习”作为与先天东西相对应的后天影响,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他说:“学孝弟,习考弟,方可谓之善学善习;孩提之爱、稍长之敬,良知良能,不待学习。过此便须加学习之功。”(注:《陈确集》第149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就是说,就人之良知良能的性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善恶之区别,是“习”作用的结果。如他所说:“盖相近者性也,相远者习也。”(注:《陈确集》第539页, 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气清者无不善,气浊者亦无不善, 有不善乃是习耳”(注:《陈确集》第45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即:“习”是万恶之源,“习”的作用是“善性”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在陈确那里,从根本上“习”是被排斥在“性”之外的。陈确非常强调“性”与“习”二概念的区别。“有善有不善之相远者,习也,非性也。”(注:《陈确集》第455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于性何有哉?”(注:《陈确集》第458页, 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圣人辨性习之殊,所以扶性也。 ”(注:《陈确集》第454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性、习之别,以习为性,从而得出了性有善有不善之论。只有从根本上将“性”与“习”区别开,才能认识“性”之善。
陈确的《性习图》更充分、更明确地表明了他所谓的性习观念,并通过性习关系说明了“习”在人的善恶形成和转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其一,在图中,“性”居中,“上智”和“下愚”分处两端,说明二者都不属于“性”的范畴。其二,形成“上智”与“下愚”的决定性因素即是“习”,“习善为智,习不善为愚;习善不移为上智,习恶不移为下愚”(注:《陈确集》第458页, 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 “习”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上智”与“下愚”、善与恶的区别。其三,智与愚、善与恶之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彼此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的中介就是“习”。陈确在《子曰性相近也二章》中说:“习相远矣,虽然,犹可移也。 ”(注:《陈确集》第459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黎翔凤:《周易新释》,第25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8月出版。)“盖移之,则智者亦愚, 愚者亦智。”(注:《陈确集》第45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这样,陈确实际上说明了:性无善也无恶,“上智”和“下愚”、“善”和“恶”都是“习”作用的结果。并且,通过“习”的作用它们还可以相互转化,即陈确所谓“人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注:《陈确集》第45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这样就等于否定了性善论。本来陈确提出“习”的思想是为了论证其性善论,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了反面,从而使其人性论陷入了致命的危机。对此陈确无奈地指出:“谓性有不善,固是极诬,即谓性无不善,亦恐未是实见,不若相忘无言,各人去尽心于善。尽心于善,自知性善,此最是反本之言,解息纷争之妙诀也。”(注:《陈确集》第455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这番话着实反映了陈确对其性善论矛盾的无奈和回避,同时也表现出他转而从人后天的道德修养过程来考察说明人性,从而使人性具有了实践色彩。
三
为了使性善论自圆其说,陈确进一步把对人性的探讨转向了对人后天的道德实践活动的探讨,把人性看做是在人的道德修养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形成的。
他说,既然与生俱来的人的素质、特性与能力等不能保证人之善,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就不能算作完整的性,而只是性的萌芽。也即“未尽之性不可以为性”(注:《陈确集》第443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以未尽之性为性,是自诬也”(注:《陈确集》第59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在他看来,“未尽之性”与“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未尽之性”到“性”须经过一个实际的修养过程,也即“继善成性”。
“继善成性”一语来自于《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与《易传》强调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相一致的。陈确把这一思想纳入自己的人性论体系,用以说明“人性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他解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中庸》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继之,则须臾不离,戒惧慎独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注:《陈确集》第592页,中华书局, 1979年4月出版。)“继之者,继此一阴一阳之道也, 则刚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继之之功,即《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之谓。”(注:《陈确集》第447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所要说明的是,通过人后天的道德实践活动对其先天所禀赋的善性之萌芽(即“天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进行培育,就可以达到人性的完善与成熟。所谓“继之”、“成之”,都是就人的实际修养活动而言的。他说:“成之也者,诚之也;诚之也者,人道也,而天道于斯乎见矣, 故曰性也。”(注:《陈确集》第44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就是说,“继善”成之, 就可以得“人道”——蕴含了“天道”的天人合一,这样就达到了完整意义上的(非萌芽状态的)、真正的“善性”。尤其“成之”,作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于人性的存在和完成而言,是一个必要条件。他说:“向非成之,则无以见天赋之全,而所性或几乎灭矣。故曰:成之谓性。”(注:《陈确集》第44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这进一步说明了通过后天的道德实践活动对先天所禀赋的“善性”之萌芽进行培育可以达“善性”,并充分肯定了“人性”对于“成之”这种“人道”(人的道德修养活动)的依赖性。他进一步说明:“各正、葆合,虽曰天道,熟非人道?今夫一草一木,谁不曰此天之所生,然滋培长养以全其性者,人之功也。……非滋培长养能有加于草木之性,而非滋培长养,则草木之性不全。”(注:《陈确集》第450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草木之性如此,而人之性也如此,“责重人道,以复天道。盖人道不修,而天道亦几乎息矣”(注:《陈确集》第450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也就是说,对于“人性”而言,天道的作用仅仅在于提供了性之萌芽、胚胎。“天道”生之,“人道”成之,关键在于“修”“人道”(道德修养活动)以“复天道”(完善和形成“善性”)。若“人道”不修,“天道”也难保存,这进一步说明了“人道”在人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强调了人性对后天道德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不仅如此,在陈确看来,“人道”、人的道德修养活动不仅使得人性形成和完善,即“成己仁也”,而且“成物知也”,即达到了对外在事物的认识——“知”。因为“天道”与“人道”是统一的,如陈确所言:“人道也,而天道于斯乎见矣。”(注:《陈确集》第448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就是说, 陈确所谓的人性同时包括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过程和认识事物的外在实践活动。于是,人性在陈确那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仅仅是生而具有的人的素质与特性,而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且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实际过程。它直接与人的道德实践过程融合为一。关于这一点,陈确明确指出:“空口言性,自谓知性,而不力于迁善改过工夫, 性善何见? ”(注:《陈确集》第443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又说:“尧舜之学,性之也。”(注:《陈确集》第430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孳孳为善,虽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注:《陈确集》第443页, 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这些都说明“性”存在于“学”的实际过程中,而不是脱离人的道德修养活动的先验存在。进而,陈确认为对于“人性善”,也必须通过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去考察和体认。他说:“为善,自知性善耳。”(注:《陈确集》第461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若但知性善而又不力于善,即是未知性善。”(注:《陈确集》第442页,中华书局,1979年4月出版。)从而把对人性善的认知也溶化于整个知善行善的过程中。这样,陈确的“性善论”就与传统的“性善论”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讲,他把“为善去恶”的实际行动纳入“善性”之概念,把道德实践过程作为“性善”本身的内容,以人的活动规定人性,使人性具有了实践性质。而在他以前,虽然王阳明、刘宗周等也都肯定了人性的道德体认和道德自觉能力,注意到并承认了道德实践的修养功夫与性善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们仍把修养与人性看做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并没有从根本上把道德实践过程作为“性善”本身的内容。此外,陈确将知“性善”与“行善”联系起来,把认识“性善”建立在“行善”的基础上,赋予了“人性善”命题本身以实践的意义,并且,他在“行善”的前提下谈知“性善”,也即将“知”建立在“行”的基础上,这已包含了以实践为基础说明认识的意义。这一点是很深刻的。以上这些反映了陈确性善说的特征:他着重探讨的不是性善之来源或性善之先验根据,而是后天对性善的实现和认识,是于“继善成性”、“为善”的实践中形成、完善和认识性善。这样,“人性善”、人性在陈确那里就脱去了纯先验性,成为与后天社会活动相联系的、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存在。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在人性理论上是一个突破,是对人性理论的发展和提高。
陈确对人性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的覆灭与满人的入主中原等形成了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加强封建统治、维护社会安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农民平等意识的增强、程朱理学的虚诞空洞及其软弱无力等,都要求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注重具体和实际,反玄想,重考察,助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当时人性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要求。陈确、刘宗周、黄宗羲等人的人性理论都反映了这一特点。因此,当时陈确将人性与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以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说明人性,从而将人性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时代使然。当时其他理论思想也都反映了面向实际、立足现实的时代特点。但是,也正是陈确人性理论的时代性决定了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先验的道德性与后天的“实践”(道德修养活动)性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陈确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一切批判都是站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自我调整这样一个基本立场上的。反映在理论上,其人性学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真正地从社会历史、实践的角度唯物辩证地认识和揭示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问题。作为封建时代的代言人,他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的意义。因此,既使他强调人性与现实生活的统一,重视人性的实践品质,其所谓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行善的道德实践。所以,他所谓的人性仍然是脱离时代和具体社会生活的抽象的人性,只不过这种人性是要通过人的实际行为来实现、完善的所谓“善性”。
标签:人性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陈确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孟子论文; 天道论文; 国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中庸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