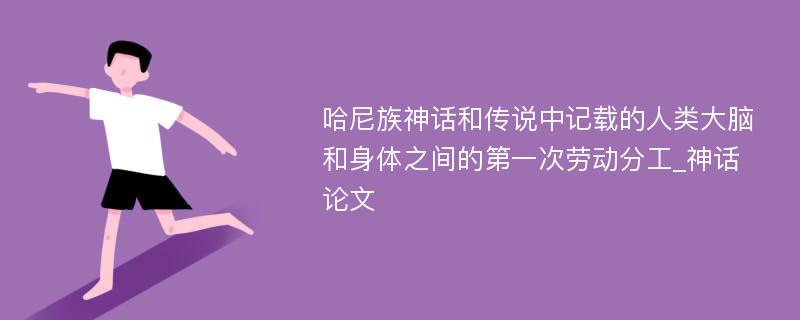
哈尼族神话传说中记载的人类第一次脑体劳动大分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尼族论文,传说中论文,人类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哈尼族神话系统的分析,厘清了中国古史上一大命题“绝地天通”神话的文化本义,是宗教神职人员巫觋的职司化,亦即人类第一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分工的完成,反映在社会组织方面,即政教分离形态的出现。文章将这一文化变革分为三个阶段:一、人人为巫,人神杂糅,是为脑体劳动相混为一的阶段;二、人神交恶,天地绝通,是为脑体劳动分工的初级阶段;三、人神交通专职化,是为脑体劳动分工的深化阶段。这一系列过程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因而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直至近现代仍在这一文化变革中。
关键词 巫觋 贝玛 神话传说 脑体劳动大分工
关于古巫的发生和变化,哈尼族先民基本上存着这样三个阶段的认识:第一个阶段,天地开辟万物滋生后,人与神并未有明显的分界限,他们之间亲如家人,互通姻娅,来往自由,只存在能量大小,居域上下的分别,此一阶段实际是天人合一时期。神并不作为实体而仅仅作为观念存在于人类头脑中,因而人与神的互相交通往来婚姻之类,也就是人人得而为巫,人人可以通神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类开罪或不讨好于神明,于是神便砍断人神交通的天梯,杀死人神交通的龙马等物。第三阶段,人神的交通仅仅限制在个别出类拨萃的精华人物身上,一般芸芸众生欲使自己的欲望通达神听,必须通过这些精华人物(西方宗教所谓“上帝的选民”)而后可,即专业神职人员的“巫”垄断了人神的联络,同时也垄断宗教文化的存贮、播扬和发展而成为宗教与政治的权威的阶段,由此又下沿各代,由政教的合一分化为政教的分离,最终形成政治、宗教的独立系统。简单说来,第一阶段就是人人可与神交通,人人皆为巫觋的时代;第二阶段是人神断交的时代;第三阶段是专职巫的时代,此中又分离出祭师与巫师,前者多与执政者发生联系,后者开始时也参与政事,后随着历史的推演,渐次被逐出社会权力圈子沦落民间,地位大幅下降。
哈尼族先民对这一认识总体上是十分朦胧的,许多范围极不清晰,如第一个阶段之所谓天地开辟万物滋生即有人神交通往来,亦即人类诞生以来就人人得而为巫,巫即伴随人类的诞生而诞生,与王国维先生的巫“与文化俱古”之说相仲伯,实在是极含混的。其称以含混,是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遗存看,旧石器时代的前期民中期,巫并未产生,人类刚刚从动物群中脱颖而出,人的许多高级属性尚未发展出来,巫作为人类文化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必须具备相当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文化符号的创造能力而后可。
下面我们来看哈尼族神话传说中关于这三个阶段的具体表述。
第一阶段,人人为巫,人神杂糅。这从始祖神话、文化英雄神话和世系谱牒中可以得到证明。
始祖神话:红河地区哈尼族一般认为其直系先祖是老祖母塔婆,关于她的出身和经历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作者调查到的若干种传说中,有一种说法较具代表性——洪水泛滥之后,人类濒临灭绝,只剩佐罗佐白兄妹俩,在天神的掇合下,他们相配成婚,妹妹佐白浑身上下怀了孕,生下七十二种人和一百七十种鬼,佐白前面的两只奶是给人吃的,后面的七只奶是给鬼吃的,人和鬼是一母所生,和睦相处,生活愉快。哈尼语称多子的妇女为“塔婆”,从此,生下七十二种人(后来成为天下七十二种民族的祖先)的妹子佐白就被称为“塔婆”而进入了世系宗谱,被人们尊为始祖。这个故事也广泛流传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哈尼族各支系中,在古歌《天地人鬼》中唱道:“(始祖)一直数到第九代/神能的安追出现/安追有个姐姐/名叫唐盘(“塔婆”的异音)/她是多子的观音/她是人鬼的阿妈/唐盘胸前有两个乳房/那里装喂人的琼浆/唐盘后背有七个乳房/那是鬼的饭袋和食粮。[①]”
另一个故事说始祖塔婆生下了老鹰、老虎和龙王。[②]塔婆作为人祖又能生育鬼神,又能生育老鹰,甚至还能生育龙王,可见这确是人鬼神灵不分的时代。
文化英雄神话:哈尼族许多文化英雄都是人在与神灵的交通过程中创造了文化器物和典章礼仪的。如著名英雄玛麦,因见人间没有稻谷种,就骑上金马飞上天宫向天神讨种,天神把自己的女儿稻谷仙姑嫁给他。新婚之夜,玛麦偷了稻种跑了,但因金马被仙姑砍断双翅,他和金马摔死在地上,从此人间有了稻谷。[③]这个故事里有人与神的交往和婚姻。
《猎神》也讲到人神的交往,并由此创立了狩猎礼仪。古时人类不会开田种谷,只靠狩猎为生,但他们支下的扣子、挖下的陷井每每失灵,后来发现是三个骑着麂子、马鹿、岩羊的汉子捣乱,这就是猎神。人和猎神到天神那里打官司,才定下狩猎的规矩。[④]在这里人与猎神是平等的,上天告状也形同出门赶集般便捷。
相似的还有《作洛搓罗》和《都玛沙莪》。前者是说乌木(大头领)的弟兄杀死魔王,后来形成葬礼中某些规矩的事,后者则是关系到哈尼族三大节日之一“苦扎扎”来历的重要神话。故事说天神派女儿都玛沙莪女神来到哈尼村寨过六月年,女神爱上了哈尼小伙子威惹,留连人间不返,与威惹生下儿女,天神不乐此事,骗回女儿和外孙,威惹便追上天廷,与天神赌赛击天鼓,天神失败,只好放回都玛沙莪和外孙,与威惹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兴下哈尼人敲硭打鼓的古规。[⑤]
世系谱牒:哈尼族各支系均有世系谱牒,作为宗支血缘辨识的依据,其中一般公认二十或二十一代为人鬼(神)、物不分的时代,以下各代始记人世谱牒。
作者在元阳县攀技花区洞铺寨、黄草岭区树皮寨搜集到的神话传说《神和人的家谱》中说,神和人的共祖“俄玛”(哈尼语“俄”为“天”,“玛”系对女性尊称,可释为“天上的老祖母”,或“天母”)是哈尼家谱中打头的始祖,其排到顺序及意义为:
第一代:俄玛——天母;
第二代:玛窝——神人合体,以背走路;
第三代:窝觉——从天上降临人间;
第四代:觉涅——遍体长毛,鬼头;不会说话,一窝一窝地在,不分尊卑;
第五代:涅直——有了头领;
第六代:直乌——以上各代身如飘蓬随风游走,直乌则活动起来;
第七代:乌突——能够蹲起来;
第八代:突玛——能站能走;
第九代:玛约——住进岩洞;
第十代:约涅——身体多种孔道还堵塞着;
第十一代:涅本——七窍均开,会闻会望会听;
第十二代:诗米乌——会认母亲,不会吃错奶头……
这些材料从诗米乌数上去,是人、神、鬼不分的家谱,自他之后,人归人,鬼归鬼,神归神,不再相混一处了。
以上材料均说明远古之世人与神鬼万物混处,这一观念的实质是什么呢?为什么先民们要一再地强调它呢?
鬼神观念的产生,前提是原始人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怪异之物产生以前,人类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旧石器时代前期、中期),虽然受到大自然恶劣势力的压抑,仍不能发生鬼神观,而只是在心灵中萌生着一种朦胧的压抑感。又由于他们在思维层次上的低弱,普遍存在着人未完全与大自然分离的意识,因而认为人与物(自然之物)是合一的,[⑥]所区别者仅是存在的形态不一样罢了,因此,就有了人与物都由一母(常常是自然界最高力量的代表者——后衍为“俄玛”之类至上神)所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类逐渐由自在之物演进为自为之物(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压迫人、威慑人的自然力量就在人类观念中形成鬼神,但这新的观念并未与旧的意识立即断裂,人与自然相融互化的脐带尚未终绝,所以又在此基础上渗进了新思维,形成人、神、鬼、物不分的现象。
这一思维产生了人人可与神灵万物沟通交往的巫觋。所谓“巫”,无非是沟通神灵之人。许慎《说文解字》释“巫”为:“神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褒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又释“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从巫从见。”(徐锴曰:“能见神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哈尼族先民认为人人与神鬼物不分,也就是人人“能见神”,能“降神”,人人为巫觋。又因彼时受限于低下的生产力,生活资料匮乏,社会无力供养专职的巫觋(从事脑力劳动者),有事欲请神灵相助皆人自为之,所以这是一个脑体劳动混然一体,人人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的时代。哈尼族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否创造了如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作品无法知晓,即使发掘出那样的艺术品,由于他们长达数千年的迁徙,也无法确定是否为其所制。但是欧洲洞穴艺术的发掘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的参照——人类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抑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可能产生巫,那是真正的“原始巫”[⑦],即人人可为之巫。
第二阶段:人神交恶,天地绝通。反映这一观念的神话传说极为庞杂广博,通常采用显形与隐形两种方式流传。
最彰显者当数《神和人的家谱》,故事讲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从俄玛(第一代始祖)到突玛(第八代始祖),人们可以自由到天上去,上下天庭的通道是一架从“九山砍来的茅草搓成的粗索子做成的楼梯”,他们“要上天,就收上去,要下地,就放下来,祖先们像山上的老猴,顺着天梯去去来来,扎实热闹好玩”。突玛是个不动脑筋的懒人,世上的千万件事他都要上天去问,起头天神们都肯帮忙,但是天天问样样问,神们不胜其烦,就用斧子砍断了天梯,不让突玛再上天问事,从此人就再无法与神交往了。
隐形神话,如《补天的两兄妹》、《都玛沙莪》等等。第一则神话说古代有一年七月,天降大雨,山洪冲坍了村寨和梯田,哈尼人无法生存,原因是天池底通了一个大洞,漏水不止。艾浦艾乐兄妹俩为了拯救乡亲们,抓起三把泥土飞上天宫去堵漏,三把泥土用完,漏洞仍未堵好,兄妹俩就跳进天池,用身体堵住漏洞。他们死后,鲜血化作满天彩霞,永远与哈尼人为伴。后来哈尼人为了追念他俩,就支起磨秋,磨秋吱吱嘎嘎的响声传上天空,把人们的思念带给舍身为民的英雄。这则神话并未说到中断人与神的交通,但兄妹俩以一躯凡体自由飞升天宫,这显然是神人交通人人为巫时代的写照。而他俩死后,人们为追念他们,则又无法飞上天空,只好凭籍磨秋的响声向两位英雄表达思念,这也间接地反映了从此人神来往之路中断了。
第二则神话讲女神都玛沙莪母子被天神烟沙骗回天庭之后,其夫哈尼族小伙子威惹种下一颗葫芦籽,葫芦籽飞快地生根发芽长叶抽藤,藤子伸进天宫门口,威惹攀着藤子上天宫与天神赌赛,战胜了天神,迎回了都玛沙莪母子,天神惧怕他以后再上天来寻衅闹事,就断其上天之路,但又送他一面小金芒,说有事尽可敲芒,天神自会来到人间相助女婿,于是哈尼族便有了凡遇大事,如死人、发生战争等等就敲芒的习俗和巫仪。
推求人神(鬼)断交天地绝通的原因,在《神和人的家谱》中是因人祖突玛懒惰,《补天的两兄妹》中补天池前人可上天,补天池后无法上天,原因也在人而不在神,《都玛沙莪》中是天神怕威惹再次上天闹事寻衅。总而言之,无论是与非,都是人开罪于神(鬼),于是方有天地不通人神异途的结果。
第三阶段:人神交通专职化,人类第一次进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大分工。
我们对上一阶段应当有所补充的是,人神断交之后,并非仅仅是神(神)能到达人间,凡人在某些特殊的时态和场景中也能一如远古时代与神交往。如借助打磨秋发生的响声可表达对化为云霞(已经是天人)的兄妹的感念,借助敲芒可以通知天神烟沙下到人间助人,借助对天神之女村寨守护神的祭祀,也可使这位女神知晓人间的欲念而保护人们不受鬼怪的惊忧,等等。这里的打磨秋、敲芒、祭祀等已带明显的原始宗教意味。
哈尼族的所有宗教活动均由神职人员主持,他们就是“贝玛”(摩批)和“尼玛尼帕”(男女巫)。前者是宗教祭典的主持者,后者是巫术活动的施行者。古代二者是合二而一的,统称“批”,“批”是哈尼族历史上最早的专职巫者。
关于“批”的诞生和发展演变,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有着清晰的记载:当哈尼族祖先从遥远的北方南迁而来,到达一个土地平旷、土壤肥腴的平原时,见多识广的祖先西斗指着大山说:“哈尼人,快看吧,天神赐给我们好地方:横横的山像骏马飞跑,身子是凹塘的屏障,躲进凹塘的哈尼,从此不怕风霜!“由于他明智的选择,哈尼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定居安寨,从一个“随畜迁徒”的民族演变为定居农耕的民族。他的远见卓识赢得了众人的赞赏,所以史诗说“先祖推举西斗做头人,希望他献出智慧和力量。”而“西斗拿出了三颗贝壳,用来占卜凶险吉祥:一颗是子孙繁衍的预兆,一颗代表禾苗茁壮,一颗象征着六畜兴旺,贝壳寄托着哈尼的愿望。”[⑧]占卜吉凶是巫者之事,西斗一身兼有头人和巫师二职,这反映出远古之世,哈尼族的部落首领和巫师是合二而一的。
这一情况可从汉文史籍中得到印证,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前后,丞相张九龄代唐玄宗所起草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云:“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误、姚州首领左威将军爨彦徵……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张九龄《曲江集》卷12)“和蛮”是唐代哈尼族的称谓,“大鬼主”即政教合一的首领称谓,唐玄宗此书证明,至迟在唐代,哈尼族尚保有宗教和政治首领合一的风尚。
当然,哈尼族社会政教分离的文化变革远在唐代之前就已发生,这在《哈尼阿培聪坡坡》第三章“惹罗普楚”里说到:
“寨里出了头人、贝玛、工匠,/能人们把大事小事分掌。/头人坐在寨堡里,/蜜蜂没有他忙碌;/贝玛天天诵读竹排经书,/哈尼的事书里载得周详;/工匠在溪边拉起风箱;/那里是他发财的地方。”
对照前面“西斗”政教合一的情况,这里所述已明确地指出属于政教分离,形成“头人、贝玛(宗教首领)、工匠”三权分离的社会统治组织机构。这种情况说明几种可能,一是“惹罗普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里哈尼族完成了宗教和政治首领由一体化分而为三的历史演主为。二是由于史诗在流传过程中融进了后期的事象使之与前期事象相混,三是在很长时期内,哈尼族各部落间共存着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两种形式,由于各部落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此一情形,不然就难以解释汉文史籍所载之唐玄宗时犹有政教合一的“和蛮大鬼主孟谷俟”的现象。[⑨]
但是无论哪一种可能,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原始宗教首领(或神职人员)巫师(在这里,我们把巫术看作一种准宗教,因为无论巫术还是原始宗教,抑或是人为宗教,其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是人与神的中介)的出现不晚于部落首领的出现,二者很可能是同时出现并集二者于一身的。
前面我们谈过人神的交通和绝其交通,那么交通断绝后并非人神绝路,而是出现了沟通人神的专职巫师,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活资料有了一定的积累,供养得起专门的宗教人员之后产生的必然现象,这就是为近现代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再探究的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脑体劳动的大分工,即由原始阶段的人人既是脑力劳动者又同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艺术家、宗教活动家(巫师),又同是猎人、牧人、农人的现象,一跃而有了区分,出现了专司宗教活动职事的神职人员巫师。[⑩]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从此这些专职人员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精力来从事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以至创造,他们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人类文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高度,是他们辅设了第一块基石——尽管原始的巫师们从事的是不科学的活动甚至常常把人类的精神引入迷途。
第一次脑体劳动的大分工,对哈尼族来说,直接的后果便是产生了“头人、贝玛、工匠”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权力组织,这一制度下沿各代,直至民国,始终成为哈尼族在各历史阶段的领导核心,对该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哈尼族民间流传着这样的古语:“没有头人,寨子不会稳,没有贝玛,哈尼不会活,没有工匠,庄稼不会熟。”这三种人已是哈尼族传统文化在社会形态方面的代表。
第一次脑体劳动大分工是人类第一次本体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复杂的斗争,作者1981年调查的哈尼族长篇创世古歌《窝果策尼果》(11)对此生动地作了描述:
1、直堵、琵堵、爵堵(头人、贝玛、工匠的诞生)。在远古的时代,天神种出头人、贝玛、工匠三种能人,并把他们引入哈尼族社会。
2、直坡、琵坡、爵坡(头人、贝玛、工匠大逃亡)。三种能人各司其职,对哈尼人的发展作用巨大,哈尼人对他们十分尊重,向其奉以优厚的报酬。但是这一合理而自然的现象却刺激了人群中一些希望不劳而获的人。他们骚动起来,取三种能人而代之。这些人想恢复到人人为巫的时代,于是三种能人便逃亡到远方。
3、直枯、琵枯、爵枯(请回头人、贝玛、工匠)。三种能人的逃亡使哈尼村寨变得一片混乱,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骨肉相残。人们尝到了没有头人、贝玛、工匠的苦头,于是派出代表历尽艰辛请回三种能人,使哈尼村寨恢复了秩序。
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包蕴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首先我们看到,“三种能人”的问世是神的旨意,必须吃过“头人、贝玛、工匠的种子”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一些具有特殊本领的人,如头人必须具备管理村寨事务的能力,贝玛必须掌握撵鬼敬神治病的学问,工匠必须具有打造工具的技艺。故事曲折的情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围绕着人类社会第一次脑体劳动大分工所进行的复杂斗争。它证明这一分工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同时是一整个历史的过程,它或许绵延了数千年,或许在同一民族的不同聚居区域出现了演进的不平衡,如在甲地哈尼族中业已完成了这一分工,而在乙地哈尼族中尚未完成。如与作者合作长达十余年之久的著名大贝玛——元阳县攀枝花乡洞浦寨的朱小和,虽然名播整个哀牢山区,来请他主持祭典的人络绎不绝,但其精力和时间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仍在生产劳动上,他本人身兼贝玛、工匠和农民,一年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无一遗漏全部参加,铁匠工作又占去剩余时间的大部份,真正从事贝玛活动只占极少部分。
这一情况证明哈尼族社会中的宗教人员,从古代人神交通断绝产生职业巫觋以至今日,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专职”(完全脱离体力劳动)。因此,从该族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的发展角度来看,哈尼族的脑体分工从来没有完成过,他们始终处在一种中间状态。
其次,我们从这些故事里知道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神断交后伴随着专职(半专职)通神的宗教祭师、巫师的出现,等级制度也出现了。《窝果策尼里》古歌中唱道,不同的子种长出了上、中、下三等的头人、贝玛和工匠,这是依据不同头人、贝玛、工匠的本领、职能定下的等级。等级制度的产生,构成了阶级社会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哈尼族社会形成了近代封建领主(西双版纳地区及红河地区的一部分)和封建地主(思茅、玉溪地区及红河地区的一部份)的社会制度。
注释:
① 见《西双版纳哈尼族歌谣》。
② ③ ④ ⑤ 《哈尼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参看拙文《神话的整化意识》,《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四期。
⑦ 时下研究民族学、民俗学者动辄称某某后进民族、后进文化为“原始民族”、“原始文化”,其指多含混不清,不知“原始”之时限、内涵、标准为何。作者认为,凡称“原始”者,一般时限为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文化事象。
⑧ 以上均引自《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⑨ 此情况从《新唐书·南蛮传》(下)所载可得证明,其云:“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按,此条所载之“和蛮大首领”较唐玄宗书载之“和蛮大鬼主”尚早79年,“大首领”已属政教分权之称谓,故可推断唐代之和蛮部落有政教分、合两种在。
⑩ 与神交通断绝之后,人神交通唯有宗教人员(祭师与巫师)方可,这正是原始宗教产生的必要条件。“宗教”,拉丁文意为连结与再结,所指正是由人与神的连结中断后的再连结,第一次的连结是普泛性的(人人为巫),第二次则是专指性的(贝玛、尼玛、尼帕之类)。
(11) 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之《哈尼族古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