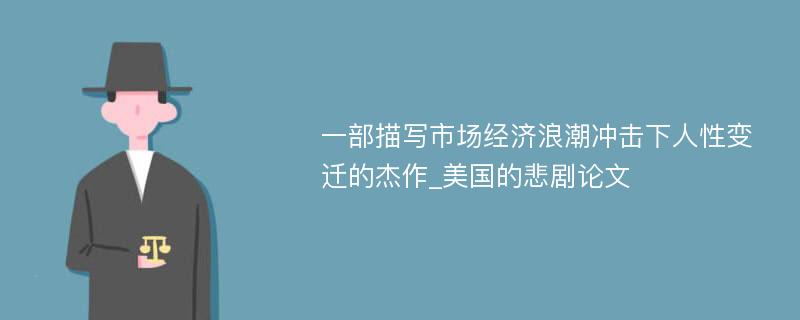
描写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人性变化的杰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潮论文,杰作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是以生花之笔抒写年轻男女对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的世界名著,无不得到世界各国年轻读者的宠爱。少年维特与绿蒂的初恋使人沉醉,而维特的枪声,催人泪下。娜拉走出家庭,大门呯然一声,宣告与玩偶生涯决裂,这关门声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还在发出回响。托翁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宁在轮下丧身;斯当达尔《红与黑》里于连·索黑尔与市长夫人的爱与恨竟然把于连引向断头台;这些既使人震惊,又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这些都写了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期间青年男女个性解放的追求及其命运。过去一个时期,这些世界各著的光华不免因某种误导,未能充分发挥其审美功能。
但历史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前进。人类的艺术探索没有停留在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类大师的艺术天地。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艺术探索。在比较纯粹的金钱统治下,在告别了国王、伯爵、公子小姐和等级制度以及相应的爱情、婚姻等等社会风尚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千千万万年轻男女对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又是怎样一个模样?对此,人们难以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描绘的艺术天地里寻找到审美的答卷来。正是所谓“李杜文章万古传,而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有关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青年男女对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的抒写,也许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学史的研究中,还是个比较新的课题,迄今尚少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卡夫卡的《变形记》,T·S·埃略特的《荒原》、以及萨特、加缪的作品和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各以某种荒诞、讽谕的形式,为青年男女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的抒写,作了某种开创性的艺术探索。然而讽谕式的荒诞式的、象征性的艺术形式固然是有益的,却难以满足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审美要求。广大读者更倾向那样的作品:既是从生活中来的艺术虚构,又能写得象生活一样真实、象生活一样朴素、象生活一样有艺术说服力。这正是市场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而环顾世界文坛,不能不说西奥图·德莱赛正是抒写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青年男女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的高手。《嘉丽妹妹》首开风气。《珍妮姑娘》继之成为双璧。《美国的悲剧》攀登顶峰,而《堡垒》这个作者最后一本杰作,又独辟蹊径,以沉重之笔,写出了一个崇尚道德规范的“家”,怎样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日益沉沦,美好的、高尚的、然而又是不无陈旧的传统——这样的一个“堡垒”怎样被无情的时代大潮一片片冲走,只留下了求美求真的小女儿嘤嘤啜泣之声。
在美国文坛,在80年代后,已经有人指出,在“有关商品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描写”,德莱赛是“一个探索的先驱者”〔1〕。 由于种种原因,德莱赛这方面非凡的才能,几十年来湮没而不彰。但今后势将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西奥图·德莱赛(1871—1945)被公认为美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却又是美国文坛争论激烈的作家。有关他的争论,从1900年开始,而1945年在其逝世后又争论了几十年,以迄于今日。仅举几个事例为证。1900年《嘉丽妹妹》出版,标志着美国文学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时期。然而作品由出版公司出版而不发行——美国式的禁书。文坛权威白璧德教授和司徒阿德·席曼教授等正人君子斥《嘉丽妹妹》“野蛮”“淫猥”、“不道德”。1915年的《天才》又一度被禁了七年之久。1925年的《美国的悲剧》标志着美国现实主义的胜利。30年代,美国文学左倾,德莱赛被公认为美国文坛领袖。1930年《大街》的作者辛克莱·刘易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第一个得主,领奖演说中称颂了德莱赛,说这个奖原本也可以授予德莱赛的;说“他往往不被赏识,总是遭到围攻,可是,也正是他,在美国小说的领域内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式的、豪威尔斯式的胆小的斯文传统,打开了通向忠实、大胆与生活的激情的天地。”德莱赛1945年逝世前申请参加美国共产党。逝世时,由著名剧作家德莱赛的入党介绍人劳逊致悼词,由美国著名演员以《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中的精彩表演著称的卓别麟朗诵了德莱赛生前所写的诗《我走过来的路》。劳逊称颂德莱赛为“我们的高尔基,我们的罗曼·罗兰。”
二战后,在冷战年代,德莱赛却又遭到了攻击。美国德莱赛专家庇才教授在1982年说:“在德莱莱逝世后五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发动了他对德莱赛的有名的攻击。”特里林指责德莱赛的作品“粗俗”“笨拙”,“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著名作家索尔·勃娄说,对德莱赛的小说可以“一目十行地看”。他们都指责德莱赛宣扬共产主义。(其实,德莱赛申请加入美共已是他逝世的那一年,至于他的文学作品没有一本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另一著名文艺评论家欧文·豪在1964年说,“有教养的美国人民已不再注意西奥图·德莱赛了。”〔2〕
可是,在欧文·豪发表其高论的前一年,即1963年,德莱赛研究专家埃伦·莫尔斯说,“我们再一次读起德莱赛的作品来了。”“复兴”降临到了我们这里。”“年轻人显然喜爱阅读德莱赛的作品。”“他一贯热爱下层人民,就象霍桑和爱默生那样,就象惠特曼那样,就象在他们之前的歌德那样。”〔3〕又一场攻击与捍卫德莱赛的论战就这样持续了三四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德莱赛作品的各种版本仍纷纷出版,有关研究德莱赛的专著也络绎问世。但据笔者所知,1991年的《歌伦比亚美国长篇小说史》,影响不小。书中对德莱赛也颇多论述,也不乏中肯见解。此书附有较系统的《美国作家传略》,其中有库伯,有霍桑,有刘易斯、海明威、诺门、梅勒、福克纳,有诺里斯和杰克·伦敦、坦倍克,有索尔·勃娄,爱泼代克等等,独独没有德莱赛。岂不怪哉?这是否表明, 到了90 年代, 有关德莱赛的论争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这从1900年《嘉丽妹妹》出版之日起的论争,贯串在近一百年的美国文坛,不正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德莱赛的贡献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么?
这位被美国文坛正人君子们骂了几近一个世纪却骂不倒的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和正人君子们有什么不一样呢?确实不一样。不仅和正人君子们不一样,并且和一般作家也有所不同。德莱赛在1943年,亦即作家垂暮之年写信给好友、著名评论家门肯说:“要知道,门肯,我和你不一样,我生来穷困。在十一月、十二月时,我曾经脚上没有鞋子穿,赤着脚走路。我亲眼看见我亲爱的妈妈吃尽辛酸——担惊受怕,痛不欲生。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不论会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论人家会怎么说,我总是维护那样一种社会制度,能让人们——那些虽然卑微却肯干的人们有好日子过”。这是为逃避兵役从德国移民来美的手工业工人之子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只有从文学到文学的形式主义者才会对这样的话无动于衷。贫穷使这位作家与人民心连着心。贫穷使这位作家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心明眼亮,明辨是非。
光贫穷并不能造就作家,更不用说大作家了。德莱赛和一般作家不一样的,还在于从儿童时代起所干的卑微的职业,加上青年时代起投身新闻工作、编辑工作,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可说成了时代的社会的耳朵、眼睛与神经。不仅是一般地了解社会、了解人生,而是与平头百姓一起欢笑,一起哭泣地深入社会、深入人生。他六七岁便和兄弟姐妹一起检煤渣,有时候除了山芋和玉米粥以外吃不到什么东西。德莱赛13岁卖报。16岁到芝加哥饭店里洗碟子。为一家金属器具批发店看仓库。18岁,得到中学时代老师费尔定的资助,到印第安那大学读了一年书。一年后无力就读,回芝加哥,为一家房地产业干活,每周工资8元。 后为一家洗衣店送衣服,每周工资8元。这一年,母病故,作家后来说, “我们的青春就此结束了。”“孤身一人。”20岁开始写有关芝加哥的小品,在《每日新闻》发表。同年在芝加哥《先驱报》找到了一个位置,在圣诞节分发玩具。德莱赛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21岁果然成了芝加哥《寰球日报》记者,工资每周15元。这一年第一次发表了短篇小说《天才的归来》,在《寰球日报》发表。从此一直在各家报纸打滚,有时担任杂志编辑以至主编,同时写短篇小说,写诗写戏, 写剧评。 1899年,28岁,动手写《嘉丽妹妹》,第二年出版。当时,正担任一家刊物的编辑。就是《嘉丽妹妹》出版后,仍任刊物编辑,象1900年任纽约《每日新闻》新闻通讯编辑、1905年任低级趣味而风行一时的刊物《斯密斯杂志》主编,1907年任风行的《百老汇杂志》及其它流行的妇女杂志主编。
杂志主编、记者与作家,两者之间本无鸿沟〔6〕。 一二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帮助了这位作家熟悉人性的秘密、人生的秘密、社会的秘密。仅举一例,德莱赛的代表作1925年《美国的悲剧》标志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在美国的胜利,而《美国的悲剧》的素材与原型便是他在1906年任杂志主编时(《斯密斯杂志》和《百老汇杂志》)获得的。而且,据作者说,类似的案件不只一件,而是前前后后一共15件之多,都是为了追求美国梦,往上爬,另攀高枝,不惜对原来的情人下毒手,搞凶杀。可见作品中的典型来自生活,才使得作品通过记者作家的艺术虚构,能写得象生活那样真实,象生活那样朴素,象生活那样具有美学的说服力。
当然光是贫穷与熟悉生活还不能产生大作家。德莱赛所以能成功,还由于他勇于掌握当时刚刚产生的并且是当时先进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科学理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样的学说既可为豪门掠夺找理论根据,但也可用来说明为什么农村姑娘(嘉莉妹妹)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刚一离开农村、踏进城市,使难逃沉沦的命运。为什么一个沿街传道的穷牧师之子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一片痴情的女工洛勃特·阿尔顿在荒凉的湖上永沉水底(《美国的悲剧》)。
德莱赛在众人还没有弄清楚奥地利的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是怎么一回事时,在本世纪初便在格林威治村这个文化人中心学到了弗罗伊德学说的精髓,因而早在1925年《美国的悲剧》中便写出了克莱特起了杀心后的恶梦等等那样一系列精彩的篇章,写得那样狰狞可怕,又那样入情入理,把这堕落的青年深层心理里情欲波涛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且这类描写迥异于后来一批又一批庸俗的性描写那类作品。他能将人性的描写,梦、幻觉的描写,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相结合,其矛头直指产生这般悲剧的金钱主宰一切的当今“美国”的社会制度、社会风尚、社会思潮。
当然,光是先进的思想学说也还不足以孕育大作家。要成为本行——文学这一行——的高手,没有继承前贤的功底,并站到前人的肩上往上攀登,在继承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开创一种新的境界,新的天地,为后之来者闯出一条新路来,不是这样的话,那还称不上大作家。古往今来,多少作家,随俗浮沉,很快便被时代所淘汰,为后人所忘却,或则因为功底差,遂致夭折;更多的是不能创新,或者为某种外力所迫只好抱残守缺,苟且贪生,辜负了人民,也辜负了少年时代的一片壮志雄心。
德莱赛所以与一般作家不一样,正在于能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冲破桎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位从检煤渣、做报童出身的大作家,一边干卑微的活,一边刻苦学习,从莎士比亚到菲尔定、萨克雷,从爱默生、梭罗到马克·吐温,从伏尔泰、歌德到易卜生、叔本华,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的《第一原理》。这个生性厚重的人,学习的广泛与勤奋,委实惊人。特别是23岁(1894)在煤都匹茨堡做记者,跑警察局、跑法院采访新闻这段期间,德莱赛那段沉醉与顿悟的经历,乃是大作家所以能成为大作家的一段佳话。下面是德莱赛有关24岁在匹茨堡做记者时写下的话:
“一扇新的有强大吸引力的生活之门,突然在我的面前打开了。这才是一个能观察、能思考、能感受的人。这才是一个能牢牢地、敏感地抓住生活的人。有哲学味道,心胸宽宏而生趣盎然。我马上和他的拉发埃尔,他的拉斯蒂涅,他的比西乌和他的皮安训融为一体。我和拉发埃尔一起走进王宫旁边一家赌场,一起在王宫桥上,绝望地俯视着塞纳河水。又从这里踅进一家经售古物的铺子……一起由于那皮子一天天缩小而感到恐怖。……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革命。这不只是因为巴尔扎克掌握生活,发现主题,并把这些抒写出来时那么才气横溢,明快锋利,而且因为他那么热情地、老练地处理的那些典型——在人类的社会、政治、艺术、做生意等各方面老是盘算着、不断追求着的野心勃勃的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拉斯蒂涅、拉发埃尔、吕蓬泼雷、皮安训)——在我看来,多么像我自己啊——(我)很容易把自己和那些老是在追求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化成一体……——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我和他一样地熟悉,他的技巧多么神奇,他那种庄严雄浑、以至不免有点儿夸大的哲理。他对文坛、社会、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处理得那么得心应手……啊,具有这样的洞察力,这是多么了不起!……匹茨堡呢?圣路易呢?芝加哥呢?……对于我自己周围的世界,我毕竟有了新的戏剧性的认识。
……对我心目中这两个城市在物质条件上的相似之处,以及在这里能像他一样大有进行描绘的广阔天地,为之警叹不已。”又说:
“有四五个月之久,我吃饭,睡觉,做梦,生活,都和他(按指巴尔扎克——引者)以及他笔下的人物在一起,都和他的观点和他的那个城市在一起。”〔7〕
德莱赛写下这一些的时候,主宰美国文坛的,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式的霍威尔斯式的胆小的斯文传统——专门正面抒写上层人物的生活,写那些带着微笑的生活,崇尚上等人的传统,崇尚上等人的道德规范的生活。只是由于德莱赛学来了巴尔扎克的艺术法则,写出了卑微者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写出了被攻击为“野蛮”“不道德”的作品,写出了最美国式的社会生活和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写出作者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人道主义之爱,这才打破了那个高雅的斯文传统。
《堡垒》是德莱赛逝世后发表的两个长篇中的一本。 作家逝世于1945年12月28日,《堡垒》出版于1947年11月,相距两年。《堡垒》受到重视是因为这是著名作家最后一个作品。又因为这是作家逝世前亲自全部校阅过的,并重写了倒数第二章。这类情况与另一本遗作(《斯多噶》)有所不同。作品受到重视,更因为《堡垒》是作家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发表25年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篇短篇仍在这段时间里发表过)。以德莱赛在当时美国文坛一代大师的地位,《堡垒》自然受到了重视。后来从五十年代起,在一片冷战声中,德莱赛遭到了持续围攻,达几十年,这自然对《堡垒》的评价有所影响。另一方面,评论界对此书褒贬不一。总的说来,认为未能达到《美国的悲剧》《嘉丽妹妹》《金融家》等的艺术高度。
评论不一是正常的,百分之百的称颂反倒是不正常的。以笔者的浅见,《堡垒》既体现了德莱赛不同于一般作家们的非凡特色,即写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青年男女对人性的追求及其命运,并且表现了德莱赛某些新的风格特色:写下了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个传统深厚、崇尚道德规范的“家”的没落,这个“家”的主人——一座传统观念的“堡垒”的陷落。笔者认为,这样的悲剧,既是十足美国式的,又具有世界意义。《堡垒》写的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几十年间的事。内战以后,美国经济起飞,铁路、采矿、机器制造业、商业、银行、金融纷纷大发展,简直是历史奇迹。市场经济主宰一切,商品经济统帅一切。与此同时,农村败落,农村里青年男女涌入城市,两极分化,贫富越来越悬殊。国王、伯爵没有了,上帝的宝座在摇晃。原始野蛮的积累在疯狂地进行。金钱坐上了昔日国王、伯爵以至上帝的宝座。市场经济社会的神经中枢,——房地产、股票市场,银行越多,越是投机猖狂。旧道德、老实巴交,不吃香,而且优胜劣汰。捞钱啊,这就是一切。而昔日的传统,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被搞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试看今日之天下,虽国情不同,本质意义有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现象,则千姿百态,有同有异。而且这一“堡垒”与“家”的没落,不只是恶贯满盈的“堡垒”与“家”没落,此外还有传统深厚、崇尚传统的道德的“堡垒”与“家”没落,因而更具悲剧性。以笔者浅见,能洞察到这类“堡垒”与“家”的没落的必然性,并作了象生活一般真实的悲凉的描写,这是西奥图·德莱赛对世界文坛所作的又一卓越贡献。
《堡垒》从触发创作动机到定稿,前后达31年以上。德莱赛这样严肃、厚重的创作风格,对后人启迪颇深。这和今日世界各国文坛相当普遍的(也包括我国)浮躁之风,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
德莱赛写《堡垒》的创作动机,是1914在年得识安娜·达顿小姐以后的事。德莱赛发现安娜的文学才能颇为迷人。据有关资料,“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她成了他的情人,后并成了他的文学经纪人。”德莱赛得知她的家庭有教友会的背景。到1914年,德莱赛已致力于写《堡垒》。作品主人公苏伦·巴恩斯即以安娜的父亲这位道德高尚的教友会教友为其原型了。1915年即已向出版商(波尼——里佛莱特出版公司)预支版税一年。安娜·达顿小姐得知后,还对出版商提出过警告,说如果以她的家为背景的这本小说出版,她要对出版公司提出控告。1923后,德莱赛忙于写《美国的悲剧》,《堡垒》未能写下去。《美国的悲剧》出版后,忙于访苏,为黑人青年蒙尼的冤案伸冤,对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特勃斯,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表示支持,并作为左倾的30年代美国文坛的大师奔走呼号,并写了大量中短篇和政论性文章。二战爆发,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共商声讨希特勒的对策(德莱赛为德国移民之子)。于是《堡垒》的创作一搁几年。但在这段时间里,也并未把《堡垒》完全抛掉不管。象在1938年,便曾访宾州的哈佛学院的校友会夏士罗佛斯·琼斯,并从他有关校友会的一本书中颇获教益。到1942年,便再度致力于写《堡垒》,并开始写《堡垒》的电影剧本。1943年3月, 写《堡垒》停止了近半年,9月又恢复写作。1945年5月5日, 《堡垒》的创作完成。1945年12月22日即病逝前六天,看了《堡垒》的校样,并重写了倒数第二章。可见,《堡垒》虽是作家逝世后出版的,但全部完工于逝世以前,这也就保证了遗作未受任何外来方面的负面影响。 〔8〕
美国有的评论家指出,对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银行司库苏伦·巴恩斯,这位传统道德规范的“堡垒”,德莱赛在笔下倾注了无限的同情,而并未出之以嘲讽的态度,可说是本书的特色之一。〔9〕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只是如果能体会到作者所写的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个“家”的败落,一个传统道德规范的“堡垒”的陷落,实乃写的另一种式样的美国的悲剧,而且这种式样的悲剧很可能出现在世界各国经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城市与乡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不可能对之抱着嘲笑的态度了。更何况,悲剧主人公苏伦·巴恩斯夫妇及其一家的命运,其中还有作家德莱赛亲爱的父母的身影和他兄弟姐妹这一家子的身影呢。〔10〕这里不妨引用全书结尾求爱真的小女儿埃达哭泣时说的话:
“啊,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或是为了我爸爸而哭——我是为了‘人生’而哭啊!”
这是否也是作者德莱赛从1914年来几十年间默察这类美国社会悲剧的不可避免性而发出的无限同情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叹呢?这又表现了作者何等的洞察力,何等的智慧的闪光,又何等深沉的人道主义!
注释:
〔1〕洛勃特·舒尔曼:《德莱赛与美国资本主义动力学》, 载《嘉丽妹妹》(1991年版)庇才教授主编的附录。
〔2〕60年代前有关对德莱赛的毁誉, 可参看龙文佩:《德莱赛评论集》。又参迈克尔·高尔德:《我所知道的德莱赛》,载《译文》,1955年12月。
〔3〕庇才:《西奥图·德莱赛》,载《美国作家传记丛书》, 卷12,1982纽约。
〔4〕麦理奥特主编:《歌伦比亚长篇小说史》中《美国作家传略》,1991纽约。
〔5〕麦提逊:《西奥图·德莱赛》,1951,纽约,230页。
〔6〕列亨主编:《德莱赛年表》,载《德莱赛选集》,1987,纽约,转引自许汝祉译《嘉丽妹妹》的《附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7〕德莱赛:《关于我自己》, 转引自贝顿·拉斯科:《西奥图·德莱赛》,纽约,1925,38—40页。又参列亨:《德莱赛年表》,载许汝祉译:《嘉丽妹妹》《附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8〕列亨:《德莱赛年表》,载北岳版《嘉丽妹妹》《附录》。
〔9〕庇才:《西奥图·德莱赛》载《美国作家传记丛书》, 第十二卷,纽约,1982,162页。
(附记:本文为德莱赛《堡垒》新译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