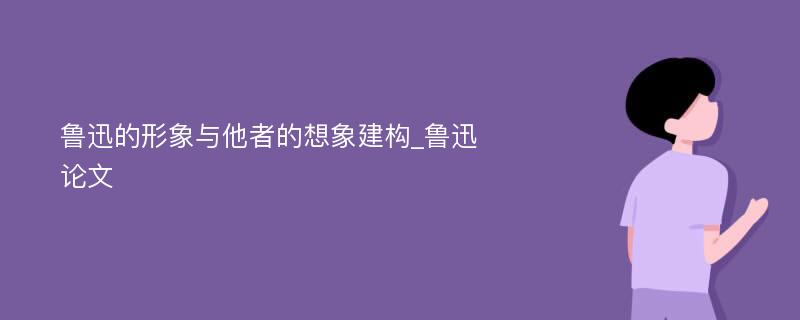
鲁迅影像及他者想象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影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所塑造的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推崇,而作家本人往往掩在文本世界的幕后,未能像其笔下的人物形象那样,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探讨作家的影像以及他者对其影像的想象性建构,便成为文学接受活动中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那么,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鲁迅,其影像是怎样构建起来的?他者对其影像又是怎样建构的?鲁迅影像及他者建构,与民国教育体制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会对我们理解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文学阅读和接受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一、鲁迅影像的自我建构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鲁迅,其身份经历了由晚清子民到民国国民的转变,由此身份转变带来的影像,自然也就打上了深刻的社会烙印,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我们对鲁迅影像自然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果没有世事的巨大变迁,鲁迅也许会像其前辈那样,继续顺着科举之路走下去;他留给后人的影像自然也就如父辈一样,绝难富有如此丰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历史前所未有之巨变的特殊时期,鲁迅像一片落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漂流而下。值得欣慰的是,鲁迅在这一历史巨变中最终成长为时代洪流的弄潮儿。鲁迅影像也就从千人一面的模式中走出来,标举了自我独立的个性,建构了崭新的现代影像。 鲁迅于1902年3月从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公派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浙江籍留学生在东京组织了浙江同乡会,会后留有合影。①从合影的模糊影像来看,鲁迅的服饰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的服饰,而是典型的日本学生的服饰。鲁迅1903年3月才剪掉辫子,从这一情形来推测,鲁迅头戴的日本制式的帽子与作为清朝子民象征的辫子是合二为一的。留学生最为显眼的发式是,“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②。这表明,初到日本的鲁迅和其他学生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把体现“清国留学生”的“辫子”这一政治符号除掉。 如果说1903年3月之前鲁迅的影像并不是自觉建构的话,那么,在他毅然决然地断发之后的影像,则是鲁迅自觉建构起来的。1903年3月,鲁迅在日本东京拍摄了身着日本学生服饰的“断发照”③,并寄给了好友许寿裳。对此,许寿裳这样回忆道:“在一九○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④把鲁迅这张照片和其自题诗结合起来看,显示了他甘愿把自我一切都献给中华民族的牺牲精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还大力推崇精神界之战士,并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追问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⑤。如果我们结合着鲁迅的“断发照”,便可以看到,鲁迅那双深思的眼睛,端庄严肃的神情,既可以看作他对风雨如磐的“故园”忧思,也可以看作他建构自己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影像的自觉。 1909年初期,鲁迅的影像出现了些许变化,这便是步入成年阶段的鲁迅开始蓄起了胡须⑥。鲁迅来到日本东京,他和许寿裳等人在1909年初的合影照片,清晰地呈现出嗣后鲁迅影像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一直蓄着胡须。显然,这胡须既不是中国传统的那种“龙须”,也不是日本那种“八字胡”(如藤野先生),更不是日本那种“鼻下须”,而是融合了中日之“长”的“胡须”,其特点是保留了上唇的胡须,只是“八字”两撇不再像日本那样“夸张”,其下唇则没有胡须,这和中国传统社会标志着年龄和资历特点的胡须有所不同。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刚步入成年便蓄起了胡须呢?这恐怕除了他有意识地塑造自我影像之外,还与其自身情况有着一定的关系。鲁迅“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若幸这样的过去了,及至二十六七岁时,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⑦。对此,有人在初见鲁迅时有过类似的印象:“这时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看着他吃东西,看来牙也是不受什么使唤的,嚼起来是很费力的。”⑧鲁迅嚼起来之所以费力,正是缘于他的牙齿已经部分脱落。鲁迅“二十六七岁时”便“有全部镶牙的必要”,这和他蓄起了胡须是有关的。鲁迅对自我影像进行建构的动因,除了在文化上赋予其深刻的意义之外,还与其自身的身体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当然,鲁迅在此时蓄起胡须,最终还是与其内在思想情感的外化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就是鲁迅对日本现代文化的推崇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这一文化诉求。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中年时期的照片,脸型是瓜子脸,没有胡须。鲁迅如果不是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一直在家居住的话,也许会像其父亲一样不留胡须。那么,鲁迅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留起胡须呢?从其较早照片来看,1904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毕业时拍摄的照片,还没有胡须。到了1909年,鲁迅已经蓄上了胡须。显然,蓄须应在这期间。这也说明,鲁迅的审美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成年男性蓄上胡须,是一种流行的审美观念,像深受鲁迅敬仰的藤野先生,便是蓄着胡须的。蓄须这一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终生的,以至于鲁迅到去世时依然留着胡须。那么,在鲁迅的这种审美观念的背后,胡须被赋予了怎样的文化意蕴呢?我们认为,这显示了鲁迅刻意要把自己和那些依然在传统羁绊下没有觉醒的子民区分开来。 留学日本之前,鲁迅的服饰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但到了日本之后,则“入乡随俗”地穿起了日本学生制服。在杭州期间(大约是在1909年)所拍摄的照片,鲁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建构现代影像。在这幅照片中,鲁迅西装革履的外表、侧面的摄影姿势、日本胡须的保留以及平头的发型等,都和留学之前的长袍马褂、正面影像的姿势、没有胡须以及那种盘着辫子的外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穿日本学生制服缘于鲁迅身在日本学校及受制于学校有关强制规定,那么,鲁迅离开日本归国之后,在浙江杭州和绍兴期间,依然身穿西式制服,则表明了鲁迅对代表西方文化的西式服饰有了自觉的接纳。归国后的鲁迅置身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依然身着西式制服,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那种“长袍马褂”的服饰截然不同,表明了鲁迅有意识地通过这种外在服饰符号来张扬自我所认同的新文化、新思想。因之,当鲁迅身着西式制服在绍兴府中学堂担任教师时,他的“特立独行”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鹤立鸡群”的轰动效应,立马显现出来。这正如其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许多教员在辛亥革命前,都背拖辫子,着长袍、马褂;吸烟用短烟管或水烟筒;走路踱方步。学生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至一九一○年下半年鲁迅先生到校,正如鸡群仙鹤,与众完全不同,一望而知其为非寻常人也,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与景仰。”“鲁迅先生原名周豫才,同学在背后叫‘豫才先生’,当面叫周先生,来校时仅二十九岁,身体甚康健,面白发黑,留有小胡子,无辫子;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执洋杖,走路得得有声;目光炯炯,识人隐微。但对学生说话幽默,和蔼可亲,不若其他秀才、举人道貌岸然,动辄训斥,望之生畏。故一见鲁迅先生到校,全校议论纷纷,咸认为是‘绍中’的进步标识。年轻教师与学生无不景仰羡慕,模仿其举止行动,亦步亦趋,惟恐不肖。”⑨如果推究鲁迅和浙江两级师范教员1909年农历冬(即公历1910年1月)于“木瓜之役”⑩摄于“湖州会馆”的合影(11),就会发现,该合影共计25人,其中4人的服饰和其他着“长袍大褂”的21人有所区别,而这4人之中,尤以鲁迅的服饰是最典型的西式制服。如此说来,学生把鲁迅视为“鸡群仙鹤”,的确是再形象不过了。实际上,归国之后的鲁迅,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方式,有意识地凸显出自我的“进步标识”,由此吹皱学校这一池经年累月“从来如此”的“秋水”。就实际效果来看,鲁迅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从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所谓的“年轻教师与学生无不敬仰羡慕,模仿其举止行动,亦步亦趋,惟恐不肖”,正是鲁迅引领“绍中”新气象的真实写照。 鲁迅1909年归国之后,其服饰还是以西式制服为主,而秋冬季则穿西式的半大衣,这自然隶属于西式制服行列。唯一例外的是1911年春,绍兴府中学堂辛亥春季于禹陵旅行时,鲁迅穿的是中式对襟的上衣(12)。这样的装束,是否为参观禹陵所必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鲁迅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其主要装束还是西式制服。如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期间,依然是标准的西式制服,这在风气已开的民国时期尽管不再那么“特立独行”,但也是少见的。从1914年5月鲁迅参与筹备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时的合影来看,像鲁迅这样穿西式制服的人员数量还是不多的。在59人的合影中4人为军人装束,仅有6人的服饰为较为鲜明的西式制服。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张合影中,身着西式制服的2人,已经端坐在合影的正中。显然,从中国社会注重次序的传统来看,端坐者无疑是占据了核心位置的人。这种细微的变化表明,那些掌握了社会权力穿着西式制服的人,正是“革命党人”。当然,从该合影的排序来看,鲁迅身着西式制服,站在后排偏右的位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在教育部这一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位置并不显赫。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1915年到1936年,鲁迅已经把自我定型于身着中式长袍的现代知识分子影像。通俗教育研究会是民国时期教育部主管的官方机构,鲁迅做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创立之初的一些工作,并担任小说股的主任。这一时期的鲁迅,其装束已非西式的制服,取而代之的是中式服饰。从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合影来看,此时的鲁迅,已经身着中式的棉袍。(13)1915年1月5日教育部全体部员的合影,和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时期的合影大致上是同一时间节点。由此看来,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便在服饰上不再青睐日本服饰,也不再钟情西式制服,而是对民族化服饰重新回归,在服饰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 在诸多影像中,鲁迅自我认同度较高的是他五十岁生辰照。该照片上,鲁迅题写了“鲁迅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14)。这幅影像是半身照,身着中袍,头部稍微斜侧,头发直立而整齐,两眼逼视前方,胡须异常醒目。而他的那种内在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超越时俗的英雄气、永不妥协的战斗性,都得以彰显。事实上,鲁迅自我建构起来的这种影像,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也的确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扩放。在这样的影像中,鲁迅身材矮小、体质柔弱等方面的影像特点,得到了遮蔽。 在鲁迅影像的自我建构中,具有生活气息的影像不是太多,值得关注的是他在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的照片(15)和同年初夏与内山完造的合影(16)。这两幅照片,为我们还原了脱下中式长袍、富有世俗化气息的鲁迅影像。前幅照片,鲁迅穿着许广平为其编织的两件毛衣,右手拿烟,左手叉腰,身体向右微侧,拍摄者采用了仰拍的方式,就把富有生活气息的鲁迅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后幅合影,鲁迅更是双手叉腰,这和内山完造的双手合拢的内敛造型相比,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富有“战斗”风姿。 鲁迅的服饰是怎样变化的固然值得关注,然而,同等重要的还有服饰的新旧,这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传达出鲁迅的内在精神。和一般人不同,鲁迅并不重视服饰的新旧,这种情形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正如有人回忆的那样:“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他从未沾染丝毫。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17)那么,穿着如此“寒碜”的鲁迅,到底是缘于怎样的考虑呢?对此,鲁迅是这样阐释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18)其实,鲁迅的这种思想恰与他所接受的“野蛮其体魄”的观念有关系。 二、他者建构的鲁迅影像 鲁迅尽管在身高上不属于伟岸之列,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他的认同乃至崇拜,而这认同乃至崇拜,恰是来自他那文学家的身份。 在民国教育体制内,鲁迅的大量作品得以传播。在作品传播的过程中,文学家的鲁迅影像便得到了凸显,这使得他者在“未见其人”之前,便已经“如见其人”。由于“如见其人”仅仅是通过阅读作品根据想象建构起来的影像,所以当人们和真实的鲁迅初次见面时,其反差之大还是足以使仰慕者“瞠目结舌”。好在有根据想象性建构起来的影像作支撑,这便反转过来促成了人们依照想象性建构出来的鲁迅影像投射到真实的鲁迅身上,进而完成“对象化”。那么,人们又是怎样把想象性建构出来的鲁迅影像和真实鲁迅对接的呢? 其一,对鲁迅的胡须、头发等赋予文化的象征功能。如果我们细读一些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可以从中发现,人们在对鲁迅的精神品格进行对象化时,更多地和其胡须、头发进行联系,通过其胡须、头发与鲁迅的文化身份对接起来,这便使得鲁迅的胡须、头发成为可以承载鲁迅思想的一种物化对象。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获得了青年学生的认可和推崇,其影像自然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如对鲁迅的头发等有人如此描述:“我被高度的感情震慑住了,当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只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灰黑色的头发是那样凌乱,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深厚的内涵,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和宝贵的智慧潜藏在里面!瘦削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我不禁在这儿涌起更深的同情和忧虑。他靠在书案上的那支手捏着一支燃起的纸烟,显得很有趣味的眼光把我们这初次来访的青年望着。”(19)至于鲁迅成名之后,其胡须在学生们的眼里也成了“美极了”的表征:“‘你看,’那位同学把我的胳膊挽着,扭转身来望着我笑,走起路来他在打倒退,‘鲁老头儿其实美极了,你看那眉毛!那胡髭!’”(20)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鲁迅依然备受推崇:“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吧,我第一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小学校里,与会的大多数人我都是新相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言。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21)对丁玲的这一回忆,我们如果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便可以发现,“黑色长袍”、“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是采用了一种写实的手法,而关于“眼神”中闪烁的“铮铮锋利”,则含有极其鲜明的情感色彩,表达了丁玲对鲁迅的无限推崇敬仰之情。文学青年草明在见到鲁迅之后,也将鲁迅的胡须赋予了“韧性战斗”的精神:“啊,先生那仰面的深邃而倔强的丰采,那两撇不屈的富于韧性战斗的胡子,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并获得了作品与人品的统一的印象。”(22) 诸多的文学青年和在校学生作为鲁迅的拥趸者,对鲁迅有着非同一般的崇拜,当然,他们在将想象中建构起来的鲁迅与现实中的鲁迅对接时,落差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缘于他们对鲁迅影像的想象性建构已经纳入到其情感体系之中,故尔,这样的接受落差还是得到了有效修补。鲁迅1927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们所看到的是“矮小”、“黄瘦”的鲁迅:“鲁迅来到广东的时候——仿佛是冬天吧——我独自向服务的机关告了假,渡江到中山大学去听他到广东后第一次演讲,坐在拥挤不堪的听众中间,待朱骝先校长介绍了以后,出现的却是个矮小的可怜的黄瘦的人,这自然有点使我失望,然而我却马上从他那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他那战斗的精神。”(23)缘于从既有的阅读中所建构起来的鲁迅的伟岸影像,使文学青年见后感到失望,但他仍然从鲁迅的“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鲁迅的“战斗的精神”,这样的修补和重构,正是既有的思想和情感对象化过程中的产物。 实际上,鲁迅作为一个陌生人进入文学青年的视野时,其初次见面的影像原本是这样的:“车停在老靶子路的时候,夹在一群人当中,挤上一个矮矮的老头子来,褪色了的灰布长衫裹着瘦小的身子,蓬乱的短头发里夹带着不少的白丝,腮很削,颧骨显得有点高耸,一横浓密的黑须遮住暗红的上唇。他挤进了三等车厢,就屹然地站立在人堆当中,虽然矮小,却显得倔强;明锐的眼光时时扫射在同车的人们的身上,时时又定定地瞪视着远方。”(24)鲁迅给文学青年以群留下的影像是“矮矮的老头子”、“瘦小的身子”、“蓬乱的短头发”等,显然,这样的影像和那种文化巨人的影像是不合拍的;但是,缘于这样的影像是鲁迅留下的,所以,以群在这一影像中,又发现了这个矮矮的小老头那“有点高耸”的颧骨、“显得倔强”的性格和“明锐”的眼光。其实,这样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恰是文学家的鲁迅通过其作品投射到包括以群在内的文学青年心里的。可见,文学青年把鲁迅的头发当作其“卓尔不群”的对象化特征,他把阅读建构起来的巨人鲁迅的影像和现实中的普通鲁迅形象对接了起来。如果没有文学家的鲁迅作支撑,那鲁迅也许最终会“泯然众人矣”,甚至可能连“众人”都不如。这种情形,在有关鲁迅的遭际中不是没有出现过。如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一文中,便为我们转述了鲁迅所遭遇的一次“非人”待遇:“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指鲁迅,引者注)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们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通,于是乎说‘走出去!’”(25)当然,鲁迅在这里遭遇到“非人”的待遇,除了没有那种“范儿”之外,还与其穿着较为普通有关系。但这也正说明,司机由于没有预先建构起文学家的鲁迅影像作为接受前提,所以才把鲁迅当作“下等人”赶了出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无独有偶,除了中国人将鲁迅的胡须和头发作为凸显其思想的载体之外,外国的一些友人对鲁迅的影像感知也是大体上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就这样写道:“他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26)在这里,史沫特莱特别凸显了鲁迅的头发,并且还特别指出了鲁迅的头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鲁迅的脸型尽管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但缘于文学家这一影像的支撑,也就顺理成章地使鲁迅成为她“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至于日本友人眼中的鲁迅影像,则是“短个子、粗胡须、风骨凛然、脸色苍白、看上去身体很弱但眼光似乎有点特别,很像我国的犬养木堂似的中国绅士”(27)。在长与善郎的叙述中,鲁迅尽管“短个子”,但这并不影响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风骨”,这其中的标志便是“粗胡须”。显然,具有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取着同一路径的认同乃至推崇,除了鲁迅的胡须和头发有着独特之处以外,也说明了其胡须和头发的确承载了他那率真、倔强的性格,并由此成为鲁迅独立精神的象征。 其二,对鲁迅的眼睛赋予心灵窗口的透射功能。眼睛作为人的心灵窗口,其眼神自然就透露着人的内在精神气质。鲁迅曾就小说中如何刻画人物形象问题有过这样的论述:“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28)而最能够标识出人物特点的,则是人物形象的眼睛:“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29)其实,从事小说创作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大都将“画眼睛”当作建构鲁迅影像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如萧红就这样刻画过鲁迅的眼睛:“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30)萧红在这里对鲁迅的“眼光”的描写,不仅把其眼睛背后所隐含的“功能”呈现了出来,而且还把眼睛中的“眼光”予以了升华,把其视为“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这样,就把鲁迅的“眼光”置于“旷代”的时间坐标上,由此显示出了鲁迅“眼光”的意义。 实际上,将鲁迅的眼睛赋予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只萧红一人。在许多人那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路径。姚克便这样描写鲁迅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转动的很敏捷,但看人的时候却很定直而尖锐,又隐隐约约有一丝Pathetic的微茫,使人觉得这一双眸子不但‘读书破万卷’,并且也曾阅尽了这‘人间世’。”(31)这就把作者所见到并想象出来的那双“眼睛”,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使得这双“眼睛”阅尽了“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具有了内在的透视功能。 除了那些刻意突出鲁迅影像的思想意义的文章之外,也有一些文章重在表现非常状态下的鲁迅影像,这样的影像尽管褪去了其思想的外衣,但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嗔有怒的本真的鲁迅形象。鲁迅尽管有着非凡的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所有的行动都是中规中矩的,鲁迅也有失态的时候。如醉酒中的鲁迅,便具有了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气概:“席上闹得很厉害,大约有四五个人都灌醉了,鲁迅先生也醉了,眼睛睁得多大,举着拳头喊着说:‘还有谁要决斗!’”(32)鲁迅在此表现出来的“醉眼中的朦胧”,对我们理解性情中人的鲁迅,具有更大的意义。尽管鲁迅身高没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柔弱”的。显然,在“酒神”的感召下,鲁迅被压抑已久的“决斗”欲望找寻到了喷发口,而其眼睛则成为传达其真实性情的窗口。 对鲁迅的眼睛,外国友人则淡化了其中的那种“横眉冷对”的战斗意味,多了一些“春风化雨”的文化赋予。如史沫特莱便这样描写过她和鲁迅相见时的情景:“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33)史沫特莱作为外来者,也许对鲁迅所身处的国家缺少更为真切的把握,但在她对鲁迅眼睛的感知上,突出了“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的闪耀着”的特点,而这样的感知,正是她从文化的视角对鲁迅独特性的把握。鲁迅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属于民族的、中国的,而且还属于人类的、世界的。也可以说,鲁迅即便被纳入到美国文化之中,也自有其独到的“智慧和兴味”。 鲁迅影像的这一独到之处,在被纳入到美国文化之中加以审视时是如此,在被纳入到日本文化之中加以审视时也是如此。藤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就为我们描画了留学日本时的鲁迅早期影像:“周君身材不怎样高,圆脸,是聪颖相的人。脸色看上去不太康健。我教的是人体解剖学,他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总之在入学时好像不大能充分地说日本话,听讲也不大理解。好像用功得非常吃力。”(34)鲁迅给藤野先生留下最深的影像就是“身材不怎样高,圆脸”,藤野先生的这一叙述无疑是从客观实际的印象而来的。至于鲁迅获得了文学盛名之后,日本友人鹿地亘则从鲁迅的初期轮廓聚焦到了其眼睛上:“我忘记不了垂问我的健康的鲁迅那双充满了挚情的眼。”“我必须谈谈鲁迅的眼。”“他的眼睛,是怎样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啊!他的眼就像在底里荡漾着光辉的深泉那样澄澈着。当房门推开,穿着宽大的华服的他,静静地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我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对坐着,为他那静穆的神情所震撼,就像怕在泉中激起波纹似的沉默着。”(35)而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作者这样的一种感觉,并不是通过长久观察获得的,而是在“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便立马捕捉到了,由此给作者带来的情感反应则是“震撼”。其实,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与其说是鲁迅有一双“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不如说是回忆者本人带着对东方文化那特有的“静穆而温挚”的想象,并把这想象投射到鲁迅的“眼睛”上的结果。回忆者作为日本文化的承载者,把眼前的鲁迅及其文章和“具有东方的深刻之成熟的古典文体”有机地对接了起来。这实际上是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加以确认,是从鲁迅的文章作为这一文化长河的“流”,来反观东方文化这一长河的“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会想到:“鲁迅的眼就是他的文章。我在他的眼里感到了他那具有东方的深刻之成熟的古典文体,他那蕴藏着激情而宁静的语言,以及他那有如波纹荡漾的流露于文章之中的Humour。”(36) 当然,在外国友人眼中的鲁迅,也并不都是带有“智慧和兴味”、“静穆而温挚”,有时候会“目光森森”、“锋棱逼射”。如史沫特莱就有过这样的回忆:“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黝黑,没有梳头,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37)可见,当鲁迅被激愤的情感占据时,即便是对中国社会还无法做到感同身受的外国友人,也依然感觉到鲁迅眼中投射出来的是那种毫不妥协的战斗锋芒。 其三,对鲁迅矮小的身材赋予博大思想的反衬功能。鲁迅尽管身材不是伟岸高大,甚至在诸多人的眼中还显得有些“矮小”,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制约鲁迅影像高大的因素。相反,在诸多回忆文章中,突出鲁迅身材的矮小和突出鲁迅人格的伟大,是作为两个极点加以对比而共生共长。如此一来,鲁迅的身材矮小便不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书写,而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加以使用。 客观地说,所有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伟大人物,在他者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影像中,往往都和“伟大”联系在一起,即便身材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身材却不然,这使许多初次见到鲁迅的人,大都有着接受心理上的落差。如马珏在初次见到鲁迅时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他是鲁迅,因为脑筋已经存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所以不很相信。”(38)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和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其所传达出来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注重的是“小孩似”的“阳光明媚”,后者注重的是“老头似”的“老气横秋”,当然,其中也不乏她对鲁迅身高失望的委婉传达。相形之下,还是一些男性作者来得更率真:“昏暗中,我望着一位矮而且瘦的老头子,穿着一件棕黑色的毛线上衣,用短促的南方口音在打招呼。”这样的文字,就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了鲁迅的身高和体型。然而,当文学青年想到这个“矮而且瘦”的“老头子”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文学导师”时,“我的心突然像跳到口腔里来,我想,现在同我们惟一的文学导师会见了”(39)。 类似的感受,在诸多的文学青年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文学青年草明便这样写道:“当我发现他瘦小单薄的身躯时,我又惊诧那瘦弱的躯体如何装得了他那博大的灵魂!后来与先生过往多些时,我又发现他另外一种气质,就是对同志极端热情,特别是对革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有如慈母。”(40)草明通过中学时期的文学阅读就接触到了鲁迅的文学作品,并由此进行了对鲁迅的想象性建构。然而,当草明真正见到鲁迅时,还是“惊诧”鲁迅那“瘦弱的躯体”是如何承载“博大的灵魂”的。显然,草明在接触鲁迅时产生心理上的“惊诧”,无疑是对鲁迅“瘦小单薄”身躯的真实反应。他在文章中把这一“惊诧”和鲁迅的“博大的灵魂”联系起来,便是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在情感上是认同的。与草明的认知一致的是姚克,他这样叙述了自己与鲁迅“最初和最后的一面”:“若只就他的身材而论,那他是很渺小的,站在平地不过五尺四寸左右高,很瘦弱的样子。”(41)“这样一个人,假使你在大街的稠人中瞧见他,你绝不会注意——渺小平凡得很。但一旦和他对面坐着,你就绝对不觉得他渺小和平凡,你只觉得他气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和猥琐。”(42)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文学家的身份作为支撑,那么,像鲁迅这样的“身材”便会“渺小平凡得很”;当你“和他对面坐着”进行交谈时,没有了这种“身材”的具体对比,而是进行思想的对话,则会感到鲁迅的“气宇的宏大”以及自己的“渺小和猥琐”。这样的表达除了作者对自我情感和思想的真实记录之外,也是使用了一种对比的修辞手法。而这样的修辞手法,又是从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鲁迅身材的“渺小平凡得很”与他思想的“气宇的宏大”的对比;二是鲁迅思想的“气宇的宏大”和自己思想上的“渺小和猥琐”的对比,这两种维度上的对比,最终凸显的则是超越身材向着体现其思想精神世界的皈依。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人的肉体这样的物质回归于自然时,能够超越肉体而留存未来的只能是其所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 三、鲁迅影像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接受 鲁迅建构起来的影像,得到了许多学生和文学青年的推崇,这其中的缘由尽管很多,但民国教育体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主要就鲁迅影像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接受维度加以分析。 其一,鲁迅影像的接受与帝制消亡以及民国体制的确立有着直接的联系。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历史发展尽管也出现了某些反复乃至倒退,但从形式上来看,帝制已经无法再像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那样继续存在下去了。与此相对应,晚清时期居于社会边缘的鲁迅,则成为教育部的公职人员,由此开始了向社会和文化中心的位移。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鲁迅通过新式教育得以进入晚清政府所主办的新式学校,并获得了留学日本的历史机缘。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断发”,这为他确立自我影像的主体性,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本来,头发的“断存”属于一种私人化的行为,但是,这种带有私人化的行为,却被清政府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要求汉族要像满族那样也“留发”,由此使得“留头”“留发”不相兼容,清政府由此达到征服汉族的族群意识,进而皈依满族统治的目的。从这样的维度上看,在早期影像建构中,鲁迅的“断发”壮举,便不再仅仅属于私人化的行为,而是具有极强的革命内涵。 如果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断发”还不至于有“杀头”之虞的话,那么,留学归来有无“头发”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对此,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便用第一人称这样写道:“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然而,当“我”回到故乡,旁人“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43)至于在小说《风波》中,鲁迅更为人们展现了有无“头发”所带来的巨大“风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44)从《风波》中可以看出,从“我”到“七斤”,从“旁人”到“七爷”,如果皇帝继续坐龙廷,他们都将被“头发”的问题所困扰。解除头发的困扰,是一大批革命前驱毅然决然地告别传统、走向新生的重要标志。 鲁迅的断发影像,在回国之后所产生的反响还是非常大的。“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45)但是,这依然在学生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鲁迅的学生吴耕民有过这样的回忆:“因鲁迅先生无辫子,我甚至不怕王法,冒着大逆不道的罪,用鲁迅先生从日本带来的轧发剪(他因自己要理发,交给了当时绍兴府中学堂的理发师),请理发师把三尺长的辫子剪掉。同时立志苦读,希望将来也可如鲁迅先生出洋求学,学些本领,回国做一个好教师,培育人才,使国家趋于富强,免受帝国主义欺侮。从此,开始树立了我反清爱国的思想。”(46)鲁迅的断发“壮举”之所以被特别推崇,既意味着鲁迅当年那种迫于无奈而被迫“走异路,逃异地”(47)之举,正在为更多的学生所接受,更意味着其“无辫子”的影像已经开始为学生所效仿。然而,如果没有民国政体的确立,不但学生的这种接受和效仿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鲁迅的影像能否长久地存留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对此,鲁迅这样说过:“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48) 其二,鲁迅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佥事、新文学作家以及大学兼课教师的三重身份,使得鲁迅影像的建构与接受获得了多重因素的支撑。 严格说来,鲁迅并不是游离于民国教育体制之外的人,而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于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人,只不过这种体制内的身份有时候紧密一些,有时候疏离一些。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鲁迅便进入了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教育部,可谓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最早的一批公职人员;南北和议之后,鲁迅又北上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供职,并担任了佥事一职。在此期间,鲁迅主导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工作,制定了《小说股办事细则》,规范了有关审核小说的范围及程序。该细则对小说的调查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指出:“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训查”(49)。尽管这种调查由于鲁迅的离职没有全面展开,但是,这种调查的自觉意识,却使鲁迅对小说有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读者的文体意识。为了开展好这一工作,鲁迅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小说,并勾勒出了中国小说史的大纲。我们如果把鲁迅的这一工作同他在此前所从事的异域小说的翻译联系起来看,便会发现,鲁迅身在教育部,借助教育部的诸多便利,已经初步打通了古今中外小说的基本脉络,这既对他起草指导全国的通俗小说发展的细则提供了支持,也为他从事新文学创作、进入大学担任兼课教师提供了支撑。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鲁迅凭借对古今中外小说较为全面深入的把握,在陈独秀(50)、钱玄同等人的再三邀请下,开始了现代小说的创作。其《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意象,是凝聚作者心力的艺术创造,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具备深邃情思蕴涵和阐释空间的意象”(51),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和现代文体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鲁迅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并逐渐建构起了文学家的影像。许多人之所以对鲁迅的影像有着想象性的建构,恰是通过阅读了他的小说才开始的。 正是由于鲁迅具有新文学作家的显赫声誉,同时又具有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洞幽烛微的评判能力,于是,许多大学开始聘任鲁迅担任兼课教师。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称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鲁迅担任诸多大学的兼课教师,便使他迈出教育部幽深的大院,走下新文学创作的圣坛,来到了学生们中间,这对学生传承新文学的精神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至于鲁迅1926年离京南下、最终脱离了教育部这件事,严格说来,也仅仅意味着鲁迅脱离了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部。但是南下之后,鲁迅在许寿裳的推荐下,被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于1927年12月聘为“特约撰述员”。由此可见,鲁迅脱离了北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部之后,又进入了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教育体制内。显然,这样的“特约撰述员”身份,不仅对鲁迅专心从事写作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而且还对鲁迅获得相对优裕的政治空间提供了保障。 鲁迅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佥事、作家和兼课教师这三重身份,使他成为深受学生崇拜的对象,他的每次演讲都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对此,鲁迅似乎也有所感知。1931年11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有学生后来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都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52)这就是鲁迅具有非凡魅力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形在鲁迅到了上海之后,也依然盛况如前,正如郑伯奇所说的那样:“大夏大学的礼堂兼操场是挤满了人。当时左联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毫无意义(53),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来的。”(54)鲁迅的这种非凡魅力,不仅征服了许多青年学生,而且还折服了外国友人。海外友人曾回忆道:“接连不断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时候,就会恍恍惚惚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55)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超越了外在身材的渺小,在青年学生乃至外国友人的情感心理上建构起了文化巨人的真切影像。 其三,民国教育体制确立了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合法地位,为鲁迅的作品进入大中小学课本提供了机会,这自然使鲁迅影像获得了发扬光大。 随着民国教育确立了白话文在语文教育中的正宗地位,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便一下子取代了过去被奉为圭臬的“子曰诗云”,成为在大中小学影响学生的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重要教材。显然,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同时代的文化人,能够被现时代所接纳甚至推崇,这在历来推崇孔孟之道的私塾教育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何况是在重视“祖宗崇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在民国教育体制下,鲁迅的文学图景则徐徐地铺展开那迷人的魅力。许寿裳曾经这样回忆道:“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十余年前,在孔德学校小学班已经读了鲁迅的作品。有一天,听说鲁迅来访她的父亲了,她便高兴之极,跳跃出去看,只觉得他的帽子边上似乎有花纹,很特别。等到挂上帽架,她仰着头仔细一望,原来不过是破裂的痕迹。后来,她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56)这样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几个信息:第一,鲁迅的文章已经在民国教育体制的“保驾护航”之下,进入了小学的语文课本,由此使得其被纳入到了文学教育的传播链条中,这使得鲁迅其人其文得以进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情感认知链条之中,获得了存在和被认知的根基;第二,鲁迅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备受推崇的,以至于他的影像获得了人们的无限的想象,甚至被描画为一个非凡的“西装革履”的绅士。这甚至还流传到了国外,并引发了留学的文学青年的强烈共鸣。吴似鸿曾回忆:“当民国十五年,中国蓦起革命的洪涛,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极矫健极俏皮的青年。”(57)无论是国内的学校还是国外的学校,严格说来都是民国教育体制下的产物,而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借助民国教育体制,使他者对鲁迅影像获得了想象性建构,为其接受和推崇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么,鲁迅其人其文是如何借助民国教育体制进入学生的文化视野中的呢?我们不妨借助吴似鸿的回忆来还原这一历史:“记得那时有个姓章的老师,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绍兴女师教国文,曾经向我们宣传说:‘鲁迅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他转变了,转到共产党一边了。’起初,我听了觉得很惊讶。不久,他又向我们宣传鲁迅,说鲁迅怎样刚强不屈,敢想敢说,说《阿Q正传》是怎样轰动北京,《孔乙己》又是写得那么出色和有趣。他还在课堂上形容孔乙己的茴香豆是怎么好吃,唱阿Q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打死你昏君命一条……’唱腔,等等。本来我们的国文课中没有鲁迅的作品,章先生叫学校印了活页,选读《阿Q正传》和《孔乙己》两篇文章,讲给我们听,讲得活灵活现。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心灵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开始觉得中国正需要像鲁迅那样的人物来影响人们,由此产生了对鲁迅非常敬仰与崇拜的感情。”(58)包括“绍兴女师”在内的学生,之所以对鲁迅产生了“非常敬仰与崇拜的感情”,正是借助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学校课堂教育。在这样的课堂上,那些在大学亲炙鲁迅其人其文熏染的学生,一旦转化成为教师,便会从他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之中,“复制”出他们所接纳的文学教育的路径,进而“还原”给他们所执教学校的学生,由此使得鲁迅其人其文通过民国教育这一渠道完成了代际的传承。这样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鲁迅,已经深受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的推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推崇还延及一些小学生,这对鲁迅其人其文确立起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合法性地位,并获得进一步的传播和推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认同和推崇的基础上,鲁迅便成为一个“跟封建势力勇敢作战”的战士,在诸多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此,欧阳山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鲁迅跟封建势力勇敢作战,在北京反对北京的黑暗势力,所以在青年,特别是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青年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不仅把他看作文学上的大师,同时也把他看作一个革命家,一个跟黑暗势力战斗的战士。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他的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也成了报纸副刊文章的题目。在广州的青年们确实没见过这样的文学家、革命家:穿蓝布或黑布长衫,穿那种叫做‘陈嘉庚’的帆布胶底鞋,抽比‘美丽牌’还便宜一半、一毛钱二十根的廉价的‘彩凤牌’香烟,胡子长长的,头发也是长长的,几个月也不理一次发,好像是一个乡下老头子。如果他只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文人,自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但他却是个大文学家,又是个对黑暗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战斗的革命家,那影响就不同了。青年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甚至连他到哪里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哪里理发,和许广平到什么地方去之类的事情,都喜欢多方打听。在他住的大钟楼的附近,平时都有很多青年人在那里徘徊张望,留连忘返,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即使是远远地望一眼也好。”(59)欧阳山的这一回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带有流行的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明星”形象,而年青人则是这一“明星”的热烈“追星一族”。如此热烈的盛况,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物换星移”的文化场景。这种场景,正是曾经怀揣着梦想的鲁迅所企求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0)的场景。十几年前,鲁迅曾经在自我反省中谈到自己“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其前面的修饰语“决不是”恰是鲁迅热切地期望着成为这样的英雄的明证。然而,这一时期的鲁迅已经是不再需要“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英雄了。 其四,民国体制的确立,为鲁迅反抗现实和抨击民国政府的战斗檄文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这使鲁迅影像的接受有了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宪法上讲,中华民国确保个人的言论自由,明确了民主与科学诉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38年的时间里,中华民国的执政府便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不管由哪个政府主政,都深受中华民国这一体制的制约。在此情形下,抨击政府的不法行为和反对中华民国体制便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在此情形下,不管鲁迅抨击段祺瑞执政府的《记念刘和珍君》,还是抨击国民政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政府具体行为的严厉抨击,自然在民国体制的许可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单就文学运动而言,左翼文学也可以看作民国体制下的产物。 1927年,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所具有的那种相对适宜和宽松的政治气候,随着奉系军阀对李大钊等人的杀戮,已经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鲁迅不得不像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一样,离开北京,先是到了厦门,然后到了广州,开始重新寻找更为适宜文学创作的政治气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东南飞”现象,极大地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使上海成为新文学的又一重镇,并带来所谓的京派和海派之争。鲁迅投奔到革命运动中心广州后,应邀担任了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和教师,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在大会上介绍鲁迅时,便强调了鲁迅的“战士”身份,但其对鲁迅的“战士”身份的认同,是基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之上的。当蒋介石在对共产党进行清剿后,鲁迅便断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来到上海,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十来年的文学生涯。在上海期间,鲁迅参与了左翼文学运动,国民政府对思想日渐“左转”的鲁迅也曾发出通缉令,但缘于鲁迅并没有像“左联五烈士”那样参与政党活动,而是以文学家的身份从事文学活动,再加上租界对政治的某些屏蔽功能,这就最终使其通缉令并没有落到实处,但这却使鲁迅在文学家影像之外,又建构起了国民政府的“批判者”影像。对此,瞿秋白把鲁迅纳入到革命文化及其阶级谱系中,确认了“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61)。冯雪峰则把鲁迅纳入到了中国文学的谱系中,确认了“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对冯雪峰的这种确认,鲁迅似乎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的。对此,冯雪峰有过这样的解释:“关于在后面说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屈原、杜甫等的精神上的传统的一点,他当时笑着说:‘未免过誉了,——对外国人这样说说不要紧,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然而我觉得:谁能够否认鲁迅比屈原、杜甫更伟大!而先生自己也没有将这一点涂去。”(62)这样一来,鲁迅在左翼文学运动中,便被逐渐地从一个文学家塑造成了一个“民族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则把鲁迅看作“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63)。到了1940年1月,毛泽东更把鲁迅看作“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4)。如果说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鲁迅影像的理解和接纳是基于个人的认识,那么,到了毛泽东那里,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影像的解读,便不再局限于鲁迅的头发、胡须、眼睛以及身材等具体的方面,而是鲁迅的“骨头”。对此,毛泽东用“最硬的骨头”这样的修辞手法把鲁迅影像塑造成了“民族英雄”。这实际上就把鲁迅纳入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谱系之中,意味着在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方面鲁迅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鲁迅影像又逐渐地被解读为“革命影像”。 综上所述,鲁迅通过对自我影像的有意识的建构,完成了自我超越,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凸显出了已经醒来者的真影像,表现了富有个性的“真的人”那种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者通过对鲁迅影像的想象性建构,使得鲁迅思想的传播获得了可以寄寓的载体,这为其接受新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说来,鲁迅的影像之所以能够超越身材等外在形式上的局限,进而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植根于人们心中的结果,又是民国教育体制得到有效发挥的结果。 ①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2页。 ③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3页。 ④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⑤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 ⑥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29页。 ⑦“若”字在原刊中为“差”,在收入《海外回响》一书中,则误排为“若”。原文见《作家(上海)》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 ⑧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⑨吴耕民:《回忆七十年前的母校》,柳亚子等著:《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⑩“木瓜之役”本身也与服饰有着极大的关联。新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夏震武于1909年10月上任,他一上任,便要整治校事,首当其冲的便是装束。他认为,这是大清国的学校,当然要穿大清国的正装。所有的教师都要依照旧制,要戴红缨帽,硬领的满清制服,开衩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这说明,服饰在清末民初的确具有政治的、文化的意义。详见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46页。 (11)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41页。 (12)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47页。 (13)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56页。 (14)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161页。 (15)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197页。 (16)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鲁迅影像故事》,第212页。 (17)孙伏园:《忆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18)孙伏园:《忆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60-61页。 (19)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鲁迅在北平》,孙伏园、许钦文等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0)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鲁迅在北平》,孙伏园、许钦文等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19页。 (21)丁玲:《鲁迅先生于我》,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76页。 (22)草明:《五十年祭》,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16页。 (23)王任叔:《我和鲁迅的关涉》,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29页。 (24)以群:《忆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43页。 (25)内山完造:《鲁迅先生》,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115页。 (26)史沫特莱:《忆鲁迅》,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3-4页。 (27)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36-37页。 (28)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6卷,第382页。 (2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3页。 (30)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39页。 (31)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48页。 (32)曙天女士:《日记片段》,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6页。 (33)史沫特莱:《追念鲁迅》,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15页。 (34)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78页。 (35)鹿地亘:《鲁迅访问记》,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80页。 (36)鹿地亘:《鲁迅访问记》,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81页。 (37)史沫特莱:《忆鲁迅》,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8页。 (38)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8页。 (39)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鲁迅在北平》,孙伏园、许钦文等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14页。 (40)草明:《五十年祭》,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16页。 (41)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48页。 (42)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48页。 (43)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63页。 (44)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第471页。 (4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2页。 (46)吴耕民:《治学漫谈》,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学人谈治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4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 (48)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9页。 (49)《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参阅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51页。 (50)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51)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 (52)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内部刊印本),1978年,第209页。 (53)在原刊发的文献中,此处的“意义”是“疑义”。在本文所引用的《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一书中,则把“疑义”误排为“意义”。 (54)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义化名人忆鲁迅》,第24页。 (55)原胜:《紧邻鲁迅先生》,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第52页。 (56)许寿裳:《鲁迅的生活》,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81页。 (57)白薇:《我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和感想》,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10页。 (58)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第157-158页。 (59)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第34-35页。 (6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61)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6-527页。 (62)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63)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6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