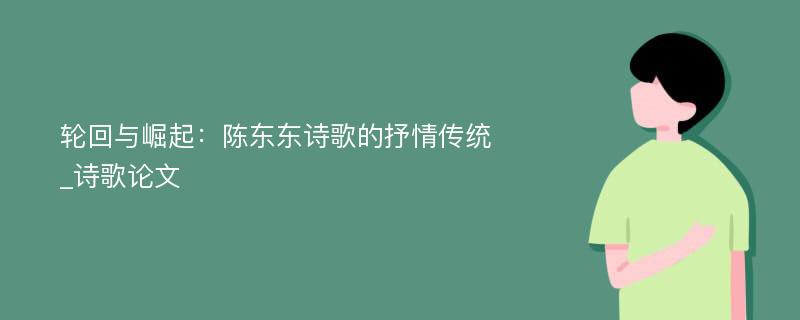
轮回与上升:陈东东诗歌的声音抒情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诗歌论文,声音论文,传统论文,陈东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3-0012-06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潮在争议中席卷而过,一部分第三代诗人试图颠覆诗学传统,在断裂的轨迹里勾勒新的诗歌脉络;而另一部分则选择在艰难的语境中延续传统,返归诗歌之根本。就后者而言,可以说,陈东东是那个时代与传统结合较为紧密的诗人之一,他不断地在中西方诗歌的交叉影响中,重拾比兴与声音,幻化出理想的诗句。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于坚、韩东等口语化的诗歌表达,抒情的意象化书写以及节奏的音乐性传达,成为他诗歌与传统之间最贴切的对接。陈东东极为重视声音与诗歌的关系,他提到过:“需要一行诗,一个词,甚至只需要一个声音,去重新落实悬浮的世界。”[1]声音所彰显的内涵,已不再停留在平仄、格律等诗学话语与评价系统中,随着诗歌内蕴丰富性的加强,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他的诗歌中,复沓、回环的诗歌结构、情绪化的诗歌语调、以及词语或者句子之间的承接中断,都构成了他诗歌创作中的声音美感,凸显出自觉的生命律动和剧烈的情感浪潮。他在诗歌中,反复提到“一种节奏超越亮光追上了我”、“她跟一颗星要同时被我的韵律浸洗”(《夏之书》),而他的诗歌文本《流水》,更是将音乐的空境发挥到了极致,“空气传递音乐,将抵达宝塔和寺僧之时,音乐却已经变成了空无”。音乐重复出现,吐露出诗人对于音乐的敏感性,犹如东坡奏起的琴歌。而诗歌中,陈东东所流露的恰是音乐性所带来的轮回与上升的抒情功能。
一、音乐性的自律
陈东东对于音乐的感觉,向来颇有自律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把握诗人的这种自律,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似乎无法抵达诗人感觉上的一种自动性。然而,陈东东在一次题为《诗跟内心生活的水平同等高》的访谈中,为其诗歌在声音上的探讨,打开了局面。“把握语言的节奏和听到诗歌的音乐,靠呼吸和耳朵。这牵涉到写作中的一系列调整,语气、语调和语速,押韵、藏韵和拆韵,旋律、复沓和顿挫,折行、换行和空行……标点符号也大起作用。写诗的乐趣和困难,常常都在于此。由于现代汉诗没有一种或数种格律模式,所以它更要求诗人在语言节奏和诗歌音乐方面的灵敏天分,以使‘每一首新诗’都必须去成为‘又一种新诗’。”[2]事实上,“有效的诗歌理论是被建构出来的”[3],即使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声音在形式上缺乏规律,但也正因为此,才更体现出声音在诗学体系中的渐趋成熟。那么,面对词句在诗篇中的存在,至少在揣摩语言的呼吸时,能够捕捉到一些节奏上的情绪。
陈东东的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而他的母亲曾在越剧名老生张桂凤门下学戏,后成为上海越剧院的演员。在音乐的家庭背景中成长的陈东东,对于声音的敏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与之相关的是,对于词语所造成的特殊声音效果,在他的诗歌中,也较为明显。柏桦称陈东东的诗歌具有“吴声之美”[4],祖籍江苏吴江芦墟,生活在上海,地域文化的浸润,已渗透于他的诗篇中。因为古时吴歌产生于江南地区,“四方风俗不同,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闻之使人酸辛”[5]。陈东东的诗歌可谓承继了吴歌复沓、婉约优美、低沉的乐音。
黑暗里会有人把句子点燃/黑暗并且在大雨之下/会有人去点燃/只言片语,会有人喃喃/低声用诗章安度残年
在青瓦下,在空旷的室内/会有人用灯把意义点燃/会有人惊醒/独自在黑暗里/听风吹雨
独自在窗下/会有人看清点燃的街景/马车驰过,似乎有千年/早已在一片夕照里入海/马车驰过,像字句被点燃/会有人看清死已可期
(《残年》,1986)
诗人渴望在黑暗里表达与残年相关的情感基调,字句所勾连起的诗章成为残年的灯盏,将意义与幻想点燃。陈东东的诗歌,被臧棣指认为“华美”的言辞[6]。似乎与叙事类诗歌或者口语诗歌相比,其诗作在华美的外表下,显得较为抽象,无法触摸到具体的所指。但华丽并不意味着空洞,因为无意义的空洞只能指向虚无主义,但在陈东东诗歌中读到的反而是形而上意义层面的实在。《残年》开篇,两次提到黑暗,是黑暗将句子点燃,同时,在黑色的雨境中,诗人的喃喃最终构成了诗篇。在铺展与延伸中,黑色被渲染至极限,从而引出“会有人”做的事。第二节中,诗人进一步延宕“会有人用灯把意义点燃/会有人惊醒”,在落笔与思索间,返回到黑暗与雨水中。第三节,“会有人看清点燃的街景/马车驰过,似乎有千年/早已在一片夕照里入海/马车驰过,像字句被点燃/会有人看清死已可期”,再次拉伸了情绪的表达,从黑色背景中,剥离出想象的空间,那点燃的意义是“夕照里入海”,是“马车驰过”,是“死已可期”,这三种场景都淹没在思绪中,又被灯点燃,幻化为字句。这首诗歌,在声音的表达上,不断地拉长抒情语调,延长抒情细节,如一滩泼开的液体,在黑暗与死亡的对照中戛然而止。而写于1981的《诗篇》,是他早期诗歌创作中的一首代表作,陈东东的青春写作,便开始尝试声音的奏鸣音效,可见,他已意识到,倘若没有声音的节奏和呼吸,那么,诗歌与散文、小说则无异。
在土地身边我爱的是树和羔羊/满口袋星辰岩石底下的每一派流水/在土地身边/我爱的是土地是它尽头的那片村庄/我等着某个女人她会走来明眸皓齿到我身边/我爱的是她的姿态西风落雁/巨大的冰川她的那颗蓝色心脏/琮琤作响的高大山岭我爱的是/琴弦上的七种音色/生活里的七次失败七头公牛七块沙漠/我爱的是女性和石榴在骆驼身边/我爱的是海和鱼群男人和狮子在芦苇身边/我爱的是白铁房舍芬芳四溢的各季鲜花/一片积雪逃逸一支生命的乐曲?
(《诗篇》,1981)
吴歌复沓回环的乐感,加之陈东东在创作中腾跃的效果,可以说,这种低沉、婉转、腾跃的音乐感觉,一直包孕于他的诗歌生命中。《诗篇》中以“我”为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语词音乐之间寻找着关联。荷尔林德说过,语言既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也是最危险的财富,而这种危险则来自于对个体存在的威胁。“语言不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7]语言即存在本身。与众多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诗人一样,关注词本身,返回语言之乡,成为其思想的皈依。陈东东将语词的追逐,与音乐之间进行了衔接。“七”在陈东东的诗歌中是一个特殊的数字,这数字首先是音乐中的七个音符,在某种意义上,其代表的更是一种声音上的命数,它指向音乐本身,也指向词语的生命律动。这种命数的规律,在陈东东27岁那年变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从唐代诗鬼李贺身上看到了27岁生命终结的命运。读陈东东的诗行,很自然地有种让人吟唱的冲动,《诗篇》的首句不断地重复“我爱的是”,在平稳的诗行中,却凸显了细微地情感变化。“树”、“羔羊”、“流水”,同样不断地加长名词的修饰成分,以绵延爱的深意。而“在土地身边”与“我爱的是土地”,“我爱的是她的姿态西风落雁”与“琮琤作响的高大山岭我爱的是”之间形成了一种回环的音响效果。结尾处又一次延续诗句的长度,又一次获得了一种情感的延宕。其中,诗篇中间“七种音色”和最后的“生命的乐曲”,无疑完成了节奏层面的音乐与词,与生命的勾连。
这种听觉上对音乐的兴趣,一直在陈东东的诗歌中存在着,从早期诗歌中直接的表达,到他的《流水》中对于音乐的抽象书写,以及最终将音乐幻化入诗句当中,渐渐成熟地升华了声音在诗歌中的独特性。可以说,陈东东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歌者,他将词与音乐交相融合,在不断地诗学尝试中,更坚定了诗歌之精髓。正如,“没有形式,就没有诗歌”的论断,诗歌首先是一种形式的艺术。然而,形式本身又不仅仅是形式,其必然因情绪与意义而生,并最终返回情感与意义。所以,探讨声音与抒情传统在陈东东诗歌中生成的可能,不得不考察其诗歌中意象的情感追求。就这点而言,笔者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归纳出禅意与上升两种并生的主题,从中反观声音的抒情性。
二、禅意的轮回
这是清凉的芦席,这是清凉的水/这是粗糙的太阳/户外浩大的太阳/这是我的居所,半个夏天的居所/这是我的诗章/供你诵读的诗章/这是街口,光滑的汽车,湿润的面容/如同黑色卵石的季节/这是鸣蝉高唱的树木/下午的余荫,耀眼的玻璃,这是/遮挡艳阳的屋檐,灿烂的/鲨鱼,归帆的姿态/这是帷幕背后的裸体,黯淡的短发/黄金的左腿/一群雨燕向街心聚拢/这是出门看海的日子,独坐的日子/低语的日子,这是/芦席清凉的,海/就在手中,背后的墙上呈现出诗章
(《诗章》,1986)
陈东东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81年,在他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诗歌中,饱含着青春的尝试,将诗歌推向了更广阔的无限中。在这些尝试性的创作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读出一种情感与意义所延展出来的节奏感,这无疑提升了诗歌在听觉上所造成的音响效果。《诗章》创作于1986年,诗歌中以“这是”的句式开头,展开诗歌的节奏,在对称的抒情语调里,诗人遵循一种情绪上的匀称性。其中,“这是鸣蝉高唱的树木/下午的余荫,耀眼的玻璃,这是/遮挡艳阳的屋檐,灿烂的/鲨鱼,归帆的姿态”,则切断了诗歌的这种匀称感,以短句和断裂的方式,加快了情感运行的速度。“这样的对称里,另一个对称的反例出现,目的则几乎是为了打破这对称的格局。”(《流水》)的确,在陈东东的诗歌中,常常出现这种回环往复的艺术特征。《词语》一诗,诗歌的每节都以“巨石之上/正对净化物质的大海”结尾,但在诗篇的中间又有些微的变化,两个相对的“正对净化物质的大海”分别出现第二节的结尾和第三节的开端之处,形成一种半封闭的诗章结构,既呈现出对称性,又加入了变化的元素。诗人在波动中延续着对于词本身的思考,与个体的思维律动感保持一致,词语已不再是词语本身,而是通向真理的符号,在诗歌结构的递进中,催化了诗歌的明确指向。同样,诗歌《点灯》,“把灯点到石头里去”,“把灯点到江水里去”,在重复中反复营造一种诗歌的匀称性,而最后的“点灯”,则打破了这种速度,变得短促、简练。如此的创作方式,在陈东东的诗歌中多次呈现,表露出诗人创作中对于声音的自在性表达。
如果说,石头,灯,雨,是他营造诗歌意境的惯用语词,那么,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色彩的多样性上,在禅意的发挥上,在思考的纵深方向上,以及在音乐与语言的追求方面,他都试图挖掘诗意上的深度。陈东东的诗歌中平静和节制多于激情,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个人空间感极强的生活方式,他内心的禅境,在少林寺的生活以及在西藏的游历,都或多或少地与诗歌中的场景构成了某种关联。敲打、钟声、匀速的节奏感,总能在诗歌中隐隐出现。他的诗句,在长短句之间变换,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自觉。1999年冬季,他曾在嵩山少林寺生活了9个月,夜晚在寺庙中看繁星的感觉,像“自己的天灵盖像是在为整个夜空打开了,可以让这片夜空沉降下来,进入我体内,我的丹田……”黑暗中,远离尘世的喧嚣后,冲淡的气息遍布诗人的词句中。在陈东东看来,写长诗是耗费体力和时间的事情。的确,对于尊重诗歌语言的诗人而言,每一次诗歌创作,都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洗劫,那么,长诗的创作更是掏空似的让诗人难以继续。就这点而言,陈东东诗歌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封闭性,他的组诗创作,由短诗连接而成,相对完整。如他的《夏之书》:
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传递着消息 在石头筑成的高台之上/乌有之王卫护的手 探寻的手 从一个白昼/向另一个白昼/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
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传递着消息 斧钺的反光把语言映照/我开口的时候有水滴凝结 像一种落花/像射日的弯弓收缩进冬天/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
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传递着消息 粉白的四壁间有我的记忆/我是在舒展的翼翅下说话 在冷风吹打的回廊里趺坐/我叙述的是我那唯一的旅行/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
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传递着消息 更高的星宿是更黑的阴影/在这座五月的城市里 乌有之王已敞开了梦境/他倾听又倾听/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见过街巷在秋光里卷刃/有多少次 我把手伸给黑暗之树/死亡之树 和太阳在葱郁中完整的另一面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潜行于秋天古老的檐下/看风景黯淡/如记忆衰退的悲恸年华/我触摸过最为寒冷的星宿/那一颗翻车鱼封冻的/太阳 看蝙蝠飞翔如疼痛的信号
我偶然弹拔毛发和琴弦 在深冬仅有的春天里对雪/我接受指引 枕放头颅于语言的河上/雾霭的窗前
鲜花里绿松石花蕊的肩头/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我衣袋里兜满了/细沙和火焰
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在酸涩的叫喊间/学会了记忆/我见过苍茫里黑暗的神 仇恨的神/阴毛卷曲的失望的神/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 从一种饥饿到另一种饥饿
都能看出,诗人在结构诗歌时,一种轮回的习惯性创作方式,自动地调整句子与句子间隔的距离。无论“黄道十二宫传递着消息”,还是“我生于荒凉的一九六一”,都像是有始有终地完成一种情绪上的完满。除此之外,较具有说服力的是他的诗歌《秋歌二十七首》,全诗分为27首,每首27行,每首6节采用5-4-5-4-5-4的行数安排,可见,陈东东在诗歌音乐性的节奏安排上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与翟永明、杨炼等叙事诗人不同,陈东东的诗歌并非在诗歌空间结构上有意为之,他所表达的也与情节无关,他的诗歌指向的永远都是一种情感上的动态,一种思绪上的意义合成。因此,在回环的封闭式形式中,陈东东将禅与词语,与音乐融为一体,集中地展现了诗意的追求。也正是由于在诗歌形式层面上的自律,才造成了其创作中缺乏开放性,他所延展的情感,在较多意义上,是偏向于节制与冷静的。也许陈东东的诗歌,在阅读上,不会唤起读者激越的心理动荡,而是通向了圆融的克制,这点正与他柔软的意象和尖锐的词语搭配,所产生的效果相仿。
三、意象的上升
大海是诗人惯用的意象之一,在海水中,能依稀感觉到诗人的情感起伏。海已经成为其诗歌中固有的生命表征。他曾经提到过,之所以对海如此着迷,一方面是因为诗人从小生活在上海,上海这座城市带给诗人的是,流动、漂泊,正如刘漫流曾为海上诗歌群体的命名一样,“被推了过来”,“或者正向岸靠近,或者正在远离,而诗是他们脚下的船,一种‘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8]。倘若说,他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与城市相关的诗歌,更强调的是都市的不真实感,那么有关大海意象的诗篇,则关注的多是一种被推动的远离感,以及动荡所带来的不安:
这正是他们尽欢的一夜/海神蓝色的裸体被裹在/港口的雾中/在雾中,一艘船驶向月亮/马蹄踏碎了青瓦
正好是这样一夜,海神的马尾拂掠/一枝三叉戟不慎遗失/他们能听到/屋顶上一片汽笛翻滚/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
当他们起身,唱着歌/掀开那床不眠的毛毯/雨雾仍装饰黎明的港口/海神,骑着马,想找回泄露他
夜生活无度的钢三叉戟?
(《海神的一夜》,1992)
《海神的一夜》将诗人创作中的两个显著的意象凝结为一体,即“海”和“马”。这两个意象在陈东东诗歌中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就“海”意象而言,在杨炼的诗歌中也频繁的出现。而陈东东诗歌中的海,更强调一种距离上的疏离,与“马”一起腾向远处,所谓的远处,指的更是精神上的流浪。肉体的对话以及城市的回响,在诗歌中得到了统一,在“海”意象的包裹中,诗人瞬间变成了浪子,在旷野奔驰、幻想,毫无限度地魂游,逃向夜的深处。诗歌以“这正是他们尽欢的一夜”或者“正好是这样一夜”展开,都将流浪推向了以下降为参照的更远的追寻。因此,从“马蹄踏碎了青瓦”,“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到“海神,骑着马,想找回泄露他/夜生活无度的钢三叉戟”,从空间意义上,构成了跳跃的思绪,使得诗歌的音乐感觉溢出文本之外。
喷泉静止,火焰正/上升。冬天的太阳到达了顶端/冬天的太阳公正浩荡/照彻、充满,如虚构的信仰/它的光徐行在中午的水面
在中午的岸上,你合拢诗篇/你苏醒的眼睛/看到了水鸟迷失的姿态/那白色的一群掠过铁桥/投身于玻璃反光的境界
排遣愁绪的游人经过/涌向喷泉和开阔的街口/他们把照相机高举过顶/他们要留存/最后的幻影
钻石引导,火焰正/上升。赞歌持续俾特丽采/在中午的岸上你合拢诗篇/你疲倦的眼睛/又看见一个下降的冬夜
(《冬季外滩读罢〈神曲〉》,1990)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中,“鸟”意象频繁的出现,在北岛、欧阳江河、西川、柏桦的诗歌中也不乏其例。“鸟”这只在高空中飞翔的生物,几乎成了诗人们形而上追求的一个意义符号,飞行的姿势无疑通向了一种仪式性的神圣。而在陈东东诗歌中的“鸟”又多了一重迷失的情景。在《冬季外滩读罢〈神曲〉》中,火焰上升与迷失的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抽象化地演绎了读罢《神曲》后的升腾感。“喷泉静止,火焰正/上升”与“钻石引导,火焰正/上升”,标示着两次情绪的膨胀,这情绪在冬季,在中午,在外滩的语境中,显得格外的突出,因此,两次突兀的“上升”,更加剧了对抒情环境的表达。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上追逐,另一方面,则渐渐进入迷失的情景中。二者交织出现,使得诗歌本身在声音表达上既激越,又迷离,陷入两种精神状态的制衡中。很明显,诗歌的第一和第二节依循情绪的高涨,而中间两节则相对克制。正如整首诗歌,即使是以上升起篇,但诗人仍在“它的光徐行在中午的水面”、“投身于玻璃反光的境界”、“又看见一个下降的冬夜”这样的诗句中徘徊,于是,上升与下降也同样在诗歌中形成意义层面上的制衡。在犹豫中,加深了“鸟”所蕴含的迷失意蕴。他的诗歌《起身》,“清晨也是欲望苏醒的时刻/是饥饿之鸟飞离峭壁的时刻/是想晒太阳之鸟飞离峭壁的时刻/也是寻找幸福之鸟飞离峭壁的时刻”,这在陈东东的诗歌中,已是较为激越的情绪表达,一次次地升华清晨之音,不断地加强句子在听觉上的难度,延长了抒情的时间。后两节中相继出现了“清晨也是精神抖擞之树”,“清晨也是雄心勃勃之日跃出大坝的时刻”,不断地明确诗句所要传达的意蕴,似升腾的血液一冲而上,凸显出内心的汹涌。结尾处,“等到我终于穿好衣服,窗下就能听见/鱼群歌唱,也能看到上学的孩子”,思绪又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像海水的浪波,又像是歌曲的音浪,有高潮,又有平静。创作于1995年的《乌鸦》,“而我却梦见另外的乌鸦/从廊柱隐秘的阴影里脱胎/它升到象征的戏剧之上/看黑夜到来——黑夜多奇异”,也同样隐喻性的将这只黑色之鸟置于上升的境地,颇具知性的思考乌鸦在黑夜中的形态,诗歌冷静、克制,诗节没有明确的情感表征,较客观地叙述了思索情境中的生命,破折号的使用,延宕了乌鸦生存背景的叙述时间。
奔马与海、鸟意象不同,如果说,“海”打开了诗人宽广的怀抱和思绪,鸟常常处于飞翔的迷失状态,而“奔马”则无疑增强了诗歌的灵动、迷幻与超现实感。这三种意象的出现,为陈东东诗歌中声音的抒情化表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雨中的马》是陈东东表达这一意象的代表作之一:
黑暗里顺手拿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
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
这乐器陈旧,点点闪亮
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闪亮
像树的尽头木芙蓉初放
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鸟
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像乐器在手
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
我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
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我拿过乐器
顺手奏出了想唱的歌
(《雨中的马》,1985)
早在1980年,陈东东就受到超现实主义诗人埃利蒂斯长诗《俊杰》的影响,使得幻想与词语之间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超现实主义更强调的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指向的是对传统的颠覆与破坏,“陈东东的‘超现实’情结其实多半源自于横亘在书写者与现实的那层紧张关系”[9]。这种紧张感,更多层面上来自于与意识形态间的现实疏离感,而并非是西方语境中的断裂,然而恰恰成为了与传统的连续层面上的诗艺转折。超现实主义诗歌天马行空的艺术特色,幻觉的流溢,为陈东东的诗歌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雨中的马与乐器交织在一起,自动地在记忆与黑夜中跳跃,诗歌中无论是重复,抑或是长短句的变奏,都极为迅速的展开,又结束,彰显出跳跃的诗歌律动。意象的腾跃与诗句的变奏,钩织出诗句的灵动与飘逸。而这种跳跃的音乐感,在陈东东新世纪以来创作的40首诗歌中也不乏其例,与之相呼应的是,戏仿与超现实的诗风变迁,更加剧了声音的动态感。以诗歌《梳妆镜》(2001)为例:
在古玩店/在古玩店/手摇唱机演绎奈何天/镂花窗框里,杜丽娘隐约像/弥散的印度香,像春宫/褪色,屏风下幽媾
滞销音乐被恋旧的耳朵/消费了又一趟;老货/黯然,却终于/在偏僻小镇的乌木柜台里/梦见了世界中心之色情
那不过是时光舞曲正/“倒转……”是时光舞曲/不慎打碎了变奏之镜/鸡翅木匣,却自动弹出/梳妆镜一面/梳妆镜一面
映照三生石异形易容/把世纪翻作了数码新世纪/盗版柳梦梅玩真些儿个/从依稀影像间,辨不清/自己是怎样的游魂
辨不清此刻是否即/当年——/在古玩店/在古玩店:胶木唱片/换一副嘴脸;梳妆镜一面/映照错拂弦……回看的青眼
如此梦幻的、不连贯的情感表达,在陈东东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中变得尤为突出。这无限的跳跃,在整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文本中都较为罕见。诗人创作中复沓回环的痕迹逐渐消失,所遵循的是更自然的生理与情绪上之共鸣。陈东东不但青睐超现实主义诗歌,他个人对于中国古典诗人辛弃疾和李贺也偏爱有加。除此之外,包括对于诗人卞之琳诗风的吸取,从其诗歌中也可窥见一二。可以说,陈东东诗歌创作的灵感,主要来自于阅读和旅行。在阅读中,汲取中西诗歌的精髓;在旅途中,融入了对于生命本身的理解。如果说李贺、辛弃疾或者卞之琳,在其诗歌创作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话,那么天马行空、洒脱、跳跃,以及对意象的多面向追求,无疑是陈东东对现实变形、幻想的创作基点。由此,多元化的尝试,自始至终在陈东东的诗歌中表现的都较为明显,这也不断地唤起读者对其诗歌的期待。
声音作为一种诗学观念,已延续至今,但缺乏较为系统的建构。探讨声音,其实从根本而言,是在探讨诗歌的传统,梁宗岱早在《新诗低纷歧路口》中就认为:“从效果看,韵律底作用是直接施诸我们底感官的,由音乐和色彩和我们底视觉和听觉交织成一个螺旋式的调子,因而更深入地铭刻在我们底记忆上;从创作本身而言,节奏、韵律、意象、词藻……这种种形式底原素,这些束缚心灵的镣铐,这点限制思想的桎梏,真正的艺术字在它们里面只看见一个增加那些散的文字底坚固和弹力的方式,一个磨练自己的好身手的机会,一个激发我们最内在的精力和最高贵的权能,强逼我们去出奇制胜的对象。”[10]事实上,自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诗歌运动发生至今,新诗已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回首,对于诗歌与声音话题的关注从未消失过,然而,迈入新时期以来,声音在诗歌中上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又以何种方式而存在,可谓一直是当代诗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在文中,笔者阐释了陈东东诗歌与声音之间的关系,在他所遵循的抒情传统中,提炼出轮回与上升的诗学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对陈东东诗歌节奏的讨论,从来都是与情感,与意义不可分割的。因为陈东东的诗歌写作“背后却仍然联系着诗人对于诗歌的文明使命的承担及其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精神性问题和终极事物的形而上思虑”[11]。尽管声音在诗人的创作中带有某种自律性,阐释也许并不能抵达其内心的绝对丰富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诗歌律动节奏的把握,始终是声音在新时期以来诗歌中存在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