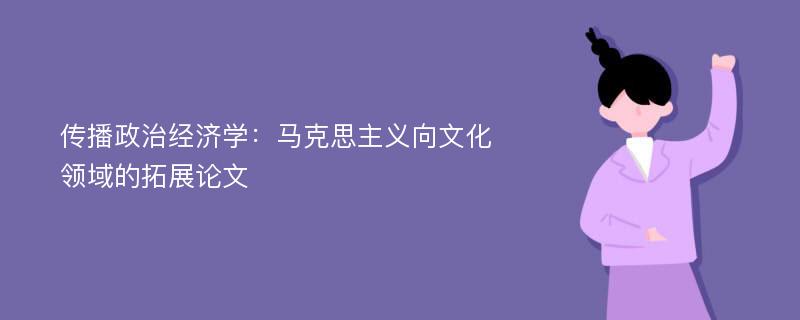
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向文化领域的拓展
刘子旭
[摘 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文化领域拓展的表现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印刷、电子乃至数字媒体的分析,探讨传播技术与资本、市场、政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代媒体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有着积极的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这些批判性的论述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提醒我们注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条件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它们批判传播领域的垄断、希望媒体重新成为民主参与的先锋,但是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产生出非营利的、与现有媒体存在结构性区别的传播体系这一根本问题。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须摆脱仅仅包含政策干预的“政治”的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普世道德要求,认真对待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本质区别,深刻剖析两种生产领域内的阶级划分,才能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真正的解放性政治和基于大众民主的信息传播方式。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美国广播史 观众的劳动 新闻与意识形态控制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对文化领域即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称的“非生产性领域”的分析当中,此类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类。第一类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对音乐、电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各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用及其政治性有诸多精彩的阐释。第二类是英国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开创的文化研究,继承的是马克思—葛兰西—威廉斯—阿尔都塞一脉相承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反思,更加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在进步事业中的关键作用。第三类是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所建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印刷、电子乃至被人们称为“新媒体”的数字媒体之中,分析信息传播技术与资本、市场、政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本文将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所有权、价值创造、阶级划分和信息民主等方面入手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化进行论述。
一、公共与私有之争:早期广播历史的启示
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历史的视角至关重要。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把广告支持的商业媒体模式视为普适性的模式,是市场竞争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但从历史上看,这一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模式,也就是美国模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才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主流形式。即便是美国模式,也绝非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具体考察电子媒体在美国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到,在美国,广播事实上也同样经历了从公共服务到盈利机构的转变,只有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原本的公共空间成为私人资本竞争的领域之后,才有了媒体市场的形成。
从1906年范信达(Reginald Fessenden)在美国第一次进行无线电语音传送直到1934年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商业广播模式的20多年是美国广播的形成期,广播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介入。无线电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在国家安全方面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而在1912年出台的第一部《广播法案》便确立了军方和商业大公司(主要是马可尼公司)对无线电的共同垄断。一战期间海军更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控制了所有的无线电台。即使是在战争结束后,军方仍然认为这一技术过于重要,因而绝不能交与私人拥有,1918年要求政府永久垄断无线电的议案提出时,海军是最主要的支持者。最终国会并未通过这一议案,但却并未否定垄断本身,而是支持由大公司(主要是AT&T、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对无线电通讯技术和广播电台的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并未立刻成为现实,早期的美国广播事实上是一种公共服务。首先,为了战争的需要,军方在一战期间暂时开放了无线电技术专利以鼓励创新,为广播技术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其次,军方培养的上万名无线电操作员在战后成为民间的无线电爱好者、技术人员、电子制造商的雇员,这批人不仅成为广播服务的第一批现成的听众,而且以其自身的技术能力普及了无线电广播并带动了社区的公共广播和流行文化的传播;最后,1912年为规范无线电通讯而出台的《广播法案》虽然原则上支持商业公司对广播的控制,并要求每一个使用无线电设备进行广播的人必须申请执照,但是却并没有对执照的颁发做出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在技术设备的成本日趋低廉的前提下,任何人,只要拥有足够的兴趣和技术能力,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电台进行广播。
在这一背景下,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尽管政府支持大公司的垄断,但在对广播执照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这一阶段成为美国广播史上绝无仅有的真正的自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值得强调的特点是:在1927年以前,既存在广告支持的商业广播,也有非营利性的、公共的广播。事实上,在1927年政府强力介入之前,广告支持的商业广播只占4.3%,① Robert McChesney,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15.并且在社会上对于广告存在着普遍的反感和抵触,对于收音机这种“个人物品”而言,广告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甚至连无线电广播的奠基者德·弗罗斯特(Lee De Frost)和美国广播公司的第一任总裁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都对广告表现出厌恶。② Sydney W. Head, Thomas Spann, and Michael A. McGregor, Broadcasting in America: A Survey of Electronic Media ,9th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31.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播作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团体进行信息传播和娱乐的工具迅速普及开来。1912年以来的自由发展形成了以无线电爱好者、教会、学校、工会及其他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主的广播网络,而商业广播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得多。在1927年,看到了广播中巨大商机的大公司以频率干扰为由提出建议加强监管,限制执照的颁发、频率的使用和发射机的功率。随后,政府建立了联邦广播委员会(FRC,后更名联邦传播委员会即FCC)出台了第二部《广播法案》(通常被称为1927年《广播法案》),在“公共利益”和“技术必要性”的名义下,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重新分配频道;二是不再颁发新的执照。1927年《广播法案》对于美国的广播发展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它认定设备精良的大公司能够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把优质频道分配给它们,由此真正确立了商业广播的垄断地位,深受大众欢迎的非营利性的公共广播被逐步边缘化而最终退出了竞争。
户用沼气池的生命周期成本回收期为户用沼气池全生命周期成本与年净利润的比值。8m3沼气池(年产气量400m3)的初始投资成本为1 762元、全生命周期成本为3 082元、年净利润为835元。根据上述值计算成本回收期为3.69a。
不再颁发新的执照则确立了广播领域的所有权结构。虽然在话语层面FRC承认频道(声波)是共有财产,不得买卖,但执照使用权的买卖并不受到任何限制。在1927年之后,要想获得执照只能通过购买已有的广播电台,执照因此也就获得了交换价值,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交换价值与频道(声波)密不可分,客观上意味着这一公共资源也具有了私有财产的属性,变成了可以购买和出售的商品。在一切皆可以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美国早期无线电广播所确立的以盈利为目的、广告支持下的商业模式成为后来包括电视、数字电视、互联网等所有大众传播媒体所遵循的模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早半个世纪就抛弃了公共广播。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广播的立法中,自由资本主义所惯用的所有权和契约话语被有意回避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公共利益的话语。只有在商业广播的垄断得以确立,频道的财产属性得以巩固之后,关于保护私有产权和商业广播公司的言论自由才再一次出现在公共辩论当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之下,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决策无疑都是政治上的选择。
二、广告与观众: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创造
把经济上的决策定义为政治的选择不仅仅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包含了“政治”的概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经济的行为,即为了实现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生产而进行的资源配置和协调,是由社会阶级关系所决定的,① Zhaochang Peng,“Bringing Both Class and the State Back in: Toward a Marxist Freedom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 vol.8, no.2, 2018, pp.226-248.剥削关系体现在了物质生产、时间管理和分工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创造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之上,看似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蕴含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奴役形式。而在文化生产和“文化逻辑”越来越重要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②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这一剥削关系甚至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展。
在实践中,我们坚持规划引领,厚植绿色根基,传承绿色文化,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品牌,构建绿色社会,初步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增绿与增收协调、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新路子。绿色生态已成为普洱最耀眼的品牌和最大亮点、卖点、营销点,绿色发展成为普洱最鲜明的标识和符号。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和价值创造有着核心的地位。一部分传播学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同时也试图突破这一传统所涵盖的范围,对新的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生产领域内的变化进行分析,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议程方面表现出了更为清晰的意识。对于这些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帮助他们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研究的“消费者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包含着广泛的、多样的研究,本质上却是一个以内容为中心的模式,③ Sut Jhally,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68.而传播过程中真正的核心,应当是被称为“受众”的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劳动。如英国学者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指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即文化的商品化,已然越来越明显地把大众传播吸纳进了商品生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分析大众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将很难在文化领域内形成抵抗资本主义的有效策略,因此我们的分析必需按照其本来的面目来进行,也就是说,把大众传播当作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的领域来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④ Nicholas Garnham,“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1, no.2, 1979, pp.123-146.
根据数模结果,采注比为1.2左右时,采收率和经济效益最好。井组日注汽120t,日产液144t左右。采油井按平均原则配产,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液面调整生产制度。因此,馆一井组单井采液量24 t/d;馆二井组平均单井采液量29t/d。
从这一认识出发,萨特·扎利(Sut Jhally)追问:究竟是观众的哪一个特定方面成为商品被出售给了广告商?观众的劳动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具体来考察一下这个过程:广告商购买的是电视节目中间的广告时段,由于观众的观看才是产生广告时段的根本条件,一个时段的观众越多,这个时段的广告价格也就越高,那么广告商所购买的,实质上就是观众的绝对观看时间,其数量大小决定了特定广告时段价格的高低。很显然,观众既是大众传媒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同时也是这一商品的生产者。也就是说,观众观看广告的时间其实并非是闲暇时间,而是他们为电视台工作,使得电视台能够从广告商那里获得利润的时间。在观众的商品化过程中,节目内容有了更为明晰的意义,既具有使用价值(节目本身的含义)又具有交换价值,而这一交换价值对于理解媒体内容在生产链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观众的这一既是商品又是商品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以及由信息(电视节目的内容)的交换价值所制约和决定的使用价值,成为其他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起点。萨特·扎利指出,被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是观众的观看时间,也就是说,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把广告时间转化为他们的劳动时间,这一劳动的产品就是作为商品的观看时间。这样一来,节目就变成了观众劳动的报偿,也就是他们的工资。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价值生产的分析被用于阐发作为劳动的观看行为,对于电视台而言,观众劳动生产出相当于制作和购买节目成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生产出带来利润的剩余价值,二者皆由广告商买单。扎利提醒我们,必需牢记观看就是劳动并不是一个比喻,观看电视广告这一行为完全是工厂劳动的延伸,因此必需按照其具体的存在方式来对待。① Sut Jhally,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 pp.71-90.
萨特·扎利部分地解决了斯麦兹的分析中遗留的问题,即被生产出来并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并不是观众本身,而是他们的“客观观看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为电视台劳动,电视台以节目为工资对其劳动进行补偿。
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一件商品,或者说一个品牌商品必然包括两个不可分割而又全然不同的部分:(1)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2)具有超越商品本身意义的品牌。后者由某个具有独特含义的标识所代表。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和品牌的集合,二者有着各自特定的存在条件和交换价值。
当前,中国石油油气管网管理体制实行“1+5+5”运行模式,即1个北京油气调控中心、5家区域管道公司、5家区域天然气销售公司。
产业工人真的生产出了商品的所有剩余价值吗?观众的观看行为真的与剩余价值无关因而无需解释了吗?对于这些问题与批评,扎利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应,而是借这些问题强化了自己的分析,并暗示了“人的(观看)行为的力量”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的缺失。② Sut Jhally,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 p.119.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斯麦兹最初的命题,即观众的劳动,并进一步追问:观众为广告商完成了什么样的劳动?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后工业社会中的独特现象:品牌的形成。
对于上述分析,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是:观众真的通过观看行为创造了剩余价值吗?莱博维茨(以及斯麦兹)质疑这一结论,认为其实观众的观看行为毫无神秘可言,因为观众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购买行为参与价值实现的,广告只不过是为了加速流通以降低生产成本的付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意识到他们出售的必须首先是品牌而非产品。在品牌时代,产品本身的生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概念。相应地,广告也不再是关于产品的广告,而是向世界传递某个公司的“核心含义”的载体。品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符号、形象,它是一个“理念”,一次“体验”,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目的在于成为我们文化经历的唯一可能方式。① Naomi Klein, No logo , New York: Picador USA., 1999, p.21.广告商的任务已不再是“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销售业绩”,而是“培养新的消费行为”、让人们有信心尝试“更好的食物、新的保持清洁的方式、各种工具的使用”。② John Sinclair,“Globalization and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vol.1, no.1,2008, pp.77-90.
当一件商品不带任何附加的含义,仅仅作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离开分包商的工厂之时,另一种生产就开始了,即将此商品制造成为某一品牌的生产过程。对于电视观众而言,品牌间的差异必然是非常明显的视觉差异,它依赖于广告的美学效果,但更取决于广告的强度和频率。
“非虚构”叙事这一概念至今仍属于较模糊、宽泛的范畴。在当代文坛,报告文学中表面化、形式化的歌功颂德已经和今日的“非虚构文学”发展严重脱节。随着近几年“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如何找到其中的“非虚构”叙事策略,在理论和创作层面进一步提炼升华是当务之急。“‘非虚构小说’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语言重述环节的绝对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脚踩大地,面对真实的场景,拒绝二度虚构,是否致力于去展现一种更高层面上的真实,或者说存在。”作家宁肯在这方面走出了示范性的一大步,并用其自成一套的“非虚构”叙事策略为“非虚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视觉媒体主导的时代,观众的观看行为成为品牌制造过程中的中心环节,它是电视台出售广告时间和广告商出售品牌的先决条件。
当然,观看行为绝不是任何无条件的行为,一则广告的意义在结构上必须被意义的“创造者”(广告公司及其客户)和“阐释者”(观众)共同创造,就这一点而言,观众的观看行为必须是积极主动的行为,始终与广告的图像和语言呈现出的思想、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相关联。以耐克为例,这个品牌的广告从不提耐克二字,但是它无人不晓的对勾式标志所象征的体育精神、运动员气质和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必须是在观众与耐克广告的互动中、通过观众自身的劳动才能产生。
在20世纪80年代,全美国大约有1700份报纸、11000份杂志、9000家广播电台、1000家电视台、2500家出版社和7家电影公司,假如每一家媒体都由不同的所有者来经营,则会有25000多种不同的声音,如此庞大的数字几乎可以保证各种社会政治思想的传播、限制权力的过度集中,并使得具有新思想但规模较小的媒体更容易进入市场。然而现实是并不存在25000个所有者,绝大多数的报刊、广播、电影、电视都掌握在大约50家公司的手中。可以说这50家公司的所有者们构成了一个私人的信息文化部。⑦ Ben H. 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p.xlv, xlvi.
消费者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消费行为已不再仅限于物质世界,尽管消费绝不缺少物质性,但它现在更多的是和形象、思想、概念相关而不是衣服、鞋、帽、手表、汽车本身。事实上,所有这些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是他们与广告的视觉形象互动的结果。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果更好地诠释了马克思的话:“消费[在概念上]表现为生产的一个时刻”。③ Karl Marx,“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in Terrel Carver (Ed.),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9.
现在我们可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做出回应:在品牌时代,存在着两种剩余价值,或者说,存在着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即在工厂里受雇佣资本家剥削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工人和在自家客厅里花钱干活的工人。只有当我们把资本和生产链条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才能有此区分。这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拓展,正如威廉斯在对“经济基础”的拓展中所指出的:“媒体传播的社会性决定了意义的生成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生产过程”。④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 London: Verso, 1980, pp.35-41.
如此一来,广告也就成为对观众进行剥削的象征机制。从电视节目的总体质量而言,观众观看广告获得的回报无疑是相当低的。同时,他们还免费为广告商工作,并在购买品牌产品时为自己创造的产品付出高额费用。从象征到物质、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飞跃构成了对于观众这一特殊工人的多重剥削。
同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在象征层面的意义生产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认识到,我们有可能讨论意义生产的前提是“真正的”生产过程——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劳动——被以极端暴力的形式从公众的视线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抹去了。尽管观众劳动这一观点有其存在的真实性,但观众毕竟在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不同于工厂工人。首先,电视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完成品牌制造,但是他们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为重要的是,在虚拟生产之外的社会现实中,二者有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参与象征层面的意义生产过程的观众可以被称为“观看阶级”,它与工厂工人的区分可以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压迫:工人唯一的“自由”在于出卖劳动力,而在意义生成的领域,真正的工人甚至连这一最后的“自由”都被剥夺,在经济上被剥削之后,在社会生活领域也被进一步被边缘化直至隐形。① 关于品牌和“观看阶级”的详尽讨论,参见刘子旭:《观看阶级:电视广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未来生长点·艺术手册·2014》,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128-143页。
由于科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时间不长,囊括了初中所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的内容,需要规范操作的实验也很多,对专业学科的教师要求也很高。
20世纪70年代末,斯麦兹提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成为“当时辩论和讨论的重要主题”,但在其后的30多年里,却“极少受到[西方]传播学者的关注”。② Philip M. Napoli,“Revisiting‘Mass Communication’and the‘Work’of the Audienc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Media, Culture & Society , vol.32, no.3, 2010, pp.505-516.这样一种“令人信服、论据充分的理论”受到冷落无疑有着制度上的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30多年间,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中的讨论有意识地避开锋芒毕露的批判也有其必然性。③ Lee Artz,“Media Relations and Media Product: Audience Commodity”,Democratic Communique , vol.22, no.1, 2008,pp.60-74.然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暴露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回到了传播学者的视野当中,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和新媒体时代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有力的武器。④ 福克斯、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Christian Fuchs,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 London: Routledge, 2016.
三、资本的扩张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议程
手机端和闸机端都需要联网,乘客用手机生成二维码刷码进出站,闸机通过网络改写二维码进出站状态,对车站网络要求较高,大客流通行对移动基站不堪重负。该技术已在青岛、南宁实现应用。
1.2 一体化体育课程建设应具有国际视野 体育作为一个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大学科,建构大中小(幼)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十分必要,对彻底有效解决体育课程改革中遇到的内容问题、评价问题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构建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要具有国际视野,要借鉴国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经验,为我国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无论从目标确立、内容选定、评价建立、实施方略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参考。力求建构与国际接轨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既要充分体现前瞻性,确保专业性,力求科学性,还要切合以人为本,具有适宜性,达到衔接性。
如果说经济上的垄断意味着社会物质财富被少数人所掌控,那么传播领域的垄断则意味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被少数人所控制,因为控制了媒体,也就意味着控制了人们能够用以了解世界的信息,虽然没有直接地决定人们思考的内容,但是却决定了人们思考的对象和可供公众讨论的议题,这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无疑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传播媒介的垄断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
观众在象征层面的劳动在工厂工人的劳动产品之外创造出了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也因此创造出了诸如“耐克”一类品牌的惊人利润。这绝非要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工人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地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工人剥削的进一步扩大——首先是工人和自己生产出的产品的分离,其次是产品和品牌的分离,即物质生产和意义生产的分离——才使得“耐克”现象成为可能,在作为使用价值的运动鞋之外存在着额外的一个符号、一个概念、一种生活的意义、一种精神。不仅如此,在品牌化过程中,原本必须依赖产品而存在的品牌名获得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此时尽管它仍然需要与某种具体的物相关联,但是它和具体物的关系却发生了逆转,获得了首要地位,而具体的产品则需要与某个品牌相关联才有可能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
上面提到的传播领域内的劳动与价值创造的过程暗含着一个重要的结论:传播领域作为生产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趋势。马克思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便揭示了资本越来越集中的垄断趋势,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6-688页。 列宁则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代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垄断组织、代表银行和工业资本融合的金融寡头和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⑥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52-364页。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必然成为资本的最新积累场域而逐步地被大的资本集团所垄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去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管制的放松催生了新的传播卡特尔的形成,垄断的程度更进一步地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着美国媒体的公司的数量逐年减少。在1984年,美国25000多家媒体中的绝大多数控制在约50个大公司手中,到了1987年,短短几年间的公司并购后,仅有26家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媒体,1993年有20家,而到了1996年,则仅剩10家(即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母、新闻集团、索尼、TCI、西格拉姆、西屋、甘尼特和通用电气)。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媒体公司并购从数亿美元增长到数百亿美元,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无疑具有巨大的结构性影响。与此同时,控制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媒体,各类媒体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如1996年迪斯尼与ABC/Cap Cities合并后,控制了报刊、书籍、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录像光盘以及电话和光缆等几乎所有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① Ben H. 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 p.xiii.
以电视这一目前最为普遍的大众传播工具为例,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以节目内容所存在的商业环境为出发点,指出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电视产业存在方式的误区:最为基本的商品交换并不在付费观看节目的观众和提供节目的电视台之间,在广告支持的商业广播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后、当广告成为电视台绝对主要的收入来源后,真正决定电视台命运的交换关系发生在电视台和广告商之间。原因非常简单,电视台的经济来源并不是观众,而是广告商。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达拉斯·斯麦兹(Dalas Smythe)所言,电视所包含的商品交换过程乃是电视台将观众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而电视节目不过是吸引观众的“免费午餐”。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广告商使得观众成为其劳动力,自我推销广告商的产品,确保了总体上的商品分配和消费。⑤ Dallas Smythe,“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 no.3, 1977, pp.1-27; Dallas Smythe, Dependency Road , Norwood, NJ: Ablex, 1980.一方面,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和观众劳动论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认识到电视台用节目吸引观众为广告商工作之后,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包含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斯麦兹特别强调大众传媒在社会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视,但是他的分析跳过了对于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分析,并且认为观众的劳动只是名义上的劳动,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其作用在于促进商品的分配和消费。这一点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持了一致,但是后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认为他忽略了传播过程中的更复杂的问题。
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金融新闻留给人的印象,仿佛它们之间常常充满了冲突和对立。事实上,竞争仅限于划分地盘、寻找新的联盟或收购小公司这些次一级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例外,大的媒体公司之间有着共同的极端保守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它们相互拥有股权,共同组成了并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关系的复杂的合资公司体系,② Ben H. 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 p.xi.不仅在经济上影响巨大,而且也左右着整个国家政治决策的走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大众传媒是统治阶级巩固其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机制。④ 赵月枝:《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 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方法首先是控制信息,当私人资本控制了新闻的内容和公共事务方面的信息,资本家阶级可以决定何种议程可以进入政策方面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其政策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则以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和扩大私有化的范围来回应其要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扩张正是在这样的大众传播环境中得以实现的。
实验结果表明,相同碳分子数、不同分子结构的单组分己烷、环己烷、苯与CO2的表面张力随实验压力的增加而减小,表面张力与压力呈线性负相关,这主要与不同分子结构烃分子与CO2作用力大小有关。相同实验条件下,同碳数的烷烃、环烷烃、芳香烃与CO2的MMP不同。由此可得到如下认识:在相同碳数条件下,不同分子结构的最小混相压力关系为MMP烷烃<MMP环烷烃<MMP芳香烃。
媒体权力必然也是政治权力。在信息传播领域被资本所垄断的情况下,存在着两对深刻矛盾:一是民主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垄断资本的商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的和平共存的要求和“垄断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政治军事需求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两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媒体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没有共识的社会中“制造共识”,就这一点而言,正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传播媒体本质上是强大而有效的意识形态机构,他们无需公开的强迫,而是依靠市场力量、被公众内化了的各种逻辑前提、自我审查等方式,进行系统化宣传。⑤ 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8, p.306.
根据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媒体会通过层层的自我审查和过滤机制,确保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在美国,这是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方式。
以新闻报道为例,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美国的宣传模式包含了五层过滤机制。(1)所有权的限制。始于19世纪的媒体(最初是报业)的“工业化”使得创立和运营媒体所需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处于垄断地位的工业和金融资本逐步控制了媒体,即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媒体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处于顶端的少数几家大的媒体公司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新闻的内容来源。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步的媒体因无力支持规模化的媒体而被日益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2)广告商的影响。掌握了信息传播和拥有大规模受众的是商业媒体,他们依靠巨额的广告收入支持其运转和获取利润。这一商业模式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后果:首先,广告商选择符合其政治立场和支持其经济利益的媒体(如早期的报纸)投放广告,这些媒体不再依靠发行费用获取主要利润后可以大大降低价格,使得其他不依靠广告的媒体在越来越缺少资金改善质量的情况下逐步边缘化。换言之,是广告商(的意识形态),而非自由市场竞争,决定了媒体的存亡;其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倾向通过广告的分配表现出来:为了吸引广告商,媒体的受众必须是引广告商所需要的类型,即富裕的、具有购买力的部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或激进的媒体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上的支持而陷入困境;最后,广告支持下的商业模式对媒体的内容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广告商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任何暗示资本主义商业体系的失败,或是关于环境恶化、军工复合体的运作、支持第三世界独裁统治并因此获利的报道,都必须彻底清除。媒体必须牢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广告商和大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非公众的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和参与。因此,严肃的、复杂的、导致争议的内容必须让位于更容易吸引眼球的、娱乐性的、让观众保持“购买”心态的内容。(3)控制新闻媒体的信息来源。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利益互惠关系(对于新闻材料的持续稳定的需求、求证真实性的成本、避免诽谤诉讼等),新闻媒体与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和商业机构形成了共生关系。在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各级市政府和警察局、商业公司和贸易团体等机构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新闻部门,为媒体提供容易获取的新闻内容,同时成为拥有特权的新闻常规来源,资助为垄断资本和政府发声的专家,设定框架和议程,让新闻为自身利益服务并有效地防止批评声音的出现。(4)对媒体的批评。在美国,真正影响媒体行为的批评来自政府部门(如白宫、联邦传播委员会)和赞助商,它们通过电话、信函、向媒体的股东和管理层抗议、自制广告、资助建立右翼的监督和智库机构(如美国法律基金会,媒体研究所,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等方式,对媒体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报道进行干预,审查媒体报道是否“准确”描述了商界行为、是否“充分”反映了商界观点,证明和展示媒体的“自由主义/左翼”① 批评媒体的“自由主义”或“左翼”的偏见并非是因为媒体真正的左倾,而是为了维持对媒体的压力,使其在不断地自证“非左”而不敢真正地支持左翼。表面上的左右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右翼的两个分支的合作共生。 偏见和反商业特征,给媒体施加压力使其遵循商业议程和右翼的内政外交政策。(5)反共机制。反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首要原则,这一含糊不清、缺乏具体证据而又无需自证的原则可以被用来压制任何威胁到财产利益或是支持共产党政权和激进政权的言论或行为。作为政治控制的机制,它有效瓦解了左翼和工人运动,那些迫于压力不得不自证反共的自由主义人士在行动上越来越接近反动人士。这一原则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颠覆别国政权(如1964年的巴西、1981—1987年的尼加拉瓜等)的借口。② 关于控制媒体的过滤机制的详细论述,参见Edward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chapter 1.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解媒体的运作方式及其代表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在国际事务的报道中,同样的反人民罪行,如果是美国的盟国所犯,则不会报道或者一带而过使其湮没在海量的其它新闻之中;而如果是美国的敌人所犯,则会在各类媒体中得到大肆渲染,甚至于编造谎言也在所不惜。近者如以色列(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杀伤巴勒斯坦平民和关于叙利亚(美国在中东的敌人)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远者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媒体对于尼加拉瓜(美国的敌人)政府军“暴行”的大量报道,和同时期对萨尔瓦多、智力、危地马拉(美国的盟友)等国同类暴行的遮掩,都遵循这同样的原则:集中报道敌人的暴行,忘掉朋友的暴行。虽然这一宣传模式是在30年前提出的,但其有效性显然并未因时间的久远而减弱。
四、结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
以上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并不期望面面俱到,但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处以核心位置的劳动和价值、所有权、信息民主等方面都有所提及。作为结束语,希望探讨一下这个学科的一些局限和未来的发展可能。
首先,在21世纪的“新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仍然必须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质疑,即观众的劳动是否真正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并未得到最终的解决。就这一点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证明了观众的劳动,而是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需要的新的分析视角。而它的缺陷或误区则在于用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劳动”阶级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点虽然有其现实意义,但客观上进一步将作为真正的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工人阶级边缘化。不但如此,当社交网络的使用者成为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主要组成部分,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Christian Fuchs,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Eran Fisher, “Class Struggles in the Digital Frontier: Audience Labour Theory and Social Media User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 vol.18, no.9, 2015, pp.1108-1122.社会革命的主体从工人阶级变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转换在政治上的消极后果值得我们关注。
表面上看,在企业整个供应链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关系,比如企业做社会公益看起来并不会给企业带来营收,但品牌建设是一个积累企业无形资产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品牌无形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层面思考,企业承担并履行一部分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品牌建设和长期发展都很重要。这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其次,在论述传播媒体的经济特点时,很多批判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却终于躲避政治经济学真正的政治议程,从政治出发但得出了非政治和非历史的结论。例如,斯特里特关于美国广播历史的著作深刻剖析了美国的商业广播得以建立的具体社会条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却把广告这一经济行为和创造市场这一政治行为化简为“商业自由主义”文化的作用,削弱了其中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即商业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成就,更是一个政治成就”。② Thomas Streeter, Selling the Air: A Critique of the Policy of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39.而麦克切斯尼等强调媒体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作用的学者,则把作为手段的民主视为最终目标,忽略了他们所有分析的起点在于考察商业媒体系统得以建立的社会物质条件。他们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产生出非营利的、与现有媒体有着结构性区别的体系。③ Robert McChesney, Telecommunication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在这些批判中,“政治”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干预,从制度、政策、政治经济学入手的分析,结论却是关于自由主义和普世道德要求的唯心主义观念。
诗歌用白描手法罗列了生活中负面现象:正直美好的事物被遗忘,或受到猜疑;人在失势时,即使缺失只有毫发之小,功劳有如丘山之大,也不能见容。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上的限制压迫了理论研究的空间。在过去30年间,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并无太大的发展,即使是新媒体的出现也未能突破“旧”媒体理论的框架,仍然是基于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和观众劳动的范畴。虽然有观众的观看时间作为商品和关于受众的数据作为商品这样的修正,④ Eileen Meehan,“Rat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 vol.1, no.2, 1984, pp.216-225.以及数字劳工和剥削2.0这样的演进,但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都需要突破模拟时代的理论框架,真正实现“新媒体”的“新理论”。
最后,这些始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性论述提醒我们注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条件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媒体的本质和运作规律有着巨大的帮助。但是,在批判传播领域的垄断并希望媒体重新成为民主参与的先锋的同时,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有传播体系之间的关系的回避也使我们认识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须摆脱仅仅包含政策干预的“政治”的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普世道德要求,认真对待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本质区别,深刻剖析两种生产领域内的阶级划分,才能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真正的解放性政治和基于大众民主的信息传播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0;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3-0090-09
作者简介 刘子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英文季刊《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张 超
标签:传播政治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美国广播史论文; 观众的劳动论文; 新闻与意识形态控制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论文; 英文季刊《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