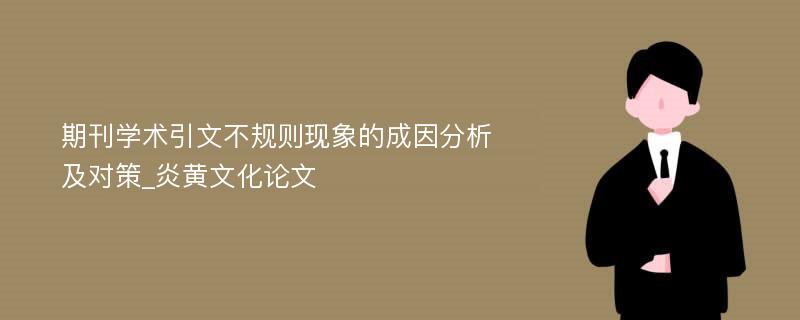
期刊学术引文不规范现象的成因探析与应对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文论文,探析论文,成因论文,方略论文,不规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5)06~0150~07 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发展,学术规范问题已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重视。在期刊学术论文中,引文使用的规范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部在200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提出:“依照学术规范,按照有关规定引用和应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学术引文的使用仍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在向以学术严谨、规范严格著称的国内学术期刊所刊登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学术引文不规范现象也同样屡见不鲜,如有的学术论文通篇没有引文,有的使用引文而未标示出处,有的使用引文衍脱错讹,漏洞百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引文规范的纯粹形式上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亟须对引文规范在认识上加以深度阐释和把握的理论问题。或者说,引文规范的理论认识是制定和遵循引文规范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对引文功能及其规范意义有了深入认识和把握,才能更好地制定和遵循引文规范。目前,探讨引文规范的论文大多侧重于技术性研究,而理论性探讨尚显不足。正因为如此,针对与引文规范有关的一些认识问题,如学术论文为什么要有引文,引文到底有什么作用,学术论文是否可以不用引文,学术论文中的引文为什么会错误百出,怎样才能规避引文的错误使得引文更加规范,本文拟从理论上作以阐释。 一、引文在学术论文规范中的必要性 学术论文是否可以没有引文?目前,学界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一般而言,学术论文通常都有引文,但也有些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没有引文,这就说明在有些学者的心目中,引文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说是可以不要的。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学术论文,就是对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见解的阐释,至于其他人是怎样论述的,自己与其他人的论述有什么不同,则是可以毫不顾及的。更有甚者,有些学者还把自己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没有使用引文当作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认为没用引文,正说明了自己的前沿性、独创性,是自成一家的表现。因此,在这些论文中,作者径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并不顾及前人说了什么、同辈说了什么。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径直阐释自我观点的论文,严格讲来,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因为,作为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引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规范。 从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离开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转化,离开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传承和提升,那人类自身的文化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篇学术研究性的论文,都应该是带有创新性的论文。而所谓创新,就是要对接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学术上新的突破。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国外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极其重视论文被引用的情况——被引用的数据高,就意味着自己的科学研究占据了前沿位置,成为同时代的科学家进一步提升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学术界在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时,便非常重视该成果被引用的频次与层次,并由此建构起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期刊评价体系。与此相对应,随着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被纳入世界科学研究的体系,中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基本上也接受了西方这套评价体系,各高校在评估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时,都把《自然》《科学》等西方重要的学术期刊视作顶尖级的期刊,在科研成果的评奖和奖励上予以重奖。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融入西方业已成型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话,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学术界的这种融入还无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相提并论。这固然与中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有直接的关联,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操持的话语体系和西方难以对接有密切联系,但也由此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西方所特别重视的传承代际关系的引文,在中国学者看来似乎并不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截然不同的特点,引文尽管就其本身来看是一件小事,但就其核心而言,实际上是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换言之,在如何对待引文的背后,隐含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到现在,中国学术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但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在这百年里建立起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国家大部分时间处于动荡之中,没能建立起一个学术规范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起码应该建立起大家共同遵循的基本规范,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不仅没有建立一个可以遵循的规范,而且在“文革”时期堪称混乱。到了新时期,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学术规范的春天依然很遥远。直至新世纪后,这样的一种学术规范才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学术界才初步确立了在“学术共同体”内共同遵循的规范。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这里不妨以几本学术期刊为例来看其引文的沿革。在1957年创刊的《文学研究》(后来改为《文学评论》)中,首篇是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该文采用的是页下注,作者在引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时,首次出现的注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三一页。”①在1959年的《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刊发的田仲济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则采用了文末注,其所引用的匡亚明评论郁达夫的话,在文末这样注释:“匡亚明:‘郁达夫印象记’。”②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不管是权威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学研究》,还是普通如山东师范学院编辑出版的《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均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引文规范。 与国内学者这种引文上的不规范相比较,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不仅仅是将引文当作自己文章的一种注脚,而是将引文纳入到自己的学术传承链条中。这样一种链条,使引文就具有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自己的论点得以展开的前提,也是自己的论点得以深化的基点。举例来说,西方学者的论文开篇部分,大都是对本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的汇总,这甚至已经演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论文写作范式。但在中国却还没有这样一种基本范式,很多学者往往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从而使其论文成为一种散射型的结构形态。 当然,在西方也有例外,比如,康德的一些著作中,就没有多少引文。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这既与康德哲学的特殊规律有关,又与康德注重自我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有关——也就是说,康德更注重建构一个自我独立的哲学王国。实际上,康德在建构这个哲学王国时,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在广泛涉猎大量的前沿哲学问题的基础上,才逐步完成了他的庞大理论体系的创造过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康德作为一个个案,并不意味着西方就否定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关注。 为什么在中西学者之间,对引文的重视程度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恐怕与中西学者对学术的态度有极大的关联。中国学者接受的学术传统,往往注重代天地立言,为黎民请命。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就使中国学者特别注重自己所说的话,而不很看重别人所说的话,似乎只有自己所说的话才有学术价值;如果注重引文,就会因此而削弱自我话语的中心地位,从而遮蔽自我话语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自我言说的需要,致使后人根据自我体验所获得的认识,在用学术话语进行呈现时,往往会出现一种重复的现象,即对前人话语的重复。当然,对前人话语的重复,是基于对前人体验的重复,毕竟作为置身于相似的生活和社会中的个体,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往往都具有某种相似性。尤其是在传统的社会形态中,缘于社会进化节奏的缓慢,相似的生活往往会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地重复着。由此一来,后人基于前人基点上的创新是绝难完成提升的,自然也就更谈不上飞跃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文化的传承链条中,除了被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外,其余所有大儒对前人的阐释,几乎都可以被后人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径直对接到原典那里,便可获得自我体验、自我提升,而无需再传承前辈层层累积起来的知识。更有甚者,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个体的自我独到体验,它是一种指向自我心灵世界的学问,因此,后人便没有必要特别关注前人代际累积的成果,而只需关注自我的心灵世界即可。其实,这样的一种指向自我心灵世界的学问,正是儒家那种“内圣外王”范式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反,西方的知识,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已经实现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精神的全面飞跃。这样,从物质生活的层面来看,他们已经不再是基于既有的传统社会的节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迅疾变化发展了的社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自然就有别于前人,他们由此而获得的自我体验自然也就有别于前人,由此而来的,自然就是学术的代际传承和代际积累。至于自然科学,更是如此。正如所有的科学发明一样,当瓦特发明出蒸汽机之后,后人所要解决的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推进蒸汽机的发展,无需再有一个瓦特从头开始重新发明蒸汽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发明一旦完成,尤其是这样的发明得到了有效传播之后,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便不是如何来再次发明同一种东西,而是如何使这种发明更趋于完善乃至高效。自然科学这个代际传承的特点,便决定了任何新的科学理论、任何新的科学发明都无法离开对既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把握。要把握好既有的科学成果,便必然地要求对既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准确把握。具体到引文来说,则表现为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引文中的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导致此后的研究走弯路,乃至误入歧途。 中国在学术研究中不重视引文的作用,客观来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既有的学术研究,这是因为所有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对接往往是可有可无的。换言之,引文在学术论文中,已经不再是思维展开的基点,而是被外在地置换进来,或是为了符合学术规范而不得不强加进来的。这样一来,引文便不是被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论文中,成为论文的思维得以展开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是镶嵌到论文中,使得论文更像学术论文的样子。这样的点缀,既是可有可无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引文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思维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学术的创新性和继承性的关系,而一味地满足于自说自话,引文便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只能异化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品。 二、引文偏差的内在机理 在学术期刊的编辑实践中,我们发现,学术论文中的引文错误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有引必错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要弄清产生这些引文错误的内在机理。 其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它对精密的要求本身就不是很高,这导致“差不多”被视同为“合格”要求,从而使引文的准确性规范没有在文化传统上获得足够的支撑。其实,像“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相差无几”的认知,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初,就遭到了鲁迅、胡适等现代作家认真的批判。遗憾的是,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差不多”便成为一些学者潜意识的认知方式。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差不多”的存在还具有某些现实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差不多”应该无法满足社会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就人们认知的精密度来说,认知方式已经不再是停留于眼睛的目测上,认知行为已经不再是凭借感觉,而是依托仪器。现代高科技的精密仪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微观世界,其所观照的对象,也随之有了更为微小的原子、粒子。除了传统社会中所说的毫厘以外,还有比毫厘更为微小的单位。从这样的意义出发,别说“差不多”已经失却了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即便是“差一点”也会失却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从自然科学研究上获得了全面实施,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尚未获得有效的支撑和实施。这样就使得一些学者在撰写学术性论文、尤其是使用引文时,不能高度重视引文的准确性,往往满足于“差不多”。一些学者在抄录引文时,大体上理顺一遍即可,觉得引用后的引文从意思上能够讲得过去,便不再进行更为准确的校对,至于其中的一些标点符号,则更是无所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引文出现错误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其二,许多学者在对待引文的问题上,因其引文价值观念的偏差,致使引文被价值边缘化,而所谓的自我表达则被置于更高的位置上。由于“立德、立言、立功”这种传统的“三立”价值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往往满足于自我思想的表达,以达到通过立言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许多学者不去重视别人在“说什么”,即便使用了别人所说,也不重视别人是怎样说的,这就导致在使用引文时,不重视引文的精确度,而将其精力更多地放在自我的言说上。在他们那里,往往重视的是阐释和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学术见解的崇拜,以至于许多学者都注重在众声喧哗的场景中,侧重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进而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许多学者往往挖空心思地去标示自我的独特性。而要标示自我的独特性,就需要和其他人不一样;要做到和其他人不一样,就需要和别人所说的话不一样。如果有学者对于一个命题是正的,那后来者要想否定这个命题,就努力从反的方面来切入。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命题思维形式,就使一些学者没有从创新上下功夫,而是注重顺承着既有的思维模式,从反的命题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严格说来,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其实是典型的矮子思维模式,正所谓“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话短长”。而这里的随人话短长,仅仅是从反的命题上话短长,而无法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独辟蹊径,完成一种学术上的创新。实际上,在学术发展史上,许多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见解,并不是顺承前人既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思维,而是从新的基点上进行超越性的思辨。 除了以上所说的那种从反的命题坐标上进行所谓的创新之外,还有一种是典型的自说自话的所谓学术创新。所谓的自说自话,其情形甚至还不及上面所提及的模式。上面所提及的情形,还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现状把握的基础上,其不足的方面仅仅在于没有把创新的思辨能力顺承科学的规定前行;而后者则不然,其罔顾学术研究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味地闭门造车,通过所谓的冥思苦想,在豁然开朗后获得所谓的创新性观点。然而,这所谓的学术创新正是自说自话,其所谓的创新性观点实际上早已经被前人论述过了。 其三,学术研究本身的异化,致使学术研究成为某种功利性诉求的工具,这自然也就导致引文被置于边缘化的位置。有些人把学术研究当作自我获得某种利益的手段,当作自我功利性诉求的一种实现桥梁。这样一来,所谓的科学研究本身,且不说其引文是否精确已不重要,就是自我的言说是否有益于人类,也已无足轻重。这自然就把学术研究异化了。在此基点上展开的引文是否准确,就更不是其所关注的对象了。 在学术研究异化的当下,学术论文本来应该成为学术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但是,由于学术研究被附加上诸多的功利性诉求,致使两者的关系被倒置,学术论文并不是基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之果,而是一种功利诉求基点上的必然之果。这样就必然导致学术研究被置于一边,而将学术论文的写作当作一种目的。如此本末倒置所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其引文自然成为学术论文外在范式的点缀品,而不再是学术论文无法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学术研究的异化表象中,体现学术研究成果的论文,已经被异化为职称性论文、学位性论文、任职考核性论文等。这些论文就其基本的功能而言,主要是满足其功利性目的,而不是以求真为目的,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了,至于引文是否准确,更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可说。笔者曾接触到一作者对李泽厚《孔子再评价》的引文,其中便出现了不少问题。客观地说,《孔子再评价》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是李泽厚早期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中国知网收录了该文,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也收录了该文,如果稍微用心,是不难找到的。但是,就是这样一段很容易查找的引文,该作者却是这样引用的:“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单纯从这段引文来看,本身可以讲得通,似乎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比照李泽厚的原文,便会发现其中的错误几乎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原文是:“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引文,却会出现如此多错误呢?为此,笔者“百度”了一下,发现北京大学知名学者陈来的文章,曾经引用了该段引文:“‘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34页)”④显然,陈来在引用该文时因为不慎出现了许多错误,有句子的遗漏、字词的遗漏以及版本的错误。这段带有错误的引文有可能被上面所提的那位作者直接“借用”了过来。也许,“借用”得不够严谨,在陈来引文的基础上,往前再走了一步,把其中的“事务”错写成了“事物”。所谓的“以讹传讹”的现象,便有了如此实实在在的例子。这样的引文错误之所以会出现,从作者的论文写作目的来看,恐怕是基于一种功利性。正是有了这样的功利性,论文在刊发后实现其目的即可,至于引文的正误便被置之脑后了。 在引文异化的现象中,还有一种情形也是出现引文错误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受诸多评价指标体系的干扰,不管是否需要,便硬性地进行对接,致使许多引文已经变味,走上了学术的不归路。从期刊的评估体系来看,有些期刊缘于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注重考查论文中的引文,于是就拼命将一些引文塞到了论文中,这种情形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奖项的评估体系来看,有些作者缘于评奖也拼命地把一些无关宏旨的引文,硬塞进了自己的论文中。如此一来,便使得许多期刊和作者为了使期刊或论文获得更高的影响因子,一味地在引文上下功夫。在此目的的驱使下,因为其所重视的仅仅是引文这种形式,而不是引文的内容,其引文出现错误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更有甚者,有的作者为了避免自己的论文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时查重率过高,竟人为地对引文文字进行改写;有的作者为了避免自己的论文对前人学术观点的借鉴,有意识地不使用引文,而是改成自己的话来表达相似的观点,这些有悖学术基本规范的极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警惕。 其四,由于受引用者的自我思维定势乃至心理结构的整合作用,引文从客观的存在转化为主观的认知,即引用者在接受之初,便已经把客观的话语整合到了自我的认知体系中,从而直接地改写了引文的内容。因而,引文便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从认知理论来看,引用者在引文之前,其大脑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已经建构起了认知客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使人在摄取客观对象时,更容易接纳那些已经和自己的思维具有某种对接的内容,并由此纳入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之中,这就使人的认知和接受,在没有展开之前,本身就已经建构了一个认知外在对象的范式。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范式,作者在获得信息后,就会“想当然”地改变客观对象的既有本真面貌,由此出现某些偏差。如笔者对《国文月刊》的目录进行辑校时,便把“夏丏尊”误打成了“夏丐尊”。⑤追根溯源,因为这一错误在第一次出现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再三的核对,在出炉之后,以后的所谓校对自然就变成了“走过场”。与此相对应,当这样的一种错误随着引用者不断地自我强化之后,又逐渐进一步地巩固了这种认同,即由当初还显得有些不够踏实的感觉逐渐地建构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感觉。在此情形下,如果再让作者自己来校对文稿引用上的错误,便是不现实的事情了。 另外,眼睛的存储和记忆的递减问题。根据生理学的规则,人的眼睛在摄取对象时,有一个在大脑中存储和记忆的过程。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本身是复杂的,人在摄取对象后,在存储和记忆时,总是有一个记忆上的错漏问题。从引文的实现过程来看,第一个程序是作者先通过眼睛,获取所需要加以引用的引文的信息,然后存储在大脑中,从眼睛获取信息到存储信息,本身便有一个信息损减或者增益的过程;第二个程序就是作者在获取和存储了信息后,再进行外化的过程,从大脑存储到外化,本身又有一个信息的损减和增益的过程;第三个程序就是核对的过程,由于在核对的过程中,引用者依然存在一个从获取信息到核对信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难免会出现损减和增益信息,致使一次核对难以真正地做到精密准确。在引文的核对中,从其引用的过程来看,受制于眼睛阅读和传递中的“能量”递减,致使引用的过程难免在信息传递中出现遗漏。一旦作者在第二次核对中没有发现问题,就会从思想上认定,引文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就难以再次核对其准确与否,从而使引用者不再怀疑引文会存在偏差之处。 三、如何规避引文错误 引文在学术论文中既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极易出现错误,那么,怎样才能规避引文的错误,使得引文能够更好地遵循学术规范呢? 其一,在理念上要树立科学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许多卓有成就的学者都有过阐释,如有些人把学术研究的目的视作求真,有些人把学术研究的目的视为自己对人类贡献聪明才智,由此找寻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实际上,从学术态度的角度来看,对引文的关注和重视意味着学者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学者许志英对学术论文中的引文就非常重视,正如其学生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审读一篇论文,先不急着阅读论文内容,而是翻到论文的最后一页,核对几条引文注释,看看是不是准确。如引文与原文出入较大,错误较多,先生总是要毫不留情地将论文退回……先生对自己的书稿的引文注释也从不敢大意,总是找来原文反复核对无误才放心。”⑥可见,引文在许志英那里,已经上升到了治学态度这一高度,成为衡量一个学者如何对待科学研究的“大是大非”问题了。 严格说来,科学不能有侥幸心理,更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严谨态度,是一个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如果“差之毫厘”,在实践中便会“谬以千里”,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可以“验证”的。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不然,在引文中出现一些错误,既不会立刻得到“验证”,也不会立刻导致“谬以千里”的结果,这就使得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难以体验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者因为“验证”而来的焦虑感和神圣感。因此,作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要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那样,在心中确立起一个不可撼动的信念:客观事实无论怎样,都应以其本真的面貌来呈现。任何点滴的改动,都会违背科学的原则。其实,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地切割客观现实,在科学信念并没有被推崇到无以复加高度的中国学者那里,从文化心理结构上便没有把科学的求真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20世纪初,鲁迅留学于日本学习解剖学时,便出现过这样的偏差。对此,鲁迅这样回忆藤野先生对他的婉转批评:“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⑦藤野先生用科学的求真原则纠正了鲁迅既有文化观念中的主观性成分,这对鲁迅后来走上秉承写真实社会人生的文学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通过鲁迅在事过20多年对此事还有着深刻的记忆来看,藤野先生手把手教给他的科学求真原则,已经转化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如此说来,具体到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对引文的科学求真的原则,便超越了具体的事实本身,而具有了更为宏大和久远的文化意义。 其二,在版本上要注重使用原始版本,切忌道听途说或借用他人的引用,真正做到不见“真经”不引用。在急功近利的当下,学术浮躁风气日盛,大学排名要看论文,学者晋级要看论文,工资奖金也要看论文。在这种功利的诱惑乃至驱使下,学者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学者那种“坐冷板凳”的心境,更没有那种甘愿忍受“十年苦”的志向,学术正在演绎为一块“敲门砖”,不管这“砖”到底是由什么烧制而成的,只要能够“敲开”功利之门便是一块“好砖”。在此情形下,人们对原始的版本就不再特别重视,而是把别人引用的内容抄录下来,且不说部分学者在抄录的过程中可能会“散失”多少内容,单就他人的引用本身是否准确来说,也是需要质疑的。至于有些学者仅仅满足于抄录别人的引文而没有阅读原始版本,更没有将其所引用的内容放到具体的语境下加以确认,由此出现某些偏差,更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前人的原始文献或者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时,必须要回到原点上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种“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话短长”的尴尬局面。 其三,从方法论上看,要采用读校法和互校法。从事学术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从引文出现的错误来看,“丢三落四”的原因往往就在于有些学者“搬运”资料时方法不对路,致使在“搬运”过程中没有做到“全覆盖”,最终导致某些内容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那么,要想实现“全覆盖”,最佳的方法就是读校法。所谓读校法,就是一个人读,一个人校。读者逐字逐句,包括其中的标点,都要“一板一眼”地读出来;然后,校者再用。也就是说,引文的规范性问题仅从理论上认识是不够的,而只有“一字一顿”地过滤一遍;其中出现多音字、人名等容易混淆的字符,要停顿下来,再进行认真的核对。如果无法做到一人读一人校,可先用录音把原始版本的内容录下来,然后再回头来进行校对。这种方法尽管繁琐了一些,但校对出来的引文一般都能达到很高的准确率。至于互校法,在学界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推崇,成为人们常用的一种校对方法。互校法的优势在于,把自己的文稿请学界同人帮助校对,可以有效地规避思维定势对错误的熟视无睹。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把引文核对代入到不同的思维定势之中加以筛选,由此最终把那些既有悖常理、又背离原始版本的错误引文校正过来。 其四,从认知上看,要秉持未经确证前的审慎怀疑态度。思维定势致使引文出现某些偏差,就其根本来说,还是根源于对其引文过分的自信。这里所谓自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过分相信自己的引文不会出错。正因为相信不会出错,自然也就不会再去怀疑引文存在什么偏差了。思维定势导致的引文偏差,说到底,还是一个科学态度的问题。在科学面前,应该老老实实,而不能心存侥幸。如果对待引文能够上升到科学的高度,那么,思维定势就不会再用自己的思维来整合对象,而是改成用客观对象来整合自己的思维。换言之,不是客观事物要迎合或俯就自己的思维,而是自己的思维要符合客观事物本身。因此,面对在学术论文中出现的引文,不能先入为主地自认为没有错误,而是要以怀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引文肯定会有错误,然后再用排除法来排除其中的每一个疑点,从而确保引文真正能够经得起客观现实的再三检验。 总的来说,引文作为学术规范应该遵循。但是,引文不仅因为学术规范而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作为一种学术态度得到了特别的凸显。毕竟,作为引文,是否正确,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引文的规范性问题,仅从理论上认识是不够的,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才能真正有效地避免引文中相关错误的产生。 注释: ①蔡仪:《论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 ②田仲济:《郁达夫的创作道路》,《山东师范学院学报》(现代文学版),1959年第3期。 ③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④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读书》,2007年第11期。 ⑤李宗刚:《〈国文月刊〉(1940~1949)目录辑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⑥施军:《怀念恩师许志英先生》,沈卫威、王爱松、翟业军编:《往事与哀思:怀念许志英教授》,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⑦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学论文; 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