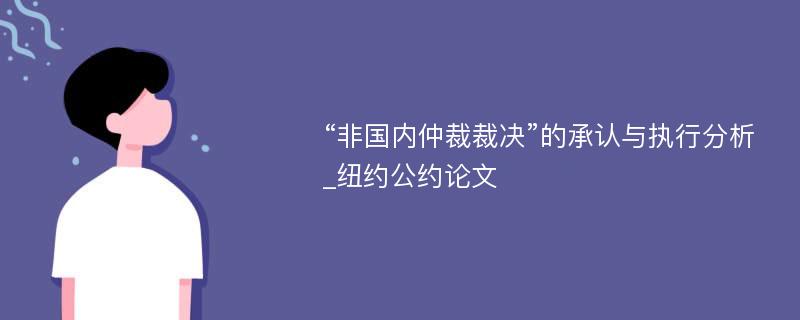
“非国内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仲裁裁决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非国内仲裁裁决”是涉及到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能否摆脱特定国家国内法支配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探讨了“非国内仲裁裁决”概念及基本类型,分析了有关国家对一项“非国内裁决能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司法实践”,认为“我国当事人不应谋求通过‘非国内化’仲裁解决争议,我国法院对‘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亦应持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非国内仲裁裁决 仲裁程序 可执行性 纽约公约
在近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试图使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摆脱特定国家国内法(尤指仲裁地国法)支配或控制的新动向,西方学者一般将之称为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sation)或“非当地化”(delocalisation)。 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断言,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已出现了“非国内化”或“非当地化”的发展趋势〔1〕。 ”这种“非国内化”仲裁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非国内裁决”(a-national awards)。这种仲裁裁决, 能否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在有关缔约国获得承认与执行,不仅直接关系到“非国内化”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司法机关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目前,“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已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我国已加入1958年《纽约公约》,“非国内裁决”能否依据公约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以及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种裁决应持什么态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非国内化”仲裁与“非国内裁决”
按照传统法律观点,国际商事仲裁应当也必须受某特定国家法律的支配,而支配仲裁程序的法律,则是仲裁举行地国法。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仲裁程序受仲裁地国法支配,可以说是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实践。然而,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举行地”作为决定仲裁程序法适用的连结因素,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表明,无论仲裁适用的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均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只有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仲裁程序才适用仲裁举行地国法〔2〕。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使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摆脱特定国家国内法支配,仅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或仲裁庭直接确定的仲裁程序规则进行仲裁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国内化”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仲裁程序不受任何特定国家国内法支配,仲裁裁决是基于一个完全“自治”的程序规则体系作出的,与任何特定国家国内法均无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属于一种“非国内”(a-national)裁决,西方学者将这种裁决形象地称为“漂浮的裁决”(floating awards)〔3〕。
尽管各国学者对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国内化”理论,评价不一,褒贬皆有,但从实践上看,的确存在着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国内化”现象。不仅在有关国际公约、国内立法及常设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4〕,已出现了承认和支持国际商事仲裁“非国内化”的规定, 而且有关国家也出现了承认与执行“非国内裁决”的司法判例。因此,“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已不仅是各国学者所“假想”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各国司法机关所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各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争论的焦点是:1958年《纽约公约》能否适用于“非国内裁决”?当事人在获得一个“非国内裁决”后,在败诉方当事人不主动履行裁决义务时,能否依据公约规定向有关缔约国申请强制执行?对“非国内化”理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国内法对裁决的适用性,是公约得以适用的前提条件,因此,一项“非国内”仲裁裁决,是不能依据公约在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5〕。 虽然实践中有“非国内”裁决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先例,但各国的实践很不一致,这种裁决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当事人如欲进行“非国内化”仲裁,就必须冒其裁决在有关国家得不到承认与执行的风险,这正是“非国内化”理论最为致命的缺陷。支持“非国内化”理论的学者则极力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规定的精神,一项仲裁裁决要获得执行,并不必须有一个“国籍”,即使没有“国籍”,裁决一样可以在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公约本身就是“支持仲裁裁决摆脱国内程序规则的国际手段”〔6〕。
二、“非国内”仲裁裁决的概念与类型
从“非国内”仲裁裁决问题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非国内”仲裁裁决,准确地说,是指非依仲裁地仲裁程序规则作出的裁决,并且该裁决依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称之为“内国裁决”(domesticawards)〔7〕。很显然,一项“非国内”仲裁裁决的作出, 即意味着仲裁摆脱了仲裁地程序法的支配。为了准确地理解“非国内裁决”的概念,必须明确三个问题:
首先,“非国内化”仲裁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了任何国内管辖。一项“非国内裁决”,如败诉方当事人未能主动履行裁决义务,胜诉方当事人如欲获得裁决的实际执行,必须向有关国家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该项裁决仍然要面临着被申请执行地国法院的司法审查。它与其他裁决在性质上的区别在于,它不象依特定国家国内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那样,事先获得法律上的执行许可。因此,从“非国内裁决”的执行上来说,“非国内化”仲裁是不可能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管辖的,“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仍然依赖于国内法院的支持。
其次,当事人选择或仲裁庭确定适用仲裁地国实体法或非仲裁地国实体法,对仲裁及仲裁裁决的性质,均无实质性影响。根据国际私法中通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享有选择仲裁适用的实体法的充分自由,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地国以外的其他特定国家的实体法,甚至选择适用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商事惯例等,并不能使仲裁具有“非国内化”性质,当然,也不能使仲裁裁决成为“非国内裁决”。
第三,“非国内化”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当事人选择或仲裁庭确定的非仲裁地国的程序规则,至于其国家的仲裁程序法能否适用,在“非国内化”理论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们中间,观点也不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排除仲裁地程序法的适用,依据是很充分的,但如排除任何特定国家仲裁程序法的适用,则会使仲裁丧失任何国家法院的司法监督,除非当事人协议规定了一个司法监督体系,并且有关国家愿意接受这种监督管辖。的确,当事人选择仲裁适用的程序法,往往是出于维护其合法利益的法律考虑,而仲裁地的选择,则往往是出于非法律的中立或便利的考虑,这种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一个纯属偶然的因素来确定适用于仲裁的程序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当事人在仲裁中要求摆脱仲裁地国程序法的适用,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仲裁中能否排除仲裁地国程序中的“强制性规则”(mandatory rules)的适用, 则是值得讨论的。
根据“非国内裁决”产生的原因不同,我们可以将“非国内裁决”分为三种类型:
(一)意外的“非国内裁决”。如当事人误解了所选择的仲裁规则的性质或误用了程序,均可导致“非国内裁决”的产生。例如,在“戈塔韦肯·阿伦达尔船厂诉利比亚国家海运总公司”案中,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了有利于申诉人的裁决,但被诉人拒绝履行裁决,申诉人即在瑞典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份裁决。被诉人利比亚海运总公司遂向巴黎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消裁决。〔8〕被诉人试图向法院证明, 该案适用法国法至少是他这一方当事人的本来期望,并且“戈塔韦肯”已经承认裁决是依据法国程序法作出的。然而法国法院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巴黎上诉法院认为,国际商会的裁决不是依法国程序法作出的,不属法国裁决,超出了法院的管辖范围,因此,拒绝受理此案。这样当事人所获得的裁决无疑就成为一项未预料到的“非国内裁决”。在另一案件(SEEE)中,瑞士州法院拒绝登记裁决,其理由是该案仲裁是由两名仲裁员而不是由根据该州法所要求的奇数仲裁员所进行的,这样瑞士法院就把“SEEE案”裁决置于了“无国籍”的境地。然而,仲裁裁决的确是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在指定的仲裁地,由两名仲裁员作出的,显然这是因当事人没有理解他们所选择规则的意义所致,这种“非因内裁决”的产生,当然也是出乎当事人预料的。
(二)、仲裁员创造的“非国内裁决”。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或指定仲裁程序规则时,就必须由仲裁员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仲裁员选择适用非仲裁举行地的程序规则,那么当事人所得到的就是一项“非国内裁决”。例如,在利比亚美国石油公司案(LIAMCO)中,独任仲裁员发现当事人没有协商同意应当遵守的程序规则,而受“仲裁受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支配”观点的影响,认为该案仲裁程序应按1958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仲裁程序公约草案》中所包含的一般原则的支配〔9〕。 这样,仲裁员没有适用任何国内程序法,仲裁就成为“非国内化”仲裁。
(三)、有意采取“非国内化”仲裁而产生的“非国内裁决”。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当事人为了摆脱仲裁地程序法的支配,而有意采用“非国内”仲裁程序规则,据此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即为“非国内裁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81年根据解决伊美求偿问题的声明所成立的“伊—美求偿仲裁庭”,仅根据其特定的程序规则(该程序规则是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为蓝本修改、制定的),而没有根据包括荷兰(仲裁地)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国内仲裁程序法作出了大量仲裁裁决。这种仲裁裁决是典型的“非国内裁决”〔10〕。此外,建立在《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基础上的“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仲裁,根据公约第44条规定,也完全排除任何特定国家国内程序法的适用,其作出的裁决自然也属“非国内裁决”。
根据国内法是否能产生“非国内裁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1987年12月18日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的颁布,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该法关于国际仲裁适用程序的规定,反映出瑞士立法存在着国际仲裁摆脱国内仲裁法制约的倾向。该法第182条规定:“1.当事人可直接规定或通过援引仲裁规则的方式决定仲裁程序;他们也可约定使仲裁程序服从某一程序法。2.当事人未规定仲裁程序的,仲裁员在必要范围内,可直接或通过援引其法律或仲裁规则的方式确定程序。”由此可见,瑞士仲裁立法允许当事人按照其指定的仲裁程序规则或法律进行仲裁。同时,通过签署适当的排除协议,当事人也可完全排除诉诸瑞士法院的可能性〔11〕。既然瑞士仲裁法倾向于使国际仲裁摆脱仲裁地法支配,并且允许当事人和仲裁庭选择或确定非仲裁地法的适用,那么依据该法所进行的国际仲裁,完全可能是“非国内化”仲裁,基于此种仲裁所作出的裁决,无疑也就是“非国内裁决”了。
三、对“非国内裁决”可执行性的实践考察
“非国内裁决”是国际商事仲裁“非国内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直接关系到“非国内化”理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无论“非国内化”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此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各国司法实践所表现出的立场和态度,却很不一致。据已公开报道的几件判例分析,有些国家法院对“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持明确的支持态度,而多数国家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SEEE案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花费了三十年时间,即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很有必要对有关国家的司法实践作一初步考察。
(一)美国的实践。在“非国内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缺乏有力的司法判例的支持,一直是困扰“非国内化”理论的倡导者及其支持者的一个问题。1989年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对“伊朗国防部诉古尔德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在该案中,法院面对一项由“伊一美求偿仲裁庭”所作的“非国内裁决”,明确判定该项裁决可以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强制执行。审理此案的奥斯坎兰(O'Scannlain)法官认为,对公约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公约适用于“非国内裁决”〔12〕。这一判例有着坚实合理的依据,已为美国不少学者接受,尽管这一判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贬损该判例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美国第一个清楚、完整地表明,根据《纽约公约》,“非国内裁决”具有可执行性的判例。但是,美国对于“非国内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实践并不一致。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伯格森”(Bergesen)案的判决,则没把“非国内裁决”纳入《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瑞典的实践。在“戈塔韦肯”案件中,申诉人胜诉后即向瑞典斯维(Svea)上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诉人则在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对裁决提起异议,要求撤销裁决。被诉人以裁决已在巴黎上诉法院提起异议为由,请求瑞典法院中止执行裁决。瑞典法院拒绝了被诉人的请求,并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 )项规定裁定执行裁决,瑞典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法国法院则主张裁决不属法国裁决,因而拒绝对该异议行使管辖权。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瑞典法院执行了这一项“非国内裁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非国内裁决”可以按照《纽约公约》得以承认与执行。因为瑞典最高法院在维持执行裁决的裁定时,并未把该裁决视为“非国内裁决”,而是将其视为“外国裁决”(即法国裁决),而戈塔韦肯在申请执行裁决时,也是将之作为“法国裁决”对待的,这就使这一判例在论证“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同样,瑞典法院在处理LIAMCO案的执行问题上,也没有讨论裁决的“非国内”性质,而是将之视为瑞士裁决,明确根据《纽约公约》予以执行。然而,在瑞典法院发出执行令后,瑞士联邦法庭却判决,根据瑞士法,裁决的执行与瑞士无充分的联系。从此可以看出,瑞典法院在执行裁决时,似乎是不考虑当事人在裁决作出地法院对裁决所提起的异议,这一点倒是与“非国内裁决”与仲裁地国程序法及法院无实质性联系的观念相一致的,就此而言,可以说瑞典法院是倾向于执行“非国内裁决”的。
(三)瑞士的实践。瑞士法院对“非国内裁决”执行问题的立场尚不十分明确。从SEEE案的执行看,虽然瑞士法院拒绝执行该案裁决,但其洲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是认可“非国内裁决”这一概念的。不过,关于SEEE案裁决执行的裁定是在瑞士接受《纽约公约》之前作出的,瑞士法院在该案裁定中认可了“非国内裁决”的概念,并不能证明瑞士法院在那时承认“非国内裁决”的可执行性。同样,在LIAMCO执行案件中,瑞士法院基于内国裁判法(Judgment Law)而非仲裁的性质,拒绝执行该案裁决,因此该案处理结果也不能反映出瑞士的立场。然而,1982年瑞士联邦法院在审理“伯格森”(Bergesen)裁决执行案的判决中,对“非国内裁决”的有效性提出一个概括性的主张。法院在判决的法官附带意见中称:当事人既可自己制订程序规则,也可选择既存的私法规则,甚至也可声明排除一个国家有关程序的强制性规则〔13〕。这种宽泛的表述,似乎表现出瑞士法院存在着强制执行“非国内裁决”的愿望。
应当指出,尽管瑞士法院的态度不甚明确,但瑞士仲裁立法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则是非常明确的。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不仅明确准许当事人进行“非国内化”仲裁程序,而且在该法第192条第2款明确规定,“非国内化”仲裁所作出的裁决, 可以根据《纽约公约》获得执行。从此立法分析,该法是支持将《纽约公约》解释为适用于“非国内裁决”这一观点的,该法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未依任何国内程序法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受仲裁地法院审查,并可依据《纽约公约》获得执行。因此,总起来说,瑞士对“非国内裁决”可依《纽约公约》获得执行这一问题,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
(四)荷兰的实践。荷兰法院对待“非国内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在SEEE执行案中,Hoge Read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拒绝执行裁决的裁定。荷兰法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法院没有义务在对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裁定前,考察裁决与裁决作出地国法或任何其他国家法有何联系,并且在没有这些联系时拒绝承认和执行。该法院的判决意见清楚地表明,法院站到了支持可以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非国内裁决”的这一边。然而,两年之后,在案件发回下级法院,又再次回到该法院时,法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法院认为瑞士法院判决裁决不能执行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项规定的撤销裁决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法院没有将案件发回, 而是驳回了SEEE申请执行的诉讼请求。然而,问题在于,瑞士法院曾明确指出,他们在诉讼中要决定的只是裁决是不是瑞士裁决,而非撤销该裁决。既然如此,荷兰法院的上述判决和理由就难以成立了。因此,可以说,荷兰最初对执行“非国内裁决”是持积极态度的,但目前似乎是不情愿执行“非国内裁决”。
(五)法国的实践。
通过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对“戈塔韦肯”案的判决,可以看出法国是明确承认“非国内化”仲裁的,在另外一个不是太直接的判例——“桑·古邦公司诉印度化肥公司”(Compagnie de Saint
Gobain
v. Fertilizer Corporation)案中, 法院判决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唯一理由,就是裁决系在法国领域外作出,并且当事人能够选择其适用的程序规则。尽管一方当事人在印度法院提出了裁决异议,法院仍然强制执行了仲裁裁决〔14〕。另外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法国法院在SEEE申请执行案件中,授权执行该案仲裁裁决,这一案例清楚地表明了法国执行“非国内裁决”的司法观点。同时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94条、第1495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适用于仲裁的仲裁规则或现行的仲裁法;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则授权仲裁庭直接确定仲裁适用的程序法或仲裁规则。
通过以上对有关国家司法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出,“非国内裁决”已在有关国家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获得承认与执行,这对“非国内化”理论的倡导者及其支持者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尽管有关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立场尚不够明确,做法还不尽一致,但“非国内裁决”能够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不仅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而且为“非国内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对“非国内裁决”可执行性的理论分析
反对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非国内裁决”的学者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非国内裁决”不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中所称“内国裁决”并不能等同于不受司法监督的“超国家裁决”(super-national awards), 而从公约第五条规定分析,裁决必须根据特定国家国内法作出,才能根据公约承认与执行。笔者认为,实际上,从公约的目的及具体条款分析,公约适用于“非国内裁决”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首先,从起草公约的目的看,国际商会提议起草《纽约公约》以取代1927年《仲裁条款议定书》和1927年《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时,就注意到有关国家认为这两份公约过分注重仲裁地法。由此,扩大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范围,是《纽约公约》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公约起草时,国际商会起草的原始草案(original draft)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起草的初步草案(preliminary draft)第一条, 均规定了严格的领域范围,但西欧大陆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东欧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后达成妥协,增加了“非内国裁决”标准。这一标准的增加本来是限制公约的适用范围,但最终却起到了扩大公约适用范围的作用。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为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即会议最终的立场是《纽约公约》所适用的裁决类型应尽可能地扩大。因此,尽管仅从公约第二条第(一)款条文中不可能得出公约意图适用于“非国内裁决”的结论,但同样也不能得出公约排除“非国内裁决”适用的结论〔15〕。
其次,从《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公约适用范围来看,它不仅适用于“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以外国家领土内所作成的仲裁裁决,而且适用于“经申请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的仲裁裁决。《公约》并未要求一项裁决应该受某一国内仲裁法支配,或必须根据某一国内仲裁法作出。在确定公约适用的范围时,公约采取了“领域标准”和“非内国裁决标准”。根据前一标准,只要求裁决是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国以外的国家作出,而不管支配仲裁程序的是国内性质的还是国际性质的仲裁规则;根据后一标准,虽然裁决是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国家作出的,但该国并不认为是其“内国”(domestic)裁决。例如,裁决是根据当事人选择的仲裁法而非仲裁所在地仲裁法作出。此外,公约也并不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某一国内的仲裁法。在实践中,某些“非国内”裁决,如“利比亚美国石油公司”案、“戈塔韦肯”案、 “SEEE”案等,在相关国家均得到执行。因此,缔约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执行一项裁决时,应当查明的是该裁决是否系在另一缔约国作出的,或是否为其“内国裁决”,而不必考虑适用于仲裁程序的是哪一仲裁法〔16〕。
第三,从公约授予当事人法律选择的权力范围来看,公约不仅承认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法的权力,而且给予当事人所选择的程序规则以优先权。只有在无此选择时,仲裁地的程序法才得以适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仅限于国内程序法;同时,公约也没有阻止当事人为使仲裁摆脱任何国内法体系而自行起草、确定仲裁适用的法律程序规则。
五、结论
“非国内化”仲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仲裁当事人试图使仲裁程序摆脱仲裁地法支配的强烈愿望。尽管就其理论尚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但它对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国际商事仲裁的这一发展动向,不仅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反映,而且得到了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的支持。但“非国内化”仲裁所作出的“非国内”裁决的“可执行性”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充分证实。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当事人不应谋求通过“非国内化”仲裁解决争议,我国法院对“非国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亦应持审慎的态度。
注释:
〔1〕P.桑德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发展趋势》, 载《海牙国际法学院演讲集》,1975年,第145卷,第2号,第256页;D.M.卢尤:《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1978年,英文版第590页。
〔2〕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年修订版,第471页;莫里斯:《冲突法》英文版,1984年第3版,第136页; 戴赛和莫里斯:《冲突法》,英文版,1987年第11版第534—535页;戚希尔和诺思:《国际私法》英文第11版第436页。
〔3〕A·雷德芬和M ·亨特:《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与实践》, 1991年英文第2版第82页。
〔4〕参见:1961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公约》第4条,1965年《华盛顿公约》第44条,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82条,ICC仲裁规则第11条。
〔5〕冯·登·伯格:《1958年纽约公约》,1981年英文版第33 页。
〔6〕〔14〕J.保尔森:《无约束的仲裁:摆脱裁决作出地国法的仲裁裁决》,载《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1981年第30卷,第369、374页。
〔7〕〔12〕〔13〕S·沃德·阿特伯里:《1958年纽约公约下的‘非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载《福吉尼亚国际法杂志》,1992年第32卷,第473、506—507、487—489页。
〔8〕“戈塔韦肯案”,参见《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1981 年第30卷,第385—387页;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9〕参见:《国际法律资料》,1981年,第20卷,第1号,第42—43页。
〔10〕〔16〕A·B·阿丽内森:《纽约公约与非国内仲裁裁决》,载《国际仲裁杂志》,1991年,第18卷,第1号,第6、25—26页。
〔11〕参见P·拉利夫的评论:《瑞士新国际仲裁法》, 载《国际仲裁杂志》,1988年,第4卷,第12页;注〔5〕引文,第486—487页。
〔15〕《商事仲裁年鉴》,第9卷,第437页。
标签:纽约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仲裁程序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仲裁法论文; 商事登记论文; 仲裁裁决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