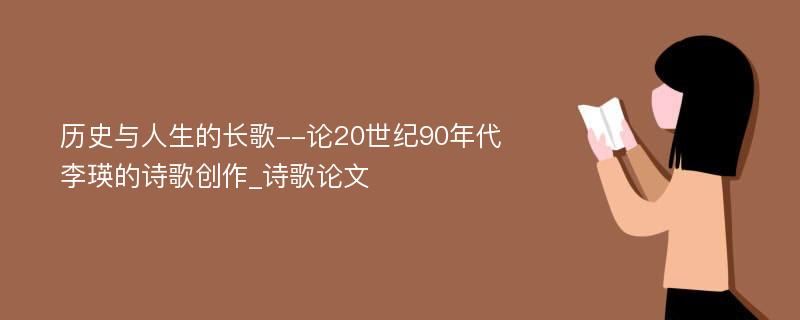
历史与生命的长歌——论李瑛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生命论文,世纪论文,诗歌创作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9-0096-04
一
1990年代,随着社会时代的转型,整个诗坛从喧嚣逐渐走向沉寂,此时的李瑛从花甲 迈入古稀,同时,他的诗学观念也随着时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晚年心境而发生了极大变 化。“岁月匆匆,在时间的冲刷中,人人都会渐进苍老。面对生命的流逝,常会使人产 生许多过去从未感觉到的东西,有忧虑、有惶惑、有无奈、也有坦然。心中的景象总是 不同于前”。对于李瑛而言,似乎人到老年诗境愈真,从激情燃烧的岁月转入苍老而沉 郁的老年境界,其诗作亦可看作一个进入老年的诗人对过往历史与生命的回顾和省思。
从文化断代上来看,李瑛属于“三八式一代”(李泽厚语)或曰“解放的一代”(刘小枫 语)。而对于这一代诗人来讲,首先可能是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而如何面对历史最终 更是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过去的李瑛似乎总是以一种不加思考的热情投入到时代中, 并且执著相信“诗,总是美的”。他的诗中,往往以国家意志代替个人思考,对时代融 入的热情表现为单一的政治热情,赞歌多于批判,讴歌的声音常常淹没理性的思考,赞 美式的抒情往往等同于政治颂歌。而在1990年代,他开始对自我反思:“确实,在今天 ,我对生活和周围的事物,和年轻时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已有很多不同了。比如青年时 喜欢读有英雄人物的书,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涉及到人的命运的书,而不大 愿读理论性强的学术著作,觉得它们抽象和枯燥;而今则更喜欢读过去所不愿读的那些 与人生密切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了,包括曾经认为是乏味的中国和外国的哲学著作”。“ 在日常阅读中,我对生命、生活、人生、艺术和美学等意义和价值方面的认识,现在比 起过去也似乎有了更深的领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使他的诗歌具备了深沉的理性思考 和哲学意蕴,而诗人“美”的诗观,也开始有所深化,在《历史、自然、诗、美、生命 和我自己》一文中他详尽阐释了新的诗学主张:“一个诗人不仅是美的代表,同时还应 是而且首先还应是真实的代表。一个诗人应该成为一个种族的触角,任何时候都不应淡 化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声音。”在我看来,这里的“真实”既包括历史真实,也包括生 活真实,历史真实伴随着历史理性的崛起,生活真实则是随着时代变迁必然褪去各种伪 饰外衣而现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哪怕是残酷的真实。
过去诗人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在积极的“入乎其世”之中往往不必思考为何入世, 此时的“出乎其世”也并非与“入世”对立的出世隐居或忘却人间现实,而是带着更深 的忧患和责任反思过去与当下的时代与感情,这应是一种具有理性的自知、自省精神的 积极“出世”。而对于一个曾被时代飓风震上颠峰的老诗人而言,或许最可贵的就是这 种自知和自省,它是在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或辉煌之后自然归于淡泊和沉思的情感,它是 一种“抽身而退”的“出乎其世”,在这种“抽身而退”中,诗人对文学、对时代、对 自己命运的浮沉,已经有了更为深切的感知,“只有在万丈云空/才能望穿千寻海壑” ,《巢》中的诗句可以说是诗人回望生命与历史的自况和自我总结,带着一种世事变换 的沧桑感,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具有一种来自生活的朴素哲理。
随着诗学观念的变化,李瑛诗歌的主题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生活与时代使诗人悟出更 为真实的哲理和诗意。1990年代主要写诗人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感悟,充满历史意味和生 命意识,如果说过去的诗歌属于“激情的诗”,那么1990年代的诗歌则属于“沉思的诗 ”。如《生活》中对历史本身的思索和个人在历史的定位感:“历史已经醒来,/听山 和海和你对话/每个人都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懂得生长双手的意义”,“长天下,老 祖父的荒坟/摇曳着一岁一枯荣的野草/我们把墓碑上的苔藓和水迹/称为历史”。显然 ,这时的诗歌功用已经不再仅仅作为时代的号角与传声筒,而是如“丝绸”般的柔软温 润,如“灯火”般的明亮温暖,如“锋刃”般闪烁冷峻尖锐的光芒。换言之,诗人在这 首诗里透露出了一种对写作、人生的全新理解:豪壮与优美、激情与柔情构成多层面的 人生,政治性、革命性之外包容更具个人性的人情人性,种花之外也种刺。这应该是李 瑛这一代诗人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一种丰富或者说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的导引下,李瑛的诗歌呈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具 个体感受的生命意识。比如他通过“春天的树”、“柳枝”讲述关于生命与生命的燃烧 。“走过坚硬的冬天的柳枝”给人的启示是“燃烧着希望的无畏的生命”。《春天的树 》歌唱的是“生命的力与美/纯朴与精壮”。同样的生命主题在《生命》一诗中有着意 蕴复杂的表达,被晾在绳子上的一条条鱼的生命,是“一条条身体和思想都已干瘪的鱼 ”。李瑛笔下僵硬、风干、失声的“鱼”既非艾青笔下的鱼化石,借完美的鱼化石诉说 自己关于生命的自我隐喻——虽然被掩埋但仍然完整、仍然不忘“斗争”和“运动”; 也非卞之琳笔下的鱼化石,在“鱼”和“水”的完形中寄托爱情和人生的理念。李瑛观 照的是“鱼”和“海”的关系以及失水后“鱼”的命运,试图透视的是一种主体(人或 物)与环境的关系。这首诗最后以“大地映出一道道凝重的投影”结尾,情感颇为冷峻 、激切,完全没有了过去诗歌的乐观与激情,由这首诗引出的追问可能是:这一条条“ 鱼”是谁?是诗人自己,是诗人所代表的一代人,还是普泛的有追求的所有个体生命?同 样的思索是:在时间的无涯长河里,个人生命是极其短促的;在历史的漫漫瀚海中,各 个时代的纷争也不过是其中飞溅的浪花而已,而个体将如何融合、脱离或对抗自身的环 境而存在?《生命》一诗的启示是痛苦、凝重甚至是冷峭的,其复杂深远的主题指向也 迥异于过去简单明确的主题指向,这是1990年代李瑛诗歌的重要品质,一种源自自然、 源自个体生命而升华的思考力量和哲理向度。
过去,他把自己的诗歌视作“是我们的战士和人民的战斗生活的回声”,正像他的诗 集名《时代纪事》一样,他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诗歌基本上可称作一种“时代纪事 ”,他以诗人对时代政治的敏感和热情写出了《战场上的节日》(1952)、《天安门上的 红灯》(1954)、《颂歌》(1961)、《献给火的时代》(1964)等诗集。在1990年代,他的 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倾诉》中的情感和诗风明显转向内敛和深沉,诗歌内涵也 从“时代纪事”转向“生命纪事”,构思诗作时往往以小见大,以幽微见深意,显示了 他试图从大向小、从外向内、从时代向自我回归的倾向。李瑛1990年代的诗歌选取的意 象也多是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如《钥匙》中的钥匙、蝴蝶标本、羊角壁饰、蜡烛、鸟笼 、眼泪、家等,生活化与个人化的事物,与时代的大风大雨不同,诗人摆脱了带有国家 意志的宏大叙事而使诗情更加贴近了带有个体温润记忆的日常生活,这种寓深刻于平凡 的诗学追求似乎也契合了诗人从辉煌向淡泊回归的人生追求。
李瑛在1990年代的创作很多是回忆往事、回忆童年的诗歌,这类诗歌可以称之为他的 “忆旧诗”,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诗作。在1990年代,老诗人已从花甲逐渐走入“古稀 ”之年,晚境将至,回忆亦纷至沓来,尤以童真清纯的童年与少年的记忆为主,因为这 个时期是带有“人之初”的天然稚纯。“思念的触须总向童年延伸”(《回忆童年》), 于是,他带着“温情与深情”以及“质朴的诗句”,在“隔着四季/隔着茫茫烟云和数 不尽的山水/时间和空间”(《怀念远方的朋友》)里,开始写下对童年生活以及过往岁 月的回忆,如《回忆童年》(1993)、《回忆:关于春天》(1992)、《回忆:关于青蛙》 (1993)、《回忆:关于野菜》(1992)、《回忆:一次送行——给我的中学老师》(1992) 、《摇篮曲》(1993)、《一只马蹄铁》(1993)、《回忆》(1994)、《怀念远方的朋友》 (1994)、《假如窗外有雨》(1994)等。这些诗歌多情蕴其中,真切感人,表现了诗人经 历了岁月洗刷后的人世慨叹,有一种人至晚境回眸往事所迸发的赤子真情以及岁月流逝 的唏嘘。
对于过往人事的忆念,李瑛曾夫子自道:“在思想上,我一向是生活在未来多于生活 在现在之中的,而近年我发现自己常常是不自觉的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之中……我 常常想起父母,想起童年,想起一起长大的散居四方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众多的小伙伴 和年轻时的朋友们,想起当年贫苦年代的艰辛生活,曾经历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件 和一些可怕的荒唐岁月,以及许多不无懊悔的往事。”在这种返朴归真之情的观照下, 诗人的定位已经不再是声名隆盛的时代名人,也不仅仅是诗人骄傲自豪的“战士”,而 完全还原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一个有着深挚亲情与温暖人情的人,一个有着酸甜苦辣 生活的“苦儿”或“少年漂泊者”形象,诗中包孕的是一颗稚子童心,是一颗原初真心 ,在他的忆旧诗里透出一种质朴和沉实的美。与过去相比,诗情少了一些狂放和豪迈, 多了一些怅惘和哀叹,少了一些赞美和激情,多了一些苦涩和沉痛。
建国后30年的主流诗歌往往很难容纳人性人情的情感,诗歌的情感空间豪情满溢而温 情缺失,充斥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忘我”与“无我”之情,所以常常显得空疏冷漠, 难以打动人心。而李瑛的这些带着个人体温的回忆诗作,在某种程度上既折射了诗人自 任繁华落尽的淡泊心境,也是对过去张扬“大我”而疏离“自我”的一种反拨,同时更 是一种人性回归和人格提升。
二
李瑛在1990年代之后逐步修正、抛弃了过去那种简单地“为阶级”、“为人民”、“ 为时代”等有具体所指而且高度政治化的“为……代言”的诗歌模式或曰诗学观念,他 开始对过去简单的“服务论”进行了一些调适和充实,而是以一种更为宽广、理性的民 族情感和人类意识深掘民族、人类与宇宙、自然的精神,这使他的思考达到一种纵横捭 阖的开阔境界,并且为个人置身于历史、个人植根于现实找到了一条深广的出路或者说 契合点。所以,他的诗歌创作里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纯粹的政治抒情明显减少,诗歌表现 的历史主题与他过去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过去他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仅仅限于斗争生 活的主题和表现当时时代风貌以及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他曾经宣称:“我觉得一个诗 人的任务就是一个战士的任务,诗人的声音应该是时代的声音。”这样就使他的诗中呈 现出一种相对固定的艺术特色:时代口号夹杂革命激情,情感模式是单一的而不是幽微 复杂的、是稳定的而不是波澜起伏的、是切近时代主旨明确的而不是深远的宏阔的,所 以诗歌情感空间没有任何怀疑惆怅彷徨等复杂的心理波动,也没有更深沉的历史人文的思考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李瑛在1990年代创作的思维方式显示出一种明显“向内转”的倾向,诗人不再单一地 以“外视角”从外部世界尤其是政治视角看待历史和生活,而转化为以“内视角”的观 照方式回到内心,同时,他并没有置身于生活之外,而是始终把个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 时代与历史的变换中:“当回望身后的路时,常希望能找到精神之所在,把自己,当然 也包括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类置放在广袤宇宙之间,从那里寻找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这流露出诗人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样的诗学观和人生理念主要体 现在他的“诗”中,通过对古代贤哲多蹇命运的深沉幽思,以及对仁人勇士的悲壮浩叹 ,表达诗人面对民族文化、历史风物时的一种悠长思索和深沉凝重的文化关怀,从关注 现实斗争到探寻远古人文精神,李瑛诗歌的文化内涵更显丰富与厚重。
过去,李瑛诗歌的语言往往直抒胸臆,直白而少韵味,基本是“以抒情为主线的结构 艺术”,而在1990年代的许多诗中,能够看出老诗人在结构与语言上更为讲究,理性崛 起后,抒情淡隐但并没有完全退出诗歌空间,只是他常常以“意象”作为结构诗情的主 线,语言大多排除了切近政治的时代语汇而着力营造可感可触的个人语汇,理性的渗透 带来思想的沉淀,同时使诗歌语言更为讲究锤炼和打磨。如《纤道》一诗以“纤道”这 一令人震撼、醒目的意象写出了震铄古今的民族记忆和深重的苦难意识,被认为“既有 深远的历史感,又有凝重的现实生命体验”。那一条“像鞭子一样”静默、冷酷、消瘦 、流血的沉重“纤道”是一个民族走过的路,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因为它见证了祖先的 艰辛泪水,它本身就是民族苦难的历史见证。此诗对于民族之情的抒发饱含“隐痛”的 深情,寄意遥深且境界开阔。组诗《刘公岛的涛声》则通过“刘公岛的涛声”对已过去 百年的“甲午海战”进行了个人化的历史言说:“在最冷的波涛与最热的血之间/在乱 卷的云和撕碎的风之间/沉默的历史闪着霜刃/霜刃般的历史望着今天。”诗末写道:“ 当我懂得这一切,我便/长出了鳞、长出了鳍、长出了鳃/我要冲向一百年前大海深处/ 那场不屈的血战”,诗情虽以豪放直接为主,但诗中“懂得”二字使得诗歌的意蕴超出 一般意义的爱国情操,而是于慷慨悲歌中蕴涵深沉情怀,于赤子血性中更见理性精神。 李瑛的“怀古诗”从现实生活的观照回到历史长河的钩沉,无疑给他的诗歌带来一种历 史的纵深感,其中既有痛苦的历史追问,也有“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现实意义,同时深 藏了民族精神的诗性探寻。
李瑛表现历史文化意识和民族记忆的诗歌除了“怀古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西部 诗”,这类诗作多是关于西部风土人情的描摹和感悟,与“怀古诗”体现的历史感相比 ,“西部诗”体现的是诗人的“现实感”或曰“现实情怀”。不过,李瑛的西部诗不仅 仅是纯自然的客观写实,而且在客观自然中融入诗人主体的深沉情感和生命体验,这与 他早期描写自然的“即景状物诗”或者程式化的、简单比拟的“以物喻人诗”是迥然不 同的。自古以来,歌颂祖国山水河山的诗人与诗歌并不少见。就李瑛而言,自1940年代 以来,他的足迹就踏遍了祖国各地、长城内外,在这种游历中,他说“我发现:在我的 祖国,阳光、大海、溪谷、山峦,无一不跃动着蓬勃的生命;特别是劳动在她胸怀中质 朴的人民和保卫着她的忠实的士兵,他们的新生活、新感情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美好的 感受。”所以,他以借景抒情、以景寄情的方式表现美好生活、歌颂英雄人物,在他寄 情山水的诗篇里,北疆南海、西部戈壁、边防哨所,森林、大海、草原、山峦等均成了 他歌颂祖国和英雄的触媒。只是他的“山水诗”或曰“边关诗”既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 田园山水诗歌的恬淡隐逸,也不同于古代边塞诗歌的慷慨悲凉,而是实现政治抒情的一 个部分或者说一种变体,属于“情感赞美体系”的延伸,其局限是往往流于简单的“游 记诗”和“山水加政治”的抒情诗,所以,在他过去的这类诗中,常常喜庆有余而悲沉 不足,赞美过剩而沉郁阙如,整体上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深透力量。
李瑛在1990年代曾经访问了中国西部,诗人行走在西部、写作在西部,为西部留下一 系列大型组诗,共255首诗歌,且颇多佳作,主要有:访问新疆时所写的《戈壁海》(46 首)和访问山西时所写的《黄土地情思》(30首)、访问云南时所写的《红土地之恋》(22 首)和访问广西所写的《漓江的微笑》(19首)、访问甘肃时所写的《祁连山寻梦》(29首 )、访问陕西时所写的《黄土地上的蒲公英》(29首)和访问青海时所写的《青海的地平 线》(25首)、访问西藏时所写的《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32首)和访问宁夏时所写的《 贺兰山谷的回声》(23首),可以说,李瑛用诗歌和行为表现了对西部的关注。
李瑛的“西部诗”虽然着墨较多的是西部人民生活的疾苦和西部风土人情的抒发,但 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旅游猎奇或访贫问苦,其中透视出的是一个诗人对于民族文 化精神的游历和重塑。在他的组诗《祁连山寻梦》中,仅从作品的题目就可见诗人走过 西部的足迹,或者说走过中国文化的旅程,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陕甘宁青到新疆西藏 ,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从祁连山脉到雅鲁藏布江,从“荒滩下的古墓”、“荒原上 的向日葵”、“戈壁滩上的风”到“逆风飞行的鸟”、“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它们 带着历史的烟云和岁月的风尘呈现在诗人的笔下,以及敦煌莫高窟、汉长城、嘉峪关、 疏勒河、月牙泉、鸣沙山、高原上的风暴、落日、骆驼刺、小蜜蜂……每一处自然景观 或人文景观,每一个自然生命的生长无不浸透、传递着诗人自我生命参与的温热,这是 诗人的一段“生命的流程”:从《寻找一条路》开始诗人进入西部的文化苦旅,《凉州 词》、《题武威马超龙雀塑》……表达了对西部热土的眷恋,西部山水的苍茫辽阔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总之,在李瑛的笔下,既可以看到西部的雄奇、壮美,也可以看到 西部的贫穷、苦难,而透过一个年逾花甲的身影,既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西部的感慨和 叹惋,也可以感同身受于诗人赤诚的文化关怀,而走向西部不仅是地域的行走,更是心 灵的行走。
1990年代,李瑛“向内转”的倾向表现了回到内心、回到自我、回到个人化写作的努 力,但他的“西部诗”表明他仍然关注时代与现实,仍然怀有一腔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 ,他所排斥的只是纯粹个人化、纯粹内心化、不闻世事的文学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希望我能写出有时代气息、有生活实感、有真情韵味和有新鲜艺术追求的诗,力求 使其摆脱某些与虚伪、矫饰相像的东西,使自然在自己笔下恢复最初的朴素,不断达到 一种新的深度。总之,尽量想把每一首诗的写作,都当作是在继续探索那些尚未达到的 领域的新起点。”这是他在人生新时期的诗学追求。可以说,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对现 实介入的热忱,注定了李瑛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游戏诗人,或是对现实、时代无关痛痒 的高蹈派诗人,而始终是一个关注时代、民族前途与人类命运的诗人,更何况对于一个 习惯于为时代风云献诗的诗人,他不可能完全忘情于时代现实,个人意识、主体意识的 张扬必然胶合着社会意识、现实情怀的倾注。“我从不认为自己心灵贫瘠,精神匮乏。 但我从不愿把自己关进书斋一味低吟浅唱那些完全囿于个人化的狭窄的内心世界”。我 以为,这恰恰是今天日益走向心灵封闭的“先锋”诗人们应该学习和张扬的精神,这也 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道义和担当精神。
三
李瑛诗歌观念的现代意识使他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运用许多现代诗歌的手法,从而遏 制了过去过度夸张浪漫的激情想象,以及过于粘滞现实或政治而缺乏思想的超越性。具 体而言,诗人在语言、意象、修辞手法、情感基调等方面都借鉴运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 手法,呈现出艺术创造的探索性、丰富性和多样性。
李瑛过去多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主题先行、概念先行的构思方式,常常使诗情呈现出 平铺直叙和一览无余的弊病,缺少跌宕起伏的委婉韵致和意味深长的思索余地。对历史、时代的反思使他不再是直白的陈述与激情的宣泄,而是委婉地通过一些意象来启迪诗 思,营造诗歌的氛围。不是单一的抒情,而是深沉的思索,浪漫的想象让位于理性的反 思,政治豪情不再拒斥日常人情,革命激情在历史语境和生命的变换消逝中得到了沉淀 ,具有一种深沉的哲思意味,即使是一些仍具朗诵诗风格的诗作,在保持他一贯优势的 同时,也进行了别样的转换。如“再不是神话的梦幻/我的为你而生、为你而死的/祖国 ,我们已埋葬了/饥饿的胃和咯血的肺”(《我的祖国》)。李瑛在1990年代诗歌的情感 基调也由过去的光明、热烈转向凝重、沉郁,克服了过去清新有余、深刻不足的弊病。 诗情不是高昂的而是低沉的,在沉雄与沉郁的诗情之中,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悲凉和沉 痛。
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李瑛1990年代的诗歌,减少了以前经常用的夸张、排比、拟人 、简单的比喻、比附,而更精心于构造意象,且不同于过去那种简单直接的比附。意象 的自觉营造使得他的诗摈除了直白而更重暗示,摆脱了过去意义指向的单一性和直接性 ,而带来诗歌意义的多向性、丰富性以及意境的深远性,亦显现出诗人内心世界以及现 实世界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李瑛过去擅长运用“比喻”,通过比喻把世间最光辉、最崇 高的赞美都给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其主要目的“就是用在人物身上的比喻几乎都是用来 歌颂英雄战士的”、“更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比喻将自己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赞美的激 情深藏到诗里去”。李瑛过去最有代表性的比喻就是“树”的形象,他自言:“我以挺 拔的白杨喻英姿飒爽的女民兵,以坚强的青松喻北国勇敢忠贞的士兵,以红柳、沙枣、 白茨喻满怀豪情、扎根瀚海的青年男女,以灼灼木棉花喻南国士兵热烈豪爽的粗犷性格 ,我讴歌被风吹折的羊角树的顽强抗争精神,我礼赞战斗前沿胶林滴乳的奉献精神…… ”尤其是他的名作《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更是以树写人的典范:“我写了一棵树,实 际是写了一个人,一个胸怀远大理想,对人民至死不渝、肯于无私奉献的人的形象,一 个战士的形象,一个革命者的形象。”由此可见,他的修辞体系是直接的一一对应:“ 树”——“人”——“精神”,无论“树的形象”如何变化,如何铺陈升华,诗人总能 百转千回地与所要歌颂的“人的形象”(战士、女兵等)联系在一起,结尾所谓的“卒章 显志”不过是为了阐明早已规定好的某种“精神”或“理念”而进行的所谓“升华”或 “提升”,这其实是李瑛同时代诗人共同的诗学追求。
总之,充满人性人情的生命意识、深沉的历史感、执著的现实情怀与浓厚的现代意识 构成了李瑛1990年代的总体诗歌特征,它不仅代表了李瑛本人的创作蜕变,也代表了一 代诗人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创作提升。同时,李瑛过去的诗学追求及其成功并不是一种 孤立的个体现象,而是暗含了建国后30年整个诗坛的全部状况,也典型地代表了与李瑛 同时代诗人诗学道路的主要走向。当然,1990年代的李瑛尽管在诗歌创作上进入了一个 新的境界,但似乎作者的诗歌观念还有待进一步走向自由境界,其诗歌作品虽多有珠玉 ,亦不乏瑕疵。比较而言,《生命是一片叶子》的“人间拾叶”辑里似有一些应景之作 ,个别诗歌情感高昂却有矫情空洞之感,一些诗歌的格式单一,诗味仍嫌清淡,内容也 流于平庸。我认为,李瑛作为一个曾被时代洪流裹胁的、年已古稀的主流诗人,相比他 的同时代人而言,最可贵的是他的超越精神——创作上的超越、精神上的超越和对时代 的超越,只有在这种超越中,他的诗性与理性、历史感与现实意识才能更好地体现在作 品中,诗中所传达的历史沧桑感与沉重感,对自我生命的反省与沉思才更为凝重深刻, 其思考人类与宇宙时才能抵达更为开阔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