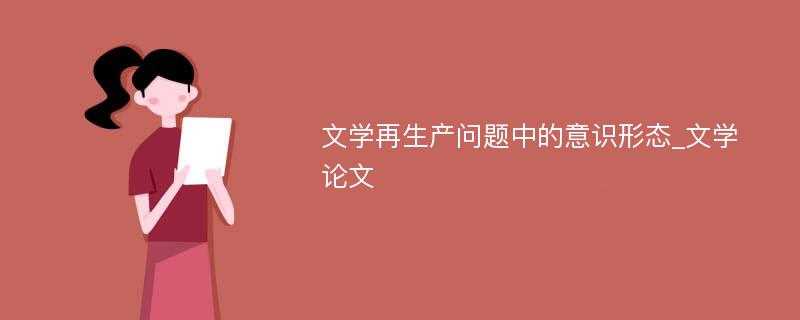
文学的再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了”。这句话几乎成为传统现实主义被奚落的标签式话语,一个漫画式的标签,幸好这位夫人是不存在的,受嘲弄的不是这位夫人,而是经常在笔下写到侯爵夫人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以前几乎很少被人置疑,虽然各种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定义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但是普遍认为这种关系之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经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这种曾经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早已不是天经地义,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经过现代思想的洗礼,侯爵夫人五点钟不再出门了,也不再有人被冠以侯爵夫人的称号。然而,即使在现代作品中,各式各样的人依然在某个时刻出门,不管他是马尔多罗①还是杜蓬②。一方面,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对现实的再现(représentation),另一方面,曾经彻底否认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先锋派思想也没有成为一种共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自柏拉图以降,关于文学再现的问题就从未停息争议。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始终强调他们在认识论上的优势,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意义。巴尔扎克就宣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记录员:“无论什么时代,叙事人都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主题完全虚构,与任何现实远近不着边的书,大部分是死胎;而以观察到的、铺陈开来的、取自生活的事实为基础的书,会获得长寿的荣光。”③为了再现真实,现实主义文论普遍重视细节的描绘和刻画,巴尔扎克说:“小说如果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④而细节的真实不是为了炫耀描写的技巧,而是为了表现对生活本身的忠实,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通常都是为了确定小说中主人公的环境,那些细节的描写决不是文字上的装饰,相反对于叙事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人批评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环境描写过于累赘冗长,卢卡奇为他辩护说:“巴尔扎克底环境的描写从不仅止于赤裸的描写,而几乎总是转化成行动的……描写之在巴尔扎克,只不过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底广阔的基础,为了把戏剧性的因素引导进写作之中来。巴尔扎克底那些非凡的形形色色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假如他们的环境不是如此地细节的表现出来,他们绝不可能以这样的戏剧的效果发展下去。”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相信“真实性”是文学必然的追求和价值,通过对现实的描绘,作家把真实的世界展现在作者面前,并且进一步表现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现实主义文论在二十世纪所遭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二战以后,在文学领域发生了一次语言学转向,文学从面向世界变成面向语言。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同构关系受到强烈质疑,法国的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与现实之间没有一致性,也不可能通过文字来表现现实。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封闭结构,使用语言的文学不可能表现世界,它应该专注于书写本身,而不应该“假装”表现真实。“真实描写”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某种“真实性效果”,而非真实世界的再现。里法泰尔在《文本生产》一书中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得出的结论是:“当文本不仅仅显得像是真的,而且可以验证其准确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种准确性的感知也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我们欣赏巴尔扎克的心理描写多么细致入微,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与他的一样”⑥。因此,考虑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对文本的考察只能把文本放在文本身处其中的语意系统之中。”⑦
语言学转向使文论更关注先锋作家和超现实主义等拉开文学文本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距离的文学作品,而现实主义文论也试图把文学价值已经得到承认的作品纳入到自己的领地,因为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就要么必须承认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文学理论,要么否定这些艺术家的价值。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加洛蒂(Roger Garaudy)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他把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都划归现实主义艺术。实际上,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由此得出两个结论:没有非现实主义、即不参照在它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现实的艺术;这种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不考虑作为它的起因的人在现实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极为复杂的。”⑧
结构主义之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论在理论上受到了极大挑战,各种新理论新分析方法层出不穷,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目前大部分小说最主要的写作手段还是现实主义的,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被忽视和抹杀。虽然巴尔扎克似的描写已经不多见,但是“真实”问题依然重要。法国新小说的旗手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曾经说:“所有作家都想成为现实主义者。没有任何人自认为是抽象的,处于迷雾般的幻觉幻象之中……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可以使不同小说家对立起来的界定清晰的理论;而是一面大旗,今天,在这面旗子下围绕着绝大部分小说家,假使不是全部。”⑨
关于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文论史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彻底否定文学与现实世界之关系,一个则是认为一切文学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是各种折中和调和的说法。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地澄清和梳理。文学中是否再现现实这个问题,到底属于对事实的认识,还是对一种写作方式的评判?历史上的各种文学观,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再现这个概念都常常把本体的问题和风格的问题混为一谈,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形成了一个短路,从而遮蔽了这些判断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用模仿(mimésis)概念来讨论再现这个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赋予模仿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在第三卷中,模仿指的是一种诗的风格,类似我们所说的直接引用,与叙述(diégésis)相对立,其意思是,如果诗句实际上是以人物的角色在说话,那么此时诗人似乎在模仿他的人物。“但是如果诗人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么模仿便被抛弃,他的诗篇就成为纯纯粹粹的叙述。”⑩在此处,模仿是与叙述相对立的叙事方式。以这种分类为基础,柏拉图把诗歌和故事分为两种基本体裁:一种是模仿,以悲剧和戏剧为代表;另一种是抒情诗。而史诗则常常是两者的混合。在第三卷中,柏拉图所说的模仿是同质性的,悲剧中,演员模仿人物,也就是说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从性质上来说是相同的;而在史诗中,诗人的语言模仿人物的语言,这种模仿可以说是一种同化的行为(identification)。
然而,在第十卷中,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成为诗的本体,是诗歌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任何描述外部世界和人物的语言都是模仿,包括前面所说的叙述也是模仿之一种。与同质性模仿不同,这里所说的模仿是异质的,模仿者是语言,被模仿者是人物和事件,诗人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描绘成为模仿行为,不管是直接引语还是叙述,都是模仿。在柏拉图眼中,诗歌无可避免地成为对现实的拙劣模仿,永远与现实隔着三层。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他以“床”为例,首先是自然的床,它是床这个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的形式,只可能出自神的创造;现实世界中由工匠制作出来的床是对“自然的床”的模仿。而画家的床只不过在模仿事物看上去的样子而不是事物实在的本身,因此画作是对影像的模仿而不是对真实的模仿,跟真理隔了三层(11)。
柏拉图关于模仿的讨论最终落脚在伦理学,他对诗人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他们不与诗歌中的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关于这些事务的正确知识,因此他们的话都是不正确的,只不过是假装表现其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但是,如果他们与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再是诗人。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既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篇对话中,模仿具有双重的涵义,而柏拉图却没有加以区分。第一个涵义:诗人模仿现实事物如同画家,比如说画一张床;第二个涵义:诗人模仿其他人,让我们看看柏拉图对荷马的指责:他虽然从未真正统治过任何城邦却以一个统治者的方式说话,虽然从未制定任何法律,却以立法者的方式说话(12)。因此,当他批评荷马的诗远离真实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荷马对政治、战争和教育等公共事务缺乏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所说的话远离真理;另一方面,荷马本人与那些在特殊领域具有真正知识的那些人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柏拉图对诗人和画家所作的对比,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根据柏拉图对模仿的定义,画家虽然模仿工匠所做的床,但是并不能说画家模仿工匠本人。画家的工具是笔和墨,而工匠用的是斧头和锯子,因此柏拉图并不指责画家模仿工匠。然而,诗人与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对一切人都是共通的语言,诗人与他们的模仿对象有一种本质上的类似性,于是在柏拉图眼中,诗人不仅仅模仿对象,而且使自己变得像被模仿的对象,形成一种双重的同化。这种双重的模仿实际上使诗人完全成为诗歌所描绘的世界的附庸,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眼中,并非诗人创造了诗歌所描绘的世界,而是诗歌的世界创造了诗人,一个纯粹的依附者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柏拉图对模仿问题提出的两种不兼容的定义分别属于风格和本体,它们所引发的伦理学思考实际上规定了后来者在这个问题上讨论的范围。柏拉图在第三卷中从风格的角度来看问题,诗人可以进行选择,对于诗人而言,模仿是一个主动判断的结果,诗人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进行模仿或者不模仿。他要求诗人为了城邦公民的教育,放弃模仿性的直接引语,选择叙述。但是,在第十卷中,从本体的角度来看,诗人则无法进行选择。“诗是模仿”,这个命题的反命题是:非模仿者即非诗。出于反对模仿的伦理要求,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里全部驱除干净,即使伟大的荷马也不例外,因为诗人不可能不是模仿者。然而,后来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把风格问题和本体问题混杂在一起。
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如果模仿属于风格的范畴,那么这就是文学的内部问题,作家根据其伦理或美学的判断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抉择。如果模仿属于本体的范畴,实际上这就成为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实质是探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学之外的世界处于何种关系。因此,前者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学内部的实践问题:模仿是好的文学还是不好的文学?后者则更多的属于认识论问题:文学是不是模仿?然而在后来诗学和文学理论的讨论中,无论是模仿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是与非”和“好与坏”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却常常纠缠在一起,似乎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推论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再现说进行了辩护,让我们看看他对悲剧的著名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3)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同化(identification)不是现实性的,而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诗人所再现的不是现实中的“行动”,这个行动只在“想象”中存在,“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4)对比上面引述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历史学家所作的才是真正的模仿,他们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诗人模仿或再现的对象并不是事实,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它是虚构的。实际上,诗人的话语能够再现的仅仅是它本身而已,因此,与其说是再现(representation),不如说是自我再现(auto—representation),而此处的re-其实只是一个虚拟,因为它本身就是首次出现的,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事物。因此很自然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是真的模仿吗?抑或仅仅只是做出模仿的样子,打出模仿的旗号?安托万·贡巴尼翁指出:“《诗学》所关注的从来就不是被模仿或再现的事物,而是模仿者或再现者,也就是说再现的技巧,情节的组织。”(15)
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到底是什么?首先,对于柏拉图来说,文学的性质和目的就是模仿,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模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引发怜悯和恐惧并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其次,模仿符合因果律,是可能发生的,而且这种可能必须符合观众的心理,情节发展的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16)最后一点,也是从文学本体论来看最重要的一点,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有考虑过文学是有可能不再现现实的,无论是伟大的索福克勒斯和荷马或者三流诗人,他们的诗句必然是对现实的再现,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再现是否美,是否能够打动人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诗学》的根本问题并非模仿与被模仿之间的关系,而是模仿者的组织安排问题。
在此处又出现了一个悖论,显然这个悖论与前面说过的那个“悖论”具有某种一致性。我们知道,客观的现实世界是绝对唯一的,倘若文学是现实世界的再现,那么所有的文学就应该再现相同的事物,在同一个文化现实中,文学就应该只有一种。幸好文学并非如此,而是如星光般繁多,如春花般异彩。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意味着文学不是对这个唯一的世界的模仿,它的来源是人的多样性,千差万别的人类心灵才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学。这种差异和多样性是我们对文学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因为只有面对有差异的事物,美与丑、好与坏的判断才有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此处落入了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悖论陷阱:一方面,他肯定文学是对唯一存在的世界的摹仿,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种文学;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文学是有差异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如何创作好诗)对他自己给诗所下的定义构成了某种挑战。
很显然,文学(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就是戏剧和史诗)并不是再现(représentation),它只是做出再现的样子,让观众进入角色,通过观摩虚拟的事件使心灵得到净化(katharsis),这种制造真实性幻觉的手法后来被罗兰·巴尔特称为“真实性效果”(l'effet de réel)(17)。根据现代语言学理论,作家使人相信他之所言为真的种种方式都不过是幻觉而已,它的有效性依赖于约定俗成的理解(convention),而不是与客观世界的符合。菲利普·索莱尔斯在《小说与极限经验》一文中写道:“所谓现实主义……这种偏见就是认为一种写作应当表现某种事物(其实本来不是如此),关于这件事物所有人能够马上形成一致意见。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共识仅仅只是出于约定俗成,现实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约定俗成的,是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所达成的默认的协议。”(18)这个定义很明显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只不过后者认为语言对于现实来说是任意的,而前者认为写作实际上对于现实来说是任意的。先锋派从这里出发,寻找自由的文本,他们不愿意受任何外在事物的限制,把语法、逻辑、描绘等等统统扔到垃圾堆。他们认为,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语言本身,而用语言再现外部世界被视为对语言的工具化利用,先锋派对此绝不容忍。在《批评与真理》中,巴尔特说:“作家不能用社会角色或价值这样的概念来定义,决定他们的只能是某种对语句的意识。作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把语言视为问题,感受语言的深度,而不是其工具性或美。”(19)语言转向自身,从而拒绝指向外部世界。根据雅格布森对语言功能的分类,语言问题被区分为六个要素:发出者(destinateur)、接受者(destinataire)、环境(contexte)、信息(message)、接触(contact)和编码(code),针对环境的功能是意指(dénotative),而专注于信息本身的是“诗性”(poétique),也就是说审美(20)。根据这种分类,文学价值最大的语言也就是最关注诗性功能的语言,从而最大程度地排除对环境的指涉。先锋派基本上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强调文本与现实的异质性,他们对文本本质的认定也立即形成了一种价值判断:远离现实的文本才是真正的文本,也就是优秀的文本。
面对现实这个问题,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体系,表面上看它们都是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出发:第一种认为文学就是对现实的再现,那么当然它越具有真实性越好,这种文学必然更加具有活力和感染力,这种文学标准在叙事文学中尤其突出,苏联的文学和中国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把这种标准视为唯一的标准。第二种认为文学再现现实不过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幻觉,因此要求文学远离约定俗成的习惯,也就是说,在文本与现实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这样的文本才具有足够的含糊性,从而摆脱现实世界的桎梏,转移到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上来。因此根据这种文学观,文本的审美性与是否符合外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应该摆脱现实的控制,走向语言的自由,使文本具有生产力,优秀的文本是能够自由生成的文本,它的作用是能够不断生发的意义生成(signifiance),而不是表达确定的涵义(signification)。
在这一系列的理论斗争中,我们看到关于文学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人们要确立文学的性质(这个性质是普遍的,对一切文学都有效),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这个性质的认定来对具体的文学实践进行价值判断。再现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再现,那么是否再现就成为文学是否好的标准;而文本理论把文学定义为非再现,那么离再现的距离是否足够远则决定了作品是否好。然而,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并没有任何必然性,而且也不应该有必然性,因为任何必然性都将取消选择的可能,而选择的可能性是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这两种思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假设再现理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切文学作品的性质都是对现实的再现,那么任何作品都再现了现实,不存在没有再现现实的文学作品,因为倘若没有再现现实的话,它就被排除在文学之外。那么,在文学的领域内部就不可能以是否再现作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没有再现现实的文学是不好的文学”,而是“没有再现的文学不是文学”。同样的,如果文本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文学无法再现现实,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理由批判现实主义,因为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与所有的其他的文本一样不再现现实,也与现实无关,那么文本理论就没有任何理由排斥现实主义。
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学理论都是从对文学事实的认知出发来决定他们文学实践的选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路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判断上的“短路”。对文学实践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来自对文学事实的认知,因为根据我们在前面确立的逻辑,文学的价值既不能取决于为对现实的再现,也不能取决于对现实的非再现。因为一旦被指定为对存在之事物的定义,就不能再被确定为一种价值的选择,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是不兼容的。然而在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中,这种短路却常常发生:一旦文学被定义为对现实的再现,那么再现是否好则决定了作品是否好;一旦被定义为非再现的文本,那么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是否大则决定了作品是否好。
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的短路?为什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类短路的判断背后,有一种范围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决定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文学话语的再现问题上,表面上提出的问题是“文学是否再现现实?”而实质上,这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再现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对现存话语秩序(l'ordre du discours)的态度。
我们首先分析再现论的文学观。再现论宣称自己再现现实,然而实际上他们所描绘的是“可信的”,而不是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因为,所谓被模仿的事实只是在假设中存在,文学的故事和情节都是虚构。有权利对是否“可信”进行裁判的不是现实世界(世界是无声的),而是读者或观众,只有他们能够将“虚构”与“现实”进行对接,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不是“真实”,而是“可信”。因此,“再现”的游戏转换为满足大众对“可信性”判断的游戏。一个所谓“忠实表现现实生活”的文本必须要满足如下条件:首先是因果律,情节的发展必须是符合因果规律的,能够被常识所理解。这种因果律主要不是符合物理定律意义上的因果规律,而是符合政治、社会、伦理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实际上仅仅存在于人们对个人行为的社会想象之中。也就是说,在叙事作品中,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不能超出可以理解的范畴,不能超出社会所能够容忍的规范。作品所激发的情感应该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在哪一点上都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发怜悯或恐惧。”(21)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麦克白被妻子煽动起巨大的欲望,并最终被这欲望的激情毁灭,在这个故事中,与其说麦克白丧身于离奇的命运(女巫的预言一一得以实现),毋宁说他丧身于当时的政治伦理的结构。在这部戏剧的表层叙述的是一个人物的激情的毁灭史,而深层结构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王权政治制度肯定,莎士比亚用讲故事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了政权的合法性。通过政权的失去(篡位)——回归(正统复位)的表象,政权在象征意义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任何针对王权的欲望都被这部戏剧预先判决死刑。
其次,在这种社会性的想象中,个人的欲望被压抑。雷奥·伯撒尼在《现实主义与对欲望的恐惧》(22)中指出,现实主义文学通常都表现出对个人欲望的压抑,人的欲望被整合到由情节或“人物命运”所表现的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一方面,凡是没有得到社会承认的欲望都被挫败,另一方面,这些欲望都被置人社会的某个固定的区域,加以分类,并最终在象征系统中得到控制。以拉辛的戏剧为例,虽然其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常常破坏了主人公的生活,但是主人公的性格却被这激情固定下来,其行为完全遵从这种固定下来的情感。他们的感情在舞台上被分类,构成某种特定的“人格”,这种人格与某种行为类型紧密结合在一起,被安放到社会类型的某个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局部的混乱其实不过成为构成整体和谐的工具而已。这些类型化的激情表现与其说在展现激情,不如说表现了这个社会如何通过戏剧这种象征手段如何克服激情,让理性获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局部叙事被整合进入宏伟叙事,个人的小故事成为总体叙事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文学常常被用来介入现实,宣传改造现实的思想,一方面它可以批判现实的阴暗面,从十九世纪以来,无情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就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表达对未来新社会的理想,或者直接描写革命行动本身。然而,在这些批判性的文学作品中,个人却常常成为现存秩序的牺牲品,个人的欲望在与社会的交锋中通常都败下阵来。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他的个人奋斗最终抵抗不过当时的社会秩序,他的死成为欲望失败之象征的祭品。宏观叙事的力量压倒了个人的叙事,于连的微观的个人反抗无法改变宏观的社会运转方式,虽然这部作品本身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和批判,然而它却依然肯定了宏观叙事本身的力量,反抗的意义和于连一起走上了绞刑架。
描写革命的文学作品有两种,一种是在革命成功之前,例如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一些青年作家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并且在苏联革命成功的鼓舞下,写作了反映中国革命的小说。虽然这类小说对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且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了实际的抵抗行动,但是这些革命者的行动却同时受到另一种秩序的支配,这些行动被整合到未来的政治框架内,虽然这个政治秩序还不是现实,但是它已经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小说中的激情与其说是个人的感情,毋宁说是想象中的社会新秩序的激情,是一种属于宏观叙事而不是个人的情感和欲求。另一种是革命胜利以后,对过去的革命行动的追认,例如苏联和新中国建国以后出现的大量革命文学,其实质是对现存秩序的进一步确认,新政权或者新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旧政权或制度的否定之上,这种否定的基础实际上是对现存秩序的肯定。
因此,所谓现实主义并非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对当下的或者想象中的社会秩序的“肯定”,这种秩序经由某种宏观叙事表现出来,现实主义叙述的“真实”意味着这种话语能够被整合进入这种宏观叙事,并且得到阐释,所谓的真实性所指的并非忠实反映现实世界,而是局部微观叙事与整体宏观叙事之间的符合程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通过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他的小说对“物”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个问题。在他的《橡皮》中,有一段对一块切开的西红柿的描写:
四分之一块西红柿很完整,是机器从一个完全对称的果实切下来的。密实的果肉均匀一致,有一种漂亮的标准的红色,非常规则地分布在放光的表皮和许多籽所处的内室之间,这些黄色的籽按照大小有规则地排列,沿着鼓起的中部,裹在一层稀薄的绿乎乎的浆液之中……在上部,发生了一个肉眼难以发现的情况:有一小块皮与果肉分开,微微翘起一到两毫米。(23)
这一段关于西红柿的描写长达三个自然段,横亘在小说中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段描写在小说中能够起到的作用,它仅仅在那里,无法找到这段描写的“可理解性”(24),任何宏观叙事都无法纳入这个段落。虽然这位“新小说”作家在描写事物的时候更遵守客观的要求,更强调准确性,但是这种描写却不能被纳入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而是反现实主义。新小说反对巴尔扎克的手段并非拒绝描写——细致的描写是巴尔扎克的典型风格,而是用令人不习惯的精确方式进行描写,这些描写使文本与人们对现实的常规想象相对立,巴尔特评论罗伯-格里耶的时候说:“瓦雷里说,哪个神灵感说他的信条就是:我让人的期待落空。而文学似乎应该是这样的神灵;也许有一天人们会把文学形容为使人的期待落空的艺术。”(25)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再现”的要求与意义并不取决于文本与外在现实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文本与读者对现实秩序的想象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特瓦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为语言革命提出了一个目标:通过改造语言来改造历史发展的主体,从而实现社会变革。主体(人)在语言的革命中拒绝被资本主义现存的象征系统所奴役,文本实践在这场伟大的进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她把文本区分为“现象文本”(phénotexte)和“生成文本”(géno-texte),根据她的分类原则,再现性的文本都属于现象文本,符合语言的规范和语意规范,不规则的冲动被压抑,从而丧失了实践性。而生成文本则充满意义的生成(signifiance),是“唯一的冲动能量的传递方式,它组织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体还没有因为被象征系统占据而成为一个越来越黯淡的分裂的整体,在这个空间中,主体虽然处于生理和社会结构的限制之中,依然通过开辟路径和标记而自我生殖成长。”(26)她认为只有少数先锋派文本达到了这种无限生成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地抗拒社会秩序的结构的控制,也就是说这些文本所起到的作用不是把自己纳入大叙事的象征系统,而是体现出对整体象征秩序的一种反叛(transgression),在这种反叛之中,文本抵制任何把它自身进行合理化的努力,它总有一些欲望(个人性的身体因素)隐匿其中,任何社会秩序和话语秩序都不能容纳这样的成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才能被视为纯粹的实践。罗兰·巴尔特在对“现代文本”的定义中说到:“判定文本的标准,至少就某个独立的方面来看,取决于它是否被高贵的、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规范是在学校、批判和文学史中确立的)所拒斥和贬低……”(27)文本是在意识形态以外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攻击和反叛的实践,这种实践的目的并非试图用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而是制造无法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实践,并且在这种绝对的反叛中感受到狂喜(jouissance)。
文本什么也不“再现”,除了它本身,不愿意指向任何其他的东西,然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表意功能成为这种文本观的障碍,在这种文本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融合,而是斗争。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极端重要的那个“re-”,对文本来说却成为某种必须去除然而又无法去除的污点。巴尔特在对安德烈·马松以字母做画的评论中说:“如果书写要显示出真实的自身(而不是作为工具),那么它就必须是不可读的,字母画家(马松)通过巧妙的设计,精心设计出不可读:他把书写的冲动从交流的形象(可读)中提取出来。”(28)所谓不可读,意味着文本无法被纳入整体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之中,从而构成对话语秩序根本性的反叛,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用一种新的话语秩序取代旧秩序,而是无秩序。文本的乌托邦是由空白的词语构成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是否“再现”这个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问题,但是其真正的关键是隐藏在事实判断之后的伦理和政治意识,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之根本正是在此,柏拉图认为“再现”式的戏剧刺激了人的感情从而破坏了理性的控制,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通过再现悲剧性的情节,可以激发“正确”的感情,从而维持社会合理化的感情关系。先锋派要求文本拒绝“再现”,转向语言内部的封闭,也是为了反抗话语的秩序,反抗被巴尔特称为“神话”的意识形态背景。虽然“再现论”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都试图把“再现”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某种真理性根据,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面对话语秩序的态度,这并非一个单纯的认识论的抉择,而且还是伦理性和政治性的抉择。
注释:
①洛特雷阿蒙的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中的主人公。
②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中的主人公。
③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袁树仁译,载于《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367页。
④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言》,丁世中译,载于《巴尔扎克论文学》,同上,第264页。
⑤卢卡奇:《叙述与描写》,吕荧译,上海:新新出版社,1947年版。
⑥⑦Michael Riffaterre,la Production du texte,Paris,Seuil,1979,p.25; p.82.
⑧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第175页。
⑨Alain Robbe-Grillet,Pour un nouveau roman,Paris,Minuit,1941,p.135.
⑩(12)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93c;600。
(11)因为工匠制作的床本身就是模仿,所以画作是模仿的模仿。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同上,595——599。
(13)(14)(15)(21)亚理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449b;1451a—b;1451a;1452b-1453a。
(15)Antoine Compagnon,Le Démon de la théorie,Seuil,1998,p.119.
(17)Roland Barthes,L'effet de réel,Communications,Ⅱ,1968.
(18)Philippe Sollers,Le roman et l' expérience des limites(1965),Logiques,Paris,Seuil,1968.转引自Le Démon de la théorie,同上书,pp.111-112.
(19)Roland Barthes,Critique et vérité,Seuil,1966,p.35.
(20)参见:Roland Jakobson,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i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inuit,1963.
(22)Leo Bersani,Le réalisme et la peur du désir ,paru originellement dans Poétique,avril 1975,repris dans Littérature et réalité,présenté par Todorov,Tzvetan,Seuils,1982.
(23)Alain Robbe-Grillet,les Gommes,Minuit,1953,p.161.
(24)巴尔特曾经在《真实性效果》一文中提出现实主义作家有可能提到一些似乎没有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证明小说是“真实的”,比如福楼拜在《纯朴的心》中提到的气压计。很明显,《橡皮》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段描写明显不属于一个日常生活中细节的观察,他使用的是“科学语言”,排斥了日常性。
(25)Roland Barthes,Le point sur Robbe-Grillet,in Essais critiques,Seuil,1964,repris dans Oeuvres complètes,Seuil,1993,tome I,p.1321.
(26)Julia Kristeva,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Seuil,1974,P.83.
(27)Barthes,Roland,Texte(Théorie du),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Paris,1989.
(28)Barthes,Roland,Sémiographie d' André Masson,Critique,mai,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