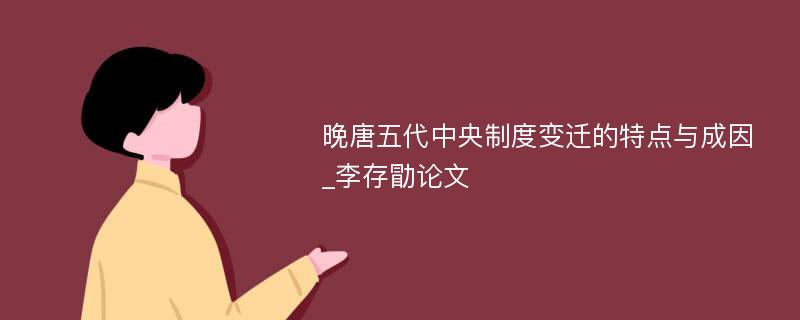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中枢论文,渊源论文,体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1]中枢体制中君相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相对于君权的稳定,宰相则是中枢体制中变动不居的部分,因而古代不同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宰相(宰辅)制度的变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而定型于隋唐之际的三省制,长期以来成为解释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框架。尽管有学者早就意识到仅至高、武之后,唐代政治体制就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阐释框架上仍无法摆脱三省制之窠臼,将唐代中枢体制看成是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将唐代的三省制分为长成、挫折、完成、破坏和转型五个阶段加以论述。参见孙国栋:《唐宋史论丛》(增订本),83-18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王素以《唐初三省制的确立》和《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两章论述唐代中枢体制的变化,主线即是三省制的酝酿、建立和破坏。参见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更有甚者,有学者以三省制为中心,将魏晋南北朝看做“三省的出现”、隋唐为“三省制的全盛时代”、两宋为“三省制的衰落”[2],浑然不顾隋代以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典型的三省制实际上仅存在数十年这一历史事实。
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新三头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枢体制的演进。袁刚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3]刘后滨先生对“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两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因而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4]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一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其设置及其演变,两《唐书》、两《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中虽都有零星记载,但皆未及详考,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演变始末始有简单总结,距枢密使之创置已是数百年之遥。中日学界对于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数十年来也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对于枢密使出现的时间、人员、职能以及它在唐代中枢体制中的作用和对中晚唐政局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注:参见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つ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3,27-32页,1953;《唐代枢密使制の发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4,41-48页,1954。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唐史论丛》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载《文献》,1991(2);王永平:《论枢密使和中晚唐宦官政治》,载《史学月刊》,1991(9);袁刚:《唐代的枢密使》,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5(43);罗永生:《晚唐五代的枢密院和枢密使》,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大学学报》,1993(4),1,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载《中国史研究》,1998(3)。)尽管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书通进始终是唐代枢密使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
据宋代王明清记载,枢密院“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和因革》)因此,唐代枢密使出现后,其内廷枢务运行程序为:承表—进呈—(人主)处分—宣传—(中书门下)施行。[5]此一程序中,第一、二、四项由枢密使负责,并没有议政权与施政权。由此可知,唐时的枢密使以宦者担任,其基本职能只是承受表奏并保存文书而已。尽管在晚唐其权力曾几度突破其职能的界限,参与外廷事务,表现出职权扩大的表象,但这种扩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宰相权力的侵夺。正如《新唐书》卷二百七《严遵美传》所说:“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严遵美父子两代分别为宣、僖时期的枢密使,他对枢密使职能的描述自是非常可信。这种侵权是与整体上宦官权势的膨胀相表里的,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因而才会有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丙午的诏书:“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相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资治通鉴》卷二六二)这将枢密使的职责重新限制在承受文书的本职之内。因此,某段时期内宦官枢密使权力的一度扩大并不是枢密使发展制度演进的结果,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唐代的宦官枢密使尽管时有干涉中枢决策之举,但远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自然也构不成所谓的“新三头”体制。
朱梁代唐之后,朱温新设置了崇政院,以心腹敬翔为使。古今论者多以为崇政院乃是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今之学者多袭此说,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对后梁的崇政院都不甚措意。(注:学界对后梁祟政使做过专文讨论的,只有李郁的《唐末士人枢密使和后梁崇政使的设置及其影响》一文,参见《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实际上,后梁的崇政院并非简单的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后梁的崇政院合并了原有的枢密院并新增了“参谋议”的职能,但它与枢密院之专掌军政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6]
晚唐五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环节是后唐枢密院的建立。据《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条载:“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记载与此同。此后学者亦多认为后唐枢密院是直接继承后梁之崇政院而来。然而从职能演化的角度来看,后唐枢密院的建立与后梁的崇政院并无直接渊源。从职能上看,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梁之崇政院有着明显的差别。最大差别在于它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其主要的职掌是军政。
与崇政院主要参与谋议而少行事于外相反,后唐时期的枢密院广泛参与行政事务,尤其是军政事务,例如调发军队(《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元年八月内辰条》)、除授军职(《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主征伐(《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元年十二月壬子条》)、掌马政(《五代会要》卷一二,《马条》)等,实际上已经担当其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角色。武事归枢密院,文事归中书的职责划分在当时已经是为中书所认可,而不如晚唐那样是对中书权力的侵夺。例如,在后唐建立的第一年,即同光元年(923年)十一月戊申,中书门下请求省并官员,其中文官事务由中书门下负责,而武官事务则由枢密院负责(《资治通鉴》卷二七二)。从中书门下主动提出的这一动议中,我们看到中书、枢密院之间在当时的确已经有了职责分工。
后唐时期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另一表现是枢密院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文书。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梦溪笔谈》卷一,《故事》)枢密院之“宣”与中书之“敕”并行,在文书运行上体现了两者的对等地位。
沈括区分了三个时期的“宣”的不同含义,恰好也表现出晚唐枢密使、后梁崇政院、后唐枢密使三者之间职能上的巨大区别。从掌文书通进到分领政事,后唐枢密院实现了其职能上的一次巨大跨越,从而也促使中枢体制发生变化。后唐枢密院在职权的划分、文书制度的运行等方面已经初步制度化,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有制度上的保证并为时人所认可,后世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格局在后唐时期初步形成。
枢密使早在唐代中期就已产生,一直由宦官担任,至后梁时期改由士人担任。在此期间,其职掌与军政并不相关,也没有能够走向外朝。那么,何以枢密院在后唐时期会一跃而为最高军政部门,从而促成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新中枢体制的出现?如果后唐的枢密院职能非继承前朝而来,又是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后唐的枢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军政方面的领导权而与中书分秉朝政,其直接的渊源即是后唐原藩镇体制下所设置的中门使。
二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后唐庄宗、明宗以及后蜀时期的首位枢密使皆出身于中门使,因此后唐中门使与枢密使的渊源关系早就为学者所关注。[7]中门使缘何独独出现于庄宗建国前河东境内?(注:后晋、后蜀的中门使源自后唐殆无疑问,三国之外中门使的记载仅陆游《南唐书》卷一四《郭廷谓传》一见,由于系孤证,不取。)除了职位上的渊源之外,中门使的职能是如何影响了此后的枢密使,从而导致了五代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这是本文所关注的。
中门使一职仅见于五代十国时期,其渊源殊难稽考,以至于有学者猜测中门使是否为閤门使之变称。[8]尽管閤门使常有,而中门使不常见,但两职并备的例子并非没有。据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一四《十国百官表》载:吴有閤门使;南唐有閤门承旨、中门使;前蜀有閤门使、閤门南院使;后蜀有中门使;楚国有小门使;南汉有内门使。所以中门使应非閤门使之简单“变称”,如果仅从名字上看,其中中门使、小门使、内门使或许会有些渊源也未可知。
有关中门使的记载主要见于李存勖灭梁前的河东境内。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九月,安国节度使李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在《资治通鉴》此条记载中,胡三省特地标注云:“晋王封内,凡节镇皆有中门使。”(《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此晋王当为李存勖而不是李克用。据《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载:“崇韬初为李克修帐下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修卒,武皇用为典谒,奉使凤翔称旨,署教练使。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917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恳辞要职。先是中门使吴珙、张虔厚忠而获罪,知祥惧,求为外任,妻璚华公主泣请于贞简太后。庄宗谓知祥曰:‘公欲避路,当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这段记载提供了关于中门使的很多重要信息。吴珙、张虔厚应该是现知最早的中门使了。据《资治通鉴》卷二六六载,李克用临终,“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吴珙为李克用临终顾命之人,其身份为“大将”,则其为中门使“忠而获罪”显然是在李存勖为晋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中门使一职应该是始于李存勖。
那么,何以李存勖嗣位之后要在封内设中门使,中门使的职能又是什么呢?胡三省在安重诲为中门使条下曾指出,中门使“其任即天朝枢密使也”,显然是认为中门使系仿唐代之枢密使而设,故职任亦相类。欧阳修也曾经说:“中门之职,参管机要。”(《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再联系到中门使仿照唐制设员两员的做法,应该说胡三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中门使职掌中有与枢密使相同的部分,即典领机要、掌管文书之类,被委以中门使者多系亲信。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七月,太常丞曹允升上奏,请求禁止以随身仆使为中门使等职,其中有云:“使府郡牧,例以随身仆使为中门、代判、通呈等,名目极多,皆恃势诛求,不胜其弊,伏请特行止绝。如藩侯郡守不能书札,请委本判官代押。”(《全唐文》卷八四八,曹允升:《请禁府郡以仆使代书判奏》)可见,藩镇之中门使多由亲信担任,在掌四方表奏之外,又负有部分类似掌书记的职责。中门使的这种职能及其人选上的密迩性质,使得它经常可能作为主上的个人代表,负沟通内外之责。如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后晋大将杜重威决定降于契丹,召诸将署降表,即是令中门使高勋赍送敌帐。(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九,《杜重威传》)这种“内传外达”的功能与唐代的宦官枢密使沟通皇帝与宰相同样是极其类似的。
但更多的资料显示出,李存勖所设中门使的职责绝没有仅仅局限于居中管理机要文书,它还广泛参与机要之事,尤其是军政事务的谋划、决策与处理。
据记载,李存勖领卢龙节度使时,便是“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资治通鉴》卷二七○),实际管理军府之事;后晋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时,也是“军府事一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八一)。郭崇韬为中门副使乃孟知祥所荐。李存勖用郭崇韬为中门副使的原因在于孟知祥说郭崇韬“能治剧”。对于“能治剧”才能的重视,说明中门使不但要参与谋议,而且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事务。这些行政事务也主要是与军政相关的事务。如孟知祥为中门使时,“庄宗与梁祖夹河顿兵,知祥参谋应变,事无留滞”(张唐英:《蜀祷杌校笺》卷三,《后蜀先主》)。可见其“事”主要便是兵事。及孟知祥避位,郭崇韬为中门使,“艰难战伐,靡所不从”(《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李嗣源镇邢州,以安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郭、安为中门使时,所处理的主要是征伐之事,所谓“艰难”、“勤劳”,足见军政事务之繁。
饶有兴味的是,后唐建国后,由中门使转任为枢密使,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有两位中门使,马绍宏和郭崇韬,前者资格更老。史言“庄宗即位,二人当为枢密使”,马绍宏自己也认为“合当枢密任”。郭崇韬也知道马绍宏可能成为枢密使,而且在自己之上,于是趁着马绍宏刚由幽州召回的机会,荐张居翰为枢密使,挤掉了马绍宏。(《旧五代史》卷七二,《马绍宏传》)由此可见,后唐时期由原河东集团所特有的中门使所转化来的枢密使,其职能与地位也必然是中门使的一脉相承,并进而扩大之。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后唐和后蜀的枢密使会在甫一建国便拥有唐代的枢密使和后梁的崇政院使所没有的专行事于外的权力,特别是军政方面的权力。
同郭崇韬、安重诲一样,由中门使而枢密使的还有后蜀的首任枢密使王处回。王处回为孟知祥之亲信,起家中门副使,孟知祥称帝后,擢枢密使。(《十国春秋》卷五二,《王处回传》)王处回一开始便已担当了掌军政的重任,在后主后期进而领兵,直接掌握军权。孟知祥建国后数月而卒,后主孟昶即位。据《十国春秋》卷四九载,后主明德元年(934年)九月甲寅,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求判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李仁罕手握强兵,为后蜀初期之实力派。欲求判六军,而需先通过枢密院,可见枢密院实掌军职之除授。像判六军这样的重大任命,一般都是由皇帝与枢密院商议,然后翰林学士院草麻。兵将的派遣也出于枢密院。广政十年(947年)三月癸巳,翰林承旨李昊请枢密使王处回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将兵急攻凤州。(《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同年十二月丙戌,后主遣雄武都押牙吴崇恽以枢密使王处回书,招降凤翔节度使侯益。(《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蜀时期的枢密使因为与中书分秉兵政和民政,故而已经与宰相一起被统称为“执政”。(《资治通鉴》卷二八八)
孟知祥与后唐渊源极深。孟知样本为河东旧人,在后唐建立之前就做过李存勖的中门使。后唐灭梁,继孟知祥为中门使的郭崇韬转而为枢密使,而后唐的枢密院已经是掌军政的机构。孟知祥建蜀后所任命的首位枢密使王处回经历与郭崇韬类似,也是先为中门副使,迁正使,后为枢密使。王处回的经历表明,后蜀时枢密院掌军政的职能并非凭空新增,而是同后唐的情况一样,直接来自于此前的中门使。
让我们再回到李存勖首任中门使吴珙的例子,对中门使设置原因做一推测。史籍中关于吴珙的记载并不多,但其身份为李克用所亲信的大将则无疑。李克用临终顾命之人五,有其弟李克宁、监军张承业、掌书记卢质,而大将李存璋、吴珙两人则是军队中的亲信。此后,张承业剪除李克宁,靠的也正是李存璋、吴珙两人的军队。吴珙身为大将,手握军队又忠于李氏,此后出任首任中门使,可以推知,其职能显然不会限于唐代枢密使的文书表奏之职,而必与军务相关。倘非如此,单纯的掌管文书,吴珙是不至于“获罪”的。再者,如果李存勖单纯以中门使为唐枢密使之任,则曾在晚唐枢密院任职的宦官监军张承业才是不二人选。考虑到彼时正是朱全忠篡唐的第二年,而梁晋怨深,存勖志在灭梁,中门使之设恐怕正与此种形势下欲加强军事上的领导有关,此后的中门使孟知祥、郭崇韬在军事上的优异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
如前所述,李存勖意在仿唐制而设的中门使在继承了枢密使的基本职能的同时,又与自己本镇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结合,赋予了它掌握军政的新功能。当庄宗灭梁,化家为国,原先的藩镇体制转化为国家体制,中门使也转化为枢密使,从而开启一代新制。此时的后唐枢密使制度较之于唐代枢密使制度已经是旧瓶装新酒,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后唐枢密使继承了唐代枢密使掌文书通进这一基本职能。据《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载,天成元年后唐平蜀后,明宗遣中使凭敕书往诛王衍一行,“已印画,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正因为枢密使掌握文书传达,张居翰才有机会改动诏书。另一方面,在新体制下的政务运行上,中书、枢密分掌民政、军政,对掌文武,同时又一起作为皇帝的最高顾问集团而共同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旧五代史》卷三四,同光四年三月丙子条)作为一个顾问整体,他们一起被合称为“执政”(《旧五代史》卷三四,《崔协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后唐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中书、枢密分掌文武、共议国政的二府体制。这种格局也为此后的晋、汉、周所继承,其间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至北宋前期,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
宋人话语中通常将枢密院掌军政看作是对“事无不统”的相权的分割,是太祖、太宗防弊之政中的一环,并奉为“祖宗之法”(《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而遵循。有的学者业已习惯了将枢密使掌军政以分宰相权看作是二府制的本质特点,是不证而自明的,并以之作为自己研究的前提。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以整个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枢密使制度的演变为着眼点考察唐宋之际中枢体制变化的过程就会发现,五代时期实是晚唐至北宋前期中枢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始创于唐代中后期的枢密使制度没有延续类似汉代尚书从皇帝私臣到外廷宰相的演进之路,而是随着后唐庄宗灭梁发生转向,成为掌握军政的外廷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从而导致唐代中后期以来的中书门下体制发生变化,以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中经中书门下体制的演变,转变为五代宋以来以职事分工为特征的二府制。
标签:李存勖论文; 枢密院论文; 孟知祥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旧五代史论文; 十国春秋论文; 五代十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