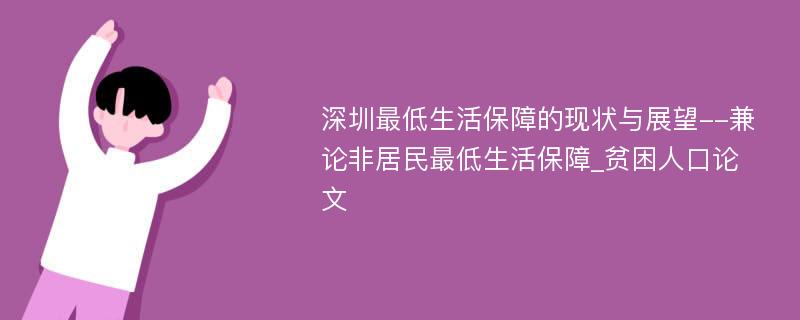
深圳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和前瞻——兼论非户籍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低生活保障论文,深圳论文,户籍论文,现状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圳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特点
深圳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是深圳常住户籍人口(包括农村户口),即实行属地原则。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分为特区内、特区外城镇、特区外农村3个档次,并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应调整。1997年,特区内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205元,特区外城镇是170元,特区外农村是120元;1998年,上述3条保障线分别调至245元、210元、150元;1999年,按照国务院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30%的要求,深圳市把3条保障线分别提高到目前的319元、273元、195元。另外,特区外的宝安区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在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实施解贫脱困计划,即城镇户口的居民家庭月人均收入不足400元、农村户口的居民家庭月人均收入不足300元的给予差额补助,所需资金由区财政拨付。实际上,宝安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市定标准分别提高127元和105元。根据市定标准,到2000年第一季度全市符合条件的贫困人数有3442人,这些人员的分布状况和构成情况见表1、表2和表3。
根据表中资料分析,深圳最低生活保障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深圳市的贫困人口在特区内外分布和城乡分布上都不平衡。根据表1,特区内4个区的贫困人口数只占全市总数的18.7%,而特区外的宝安和龙岗两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市总数的81.3%,特别是宝安区占48.3%,几乎占全市贫困人口的一半。与此相应的是,贫困人口城乡分布不平衡,根据表2,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市总数的56.6%。因此,深圳的扶贫重点在特区外,而特区外的扶贫重点在农村。
表1
深圳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
罗湖区 盐田区 南山区 福田区 龙岗区 宝安区 总计
户数
87
40 74 87 4015501239
% 7.0 3.2 6.0 7.032.444.4100
人数
135 94 189 22811361660
3442
% 3.9 2.7 5.5 6.633.048.3100
资料来源: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
第二,保障对象的结构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救济。从表3可知,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原民政对象只占总数的16.6%,而在职、下岗、失业人员及其他生活困难人员占了83.4%,这说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以“三无”人员为救助重点的传统社会救助格局。深圳的这一特点与全国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281万保障对象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其中21%为原民政对象,79%是在职、下岗、失业、退休人员家庭中贫困人口”。[1]
表2 深圳贫困人口的城乡分布
城乡
户数559680 1239
% 45.1
54.9
100
人数
1494
1948 3442
% 43.4
56.6
100
资料来源: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
表3
深圳市贫困人口的构成
在职
下岗
失业
原民政
其他困
总计
人员
人员
人员
对象 难人员
人数 48121
429
573 2271 3442
%
1.43.5 12.5 16.6 66.0 100
资料来源: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
第三,保障的标准高中见低。目前,深圳特区内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为319元,从目前的资料看,这个标准在全国是最高的。据统计,全国36个主要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保障标准大体是:深圳市319元,厦门市315元,广州市281元,上海市280元,北京市273元,天津市241元;标准在200元以上的还有大连、海口、杭州、宁波、济南、青岛等城市;其他城市的保障标准均在200元以下,其中标准最低的是呼和浩特、南昌和银川三市,标准均为143元。[2]深圳的高标准与其工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如果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工资水平相比较,那么结果可能有所不同。1999年深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714元,月平均工资为1726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平均工资的18.5%,特区外城镇的保障标准占平均工资的15.8%。其他部分城市的情况是:1996年,武汉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120元,相当于该市平均工资的24%;北京的标准是170元,占平均工资的21%;上海的标准是180元,占平均工资的20.4%。[3]可见,深圳的标准高是就其绝对数而言,其相对标准并不算高,甚至有点偏低。
第四,保障对象较少。相对而言,深圳比较富裕,但并不是说深圳就没有贫困人口,实际上贫困人口的多少是相对于贫困标准而言的。目前,深圳市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为3442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0.29%,占全市常住人口的0.085%。其他部分城市的情况是:湖南省湘潭市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有3万多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每年需要1500多万元保障资金,市财政无力负担,故在实施时将应保对象中年龄在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排除在外,实际保障对象为7900人,年保障资金430万元。海南省三亚市,应保对象11369人,实际得到保障的只有1381人。[4]这表明深圳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较少,覆盖面较窄。
深圳保障对象少的原因大体有:经济比较发达,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渠道多样化;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对标准偏低;人口结构特殊,全市405万常住人口中只有120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70%的非户籍人口无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深圳是新兴的现代化移民城市,平均年龄只有28岁,负担系数较小。
第五,保障资金和管理方式充分体现政府的责任。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全国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是上海模式。上海是我国最早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保障资金由市、区财政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负担,即家中有在职职工的由在职人员所在单位提供保障,民政对象及其他无业人员由市、区两级政府提供保障,由民政部门归口管理。这种有单位的找单位,没有单位的找政府的保障方式被称为“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至1998年,全国采取这种方式的城市有78个。二是大连模式。这种模式的做法是,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完全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保障工作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资金统一发放。至1998年,全国采取这种方式的城市有53个。在这些城市中市区两级财政负担的比例有所不同。例如,大连市市区两级财政按7∶3的比例负担,武汉的比例为1∶1。厦门市的做法在保障对象上与上述两种方式有所不同。厦门市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为民政对象和非民政对象,民政对象的保障标准高于非民政对象,如1995年民政对象的标准为220元,非民政对象为185元。在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上,采取有单位的找单位,没有单位的找政府,这与上海的做法相似。深圳的做法与大连相似,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全部由市区两级财政按1∶1的比例负担,资金拨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统一发放。
二、深圳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未来走向
宝安区是深圳人口最多的区,总人口达13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104万,贫困人口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48.3%。宝安区政府对贫困问题十分重视,在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实施解贫脱困计划,其一系列措施具有开拓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选择宝安区作为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的对象。现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探讨未来最低生活保障的大致走向。
第一,保障工作将更加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下称《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对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幅员辽阔,实际工作纷繁复杂,《条例》不可能对其一一加以规制,各地的实际工作需要地方性法规加以规范。例如,深圳对超计划生育的贫困户、购房入户的贫困户、家庭中虽无就业人员但实际生活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申请户能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基层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标准不一。不过,据有关人士透露,《深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已经几易其稿,年内可望出台。届时,深圳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将更加规范。
第二,救助手段趋于多样化。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实践中,“最低”和“保障”应该得到兼顾,只强调“保障”,不考虑“最低”,势必影响效率的实现;只强调“最低”,不重视“保障”,则有违最低生活保障的初衷。另一方面,“最低”是相对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低”的标准也会不断提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彩电、冰箱属高档消费品,而在发达国家则属于生活必需品。宝安区的解贫脱困计划考虑到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个别化、扶贫与扶志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和城乡有别的原则,规定对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贫困户子女就学缴费有困难的,相关学校免收学杂费。对农村的住房困难户、危房户,由区、镇、村三级共同解决住房问题,建房资金由区、镇、村按7∶2∶1的比例分担,建房用地由镇村解决。建房标准为家庭成员4人以下(含4人)60平方米,4人以上80平方米。除了就业、教育、技能培训、住房外,宝安区政府正在考虑对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宝安区的社会救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多样化的救助手段得到市政府的肯定,并引起其他各区的关注。
第三,救助的标准更加合理。研究贫困问题的先驱,英国的朗特里(Rowntree)在研究贫困线之初就注意到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对贫困线的影响,后来欧美各国在制定贫困线时都考虑了家庭规模的作用。以英国为例,假定1人户所需保障金额为1,那么2人户人均保障金额为0.81,3人户人均为0.64,4人户人均为0.57。(注:这些数据根据李强《中国扶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表格中的数据计算得出。)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的调查测算,假定1人户所需保障金额为1,那么2人户和3人户人均只需0.80-0.85,4人以上户人均只需0.75-0.80。实际上,我国各地的贫困线虽有所不同,但均没有考虑家庭的结构性效应,贫困家庭的救助额随人口的增加而简单增长。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反映靠政府的救济金难以维持生活的多是孤寡老人或人口少的贫困户。这一问题已引起深圳市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们表示,将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合理的救助标准。
第四,最低生活保障的专业化程度将有所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基层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承担着保障对象审核、资金发放等大量复杂的具体工作。随着保障对象的不断增加,基层工作的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基层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深圳市民政局拟通过下列途径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和管理水平:一是招聘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充实到基层民政部门;二是加强对现有人员的政策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三是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加强深港两地的社会工作交流;四是把社会救助同基层组织建设、开展社区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以社区组织为依托,建立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使之逐步承担具体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
第五,非户籍居民的贫困问题将得到重视。深圳毕竟是405万人的深圳,占总人口70%的非户籍人口长期处于社会救助制度之外,很难说这个制度是完整的。所幸的是,新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非户籍职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可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突破户籍壁垒的第一个信号。当然,社会救助与养老保险有许多不同之处,它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非户籍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做工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增多。进城农民和城市间流动的城镇职工没有就业地户口,本文把这些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统称为非户籍人口,而不称为“流动民工”、“农民工”、“外来工”、“打工仔(妹)”等。首先,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是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各类人员,不论其年龄、性别、民族,也不论其是否就业。其次,非户籍人口中并不都是来自农村,且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所工作的城市已经住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再给他们冠以“流动民工”显得不合时宜。第三,经过多年的演变,“打工仔(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否定性的价值内涵,这一称呼的承担者越来越不接受这一称呼。
《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一规定体现了所谓“属地原则”。属地原则可追溯到1601年英国的《伊利莎白济贫法》,该法规定,教区有责任救济区内无亲人照顾的穷人,但教区的救济责任限于在该区出生的人或至申请时在该区居住满3年的人。《伊利莎白济贫法》对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社会救济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确定的属地原则至今仍被各国广泛采用。该法中属地原则的“地”应是居住地,而我国《条例》第2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户籍地原则”。
户籍地原则把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挡在最低生活保障网络之外,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且各地发展也不平衡,许多地方对本地居民的保障尚感吃力,对非户籍人口的保障更是力不从心。这种观点我们可称为“经济水平限制论”。二是农民进城对城市的各个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力,如果对非户籍人口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势必诱发更多的农民进城而一发不可收拾。这种观点可称为“比较利益驱动论”。但是另一方面,非户籍职工在居住地就业,对居住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他们的贫困要求其户籍所在地政府给予救济,这对非户籍职工及其户籍所在地的政府都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规定,对长期不在本地居住的人员不予救济,从而形成非户籍人口的救济真空,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经济水平限制论虽然不无道理,比较利益驱动论提出的问题也必须面对,但它们不应成为不给非户籍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理由,只是对社会救济制度及其相关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如果把非户籍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彻底打破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户籍束缚,将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继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一重大举措涉及的问题很多,非本文所能详述,在此仅提出一些思路:
第一,赋予属地原则以本来的含义,变户籍地原则为居住地原则。这不仅仅是与国际惯例接轨,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其内部的功能耦合。众所周知,最低生活保障是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其负担的大小取决于其他保障项目功能的发挥,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协调最低工资、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比例关系,能有效减轻最低生活保障的负担,也为非户籍人口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创造条件。
第三,为防止农村人口因比较利益的驱动而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不堪重负,社会救助资源的劣质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选择。所谓“劣质化”是指一种自动瞄准机制或自动排除机制,它通过给某种资源附加种种限制而使这种资源对于某些群体来说成为“劣质物品”,由于得不偿失而放弃竞争;而对于另一类群体(通常是目标群体)来说尽管存在种种附加条件,这种资源仍是“优质物品”,值得去争取并精心使用。[5]劣质化的具体措施是:其一,进入年龄的限制。非户籍人口进入城市的年龄须在40岁以下方能取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资格,这样就保证了城市的年轻化,降低城市的负担系数。其二,工龄的限制。要求在城市连续就业5年以上,考虑到2年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那么非户籍人口进入城市至少7年以后才会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网络。其三,以低标准为起点,根据就业年限制定几档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非歧视的原则,非户籍人口享受的最高标准与户籍人口应当一致。其四,计划生育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非户籍职工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提高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