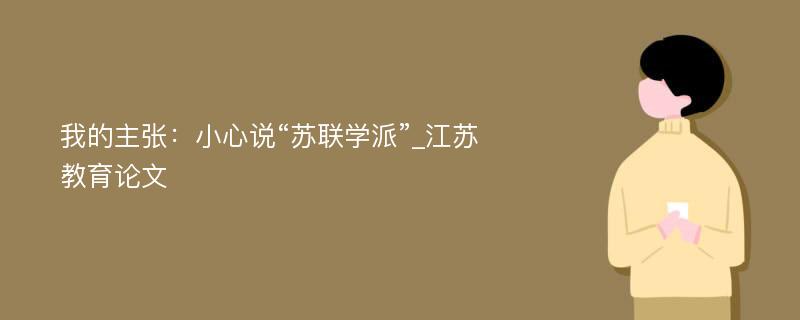
我的主张:慎言“苏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江苏的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江苏基础教育整体起步早,得地利之便,近百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与外部世界接触多,开放度一直很高;科举时代留下的应试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学术探究兴致,都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一百年内乱外祸,士绅工商在乡土办教育的启蒙尝试从没停止;即使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仍然有精神战士在思想禁锢下勇敢地探求。江苏百年教育史上,有过陶行知、叶圣陶、吴贻芳和吴天石那样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实绩,是江苏教育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教育史应当铭记的。
回顾百年江苏语文教育史,叶圣陶的贡献,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教育家吴天石的贡献,青灯黄卷50年的顾黄初的贡献,斯霞老师一生的追求等等,都盖棺论定。当然,也有令我们伤感的记录,吴天石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影响甚大,但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文革”开始时,他被南京师范学院的造反派们活活打死——这是江苏教育的耻辱。这一笔,我们也不能忘却。
自然也要提到当下。我想强调的,也是重要的,是江苏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江苏在全国首先建设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涌现出一批有个人研究方向的教师,各地也形成了不同层次、各具教学风格的学术群体。这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提到江苏教育,外地同行都很尊重,这也就促使我们思考和总结,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总体上看,江苏的教师,读书写作的自觉风气、研究问题的意识,的确多于其他地区。这是作为江苏教师队伍最显著的特点。有几家期刊主编说过,如果没有江苏教师的来稿“撑”着,刊物的质量会大受影响。这种表扬,也归功于一部分江苏教师的职业追求。而非常可贵的,是有相当一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教育观念的转变比教学技术的提高更为重要。
总结江苏语文教育的特征,不能不从百年语文教育的源流入手。研究江苏百年语文史,弄清发生过些什么,对叶圣陶诸贤所作的开创性工作,都要静下心来,一个一个地研究观察。无论如何,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浮躁,急于事功而贻笑大方。
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践行常识:教师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让学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增进智慧。研究教育教学,如果能站在学生的位置观察教师的教学行为,就能有更多的发现。能够时时处处反思自己的教学,才是合格的教师。研究苏派教学艺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点。江苏很多教师在开拓学生思维、自主学习方面有许多现成的经验。这方面课例很多,我无法一一介绍。但也有一些教师至今没能明确语文教育的本质,没能把握教学过程的目标,而只是“在一张考试卷上打滚”。科举史上,江苏是出了不少状元,但这绝不表明所谓“苏派”等同于应试。把学生教得比我们聪明,当然是值得追求的教育高度;然而,如果学生接受了12年的教育之后,最终未见“聪明”,而是有朝一日的“醒悟”,那就坏了——他想到教师在6年的中学教育中,一直忙碌的不过是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是为了个人教学的“业绩”,语文教给学生的仅仅是识字,那他心目中的教师地位可想而知。
学生的思维发展,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在阅读积累达到一定量后,才有可能谈到“感悟”。现今绝大多数语文素养好的人,都是因为读书多、勤于思考。优秀教师的作用,常常在于他有独立人格,善于启思导疑。
教师有创造意识,才会有灵动的、智慧的课堂。江苏的教师,最让我佩服的,是思想比较开放,有创造意识。教材重要,比教材更重要的是教师的创造意识和智慧。在非常年代,聪明的教师拿一张报纸也能把语文课上起来。在苏教版语文教材使用过程中,我常看到一线教师的创造,他们懂得什么是“教材”,知道如何“二次开发”,以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的课堂设计经常能体现思想者的智慧,他们重视在实践中去发现。江苏有许多中小学基层教师在课改之前就开始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的课堂上有“好的语文”,他们培养了学生对语文的热爱。他们的创造和发现,对目前我们江苏良好的师资状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正是他们,撑起了江苏教育的“牌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从不因默默无闻而放弃教育理想与教学追求。
教师要自觉地读书学习,克服孤陋寡闻。江苏的教师读书较多,这是传统影响,也和江苏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长江三角洲的教育发展在国内是领先的,而享有这样的优势,多历年所,并非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二、对“苏派”的提法宜持谨慎态度
对于母语教育的“流派”是怎么回事——苏派教育、苏派语文、苏派语文教学风格,我甚是疑惑。我以为,弄清这些名称,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思考多日,倒是记起几件旧事。此前多年,有过“京派”、“海派”之说。1985年,北京有位名校的老教师听了我的课,问:“王老师是‘京派’还是‘海派’啊?”我听了不大开心,凭什么我非得入某个“派”?但随口应的是:“年轻,无宗无派。”这位老教师又问了我们学校作文教学的情况,他矜持地说:“我们至今仍然用毛笔写作文。”——这是“京派”最引以为豪的“守正”,但如今,还有哪个学校能坚持用毛笔写作文呢?至于“海派”,似乎处处透着一股优越感。但更多的教师没有这类宗派意识。记得于漪老师2002年曾对我说:“我还是看重你们的试验,从来不吹,做了那么多有价值的尝试,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有分寸地介绍几句。”——我一直感谢她的表扬。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
由此不能不说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很容易地由“苏派教育”联想到“菜系”。江苏人爱说维扬菜,维扬菜作为“菜系”,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和“小吃一条街”是两码事。唐振常先生认为,重要的菜系都是地主阶层研发总结的,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地主忙于经营的时间有限,这就有闲从事园林建设,研制美味菜肴。所以八大菜系,满汉全席,只能是这少数人的乐趣。快餐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资本家的经营节奏过快,分秒必争,不可能有地主那样的悠闲和情趣。这些,也颇耐人寻味。之所以想到这些,是看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作为劳动力的教师的生存状态,“流派”,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遥远。
教育究竟归属哪个领域?教育是不是科学?如果教育是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能不宜有流派。如果是艺术,可以有流派。但普通教育,特别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学科,可能没有“派”,也不应当有“派”。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往往有很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地域观念的限制,信息的闭塞,乡土情结,家族血缘及师承等等。现代信息社会,地球已经变小,流派的一些“形成因子”已经弱化了。
叶圣陶诸贤在开创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时,虽然处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却并没有设想过“流派纷呈”的局面。当今之势,好像更没有产生流派的可能,主流社会强调“统一思想”,充其量只会允许技术层面上的不同风格。当今教育界,连教材的“一纲多本”还是“一纲一本”这样的问题似乎都不敢争论,“流派”从何谈起?如果“流派”作为业内的一种探索,作为成熟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追求,倒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行政追求,我认为要谨慎,建议尽可能多听听不同意见。
作为“流派”,它必然应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方可立宗立派,比如“人无我有”,至少是“人少我多”、“人轻我重”或“人有我新”,但不可以把人所共有之物当做自己的“特色”。2005年,福建语文界亮出“闽派”大旗,主张是“求实、去蔽、创新、兼容”。我当时不太理解:除了福建,其他地方就没有“求实、去蔽、创新、兼容”?教育教学的一般常识,不可能是“流派”的教学特点或学术特征。
没有好的自由的学术环境,创新意识不可能出现。强干弱枝,结果必然是“同质化”,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说句题外话,为了抑制各种浮躁作风对教育教学的干扰,我甚至觉得必须有釜底抽薪的决策,比如,应当考虑取消中小学职称系列,取消包括“特级教师”在内的各种荣誉称号评选,将这些全部“归零”,让我们的教师能够摒弃名利,静下心来研究教育教学。
关于“流派”必备的特征和条件,不得不说说“传统”和“师承”,“流派”总不能没有源头,然而这也是我长时间思考而不得其解的。我编《师大附中文化读本》,选常任侠先生的《战云记事》,看了很伤感——抗战爆发,常先生率师生西迁,可是他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江苏籍教师行为的不堪,搞小圈子,喝酒打牌。现在呢,为数不少的教师除了忙各种考试,忙着做家教,便是喝酒打牌,“除了教学不会,其他什么都会”。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我们期望的“流派”距离太远了。
在一个需要教育启蒙、端正教育观念的时期,提“流派”可能为时尚早。我们要克服浮躁心理,静下心来做事。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讲话中提到,“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意味深长。
所以,我认为,当前教育界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做,我们的民族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启蒙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