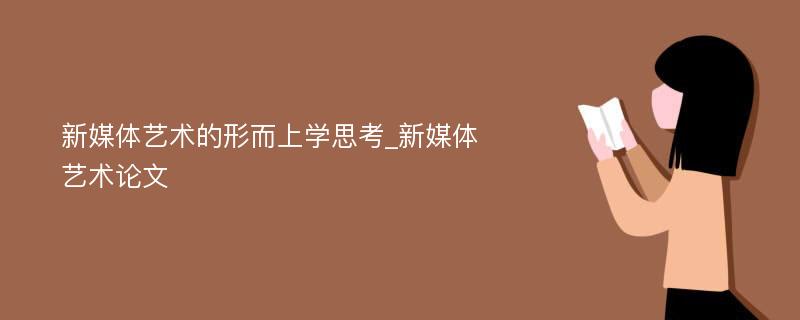
新媒体艺术的形而上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媒体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6-197-05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情境的某种需要而出现的,作为直接肇始于特定历史语境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知识形态与表意实践,该艺术形态本身或者表现为一种关乎人类生活的问题,或者表现为关乎人类生活问题的一种答案,就当下社会而言,新媒体艺术及其历史出场的特定方式就显示了这方面的含义。作为信息化与数字化生活状态的审美表征,新媒体艺术不但更新了传统艺术的表意范式,而且重构了人类文明的经验形式与精神向度,它以鲜明的新技术特征改写了艺术存在的传统方式与人类生活的现实面相,对此,学界业已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与阐释,但是很显然,仅仅立足于纯粹技术的层面来解读新媒体艺术及其经验效应至敞显了真理的一部分,甚至还是次要的一部分,毕竟新媒体艺术的本体性质是艺术而非技术,只有从艺术及其精神价值的角度来通达,新媒体艺术的本体性质才可能获得彻底的澄明与绽放。换言之,对新媒体艺术来说,不但应该从技术性的危度来揭橥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世俗化、商品化与形而下等物质层面的影响,更其重要的还在于把它当作一种新的精神现象学形式,解析其所本然具有的关乎人性本体的心灵自由、形而上诉求以及道德关切等精神超越层面的意义。唯其这样,新媒体艺术才能作为“是其所是”与“如期所是”的对象化存在,从而不但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形式,而且确证和理解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性质。
一、人性超越之维的本体论诉求
新媒体艺术是一种直接依托现代数字媒介技术与商品化世俗语境而生成的新型艺术样态,相较于传统艺术样态,新媒体艺术的生产方式显示出了更多的技术优势,而在价值理念上也显现出了更浓重的工具化、商品化与感官化等世俗性的意义色彩。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性状,人们倾向于认为,要对新媒体艺术进行有效的研究,就必须将数字媒介技术和世俗性的价值理念作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因为新媒体艺术毕竟鲜明地表征了这样的经验趋向,检视已有的相关研究,持论这种立场的似乎已构成新媒体艺术研究的主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无论技术性的因素和世俗性的事相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新媒体艺术依然不能超逸出艺术的本质规定,关于人性的精神超越、心灵自由、诗意栖居与形而上诉求是其作为艺术所无法规避的本体论承诺,就此而言,除却建构起新媒体艺术的技术形象与世俗形象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就其关涉人性的形而上与人生意义等方面对它进行澄明,以期从本体论角度建构一种新媒体艺术的精神形象。而这就意味着,人们首先需要问及的是,新媒体艺术为什么具有形而上的“应然”意义?在当下它又是或应该如何来通达形而上意向的?
基于其本身价值命意的基本取向,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可以在两个维度得到展开,即低限度与高限度两个维度,前者主要开掘新媒体艺术中的技术化、世俗化与商品化等物性内涵以建构起关于人的至下性生活场域,后者则意在发现新媒体艺术中蛰伏着的精神超越、心灵自由与形而上诉求等深度问题以其建构起事关人性存在的至上性意义图景。就当下的症候而言,人越是沉溺于新媒体艺术的实证性、世俗性以及工具性所显示的进步,人就越是离人性的本性和这种艺术的形而上本性越远,因为艺术本来是人类借以洞悉自身精神自由的对象,现在反而成为仅仅说明和表现人的被动性与有限性的一种镜像,人一旦彻底沉溺于自己的有限经验性,就从根本上阻碍了趋向无限人生的可能性,甚至还错把新媒体艺术对于世俗生活的利益忙碌表达体验为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与存在意义,而在事实上,这是对于新媒体艺术本体论身份的一种误读与误置,因为仅仅从世俗角度技术角度来观照新媒体艺术不仅低估了它的复调精神意义,而且更是对于其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降格。问题的这种提法就表明,意欲获得新媒体艺术的精神超越要旨,就必须从纯粹外在性的世俗观照中撤身回视,以植根于其深层结构中的主体性向度和形而上承诺来对其技术化和世俗化的经验存在方式进行自我省思与自我批判,唯其这样,才能建构起新媒体艺术价值表意的深度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新媒体艺术确实正在有意无意地踏上一条形而下的畏途,人们之所以倚重新媒体艺术,更多的是出于物质欲望、商业利益、感官刺激、市场需求、生活时尚、游戏狂欢等等有限幸福与大众娱乐的考量,一旦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座架,人之为人的本体论危机就程度不同地会出现,其性状一如雅斯贝斯曾经所描述的那样,“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劳动与快乐的分离使生活丧失了其可能的严肃性;公共生活变成单纯的娱乐;私人生活则成为刺激与厌倦之间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连续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实证主义也鼓励人们无休止地从事出于种种冲动的活动,这些冲动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比如:热心于数量上的庞大,热心于现代技术的发明物,热心于声势浩大的群众;狂热地崇拜名人的成就、财富与能力;在性的行为上趋于复杂造作和兽性化;热衷于赌博、冒险、甚至使生命遭受危险。”①设若新媒体艺术依然自恋于这种技术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世俗甚至是媚俗的价值框架,那它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就迟早会遭遇合法化的危机,自我救赎的可能在于,穿越世俗性的迷雾并从自我世俗身份批判的角度重构新媒体艺术的精神之维与诗意之维,增强形而上意义与“应然”意识在其意义域中的根本性存在。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作为艺术与一种人学形式,新媒体艺术也必须遵循艺术之于人性提升的一般原则,因为,“心灵,从来不满足与单纯的成果,必须要回到它自身,问它自己的内心生活得到了怎样的收获;因为它不能不把这一内心生活视为目的,与它相比,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②这就说明,新媒体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内心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审美活动,它天然地相关于形而上表意的精神谱系,尽管它目前在经验方式与结果形态上显示出了较强的物性化与技术化的倾向,但其初衷却指向某种超越性的精神事宜,伊格尔顿溯源艺术的一般审美本性后认为,“18世纪中叶,‘审美’这个术语所开始强化的区别不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区别,而是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即事物和思想、感觉和观念之间的区别,就如与我们的动物性生活相联系的事物对立于表现我们心灵深处的朦胧存在的事物一样”③就此而言,人们不但要把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进行精神性的理解与建构,而且即便是其中存在的表达世俗性价值诉求的技术性因素,也应该从精神性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与建构,美国学者费雷曾说,“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和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通过对技术的解析,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完整的信奉和信仰世界”④通过解蔽技术的存在论本质,人们就能从新媒体艺术的审美世界中敞显出一个人性意义与精神信仰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实证经验世界,只有这样的超越性的意义才能确证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本质,也才能说明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关乎人性心灵自由与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意识的精神特点。
对新媒体艺术而言,人越是沉于其中的技术性维度,就可能越是遮蔽和遗忘其中的艺术性维度,唯有从自身的技术性帐幕中解放出来,新媒体艺术的精神意义与形而上意向才可能获得澄明。对于新媒体艺术语境中的人性而言情形同样如此,建构新媒体艺术作为人性的形而上言说并不等于取消它关于人性世俗叙事的合法性,问题仅仅在于以崇高人性来批判或引领世俗人性,防止人性的物化与降格,“只有作为精神生活的独特表现,文明才可能具有内在的凝聚力、明确的意义和控制的效能,它才真能使人更新,才能抵制与人类文化每一步发展紧紧相随的人的委琐和执拗。”⑤
二、作为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
作为人类不断趋向一种自我完善的境界而言,任何文明方式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的进步,充其量只能视为人类趋向无限性存在的某种阶段性的状态。新媒体艺术及其所表达的生活方式显然也是这样的一种过程状态,换言之,新媒体艺术所表征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并非就是人类终极生活状态本身,而只是某种趋向终极人性状态的审美意向,它作为一种审美化的实践理性形式,不断地质询生活的终极意义,并以对现有人性的不断拓展与纵深开掘来表达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其尽可能地迫近那种人生的终极状态与形而上境界。以康德的美学理论观之,新媒体艺术作为关乎鉴赏判断的审美活动是一种介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人类活动能力,它的构成性形态是感性对象或者表象方式,但是一切人类活动包括新媒体艺术活动的规定根据却是实践理性原理。作为一种“信仰的确实”而非“逻辑的确实”,实践理性并不能被人们从知识概念上把握住,“对于这些理念,不仅我不想说及现实性,而且甚至我们也不能断言认识和理解它们的可能性。”⑥但是作为对自由与道德的表征,人们在理论理性与审美判断活动中却又可以体验到实践理性的效果,它体现为人们对于自由人性与纯粹道德存在的一种想望与接近过程。文艺审美活动在知识形态上并不就是实体性的道德存在或自由人性,而只是人类理性生命的功能状态,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理性能力。
检视当下新媒体艺术的内容选择与意义指向,人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认同物质功利化的价值倾向与审美风格层面的形式主义崇拜,就像奥伊肯所说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代的进步,往往把生活兴趣的中心从不可见世界转向可见的世界。”⑦仅仅立足于外在物质化与功利性的感性生活以及执著于某种审美形式技巧的实验固然也是新媒体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仅仅浅止于某种表层的物质利益追逐与形式技术游戏并不能保证新媒体艺术存在的价值合法性,相反,这还会导致新媒体艺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消费主义与商业主义的逻辑陷阱,有学者分析,“在消费逻辑中,新媒体的文艺缺少了为天地立命的雄心,也没有悲天悯人般的宗教性终极关怀,更羞于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追寻……在新媒体文艺产业化过程中,文艺生产者为迎合市场可能‘弃雅从俗’,拒绝深度写作,一切为了市场,以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文艺的生产过于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就使得艺术本身的文学性被消解,要么机械复制,要么庸常媚俗,最后只剩下一副非技术非艺术的空壳。”⑧从其基本使命与价值身份来看,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性的人学存在方式,其核心旨归不是用来反映和表达人性的物质化内容与功利性诉求,而是致力于对这个外化层面的否定与超越,就其实质乃在于对一种人生的神性之维与形而上之维的审美性言说与想象性建构。这一点对于深具世俗语境色彩的新媒体艺术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就新媒体艺术的一般属性来说,它虽然是以感性形式呈现的,但蛰伏其根底的规定根据却是理性的,它本身以及它所要实现的对象不是某种囿于现世经验与世俗生活的理论理性,而是某种趋向无限人生的实践理性,规定其基本价值意向的是某种形而上的道德法则与终极意识,也就是说,就其不得不以某种有限的经验方式来呈现自身而言,实践理性显然不能成为它的现实构成原则,但就其具有超验意向与形而上的品格而言,实践理性却又能成为其调节性的原则,一如康德所言,“我们可以把他那可以看做现象的行为看做是受物理所制约的,而在同时,就能行为的存在者是赋有悟性的存在者而论,又可以把发动这些行为的原因性看做是不受物理制约的,这样我就又可以把自由概念变成理性的调整原理。”⑨其中对于新媒体艺术当下建构的方法论启示就在于,即便新媒体艺术仍然是一种囿于现实有限经验的形而下存在方式,但是如果人们在进行意义建构时选择的基本框架不同,所植入的价值命意不同,那么新媒体艺术就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身份意识与价值性质,尽管所面对的对象并没有发生改变。
三、数字化的在世方式
新媒体艺术是当代信息技术与数字审美社会语境的意义系统,尽管它所创造的生活世界被视为一种虚拟的审美空间,但在事实上却是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显现的,一如我们每天都要遭遇的日常生活经验一样,并且还从各种维度建构人类生活的现实经验、实践方式与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机制与经验形态,新媒体艺术不但建构了丰富复杂的外在生活空间与实践场域,而且极大地更新与重构了人类内在的基本在世方式与自我理解方式。相形于传统艺术样态,新媒体艺术凸显了技术媒介的审美表现力与价值立法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新媒体艺术的技术优势重新定义与组织了人类生活的周遭世界,从早到晚的时间层面,从外在境况到内在思索的空间层面,无一不是被新媒体艺术的技术逻辑与意义边界所座架着。新媒体艺术不但改变着人类关于自然、社会的情感态度,而且改变着关于自身的意义认同与自我想象,它是人类在21世纪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所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新媒体研究学者戴森说,“对每一个将进入新世纪的人来说,绝对不能把‘数字化’等同旅途中的一次艳遇,它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一股加速度的内驱力,如果拒绝它,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剥夺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才能获得的尊严和价值。”⑩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认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数字技术与多媒体装置对于新媒体艺术而言呈现出某种悖论性的意义效果。问题的一方面在于,新的数字技术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类关于自然、社会与自我的表现疆域与经验范围,而在另一方面,当人类以这种数字媒介技术来扩展生活视域的同时,它却因为过度倚重技术的逻辑而又可能缩减人类生活的自由选择。数字媒介技术本来是人类用以洞悉和阐释生活的工具,但是对于它的极度依赖却又导致某种技术主义的表意危机。反观当下社会,我们已然发现了艺术技术化所催生的症候。很大一部分的商业广告、仿真景观、3D电影、动漫游戏、网络购物、互动电视与在线报道等等都在影像逼真的同时走向了意义失真与意义缺失的畏途,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曾经描述了上世纪的艺术因为其意义被工具理性所篡改而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运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能够证明对人性的这种信仰吗?我们不是看到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迷恋于一种横扫一切的激情,一种肆无忌惮的攻击性,一种降低所有文化的意向,把文化降低到使他们感兴趣、能理解的水平,用数量取代质量,把生活变得狂暴、粗野,并由此表现出一种无礼的自负吗?而在个体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富裕中的无谓吝啬,精心掩饰的自私,无聊的自我专注,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求出名,无端地寻衅,讨厌的伪善,尽说大话又缺乏勇气,对一切精神任务漠不关心,事关个人利益则勤勉无比。”(11)很显然,新媒体艺术必须实现自身基本立意的质性转换,即把新媒体艺术不仅视为一种应对外在世俗功利事物的技术装置与物理工具,而是更根本地把它看作一种安顿心灵与处理自我精神事物的新的意义立法系统与阐释系统,一种新的关于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的方式,换言之,新媒体艺术应该获得存在论与实践论意义的身份证明而非仅仅认识论层面的事实指认,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昭示,新媒体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文化表意方式与言说方式,它所揭示的核心内涵是关于人的存在论意义与新的在世方式。在这样的问题框架下,新媒体艺术通过扩大外在人生的经验领域就不会导致人类内心生活的缩减,相反,它在一种与外在生活对等的意义上充实了自我的内在意识,深化了人类关于自我各种可能性的认识,由于克服了人的单纯外在性约束,“从而使生命的中心转向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随着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生命似乎完全被置于其自身的娱乐之中,并仅仅趋向其自身。虽然各种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生命仍不为之所动,而显出其全部无限性,并意识到自身是至大无边的。一切外在的现象,作为一种仍未充分展开的自身存在,对生命来说都是有价值的;生命从不体验各种事物本身,而只在各种事物中体验生命自身——即生命的受动的意识状态。”(12)也就是说,基于艺术表现手段的丰富性与新锐性,新媒体艺术具有比传统艺术形式更丰富的表现手段,它能够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发展人与其周遭世界的联系,探测外在物质世界的各种幽微肌理,也能更加有效而全面地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所以它也就能相应地增加人生体验的丰富性和自由性,此时,尽管新媒体艺术所展示的是关于外在现象世界的感性丰富性,但是它所诠释的却是关于人的内在意识的自由与无限,“自由的主体性是本体的东西,不存在于现象的世界。自由是不可用概念和形象来直接把握的,它必须从实践中而不是从理论上来理解。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瞥见自己在实践中获得自由。道德的主体存在于理智的而非物质的领域里,虽然在现实世界里它必须不断而神秘地使自身的价值物质化。”(13)其中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新媒体艺术所展现的内容不是一般性的人的现实遭遇与社会关系,而是一种被现代多媒体技术与文化符号所中介和修饰了的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现实遭遇与社会关系,或者说是表现现实遭遇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内涵。
新媒体艺术的存在不单单是一种艺术事实或者说技术事实,它还是人的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方式与自我理解方式。作为数字化语境下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审美镜像与自我表征,它重构了人们的认识论框架与存在论意识,它为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价值依据与组织原则,它对于外在世界的每一次开掘与表现都旨在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以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意识的每一次搏动都是由自我意识发动的。每一项认识都改变了认识者。改变了的认识者必须在他的世界中寻找关于它自身的新认识。”(14)
美国抽象艺术家杰森·帕洛克(Jack son Pollock)曾经认为,现代艺术,不过就是从当代的角度,表现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毋庸置疑,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艺术的本体论承诺与形而上诉求,从这个视域出发,我们发现,其实新媒体艺术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人的存在的数字化装置,而是一种对于数字化语境的精神反思和价值应对,它不但建构着人的世俗形象,而且表征着人的形而上之思。
注释:
①(14)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1、7页。
②⑤⑦(11)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4、14、40页。
③(13)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69页。
④弗里德里克·费雷:《走向后现代科学与技术》,见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⑥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⑧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413页。
⑩转引自闵大洪《数字传媒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2)倭铿:《审美个体主义之体系》,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魏育青等译,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