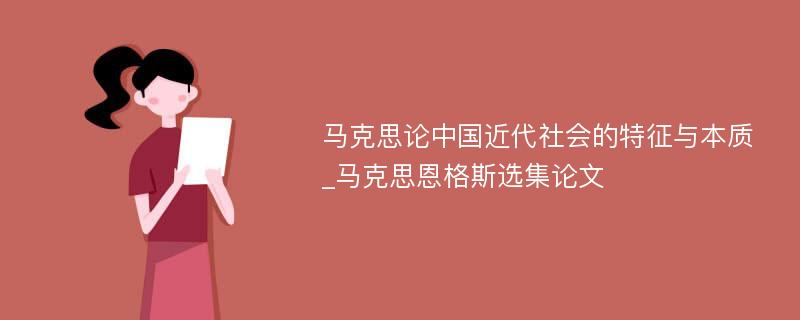
马克思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地认定一个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是决择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基本依据。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今似乎得到了公认,然而,这个结论实属来之不易,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讨和争论的过程。
19世纪中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亚洲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兴起,马克思十分关心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东、西方革命关系的重大问题。因此,马克思将注意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对印度、俄国、中国、土耳其等东方国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近300篇的系列论文和时事评述,从而创立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初撰写了19篇专题论文和时事评论,并在他后来的论著和书信中多处论及了中国。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定近代中国的特点和性质本身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依据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基础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特点,马克思并非是第一个或唯一的探求者。在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之下,首先被惊醒的是部分埋头故纸堆的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和洪秀全、洪仁玕等农民思想家,就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有了最初的认识。他们从鸦片战争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后果中,看到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和腐朽,认识到西方侵略的危险和危害。在封建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促使下,他们提出了变法自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是表面而非本质的,只是揭示社会的某些现象,并未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因此,他们希图通过封建统治者的自我调节,在固守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以挽救阶级的和民族的危机。但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中国社会作出经济的和阶级的分析,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作出科学的认定。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社会作了经济的和阶级的分析,这才真正开始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
马克思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以土地王有为基础的村社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
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均认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及此前的东方社会均不存在土地私有制。1853年6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中也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那么,最高土地所有权归谁呢?是归国王和他代表的国家。马克思说,“国家在这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主权在这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便没有任何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马克思认定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权,是在东方社会土地所有权“双重性”这一特殊性意义上论断的,即认为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结构,既存在着公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又存在着国王或国家对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权。马克思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态里,那处于一切小公社之上的综合单位,便成为高级所有者,甚至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因而真正的公社反倒只不过是世袭的占有者。”(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在国家是最高土地所有者的情形之下,便没有任何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虽然,私人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和村社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都是存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在东方,财产仅有公社财产,个别成员只能是其中一定部分的占有者,或是世袭的或不是世袭的”。(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马克思又从东方社会土地所有权的“双重性”出发,论述了近代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他说,“我曾竭力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的性质……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页。)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实际的。虽然由于中国很早以来就可以进行土地买卖,出现“地无常主”的现象,到鸦片战争前后,土地所有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国家除直接占有官田、屯田、森林、荒地之外,对其他私有土地仍享有间接的最高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这种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农村公社土地所有权相伴随的双重性结构,在历史上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并不是矛盾的。而且,马克思也承认在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注:《马恩全集》第28卷第291页。)。
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双重性”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反映在剥削方式上则是租税合一制。马克思说,“像在亚洲那样……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注:《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页。)中国大部分农民从皇帝那里得到一小块有限的完全私有的土地后,“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页。)。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正如马克思说的,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方式,“可以采取贡赋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集体劳动的形式,其目的是供养集体”(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2页。)。这集体便是国家或国王。
马克思指出,东方社会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村社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注:《马恩全集》第25卷第372页。)。这种村社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特殊结合,“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注:《马恩全集》第25卷第373页。)直到近代中国,仍然是“依靠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页。)
这种经济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这些家庭式的村社建立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同时手工织布,手工纺纱,手工种田这三种东西以特殊的形式互相结合,曾使得这些村社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农民“既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页。)。这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分散、闭塞、停滞落后的状态,农民过着“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的生活。
第二,以家长制权力统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政治结构。
马克思认为近代中国是以家长制权力统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他指出,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这样建立起“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着“家长制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的统治。“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一个人决定。”(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412页。)
马克思的论断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中国自秦朝统一为封建大帝国之后,就朝着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方向演变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政治制度更趋于成熟和完善。其表现是一切军政财等大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朝廷和专制皇帝的手中,皇帝至圣、至尊、至贵,国家一切事务皆由圣断,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谕旨便是法律和法令,对一切臣民均有生杀予夺之权,违抗者将招来满门抄斩的血腥镇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有屠戮大臣、诛除异己的事件发生。在皇帝专制下,人民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所谓“民无私说”,就剥夺了人民言论、结社等自由。所以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414页。)。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这种政治结构的经济基础,便是国家和皇帝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特殊结合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注:《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页。)在这种情况下,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剥削方式是租税合一。所以马克思说“农民国家的农民之存在,为的是让人家来剥削他”,“地租之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实现的经济形式,要有地租,必须先有土地所有权。”(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而近代中国农民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说它“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这种所有权形式的巩固根基及不断重演,便是国家政治制度之所以始终不变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马克思又指出,这种经济结构之所以能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是由于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各个小农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而自给自足,彼此间缺乏交往和联系,他们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无法形成全国性联系和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最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693页。)
第三,以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为特征的思想道德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和为基干构成的。它强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观,养成了“华人之情好静”的民族心态。儒家文化固然有培育中国人温文尔雅、敦厚纯朴的社会风气的正面作用,但也有阻碍革新、安于现状、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长期处于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孤立封闭之中,自古就形成了中国为世界中心和“华夏第一”的民族中心论的传统观念,以为中国不仅在地理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且由于四大发明的巨大成就,也认为中国在一切文化方面也是世界中心。这种传统观念和民族心态在统治者和士大夫之中世代相传,而且是根深蒂固,乃至当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时,清王朝仍然无视这种近代工业文明和世界历史新潮流,还以“天朝上国”自居,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时清王朝仍然抱着“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不放。
清王朝在这种观念和心态下,对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禁止一切反清言论,镇压一切反清人士,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禁锢一切革新思想,迫害一切革新人士。结果思想界和学术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对外则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蔑视外国为“蛮夷之邦”,“化外蠢愚”。对于西方近代科技成就视为“奇技淫巧”、“旁门邪道”,充分暴露了他们无知的愚昧和狂妄。他们对外实行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所以马克思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页。)但那时只是出于地理上和种族上的原因,而到了清代,则将“仇恨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究其原因,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第四,长期处于分散性、封闭性、停滞落后状态。
马克思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思想观念之后,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在中国也是如此,似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长久地总是保持着平衡状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经济分析。
马克思认为,近代中国村社性的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基础,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革命性作用,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为不仅农民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小单位,而且一个村社也如此。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做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变成商品的只是剩余的产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变成商品。”(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页。)甚至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因为“在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范围内,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是绝对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中国“地大物博”,可以在闭关自守中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自给自足的简单生产,并生存下来,所以马克思说“因为农民家庭在这种形式之下,由于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因此,近代中国虽然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集市贸易,但产品和商品主要是为本地区所吸收和消费,未能形成跨地区的大市场和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以及海外市场。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必然导致社会的分散性、封闭性、停滞落后性。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既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分散性。因为,无论是土地主要占有者的地主,还是自耕农和租佃农,直接生产者的农民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马克思说,这些农户和村社“散居于全国各地……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它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自给自足的小单位。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仍然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约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而且,这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封闭性农业型经济,“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为国内散居在全国各个很小地点的彼此缺乏联系的农户和村社,而且表现为与国外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马克思在评述“印度、中国都存在过”的亚洲村社时指出,这种村社“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现象……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页。)这些自给自足的小单位如果偶而遭到破坏,他们便以“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恢复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能动”。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所以亚洲各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这种社会的停滞落后性在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曾创造了古老的农业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进入近代时期却仍然沿袭着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一家一户、年复一年的从事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简单重复的生产。马克思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693页。)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头脑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成为因循守旧和传统规则的奴隶,没有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没有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也不关心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的变化。马克思指出,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页。)对于旧中国停滞落后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评述,“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况,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运动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61页。)中国的梁漱溟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的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来未曾大变过。我常说它是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之变,因此论百年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11页。)
二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展开争论,他们都曾努力地探索和判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马克思就此也曾作过不懈的探索,提出过精辟的见解。
要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必须先要确立划分社会历史性质的标准。马克思认为,这个历史标准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注:《马恩全集》第8卷第487页。)为什么以此为历史标准呢?因为某一种生产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不同性质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0页。)。但马克思在肯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的同时,又指出它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并且在许多场合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也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恩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88页,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
马克思正是根据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马克思分析了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以此为广阔而牢固基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认定近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既不是西方式的封建社会,也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它与“最现代的社会”相对的“半野蛮人”的“陈腐世界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页。),它正在由一个“野蛮人”的“野蛮政府”、“野蛮制度”,变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野蛮”,如同他们在其他处讲的“野蛮”一样,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古老社会。但马克思不认为东方国家已实现了封建化过程。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将东、西方社会作机械类比时,阐明了他的依据是:东方国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存在着农奴;也不像西方国家的贵族性的对土地的独占性;也没有西欧封建主那样享有世袭司法权和领主审判权,东方国家的司法权主要属于公社和国家。马克思正是从以上依据出发不承认印度的封建化的,他称印度社会为“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的性质。这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不称近代中国为封建社会而用“野蛮”、“半野蛮”代称。马克思否认东方社会完成封建化是同西方社会封建化作比较得出的,这当然是一个误解,但马克思强调东方和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是很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文明制度”,无疑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中国是“半文明制度”,是因为中国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仍是社会的广阔基础,从中央到地方的家长制权力统治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近代中国仍然处于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旧的经济、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并“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转变的呢?马克思指出,引起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
在经济上,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英美等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些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由于机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的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造或工业制度到处遭到破坏。那些一向或多或少落后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向以手工工场为工业基础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使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陷于灭亡的绝境……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后,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尤其是鸦片的输入,“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造成了新旧税捐的增加,使“小民其何以堪?”而且影响着中国的财政和工业结构。“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在政治上,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不仅迫使中国“付给英国的赔款”,开五口通商,鸦片贸易“致使天朝帝国银源有枯竭的危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使中国更加虚弱,而且与鸦片有关的贪污行为,也在“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页。)尤其是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望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又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这种解体不仅表现在自给自足的结构的解体,而且表现为政治结构的解体。所以马克思说,“所有这些破坏的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明代就已在封建社会中孕育和萌芽。但由于土地所有制和自然经济的结构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和艰难,并未能发展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手工工场阶段。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又无力打破它。因而,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才靠这个“外力”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说:“大工业才用机器……才彻底把可怜的多数农民剥夺,才完成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的分离,把农村家庭工业的根底——纺纱业和织布业——根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6~947页。)中国社会旧的经济结构靠“外力”打破,这又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随着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马克思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这种解体过程,正是中国从“野蛮人”的“野蛮政府”向“半野蛮人”“半文明制度”转变的过程。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解体,马克思用“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作比喻来说明它的不可避免性。而促成这种解体的直接推动力,马克思指出就是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灭绝战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马克思还断言,面对人民的普遍起义的强大革命,腐朽的清帝国尽管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终究“要在这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那么,天朝帝国死去了,中国可能将会是怎样的前途呢?马克思运用他的“历史环境”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作了资本主义前途的预测。他指出:“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恩全集》第7卷第265页。)。自由、平等、博爱是当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可见,“中华共和国”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作出这种预测的依据是什么呢?便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历史环境。
从国外环境看,当时正值世界历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为西欧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19世纪50~60年代,通过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和民族统一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国家广泛地确立,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当时世界历史的潮流和总趋势。马克思正是以此为国际背景预测中国发展前途的。
从国内环境看,当时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发生了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对这两个危机,马克思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注:《马恩全集》第7卷第264页。)又说天朝帝国“一切都烂透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注:《马恩全集》第2卷第634页。),于是改革派要求变法自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连绵十年的起义已汇合成为强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近代化的方案。
马克思正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这种国内外历史环境,预测中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马克思撰写关于中国的论文时,他只能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而作出半野蛮半文明社会的论断,当时社会实践没有提供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成的材料,更无法预测后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曲折。因此,马克思只能依据他写中国论文时的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历史环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去作出判断和预测。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土地所有权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手工业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