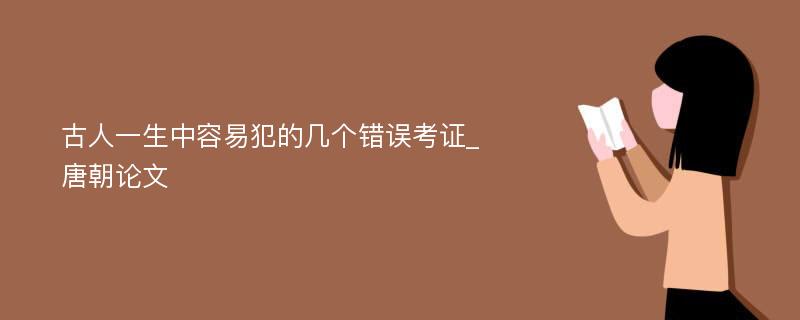
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事迹论文,几种论文,古代论文,作家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1-053-08
王辉斌同志在2001年和2003年,连着发表了《王维早期行事探究》(下文简称《探究》)[1]、《王维开元行踪求是》(简称《求是》)[2]、《关于王维的隐居问题》(简称《问题》)[3] 等三篇文章,着重对王维早期的事迹进行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与我商榷。我们知道,有关王维早期事迹的记载很少,研究者往往只能根据他一些诗歌提供的线索进行钩稽、考证,而诗无达诂,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我认为这些看法不妨并存,以待时间的检验,故而对于就这个问题同我商榷的文章,一般不作回答;然而当我仔细读了这三篇文章后,却又产生了回答的愿望。我以为这三篇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它们涉及考证方法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是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时易犯和常犯的,有时方家也难免。所以我决定将它们揭示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并作为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鉴戒,同时也是对上述三篇文章的一个回答(但不斤斤于具体事迹和琐细问题的是非之辨)。现将这些错误归纳成几种类型,分述于下。
一、为牵合已说而轻易否定古人记载
《求是》一文说:“综以上对王维‘开元行踪’的考察——是以其‘知南选’为研究的中心的。兹将所考作归纳为:开元二十八年的秋天,王维以监察御史之衔自长安经大散关人蜀,‘知南选’于黔州。翌年春正月事毕,乃由渝州顺长江东下至夏口,之后溯汉水而上抵襄阳,并于南阳临湍驿与神会等‘说经数日’,旋北返长安。翌年改元天宝,唐玄宗下诏令,‘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两转’,王维乃由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擢升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知南选”在黔州,是上述推断的核心与关键,也是《求是》的新说;然而王维今存的诗文中并无一语提及黔州,也没有任何一种记载说过王维“知南选”在黔州,所以这个新说还只是一种推测。为了证成这个新说,《求是》对凡与这个新说相左的古人记载,皆轻易加以否定。如王维《哭孟浩然》诗题下注曰:“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有作。”说的是自己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走到襄阳时写了这首诗;而《求是》却认为这条自注“当非出自王维的手笔,而是为他人如王缙等所为”,根据是:“考杜佑《通典》卷十五云:‘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又《旧唐书》卷四十四有云:‘在通常称谓中,监察谓之御史,殿中谓之侍御,侍御史谓之端公。’此则表明,《通典》——中‘御史’这职,所指为监察御史。借此,可知王维‘知南选’时所官乃应为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才与《通典》等所载相合。”按《旧唐书》卷四十四为《职官志》三,我翻查了这一整卷书,根本未见《求是》的这段引文,又用电脑检索,结果是整部《旧唐书》都无这段引文;事实上,唐时监察御史俗称侍御,而非御史,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唐人所谓“御史”,是御史台属官(包括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统称,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因话录》卷五:“凡三院(台、殿、察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这两条材料中的“御史”,都兼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唐时选派到岭南或黔中监南选的御史,既有监察御史,也有殿中侍御史,如《新唐书·柳泽传》:“睿宗善之,拜监察御史,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所以《哭孟浩然》的自注,并没有什么错误,不应轻易怀疑和否定。
拙作《王维年谱》(最初发表于1982年出版的《文史》第16辑,经修改后收入1990年出版的《王维新论》,再经修改后收入1997年出版的《王维集校注》)说过,王维曾于天宝四载在南阳郡临湍驿中与神会和尚晤谈,此说与《求是》的上述新说相左,自然也在被否定之列。先看一下有关的记载,胡适辑《神会和尚遗集·神会语录》第一残卷:“门人刘相倩云,在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和上及同寺慧澄禅师语经数日”“王侍御惊愕曰:‘大奇,曾闻诸大德言说,皆未有作此说法者。’乃谓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王维集校注·附录二》)[4] (p1245)此文称王维之官衔为侍御史,而写于天宝四载的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也有“侍御史京兆王维”之称,所以拙谱断王维与神会晤谈在天宝四载,并认为王维到南阳郡的原因,是“受制出使”(唐侍御史“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求是》说:“王维‘知南选’时所官应为监察御史。而《神会语录》中作侍御史者,确属与王维斯时的职官不合,但此一矛盾的出现,实则乃后人所为。即是说,编辑《神会语录》者与王士源撰写《孟浩然集序》的情况大体类似,其所称谓者乃王维后来的官衔,而非能证明王维斯时所官即为侍御史。……王维被擢升为侍御史,乃在天宝元年。至天宝四载,王维仍在侍御史任上,故王士源于是年秋八月所撰《孟浩然集序》乃有‘侍御史王维’云云。”按,前面说王士源在《集序》中所称乃王维后来的官衔,后面又说王维于天宝四载八月撰《集序》,当时王维仍在侍御史任上,则《集序》所称“侍御史”,乃王维当时的官衔,而非后来的官衔,前后所述,自相矛盾;某文中称某人之官衔,若非该文写作之时的官衔,便是其以往的官衔,怎么可能是未知的后来的官衔?《求是》又说:“‘南阳郡’的始名于唐乃在天宝元载以后,但此并不能证实王维的是次南阳之行,即乃在天宝四载。这是因为,《神会和尚遗集》的原刻(或抄本)与胡适所辑之是《集》,均为后人所为,即‘南阳郡’这一地名乃为编辑《神会和尚遗集》者首次使用,而非王维与神会等人在‘语经’时所涉及。”认为王维本于开元二十九年官监察御史时在邓州(天宝元年改为南阳郡)与神会相遇,然而《神会语录》的编辑者,却将当时王维的官衔监察御史更改为侍御史,还将相遇之地点邓州改为南阳郡;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有何迹象表明编辑者作了上述更改?他又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更改?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所说的更改,不过是主观臆测而已。又,《神会语录》中的资料,是近人从敦煌卷子中发现的,胡适将它们辑为《神会语录》出版,其中根本不存在上述《求是》所说的更改(日本也有同样的辑印本,又敦煌卷子今存,可覆核)。另外,《语录》为神会弟子记录其师言论的资料,有无可能神会与王维晤谈于开元末,而其弟子追记于天宝时,所以改用天宝时的地名、官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上引《语录》中的“寇太守”,即南阳郡太守寇洋。贺兰弼《唐故广平郡太守恒王府长史上谷寇府君墓志铭》:“公讳洋……历吉、舒二州刺史,南阳、广平二郡太守。”“晚加衰疾,屡表恳辞,由是除恒王府长史。将行,以天宝七载六月十五日薨于外馆,春秋八十有四。”[5] (p1672)唐天宝元年二月,“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旧唐书·玄宗纪》),《墓志》记载寇洋之历官,将州刺史与郡太守清楚地分开,则他任南阳郡太守,当在天宝元年改州为郡之后。又《册府元龟》卷四五○:“玄宗天宝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节度,镇守西陲,不能振举师旅……宜黜远藩,用戒边使,可舒州刺史,即驰驿赴任。”田仁琬盖继寇洋之后为舒州刺史者,其任舒州刺史之时间,在天宝元年二月改州为郡之前,而寇洋自舒州改任南阳郡太守之时间,则在同年二月改州为郡之后,到天宝四载,寇洋当仍在南阳太守任上。神会自“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当时亦在南阳。从上引《语录》所称地名和王、寇二人之官衔看,断王维、神会相遇在天宝四载,颇为合宜。另外,《语录》写明这条材料由亲见王维、神会相遇晤谈的神会门人刘相倩提供,也说明这条材料是可靠和符合当时实况的。所以,《求是》谓王维、神会相遇在开元二十九年春,不能成立。至于《求是》说王维在天宝元年由监察御史擢升为侍御史,则错误更甚,这问题留待后面再细谈。
《问题》一文认为王维晚年“辞职归隐于终南”,其《终南别业》诗即作于是时。然维此诗又载于《国秀集》,而《国秀集》收诗止于天宝三载,这与《问题》的上述说法明显相左,所以《问题》又说:“王维《终南别业》之入《国秀集》者,当为宋、明人所妄为。”理由呢?其一、今本《国秀集》收入的作家作品,同唐本已有差异;又“唐本《国秀集》在宋代时‘三馆’即无,而刘景文之所得又乃出自坊间”。按,《国秀集》卷首楼颖序渭此集收入“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而今本所收,实际为八十八人(其中有三人有目无诗),诗二一八首,差异并不大,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差异,属正常现象,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可靠性。《国秀集》卷末北宋曾彦和跋云:“此集《唐书·艺文志》洎本朝《崇文总目》,皆阙而不录,殆三馆所无。浚仪刘景文顷岁得之鬻古书者,元祐戊辰孟秋从景文借本录之。”《新唐书·艺文志》等未著录此集,只能说明它流传不广,而不能据以否定它的可靠性,而且到了南宋时,《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此书。其二、“今本《国秀集》卷中将王维是诗作《初至山中》,显然与诗的内容不符,盖因其中的‘兴来每独往’之‘每’字,已充分表明了王维写这诗时,并非为‘初至山中’,而是往来多次。”按,如此解诗,可谓胶柱鼓瑟,“兴来”句盖谓自己初至终南隐居时,兴致来了,每每独往游赏风景;此诗《河岳英灵集》作《入山寄城中故人》,诗题的不同,或许是因为作者后来又作了修改。《问题》又说:“要之,就必须以确凿的材料,以证实芮挺章的唐本《国秀集》乃收有是诗,而持(作于)天宝三载前说者,却无任何人对此有只字提及,其说之令人不可信从,仅此即可见其一斑。”按,绝大多数古书的唐本今皆不存,谁也无法拿出唐本来证实《国秀集》收有是诗,但以唐本的收诗数同今本相较,差错率很低,而且在今本《国秀集》中,我们尚未发现有可确断为天宝三载以后所作的诗歌,所以说法恰好应反过来:只要今本《国秀集》收有是诗,就应认定它作于天宝三载以前,如果认为唐本《国秀集》未收今本中的某诗,则必须拿出确凿的材料来。
王维《赠祖三咏》:“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诗题下注:“济州官舍作。”余以为此诗开元十二年作于济州,并说:“古代诗文中,有约举成数之例”“如果维八、九岁即与咏相识,则二十四岁时(开元十二年)作诗,便可以说是‘结交二十载’了。”[6] (p62)《探究》一文则认为此诗开元二十二年作于长安,当时王、祖二人第四次相聚(其实诗中只是抒发岁晏思友之情,并无一语言及两人相聚之事),此说明显与此诗的题下注语相左,所以《探究》又说:“这条‘济州官舍作’的所谓‘自注’,并非出自王维手笔,而是后人妄为。”又是后人妄为!作者真是勇于怀疑。《探究》此说的理由是:“当时只有八、九岁的王维,是根本不可能从其乡(今山西永济)远渡黄河到洛阳或者长安与祖咏相识的”。按,八、九岁的王维,自然不可能独自远游,但跟随父母或其他亲友到洛阳或长安去,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探究》还有另外两条理由,俟后再谈。
综上所述,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时,如遇古人的记载与自己原先的设想相左,该首先怀疑的,应是自己的设想,而不是古人的记载。这样,才能不犯或少犯主观臆测的错误。
二、因不明古代制度而误
《求是》一文说:“考《全唐文》卷三十九唐玄宗《改元大赦文》有云:‘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各赐勋两转。’所谓‘赐勋两转’,其实就是连升两级。王维开元二十九年春以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知南选’还京,至翌年改元天宝‘赐勋两转’,正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按,这是典型的因不明唐代官制而误。唐代的官制很复杂,岑仲勉《金石论丛》说:“说其大概,可分为职事官、散官、爵、勋四项,五品以上的官员,往往各项兼备,最低限度也有职事官和散官两项。”[7] (p461—466)这四项中,只有职事官是有必须执行之政务的实职,其余都是无必须执行之政务的虚衔;这四项各具独立性质,不一定随他项的变动而变动。监察御史、侍御史都是职事官职,和“赐勋两转”之“勋”绝不能混同。唐代之勋,计有十二转,《新唐书·百官志》:“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二转为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唐代皇帝遇即位、改元等事时,对九品以上官员的普遍颁赐,都是在散官、爵、勋上给予升迁,从未有过在职事官职上给予升迁的,原因很简单:其一、职事官都有具体职事,必须“随才录用”(《旧唐书·职官志》一),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连升两级”,势必造成滥竽充数、官非其人的混乱现象。其二、《唐六典》卷二:“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即每一个职事官职的品级、员数是固定的,也即职事官有固定编制,唐律禁止超编授官,《唐律疏议》卷九:“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又,自古至今的官制,都是官员品级越高,员数越少,因此如果职事官九品以上都“连升两级”,势必出现严重的超编现象。例如监察御史定员十人,侍御史定员四人,如果监察御史都“连升两级”成为侍御史,那么侍御史就要超编一倍半,这岂不乱了套?另外,唐代流内职事官分为九品三十等,监察御史同侍御史之间相差六等(正八品上、从七品下、从七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而不是《求是》所说的“两级”,可见《求是》的作者对唐代职事官的品级,也很生疏。
拙作《王维年谱》断王维寓离济州司仓参军任的时间为开元十四年暮春,《探究》认为此说误,理由是:“没有对唐玄宗在王维仕鲁期间所颁布的全部赦令予以考察。——开元十三年有两次大赦——先看第一次:‘正月……戊子,降死罪从流,流已下罪悉原之。’——王维的被贬济州非为‘流罪’,而是‘左降官’之属,而‘左降官’正为‘流已下’,且赦令又明文规定‘悉原之’,故王维的被赦即应在这‘悉原之’之列。”并认为十三年王维被赦后即离开济州。按,这条是因不明唐代的律法制度而误。何谓“流已下罪”?我国自古就有五刑的刑法制度,唐时亦“立刑名之制五焉: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唐六典》卷六)这五刑由轻至重又分为二十等:笞刑五(自笞十至五十共五等)、杖刑五(自杖六十至于一百)、徒刑五(自徒一年起,以半年为差,至于三年)、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死刑二(绞、斩)。参见《唐律疏议》卷一。据《唐律疏议》,唐时一个平民所能犯的罪,皆包括在这五刑二十等罪之中,而所谓流以下罪,即指除死刑二等之外的其他十八等罪。例如《疏议》卷二云:“诸七品以上之官……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又云:“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这是说,一个六、七品官犯死罪之外的其他罪,可减一等处罚(例如依律应徒二年,可减为一年半);又五品以上官员的妾,犯流、徒、杖、笞之罪(罪的性质属十恶的不包括在内),允许以铜赎罪(如杖一百,纳铜十斤)。唐时一个官员所能犯的罪,除五刑二十等罪之外,还有除名、免官、免所居官三种罪,它们也都属于流以下罪(参见《疏议》卷二、三)。唐律规定,犯罪人“议、请、减以下人,身有官者,自从官当、除、免,不合留官取荫收赎”(《疏议》卷二)。官当即以官抵罪,如六品以下、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等等,所以犯徒、流罪的官员,大抵都要解职抵罪;另外唐律还特别规定,官员犯某几种罪,必须除名(官爵悉除)、免官(职事官、散官、勋官俱免)、免所居官(免所居之一官;职事、散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带勋官者,免其职事官),例如犯受财而枉法等罪除名,犯受财而不枉法等罪免官等等。由此可见,犯流以下罪的官员,实际上解官者居多,而左降官则仍居官,也就是说左降官中的许多人,并非因犯流以下罪而左降,不过因工作的失误而贬官;“流已下罪”涵盖不了所有甚至是多数的左降官。正因此,朝廷发布的赦令中,如果涉及左降官,都要另作交代。如《册府元龟》卷八五:“(开元十七年十一月)戊申,谒诸陵还,大赦天下,制曰:‘……自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处。”’此次大赦是所有的五刑之罪皆赦免,但仍涵盖不了左降官,所以又对左降官的赦免问题另作交代。开元十三年正月的赦令未提及左降官,当然同王维的被贬济州无关。又《探究》所引的这条赦令,系据《旧唐书·玄宗纪》,而《纪》引录此赦令时,经大加删改,已有违原意,《册府元龟》卷八五:“(开元)十三年正月戊子制曰:‘……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宜降至流,流已下罪悉原之。’”则赦免的对象是被拘禁的囚犯,同王维更无关系。另外,《探究》误以为拙谱认为《赠祖三咏》作于开元十三年冬王维与祖咏在济州相会时,又认为这年春维已离济州,不可能与咏在济州相会,因此以王维十三年春已离济州作为《赠祖三咏》题下自注“是后人妄为”的一条理由,其实这个自注与王维何时离济州并无关系(拙谱认为《赠祖三咏》作于十二年秋),《探究》作者误会了拙谱之意。
《问题》说:“王维开元十八年因妻丧而去职闲居于家。”又说:“李白一生凡两入长安,第一次在开元十八年夏——在李白到达长安之际时,王维于此前已因妻丧而去职且‘杜门’家中。”按,唐人居官时丧妻,并不去职。《问题》所述是因不明唐代丧制而误。《通典》卷一○八:“居官遭丧:凡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父为长子、夫为妻,并不解官,假同齐衰周也。”“给假:凡齐衰周,给假三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齐衰周,服齐衰(丧服名)一周年,古时夫为妻服齐衰一年;则唐时居官遭妻丧,并不去职,总共给假三十八日。
《求是》说:“据《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可知,唐玄宗时期实行的是‘旬假制’……唐代对各种假日在时限上乃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即除特殊情况如丧假可‘给二十日’外,其余最多只三天。如果请一般性事假,则只有‘三品以上长官’可‘请假满日’(一天)。由是以观,可知当时仅任从六品下侍御史的王维,是尚不具备请假的资格的。”按,这条是因不明唐代的休假制度而误。据《唐六典》卷二等载,唐代官员除旬假外,还有不少假期,如每年有两次长假(田假、授衣假),各十五日;全年的节日假(如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等)合计达五十三日;又私家有婚、冠、丧、祭、拜扫、省亲等事,皆给假(如私家袝庙,给假五日;四时祭,各四日等),以上情况拙作《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待刊)有详细论述,此不重复。至于说只有三品以上长官才能请一般性事假满一天,则是因误解原文之意而致误。《会要》原文云:“(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御史台奏:‘伏准承前旧例,诸司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满日,正衙参见,其余品秩卑,自有本司官长,不曾于正衙参假;去年六月侍御史窦群奏,令尚书省四品、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同三品例,正衙参假讫,既失旧章,又烦圣听,今请准例三品以上假满日,正衙见……。’依奏。”奏文的意思是,三品以上长官请假期满之时,在正衙(朝会之所,指宣政殿)参见天子销假;而按《求是》对“请假满日”的解释,上引这段文字明显无法讲通。《会要》八二又云:“大和八年九月御史台奏:文班常参官旧例,每月得请两日事故假,今许请三日。……敕旨:依奏。”则所谓任侍御史的王维,尚不具备请事假的资格,可谓无中生有。另外,笼统地说丧假给二十日,也不正确,《会要》说的是:阎立德妹丧,给假二十日。唐时是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来定丧假的长短的,并非一律给二十日,详情可参阅《通典》卷一○八“给假”。
上述三文的作者,结合唐代制度来考证王维事迹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所可惜的是,对唐代的制度了解不多,因而造成不少错误。
三、因不明或误解原文之意而误
不明或误解原文之意,是考证常犯的错误,上文已涉及这个问题,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关于王维《谒璇上人》一诗的系年,《求是》说:“其一是据《景德传灯录》卷四,要知璇禅师乃为嵩山高僧普寂的四十六位法嗣之一……且《宋高僧传·普寂传》又载普寂开元二十七年终于洛阳兴唐寺。……作为普寂的弟子璇禅师以及王维母子,都应是普寂葬礼的当然参与者。如此,则王维在开元二十七年的洛阳谒见璇禅师并写《谒璇上人》,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其二是《宋高僧传·元崇传》中的一段文字:‘释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其中的‘至德初,并谢绝人事’云云,颇可注意,因为其所表明的是璇禅师与元崇在至德初年,均离瓦官寺而‘历于上京’。而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三于‘璇上人’的笺注,又可对此佐证:‘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此则表明,王维拜谒璇禅师及写《谒璇上人》一诗,又可能是在‘至德初’……的长安一带。”按,要弄清《谒》诗的系年,首先必须对诗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诗云:“夙承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夙承”二句说,上人自己早已承奉,现在在这里焚香瞻仰;“颓然”句写上人在居室中坐禅入定的情状;“高柳”二句写上人所居寺院的景物和节候;“床下”二句细述上人居室中摆放的物品。因此,此诗应是王维至上人所居寺院瞻仰上人时所作。据《景德传灯录》卷四,普寂的法嗣中有“瓦棺寺璇禅师”,《元崇传》也说开元末年禅师居瓦官寺(在江宁),可见瓦官寺是璇禅师的长期居住地(目前尚不清楚禅师是否住过别的寺院),所以拙谱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春王维自桂州北归途经江宁时。《求是》认为拙说“错误更甚”,于是提出上面引述的两项新说。现在先剖析第一项:首先,普寂的卒地是长安而非洛阳。《宋高僧传·普寂传》:“开元二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二十七年,终于上都兴唐寺,年八十九。”都城,国都,唐时一般指长安(如与“京城”对举,则指东都洛阳);上都,首都,明显指长安,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东都):“西至上都八百五十里。”又兴唐寺在长安,《长安志》卷八、《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都有明确记载;《求是》的这个错误,是由于误解都城、上都之意造成的。其次,古代交通不便,居于江宁的璇禅师,能否按期赶往长安参加普寂葬礼,颇成问题,况且说两人在参加葬礼时相会,也不符合上述《谒》诗之诗意。接下剖析第二项,先引录《元崇传》的有关文字:“释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谘受心要……璇公乃揣骨千里骏足可知,因授深法。崇灵台虚彻,可舍百神……金陵诸德请移所配栖霞寺。春秋逾纪,服勤道务……时众是瞻。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遍奉明师……遂入终南……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正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声价渐高,衣冠羡仰。……遂东适吴越天台、四明,清心养素。数年后,遐想钟山,飞锡旧居……。”《求是》将“并谢绝人事”理解为元崇、璇禅师一起辞绝世事,其实从上下文看,此传除“以开元”句以下数句交代传主的师承外,自“崇灵台”句以下至传文结束,所记皆传主之事迹,如说他移居栖霞寺,“服勤道务”超过一纪(十二年),至德初离栖霞云游四方,“遍奉明师”,先至京、洛,后适吴越,数年后,方复返栖霞等等,这中间当不会忽然夹入璇禅师之事。若以为“历于上京”、在辋川遇王维等,是元崇、璇公的共同行为,恐怕于理不顺,于义未安,因为至德元年元崇已四十四岁(据此传所载元崇卒年和享年推算),而作为普寂之法嗣和元崇之师的璇公,应早已过了云游四方、“遍奉明师”的年龄,况且此传明言王维“与崇相遇”,而不提璇公。这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并”字的解释,“并”有全部、完全之义,如《后汉书·董卓传》云:“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又云:“(韩)遂等……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盖出家为僧已是辞绝世事,如今乃连寺院“道务”也辞却,所以说完全辞绝世事。又,《求是》引赵殿成注以为己说的佐证,亦难以成立。赵注云:“《续高僧传》:元崇以开元末年,因从璇禅师谘受心要……璇公乃因授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这段注文错误不少,首先,它本引自《宋高僧传》,却误作《续高僧传》(此书所载止于初唐高宗麟德二年,不可能有元崇传);其次,它作了有违原意的删削,如删掉“至德初”三字,结果使至德初发生的事变成开元末发生的事;复次,断句有误(在交字下点断)。至于作“与崇历上京”,则和《求是》一样,是因不明“并”字之意而误。综上所述,在辋川与王维相遇的,应只有元崇一人。
王维《淇上即事田园》,“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拙谱说:“据此诗,知维尝隐居淇上。”《问题》说:“诗中所写,仅为王维‘屏居淇水上’之所见,而不能表明他斯时乃在淇上隐居。”按,隐居系作者自道;屏居者,隐居也。王维《酬诸公见过》:“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耿湋《春日即事二首》其二:“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皆可证。由于《求是》作者不明屏居之意,所以未能看出此首为写隐居之诗。
《旧唐书·王翰传》:“(张)说既罢相,出翰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探究》说:“张说罢相在开元十四年四月,则王翰出为汝州长史即应在是年四月或稍后。而《全唐诗》祖咏集中有《汝坟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舌鸟》、《寄王长史》二诗——这说明,开元十四年四月及其后的祖咏乃是在汝坟与仙州一带的。若如《王维年谱》所言,祖咏及第后即被授官齐州,(今山东济南)以东——那么,开元十四年前后的祖咏就不当以一‘文士’的身份,‘常在座’于王翰的仙州长史府。”按,陶敏说:“张说开元十四年四月罢相后,翰未即遭贬逐。其被贬当在十五年或稍后。”[8] (p22)又,据祖咏诗,知咏从王翰游,在翰改仙州长史之后;翰贬汝州长史既在十五年,则改仙州应更在其后,傅璇琮说:“其时或在开元二十年前后。”[9] (p209)所以,拙谱说祖咏开元十三年登第后,即在齐州以东为官,与《王翰传》的记载并不矛盾。祖咏《汝坟别业》:“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谓已因仕途失意而去职,遂移家汝坟;汝坟在今河南襄城,当时属仙州,故得以与仙州长史王翰往还。由于《探究》作者对《王翰传》原文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便有了《探究》的上述错误推论。另外,《探究》还以此作为《赠祖三咏》题下自注“是后人妄为”的一条理由,其实这也是个误解,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
四、资料掌握未全面而遽下结论
《问题》说:“事实上,王维天宝九载在其母卒后上表所‘施’之‘庄’,非为宋之问的蓝田别墅,而是其于蓝田所自营的一座别业。……《请施庄为寺表》一文有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乐在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其中的‘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云云,说得极清楚,二者岂可相混?若王维母亲生前所居之‘庄’,确系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且其又在天宝九载为王维所‘施’,那么,王维晚年又何来‘家南山陲’的‘终南别业’呢?”按,此说可谓道他人所未道,但错误明显。《旧唐书·王维传》:“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王维《辋川集》序曰:“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耳。”知王维所得宋之问别墅,即其诗中常说的辋川别业、辋川庄,详情可参阅拙作《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10]。唐耿湋《题清源寺》:“孟城今寂寞,辋水自纡余。”诗题下注:“即王右丞故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王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新唐书·王维传》:“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清源寺,在(蓝田)县南辋谷内,唐王维母奉佛山居,营草堂精舍,维表乞施为寺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一六:“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问别圃。维后表为清源寺,终墓其西。”以上唐宋人的记载,皆谓王维为母奉佛所营之山居,即辋川庄,它本是宋之问别墅,母亡后,维上表求施为清源寺。因辋川庄在山谷中,其地属蓝田县,所以又可称为蓝田山庄,宋之问《蓝田山庄》:“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也称自己在辋川的别墅为蓝田山庄,可证。王维所施之“庄”即辋川庄,也即宋之问别墅,这一点不少记载都已指明,而《问题》作者似乎不知,他完全撇开这些记载而按主观认定遽下结论,自然不能免于错误。又,《问题》谓王维施庄为寺在天宝九载,亦误。《请施庄为寺表》:“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臣往丁凶衅(指遭母丧),当即发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比(先)虽未敢陈请,终日常积恳诚。又属元圣中兴(指肃宗收复两京),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备周行(得充朝廷之臣),无以谢生(酬谢活命之恩),将何答施?……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表文说,天宝九载遭母丧时,自己即有施庄为寺之心,但未敢陈请,则不在天宝九载明矣,又说自己请施庄为寺的动机之一,是报答皇上的不杀之恩,则施庄为寺,当在王维因陷贼入狱,又被宥罪复官之后,即乾元元年(758)。拙谱已系此事于乾元元年,不知《问题》为何没注意到?
《问题》又说:“王维一生共隐居四次——第三次系丁母忧而再隐终南山,晚年则辞职归隐于终南。”“王维丁母忧在天宝九载——他二十七个月的守丧期,乃在终南山的辋川别业度过(陈允吉考证王维的‘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甚是,本文此处特从之),是可肯定的。”“王维晚年隐终南山,《旧唐书·王维传》乃有载:‘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又《新唐书·王维传》云:‘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已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旧唐书》所谓‘晚年隐终南山’者,所指即为王维上表以己官换王缙‘还京师’后‘放田里’事。而王维集中的《责躬荐弟表》有云:‘臣之五短,弟之五长……顾臣谬官华省,而弟远守方州……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由是而观,可知王维晚年的‘晚家南山陲’,乃系其上表‘伏乞尽削臣官’所致。而其‘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亦在是时。或以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乃在天宝三载……其说乃属不的之辞。”按,《旧唐书·王维传》根本没说过王维“晚年隐终南山”,请看传文:“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文中“维弟”以下五句,述维奉献佛事,谓其平时食粗粝之食,晚年更终年吃素;而“得宋”以下数句,则述维得宋之问别墅,与裴迪游其中,并赋诗事,前后所述为两事,故“采”字下应加句号。这段话显然不能理解成王维晚年得宋之问别墅,更不能理解成王维晚年隐终南山,实际上“晚年隐终南山”是《问题》自己的看法。《问题》称王维晚年隐终南,系其上表求“尽削臣官,放归田里”所致,也完全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只有王维的自请,而没有天子的批准,“放归田里”无法实现;其次,放归田里相当于前面谈到的“除名”,在唐代是朝廷对犯罪或有过错官员的一种处罚,如《通典》卷一—五:“臣请都督、刺史……等,……政绩无闻,抵犯贪暴者,放归田里,以明赏罚。”《旧唐书·代宗纪》:“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以元振有保护之功,削在身官爵,放归田里。”《新唐书》本传在记述王维自请“放田里”一事后说:“议者不之罪。”既然廷议不认为王维有过错,他自然不会受到放归田里的处罚。又《问题》将放归田里与“辞职归隐”等同,也不正确,因为去职的官员仍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待遇,而受到放归田里处罚的官员,其地位则同于庶人。复次,据笔者考证,《责躬荐弟表》作于上元二年(761)春,时王维官尚书右丞,说见拙谱[4] (p1373-1375);维上《荐弟表》后不久,肃宗即召王缙入朝为左散骑常侍,维于是进上《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状文末署“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则直至上元二年五月,王维仍在朝任职,而再过两月,维即辞世,哪有可能辞职隐于终南?
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问题》即据此认为王维晚年隐终南山,并认为终南别业即王维所得之宋之问蓝田别墅,又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晚年”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故《问题》又将王维得终南别业的时间落实为在上《荐弟表》后,即上元二年春;既然王维直到上元二年春才得到终南别业,那么他天宝九载守母丧时所居之辋川(终南)别业,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母丧,毁几不生”(《新唐书·王维传》)的王维,显然不可能在守丧期间大兴土木,营建别业,而且据王维《辋川图》(明刻石本),别业的规模不小,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营建的,这恰好说明拙谱断王维始营辋川别业在天宝三载近于实情,何“不的”之有!《问题》前后所述,自相矛盾,甚为混乱,这主要是资料掌握未全遽下结论,加上误解原文之意造成的。看来,误解原文之意是考证最易犯的错误,它常与其他错误交织在一起,值得我们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