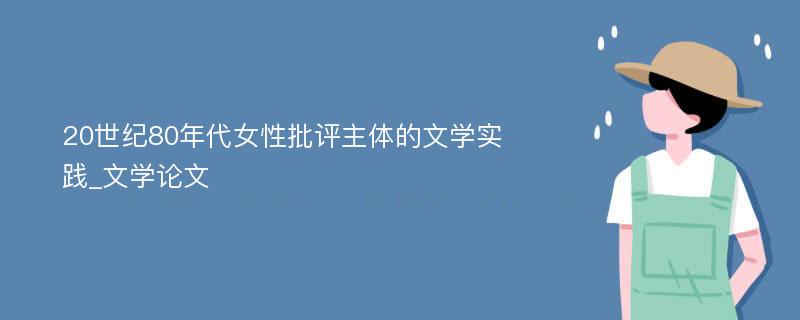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女性批评主体的文学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批评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12-0138-09 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兴盛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坛现象。对此,多年来很多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涉及性别与文学关系的现象则较少为人们注意,这就是女性作为批评主体在80年代文学界的竞相涌现以及她们所做出的可贵努力。尽管后来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和教材对女性批评家所做的工作有所提及,但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的影响很少为人关注;在有关80年代文学批评的论述中,性别意识作为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也往往被遮蔽。为此,有学者指出,“文学研究中的性别意识淡化,抑或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作祟”是造成“80年代的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处于暧昧和尴尬的状态”的主要原因。① 既有的与80年代以来女性批评主体有一定关联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侧重于考察明显接受了国外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批评活动,例如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运用以及本土化探求的轨迹;二是从理论建设、思想文化以及学术史等角度,对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女性文学研究加以审视。前者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在对历史资料做出取舍时,淡化了不便纳入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后者侧重于从整体上和理论上探讨女性文学研究的得失。两者的立意均不是将80年代女性批评主体的实践作为考察重点。鉴于此,本文在20世纪80年代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大略呈现当时女性批评主体参与女性文学研究活动的概貌,探讨其特色及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关注女性创作并积极参与文学研究实践的,当然不只限于女性,女性研究者也并非仅仅关注女作家的创作,而是往往同时在其他方面亦有成果,不过限于篇幅,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是80年代女学人围绕女作家创作展开的批评和研究。 一、80年代女性批评活动概貌 在提及20世纪80年代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创作研究时,学界相对比较熟悉的,首先是朱虹发表于《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这篇文章在国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妇女运动以及文学创作、研究发展情况,虽然主要是谈美国女作家的创作,但明确表达了有关“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看法。其次为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②。该丛书的8部著作,半数出自女性之手,其中孟悦、戴锦华所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在文学文化领域影响最为广泛。再者,白舒荣的《白薇评传》(与何由合著)和《十位女作家》也有一定影响。前者真实细腻地展现了“五四”女作家白薇的悲剧人生、创作生涯和文学个性;后者评述现代文学史上十位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启发。③ 当然,80年代参与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女学人远不止前面提到的几位,而是达数十人之多。她们大都就职于高校、作协、杂志社及科研机构。其中既有多年从事文学研究的资深批评家和学者,也有刚开始踏上研究道路的年轻人。例如李子云、王淑秧、苏者聪、吴宗蕙、陈素琰、盛英、马瑞芳、金燕玉、牛玉秋、赵园、任一鸣、马婀如、钱荫愉、黄梅、张抗抗、吴黛英、钱虹、王友琴、乔以钢、赵玫、陈惠芬、季红真、翟永明、王绯、于青、艾云、林丹娅、姚玳玫、刘慧英、禹燕、吕红、施国英等。此外,还有部分女学人当时未曾以女性创作为主要关注对象,但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如应锦襄、乐黛云、吴小美、刘思谦、饶芃子、陶洁、陈美兰、艾晓明等。80年代女性创作与批评的共同发展,几代女学人的积极参与,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景观。 80年代前期,有关研究经常以评论文章的形式出现。一些女学人对当时女性文学创作蓬勃兴起的现象做出了敏锐思考和及时回应。1982年,刘慧英在《谈女作家作品的主题倾向》一文中指出,女作家崛起之因不仅在于社会时代的转型,更源于女性自身的诉求。她们的创作“标志着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是女性要求有人的尊严、平等的表现”④。次年吴黛英发表《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认为“我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它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离不开社会历史的转型,也有文学创作自身发展的因素。⑤对于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王安忆的小说创作,陈惠芬以“从单纯到丰厚”加以概括。她捕捉王安忆创作的内在变化,指出“作为一个近年来在文坛上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王安忆在艺术上的成长显然是和她审美理想、追求目标的不断提高和延伸联系在一起的”⑥。陈素琰《论宗璞》以知人论事的方式展开论析,认为宗璞的创作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知识阶层的气质、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特有的幽雅、淡泊、洒脱、内省的精神风貌。⑦这些研究程度不同地融入了女性主体的生命感知。 除了跟踪新时期的女性创作之外,也有不少学者专注于考察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及其创作。王淑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历史地位》联系新文学史和丁玲的创作道路,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做出评价。⑧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视作洞察“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的窗口,认为对人性、洋场生活特殊本质的艺术性追问体现出张爱玲小说独有的深度与魅力,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位置不可替代。⑨林丹娅《试论庐隐创作个性中的“自我”》将“五四”的时代背景与女作家的创作人生彼此观照,认为庐隐小说最大的特色是“自我”情绪的抒发与表达。这种“自我”的张扬表达出特定时代下人性诉求的文化背景,而过于偏激的“自我”也给她的创作带来局限。⑩ 80年代,文学期刊对社会文化生活颇具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女性批评主体与文学评论期刊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新文学史料》、《当代文艺思潮》、《文艺评论》、《文学评论》、《读书》、《上海文论》、《文学自由谈》、《批评家》、《当代文艺探索》、《当代作家评论》、《女作家》、《当代文坛》、《小说评论》、《诗刊》等刊物,均曾提供发表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园地,体现了对女作家创作的关注。这种合作促进了女性批评实践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使一些读者通过期刊了解到女性批评群体的出现。 评论者的文字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发表,会更具影响力。1986年,《当代文艺探索》第5期设置“女批评家专辑”,并在文后附有作者小传,介绍了若干女作家。1987年,《当代文艺思潮》于第2期、第5期开设“当前女性文学探索与争鸣”专栏,刊载了包括钱荫愉《她们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再反思》、王绯《女性文学批评:一种新的理论态度》在内的多篇文章。内容涉及女性在文学中的历史境遇以及关于女性文学批评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惠芬的努力和主持下,《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以接近整刊的篇幅,刊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专辑”。其中包括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吕红《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兼及〈金瓶梅〉的道德与美学思考》、施国英《颠倒的世界——试论张贤亮创作中的两性关系》、王友琴《一个小说“原型”:“女人先来引诱他”》等文。正如栏目标题所示,这些文章具有犀利而鲜明的“女权主义”锋芒,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结合文学中的性别文化现象做出阐述和分析。此期还同时设有“妇女书架”,介绍了《女性的奥秘》、《女性人类学》、《女性的危机》、《金色笔记》等相关成果。在80年代国内初兴的女性主义批评中,这期刊物颇具代表性,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女性批评群体成长的过程中,学术争鸣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为女性批评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了学术讨论的场域,也促使她们在文学界为人关注。我们知道,性别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与每一生命个体相关;与此同时,作为复合型的文化符号,它又与社会、历史、民族、国家、阶级等诸多因素彼此勾连。这种状况一方面赋予性别研究丰富性和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80年代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的争鸣即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反映。例如,对于“女性文学”是否具备女性特有的艺术属性,吴黛英认为,女性文学迥异于男性话语下的传统文学,具有“美”的特质,即“美的内容、美的意境、美的语言”,且女作家更擅长于内心描摹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1)王福湘提出质疑,认为艺术美、心理描写、意识流等并非女性所特有;新时期女性文学丰富多样,错综复杂,“对它的评价不能简单化、概念化,也不能感情用事,以偏概全”(12)。此后李小江《为妇女文学正名》、禹燕《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兼论什么是“女性文学”》、顾亚维《时代的女性文学》、陈惠芬《性别——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内结构”》、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等文章,(13)可看作是关于这一讨论的延续和深化。这一争鸣关系到如何认识“女性文学”的基本内涵和特质,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学理性探索。 又如关于“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讨论。1986年,男性学者孙绍先对女性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寻找男人”这一文本现象提出批评,主张“妇女题材文学应该大力探讨妇女自身的独立价值,彻底冲破精神心理上的依附感”(14)。钱荫愉在《她们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再反思》中提出商榷。她将妇女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处境作为考察的重点,认为“两性的平等摆脱不了种种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科学发展等方面的限制,社会还没有为妇女单方面实现强者意识提供普遍性的可能”(15)。孙绍先再次发文,指出单纯强调女性性别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默认了传统性别文化的男性霸权,从而使女性沦为“第二性别”、“特殊性别”。女性文学的目标之一便应是打破这种传统性别观念。(16)这一讨论所聚焦的问题牵涉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界仍然一再被提出。 关于“两个世界”的讨论同样如此。1986年,女作家张抗抗提出女性文学创作要同时面对“两个世界”,即外部宏大的社会历史世界和妇女独特的内心世界。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首先是人,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而妇女的解放也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妇女问题”(17)。吴黛英则认为,男女两性在心理、生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等方面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承认性别意识、性别特征的存在是定义女性文学的基本前提。(18)这一讨论提出的问题关联着如何理解“女性”与“人”的关系,如何看待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解放是否应当纳入人类解放的框架之内,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是在参与者相互尊重、诚恳而理性的氛围中展开的。尽管讨论所涉及的话题当时并无定论,但它不仅激发、活跃研究者的思维,而且有助于引起读者对性别与文学之间关系予以更多的关注。直到21世纪的今天,相关思考仍在延续,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性别问题来自社会历史深处,颇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批评活动中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 1981年,夏衍在为李子云的评论集《涓流集》作序时,特别提及女性批评家的稀少,他遗憾地写道:“有了这么多的女作家,却很少听说有几位女评论家。”(19)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极少有女性的身影,类似李清照《词论》那样的著述实属凤毛麟角。明清之际江南才女参与文学批评活动稍多,但总体而言女性的声音微乎其微,在批评史上是无足轻重的存在。晚清以降,现代中国的女权思想以及女性主体认同“在‘人权’与‘国家’的张力中被建构”(20),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在这种同构中,女性主体性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缺失状态,文学领域的研究主体也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80年代女性批评群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特别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体现。 一些女学人尖锐指出女性创作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文化境遇。苏者聪《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指出,古代特定的社会文化是导致颇具才华的女作家们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同时造成了妇女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空白的现象。(21)王友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聚焦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妇女问题的关系,认为如果忽略了女作家的创作,就“失掉了现代小说中一个很有光彩的部分,遗落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历史财富,并且也难以为当代文学的有关问题找到一个恰当的起步点”。(22)钱虹《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写道:“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勾勒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概貌,是极不完整又粗陋不堪的”。该文在重审文学史的思路下,以较为翔实的史料阐述了陈衡哲、绿漪、白薇、方令孺、苏青等长期为文学史所忽略的现代女作家的文学贡献和影响。(23) 女性批评活动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立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及其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关注妇女解放以及现实语境中的妇女问题。季红真在分析新时期小说主题时概括说:“许多作家,主要是女作家特别敏感地意识到,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标志。她们对现存社会伦理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道德观念的思考,就自然地集中在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上。”(24)刘慧英《社会解放程式:对女性“自我”确立的回避——重读〈白毛女〉及此类型的作品》对妇女解放文学表述的内在话语逻辑进行考察,指出《白毛女》等作品中的“妇女解放”是置于政治话语之下的,而女性自身的诉求,即“个体的存在价值、自觉的行动选择以及自我意识等”(25),则被社会、政治的强势话语所掩盖。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一书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妇女文学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承载着文学的双重使命:“一重是解放妇女的社会责任,另一重是坚定女性主体的艺术使命”。作者十分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问题,她的《当代妇女文学中职业妇女问题——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一文,讨论了“有知识的职业妇女”在“女性雄化”、“多元角色冲突”等现实处境中的性别体验及其文学表述。(26) 处于相对敏感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对历史的反思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建构成为80年代文化活动的重要维度。一些女学者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立足于女性主体,剖析所谓“雄性化”和“女性气质”。金燕玉《论女作家群——新时期作家群考察之三》指出,1949年以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偏于“刚气”,而“文革”更是将这种“男女都一样”的“女性雄性化”推向极致。新时期女作家创作的突出价值就是逐渐恢复了女性自我意识。论者认为,“中国新时期女作家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深度。它来自对长期以来社会女性意识淡薄的反抗,又在对人、对个性的思考中获得深化”。(27)盛英《爱的权利·理想·困惑——试论新时期女作家的爱情文学》从“强权政治对于爱情的扼杀”这一视角来认识新时期女作家爱情文学的特点及创新,认为爱情在女性生命体验中的复位是女性主体摆脱了“雄性化”、“无性化”的历史束缚,重获爱的权利和自我价值的重要表现。(28)女诗人翟永明在诗论《黑夜的意识》中提出,女性文学从来就内蕴着三个不同趋向的层次。在女子气——女权——女性这样三个高低不同的层次中,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是后者。“女性”的文学才是最高层次。“进入人类共同命运之后,真正女性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赖以传达的独有语言和形式,构成了进入诗的真正胜境的永久动力。”她将个人、宇宙的内在意识称之为黑夜意识,认为黑夜意识是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女诗人将这种承担注入诗中。几年后,她在《“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中,对相关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思考。(29)王绯《女性气质的积极社会实现——读〈女人的力量〉兼谈女性文学的开放》、李小江《寻找自我——当代女性创作的基本母题》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女性气质”对女性文学的意义和影响。(30) 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质疑、颠覆和反抗,尤为突出地体现出女性批评的主体意识。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指出,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对抗性两项关系中;“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生存在“黑暗、隐秘、喑哑的世界”(31)。吕红《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兼及〈金瓶梅〉的道德与美学思考》对小说《金瓶梅》做出了颠覆性的解读。文章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金瓶梅”们作为艺术形象的特定价值,不应被传统道德观判了死刑的“淫”的表象所掩盖和抹杀,而对人物的道德批评也不可代替对文学的“历史”与“美学”的评价。“金瓶梅”们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纯粹从自然而非道德角度描写女性世界的新领域。(32)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一文则是针对男性书写的历史(history)的批判与反驳。在论者看来,历史记载和文学描写中的妇女形象(比如“家庭的天使”)渗透着男性的偏见与臆想,而简·爱不承认传统的妇女美德,不肯扮演女人的传统角色的人物塑造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女权主义宣言”(33)。黄梅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中,对男性传统阅读经验中女性人物类型的两极——“不是贤媛,便是荡妇;不是天使,就是恶魔”,做出了反思。(34)王绯《缠足文化的迫力——说说〈三寸金莲〉》、于青《两性世界的对立与合作——谈女性文学的社会接受与批评》、刘慧英《淫荡乎,贞洁乎——两种传统女性类型的对立和转化》等文,也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传统男权文化和性别压迫的质疑和批判。(35) 对妇女研究/女性文学批评本身的自省,同样是女性主体精神的反映。其中隐含了女性批评主体在理论建设方面的自觉。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可视为自觉地从性别视角出发思考文学理论建设的滥觞。王绯《批评:多轨道的向心运动——兼谈女性批评家的批评意识》讨论了“女性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及独特性,认为在至今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批评界,最应得到这种自我暗示的应当是女性。女性批评应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存在,应当提出女性批评的自觉意识和自主意识的问题(36)。王友琴指出,“就妇女问题而言,事关切身利益,然而女性作者未必就持有更正确的看法,她的作品也未必体现出更多的‘妇女意识’”;“妇女的处境是妇女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面,在这种处境中形成的妇女的心理状态是高一个层次的问题”(37)。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主要探讨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展开的妇女研究与伴随女性文学发展而兴起的女性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宏观的把握,缺乏历史感,理论素养欠缺,具有深度的研究较少等。(38)这是来自80年代女性批评实践现场的反思,显示出女学人对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提升自身研究水平的愿望。 三、女性主体批评实践的特点和价值 女性文学研究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后。与之相比,80年代的文学批评作为其先声,时效性更为明显,与文坛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此期一批优秀女学人以“对话”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此为特点之一。 其间,两位资深批评家李子云和盛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子云在80年代文坛颇具影响力,一批年轻学人和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她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她的部分文学评论,1984年辑为《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论》一书出版。作者对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张抗抗、戴晴等在当时文坛引起关注的女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细致分析女作家创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以读者身份诚恳地对作家创作提出建设性意见。比如,“希望张洁的创作道路开拓得更广阔些,现实意义更强烈些,作品的容量更大些”;希望文坛新秀王安忆体会和理解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追求精神上的深刻和艺术表达上的“力度”,而戴晴则需要在未来的写作中尽量克服太过“粗糙”、“直白”的缺点。(39)李子云还与同时代许多女作家保持通信交流,例如,《致铁凝——关于创作的通信》、《关于创作的通信——与程乃珊谈创作》、《同一社会圈子里的两代人——与女作家李黎的通信》(40)等。这些“通信”既有针对作为收信人的作家及其创作的评说,也不乏关于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文学文化现象的讨论和交流。借助“通信”,实现了批评家和作家的直接对话,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认识和了解当代女作家及其创作的机会。 盛英也是80年代较早开始关注女性创作的批评家。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和创作研究者,她热情扶植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女作家,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审美判断力。她的《真诚的追求——读部分青年女作家小说随想》一文,论述了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青年女作家在知青题材、爱情题材创作中展现的柔美、细腻、浪漫和温情,认为这些年轻女作家以鲜明的女性气质彰显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同时“愿站在女性立场,呼吁妇女的自立、独立精神,赞美妇女的自我牺牲情操”(41)。盛英还就柯岩、韦君宜、陆星儿等一系列女作家的创作发表了评论,体现了对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深切关切和期许。她的25篇评论收入后来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一书中。特别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是,从1985年开始,盛英秉持在文学活动中凸显女性意识、倡导性别平等的理念,主持进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编写。这是一部具有填补现代女性文学史空白意义的厚重之作。尽管因出版经费原因,该书迟至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夕才得以问世,但主要的编写工作在8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42) 特点之二,这一时期的理论资源、批评观念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并存、新旧杂糅的特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特别是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原则,在部分女性批评主体的实践中仍占有主导位置;第二,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人道主义、新启蒙思潮对女性批评群体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第三,一些女性批评主体尝试吸收和借鉴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理论和批评方法,运用于女性创作研究,呈现了文学批评的新形态。 翻阅当时女作者的文学评论和学术论文可以看到,在8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理论热出现之前,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实践尽管在对象的选择、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等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但大多并未真正建立起文学研究的性别维度。一些时候,研究者面对女作家的创作,采用的仍是偏于“传统”的思维和评价尺度,“性别”没有能够作为文学批评的有效范畴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研究就一定是过时、“落伍”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静下心来认真品读或许可以感受到,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不再应时的研究成果,仍有着值得汲取的优长。一方面,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批评活动留下了具有时代现场感的思想文化材料,其中不乏颇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信息;另一方面,批评个体在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审美眼光、理论兴趣以及研究意图等所做出的阐释和判断,理所应当是丰富的存在。 特点之三,此期女性主体展开的文学批评在关注作品内容的同时,比较普遍地注重文学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表现。比如,李子云非常关切女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表现力。她说,“读宗璞的作品,是一种高度的美感享受”,能够“提高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这便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她强调“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必须以艺术形象本身的力量感人,仅仅动人以理是不行的,必须先动人以情,在使人动情的过程中引人思考”。她的《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一文,将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格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女作家在当代文坛的独特贡献。(43)吴宗蕙从“女性形象”塑造的角度考察王安忆短篇小说《流逝》,对小说主人公欧阳瑞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44)其他很多研究者也是如此,如牛玉秋《女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中的新探索》、陈素琰《美丽的忧伤——舒婷的〈惠安女子〉》、王绯《在梦的妊娠中痛苦痉挛——残雪小说启悟》、任一鸣《女性文学一种新的审美流变——“荒诞”》、季红真《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艾云《把女人的性别发挥到极致——论〈玫瑰门〉中的司猗纹》等文章,侧重点均在于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质地。(45) 特点之四,部分研究实践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反思精神。如乔以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一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古代女性创作的历史文化土壤,在传统思想文化的脉络中把握古代女性创作的特征,指出深层文化心理建构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值得探索。(46)于青认为,女性文学作品通常是“从社会文化中寻找女性的社会化缘由及其生成”,缺少“从女性自身去反射和反馈社会文化”。而张爱玲、施叔青、刘西鸿等人的作品能够以女性独有的视角探讨和审视女性意识的文明进化与变革,体现出对深层历史意识的探寻和思考,是女性文学发展脉络中不应忽视的重要收获。(47)针对当时研究实践中逐渐兴起的在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框架下阐释本土文学的现象,马婀如在《对“两个世界”观照中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兼论中国女作家文学视界的历史变化》中提出,“目前,在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把西方女性文学作为研究参照,这对开阔人们的视野、更新研究的方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但西方女性文学是在西方特有的政治、文化、妇女生态土壤上开放的文学之花,它们不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楷模,更不会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归宿。中国女性文学完全有条件、有理由具备我们时代和民族的特点”(48)。其他一些女学人也有相关阐述。虽然此时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命题尚未十分明确地提出,但她们对于如何恰当地借鉴西方理论已有自觉的思考。 总的来说,80年代女性批评主体并非以对抗性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场域,而是基于逐渐建立起来的性别自觉,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着传统的文学批评格局。反映在批评文本上,女性评论者既可能与男性批评家持有相近的批评理念和审美判断,也可能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理论方法的运用以及文本的解读乃至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女性批评群体内部同样存在诸多差异。80年代女性批评主体的文学实践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仍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 首先,对性别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往往倾向于男女两性二元结构,有本质主义倾向。其次,由于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与研究对象之间关联密切,在未能自觉拉开必要距离的情况下,有时对理性判断带来影响。再次,批评主体的理论修养不足,影响到研究的深度。而无论是成绩还是不足,都为推进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987年,有文章写道:“在我国活跃在批评领域的女性批评家的队伍还是十分弱小的一支,就整体而言,两性批评家在视野的成就上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但是批评的世界里毕竟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女性的声音,这预示着女性文学批评将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文化,向世人表明新理论态度的可能。”(49)这里所说的“可能”显然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它关系未来。在回顾女性文学批评历程的时候我们当记得,80年代,一批女性先行者在文学领域为了文学,也为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①林树明:《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评论中的性别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部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989年出版。 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白舒荣:《十位女作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④刘慧英:《谈女作家作品的主题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3期。 ⑤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⑥陈惠芬:《从单纯到丰厚——王安忆创作试评》,《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⑦陈素琰:《论宗璞》,《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⑧王淑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⑨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⑩林丹娅:《试论庐隐创作个性中的“自我”》,《福建论坛》1983年第3期。 (11)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12)王福湘:《“女性文学”论质疑——与吴黛英同志商榷兼谈几部有争议小说的评价问题》,《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2期。 (13)李小江:《为妇女文学正名》,《文艺新世纪》1985年第3期;禹燕:《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兼论什么是“女性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5期;顾亚维:《时代的女性文学》,《文艺评论》1986年第2期;陈惠芬:《性别——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内结构”》,《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14)孙绍先:《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15)钱荫愉:《她们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再反思》,《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2期。 (16)孙绍先:《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兼与钱荫愉等人商榷》,《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17)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18)吴黛英:《女性世界与女性文学——致张抗抗信》,《文艺评论》1986第1期。 (19)李子云:《涓流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页。 (20)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姚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21)苏者聪:《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22)王友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3)钱虹:《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24)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 (25)刘慧英:《社会解放程式:对女性“自我”确立的回避——重读〈白毛女〉及此类型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26)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0页;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中职业妇女问题——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27)金燕玉:《论女作家群——新时期作家群考察之三》,《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3期。 (28)盛英:《爱的权利·理想·困惑——试论新时期女作家的爱情文学》,《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1期。 (29)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诗歌报》1986年11月15日:《“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第6期。 (30)王绯:《女性气质的积极社会实现——读〈女人的力量〉兼谈女性文学的开放》,《批评家》1986年第1期;李小江:《寻找自我——当代女性创作的基本母题》,《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6期。 (31)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32)吕红:《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兼及〈金瓶梅〉的道德与美学思考》,《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33)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34)黄梅:《“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读书》1987年第10期。 (35)王绯:《缠足文化的迫力——说说〈三寸金莲〉》,《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6期;于青:《两性世界的对立与合作——谈女性文学的社会接受与批评》,《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刘慧英:《淫荡乎,贞洁乎——两种传统女性类型的对立和转化》,《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 (36)王绯:《批评:多轨道的向心运动——兼谈女性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批评家》1986年第6期。 (37)王友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8)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 (39)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3、48、214页。 (40)李子云:《致铁凝——关于创作的通信》,《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关于创作的通信——与程乃珊谈创作》1984年第7期;《同一社会圈子里的两代人——与女作家李黎的通信》,《读书》1986年第5期。 (41)盛英:《真诚的追求——读部分青年女作家小说随想》,《朔方》1984年第3期。 (42)盛英:《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43)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灵——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读书》1982年第1期;《有益的探索——张抗抗的小说读后》,《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 (44)吴宗蕙:《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评〈流逝〉中的欧阳瑞丽》,《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45)牛玉秋:《女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中的新探索》,《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陈素琰:《美丽的忧伤——舒婷的〈惠安女子〉》,《名作欣赏》1987年第1期;王绯:《在梦的妊娠中痛苦痉挛——残雪小说启悟》,《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任一鸣:《女性文学一种新的审美流变——“荒诞”》,《艺术广角》1988年第1期;季红真:《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艾云:《把女人的性别发挥到极致——论〈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46)乔以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47)于青:《来自历史深处的关注——对女性文学女性视角的思考》,《东岳论丛》1989年第1期。 (48)马婀如:《对“两个世界”观照中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兼论中国女作家文学视界的历史变化》,《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49)王绯:《女性文学批评:一种新的理论态度》,《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读书论文; 王安忆论文; 历史论文; 李子云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