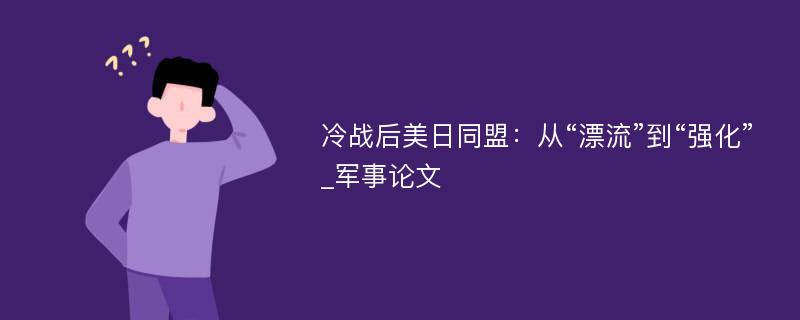
冷战后美日同盟:从“漂流”到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战后论文,同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35X(2006)03—0012—05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国,美日双边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进遏制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美日关系内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分歧,但双边军事联盟体制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逐步弱化,反而出现了不断巩固和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并继续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地区形势发展的关键性因素。21世纪初,美日同盟的发展方向将会是怎样的,以及美日韩体系能否构成新世纪东北亚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权力运作主体,对于未来东北亚安全结构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美日同盟的缔结:现实主义的安全合作观念
现实主义理论对安全合作持消极态度。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关注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必须采取自助(self-help)或联盟(alliance)的方式。在这样的体系中,各国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安排(同盟或联盟)进行合作,以增进他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1]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对国家结盟的动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结盟与势力均衡密切相关。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互竞争环境中的主权国家为确保或改变自身的相对物质实力地位,可以做出三种选择:其一,增加自身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自己的权力之上;其三,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其他对手的权力之上。第一种选择的结果是引起军备竞赛,第二种和第三种选择的结果就是结盟。[2] 从17世纪近代国家出现到一战爆发的这段时期,是国家之间建立正式军事同盟的活跃时期,“安全因素构成了同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动机”。[3] 一般说来,弱小国家利用同盟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强国则利用同盟关系调整国际体系。强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寻求同盟国,以确保在一定区域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美日同盟作为一种军事安保关系,它产生的动机亦是如此:它是确保美国对东亚地区具有主导权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护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
二战后,美日两国通过缔结《美日安全条约》(1951)、《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以及《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1960),形成了美日军事联盟体制。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两个支点,美日同盟和美欧同盟构成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两大核心,是其谋求欧亚大陆主导权的重要工具。在冷战期间,这一同盟体系的主要任务是遏制其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于日本而言,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表现出擅长依附于大国的个性。19世纪末以来,它曾相继同英国、德国和美国结盟,除了在二战时期与德国结盟遭到惨败外,与另外两国结盟都获得了成功。冷战后的美日同盟关系是日本建立一切对外关系的基石,在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驻日美军的存在,使日本可以从容地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国内经济建设,推动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根据是否具有近似的能力和力量或者是否做出近似贡献的条约,同盟分为对称性(symmetric)、平等(equal)与非对称性(unsymmetric)、不平等(unequal)同盟。具有近似的综合国力的国家之间的同盟是双边的、对称的,而且存在着平等的义务与期待。在力量对比上差距较大的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同盟是不对称的,存在着不平等的义务与期待。[4] 从这一意义上说,美日同盟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不平等同盟。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优势,排斥盟国,从单独军事占领和控制对日管制机构两方面实现了对日本的独占。[5] 281951年9月8日,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条约》,规定“由日本授予、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陆、空、海军之权利”;“驻日美军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可用于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1952年,双方又签署了相关行政协定,规定驻日美军、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均享有治外法权。作为一个不平等的军事同盟条约,《美日安全条约》使日本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和限制,是战后美日非对称性同盟的法律依据之一。[5] 1951954年3月8日,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有:日本“履行日本政府依照美日安全条约所承担的军事义务”;日本在其经济条件许可的限度内“对于发展和维持其自身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做充分的贡献”;日本向美国转让美国需要而又缺乏的原料和半加工材料;美国尽可能“在日本采购供应日本及其他国家使用的供应品与装备”,“并向日本防务生产工业提供情报和便利其技术人员的训练”;日本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等。[5] 201这一协定使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日本的军事工业也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得到迅速发展。
二、美日同盟的“漂流”:非对称性同盟的困境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组成同盟以实现某种预期目标时,每个国家都会考虑单独行动同成为同盟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效益的差异。各国结盟的原因在于预期的收益大于所负担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的关系是由一国与其最有可能的对手之间的实力关系决定的。一旦同盟成立,同盟国之间就会进行广泛而持久的讨价还价,以实现同盟利益的最大化,应对敌国的安全挑战。这样就会产生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的“被抛弃的恐惧”(特别是对于被保护的一方来说)和“被拉下水的恐惧”(对两个当事国来说卷入对方战争)。前者是担心在需要获得必要的援助之时,也许对方会撒手不管;后者是正好相反,在不想介入的情形下,担心会被迫卷入同盟国的战争。[6]
冷战结束后,曾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标的美日同盟体制是否应该维系下去,一时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乔治·利斯卡和威廉·赖克曾论述道:一旦达到目的,同盟就会解散,原因是成立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某事”。[7] 著名战略家托马斯·麦克纳格和乔治·凯南也都认为,伴随冷战的结束,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意义和现行的防卫政策本身应该进行重新研讨,既然共同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就应该解散美日同盟。[8]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则认为“获胜的同盟必将伴随胜利的到来而崩溃,胜利越是具有决定性,崩溃也就越具有必然性。”[9]
在日本国内,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美日经贸摩擦的加剧,要求摆脱在美日同盟中不平等地位的声音此起彼伏。冷战结束前夕的1988年,依靠美国的力量重新崛起的日本GNP占世界之比从1960年的2.8%上升到15%,而美国则从33.3%下降到21%;日本的海外净资产累计达2917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累计达5325亿美元。[10] 与此同时,美日贸易摩擦的广度、深度和频度都远远超过了从前。两国贸易摩擦开始呈现出政治化趋势,上升为国家关系层面的问题(National issue)。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学界和民众日益表现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布什总统,提出以日美欧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日本学界则提出了弱化同盟的主张,认为美日同盟限制了日本的发展,使之陷入同盟困境(alliance’s dilemma)——即在弱小国家与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同盟关系中,弱小国家得到大国的安全保障而在自治权方面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中对美国不满的情绪也迅速蔓延,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一书中,呼吁日本人抛弃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和屈从美国的意识,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1994年日本《通口报告》提出了“多边安全保障结构”的概念,主张应“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建立起在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主要国家合作集体处理冲突的保障体制。[11] 对于这一报告,美国非常敏感地认为这种多边主义的实质在于“减少对美国依赖,进而将从两国防卫合作中逃逸。”[12] 1994年美国的《核战略评估报告》立即对日本离心倾向发出了警告,美日矛盾与分歧更加突出,加之日美经贸摩擦的加剧,使同盟处于一种“漂流”状态,面临着解体的危机。
三、美日同盟的强化:霸权稳定模式的选择
在冷战结束之初至1994年,美日同盟处于一种“漂流”状态。但是,它却没有像很多战略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自然地消亡,也没有人为地消失,而是以某种“新战略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从美国的角度分析,随着美日摩擦的加剧,美国官方和主流学派逐渐认识到,日本正试图变为“普通国家”,“压住瓶塞”——即努力维持现状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应适应日本的崛起,这样才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强化美日同盟与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一致的,其利益主要有三:第一,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这一地区(阻止针对美国的霸权国家或联盟);第二,使这一地区保持适当程度的秩序和稳定(确保美国的介入);第三,维护经济利益,确保美国的自由贸易和国家繁荣。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维持同盟现状”派认为当前的同盟能最好地为美国服务。因为,美国可以使用日本的基地,美国军队能对亚太及其更远的地区突发性事态迅速做出反应。同时,美国对日本及其他亚洲盟国的安全承诺使日本安心并使他们秉承适度的防卫政策,这又使那些对日本战略意图和能力心存疑虑的亚洲国家感到安心。这一观点因其维持了同盟的不对称性——美国占据支配地位,日本屈从从属地位——而成为许多美国人的首选。[13] 有鉴于此,1994年10月,美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新任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奈氏倡议”,建议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关系进行广泛的双边审议,建立一个“超越一般利益的、具有增强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战略”,主张必须正确面对一个“大国化”的日本,“笼络日本”,反对“敲打日本”和“封锁日本”。奈氏的上台成为美国重新思考同盟关系的一个标志。1995年《美国国防部美日安保关系报告》和《美国东亚战略报告》都对日本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日本是主要支持国家中最出类拔萃的”。[14]
从日本的角度分析,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它感到自己在东亚谋求霸权的目标受到了重创,而强化美日同盟才是其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基石。通过同盟的调整与强化,日本既可以保障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为实现政治大国地位提供军事支持;还可以通过美国的“以台制华”等政策对中国进行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日本政局的日渐保守化和右倾化也为强化军事同盟提供了政治基础。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两国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标志着同盟关系得到深化。1997年9月,两国签署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规定发生周边事态时,两国相互合作的领域多达40多项。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新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完善并深化这一同盟关系。200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2001年度-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日本的防卫费用总额在2001年度至2005年度内将达到25.16万亿日元的规模,并主要从改编自卫队体制、更新装备、提高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及与美军联合作战能力等3个方面来加强防卫力量的建设。
2000年,美国推出“阿米蒂奇报告”——《美国和日本:共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塑提出了7点建议:1.美国应该明确“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防卫负有责任和义务”,日本也应该成为对等性(负有保护美国的责任和义务)的同盟国;2.为使安全保障条约发挥切实的机能,日本应该沿着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确定的方向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制;3.必须密切加强美日军队的具体合作,使之能够共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4.日本现行的国际维和法限制太多,日本应该取消这样的限制;5.以维持应对危机能力为先决条件,尽可能地削减包括冲绳在内的驻日美军基地;6.美国应该优先向日本提供与防卫相关的技术,鼓励美日防卫产业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7.推进弹道导弹防御的有关合作。其主导思想是美日由“负担的共同分担”向“权力的共同分享”转换。[15]
“9·11”事件后,美国意识到,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整合国际社会,达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就需要依靠盟国的力量,辅助其推行全球战略。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但是由于其身陷中东地区,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控制伊拉克局势和威慑伊朗。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主要盟国的日本,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日益显示出特殊的战略意义。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指出“联盟与多边机构能够增加爱好自由的民族之力量。……没有盟国和朋友的持续合作,美国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具有持久的效果。”[16]
21世纪初,日本政府加快了开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步伐。2002年12月,在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004年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NMD)之后,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随即声称日本将把日美两国正在研制中的TMD推进到开发和部署阶段。2003年6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资从美国购入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构筑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和地基末段防御系统组成的双层防御体系。同时,日本开始效仿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并不惜冒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
为了适应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需要及新军事变革的形势,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顺利通过作为今后10年(2005-2014年)日本防御力整备指针的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下一期《中期防御力整备计划》(2005-2009年)。这一防卫政策指出,日本的国防原则已“从单纯的自卫走向全球性战略”。[17] 这是二战以来日本自卫性军事政策的大逆转,表明它将摒弃“和平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和路线,采取更加自主化的军事政策,彰显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预示着一股可怕的军事暗流正从日本向亚洲乃至全球蔓延开来。
2005年2月19日,美日发表《美日共同声明》,公开宣布两国在亚太地区的12项共同战略目标中,涉及中国的有3项(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海问题以及中国军事事务透明化),涉及俄罗斯的有2项(鼓励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扮演建设性角色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涉及朝鲜半岛的有2项(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美朝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是日本首次公开将中国台湾以及俄日北方领土、朝核危机等问题列入两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是对1997年《周边事态法案》的细化,标志着美日军事同盟已彻底变质,美日同盟关系已不再仅仅是日本继续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为日本提供核安全保护伞的双边关系,而成为美日共同谋求亚太霸权的手段和工具。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同盟的维系与变革实际上代表着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重塑新的安全体制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核心、以多边安全为补充的霸权稳定模式。根据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观点,霸权秩序有3种:(1)建立在强制性支配的基础上,弱国和二流国家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积极要求推翻这种秩序;(2)建立在最低限度的利益融合基础上,支配国或许可以为从属国提供一些有用的“服务”,如安全保护或市场准入,从而防止从属国推翻现有秩序,美国为西欧、东亚和中东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就属于这种形式;(3)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秩序的等级完全模糊,权力的运用真正受到制度的限制,政治互动的进程包容在一起,是一种准规则化的、开放的、温和的霸权。美国的霸权就属于第3种。二战后,美国缔造了国际安全、政治、经济的制度网络,并借此将明显不对称的权力体系转变成更遵守准则的、有节操的、互相都更能接受的秩序,其特征是多边主义。[18] 也就是说,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组织等4个核心领域的霸权地位,构筑起了相对完善和稳定的美式霸权体系(Pax-Americana)。
按照已有的霸权理论模式,每个霸权体系在建立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霸权的挑战者与之相抗衡,霸权国家与挑战者之间的这种斗争,将会对整个霸权体系带来全局性的影响;而霸权国家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限制和削弱霸权的挑战者,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19] 美日同盟关系的这种结构性调整,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美国所认定的霸权挑战者,或至少是潜在的挑战者。美日同盟强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美日在核心利益——联合防卫挑战者的目标达成一致之后,共同谋求东亚霸权的过程。正如摩根索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是否采取结盟政策,它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结盟能否维系取决于盟国之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2] 美日同盟的强化,必将打破东亚地区的军事战略平衡,促使中国与美日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