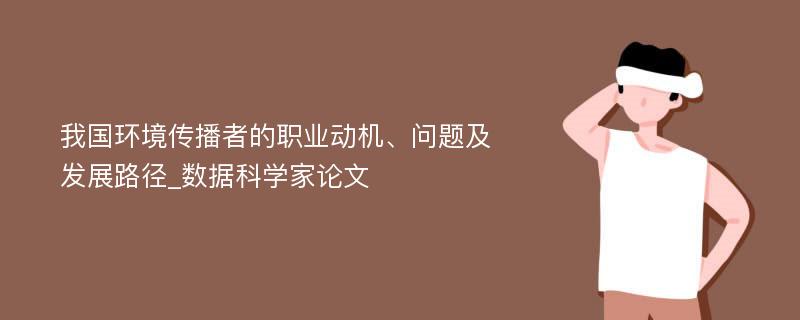
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职业动力、问题及其发展径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业者论文,动力论文,环境论文,我国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05—0163—07 从新闻传播的信息生产角度来看,我国现在从事环境传播的人员主要集中于媒体环境新闻记者与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成员这两大类人群当中。从理论上来说,前者从事大众传播活动,后者主要从事人际传播活动,属于传播的不同领域。我们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98份有效调查问卷基础之上①,以此描述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现状、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探索问题解决的径路与逻辑。 一、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的动力系统分析 在环境传播从业者现状各要素的考察中,我国环境传播在年龄结构、知识层次与环保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优势;在环境传播从业者内部,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人员初步形成良性互动。这些都是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所具有的积极的动力特征。 (一)从业者队伍的优势 从年龄结构来看,环境传播从业者以青年人为主体。从样本中环境新闻记者的年龄结构来看,20岁至39岁之间的记者比例为86.3%,青年人占据着主体地位。其中30至39岁这个年龄区间的人最多,占50.9%,超过总数的一半;20岁至30岁之间的青年人为35.3%。40至49岁的记者仅占9.8%,50岁以上占3.9%。ENGO成员也存在同样的优势,样本中20至39岁的从业者比例为74.5%,30至39岁的人达到53.2%。针对我国ENGO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ENGO产生时间较晚,最早的一家是1991年成立的辽宁锦黑嘴鸥保护协会,后来才有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等组织。然而真正有影响力是在引导公众参与怒江建坝、圆明园保护与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一系列事件中。这是2003至2005年的事情了,这些事件传播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参与,ENGO也随之扩张影响力。到2004年春全国已经有3000家ENGO在民政部门登记[1]。 我国之前只有《中国环境报》这样的政府专职部门主管的报纸坐拥环境新闻记者,但主要是以政策导向型的由上往下报道的方式为主。在我国的学术期刊网中,正式把“环境新闻”作为问题研究的是1999年《新闻采编》上的一篇研究环境新闻舆论功能的学术文章[2]。之前的“环境新闻”无外乎是“XX年国内十大环境新闻”、“国际环境新闻组织成立”之类的消息,并没有从环境新闻本身特征出发研究本国问题的文献。因此,我国的环境新闻记者主要是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受中国环境污染现实的影响,还有媒体、ENGO带领公众参与所造就的新的舆论环境。 有资深的绿媒体人认为2003年的科学发展观与建坝之争是环境传播与公众参与之发展的关键年份。这本由一些媒体人对怒江建坝项目质疑和审慎的态度而呼吁一些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中媒体人特别强调公众参与,关键是“正”“反”两方面的知情权,这样才能发挥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南方周末》、《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均深入参与这一“正”“反”知情权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与ENGO一起影响中央政府决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我国正式以调查性报道成立专业绿新闻媒体的是《南方周末·绿色》,创立时间是2009年10月8日。与1986年成立的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意义不同,不是把一群政策性的记者聚集在一起,《南方周末·绿色》是把以问题为导向的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生产主要形式的绿媒体。一大批有理想、有责任感的年青环境新闻记者就是在这样一些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从样本数据来看,目前的环境传播从业者在知识结构、经济水平与价值取向上都有当今积极的时代特征。在知识结构层面,环境新闻记者100%都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其中,有硕士学历的记者达到31.4%,具有本科学历的为68.6%。在这群环境记者中,在环境新闻领域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其中具有6年以下从业经历记者占68.8%,这里1至3年从业时间的为33.3%,从业时间在10年以上的环境记者仅占3.9%。调查还发现,在从事环境新闻记者职业之“最大的动力来源”的选项中,有94.1%的记者选择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太严重,尽自己努力教育公众使情况逐步好转”的选项;仅有5.9%的记者选择了“信仰环保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较为中立的选项。 从ENGO的角度来看,与记者大体相当又各有不同。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本科学历的ENGO人员达到53.2%,硕士占据19.1%。本科以上达到72.3%,占据主体地位。但与环境记者不同的是,ENGO人员里还有27.7%的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其中大专比例为17.0%,高中、中专比例为10.7%。其原因在于,环境新闻记者多受雇佣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媒体部门,对学历的要求比较高;环保组织出自民间多具有草根性质。不过ENGO人员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者达到72.3%的比例已经相当高(由于样本所限,实践情况可能比这数据要低得多)。ENGO人员多数从业时间较短,从事ENGO工作在1至3年间的比例为44.7%,将近一半;从事此行业达10年以上的比例仅为12.8%。ENGO人员从业动机里,有78.7%的人员比例“最大的动力来源”来自“我国的环境污染太严重”;有14.9%的比例“看中非政府组织的前途”;有6.4%的比例“信仰环保的生活方式”。 从总体样本统计数据来看,目前环境传播从业者是一群以青年人为主的队伍,他们高学历、从业时间短、有历史责任感、且敢于直面当前的环境问题。这些特质与西方经历了半个世纪环境运动的较为保守的环境保护群体不同,我国从业者表现出年轻人的朝气和理想,是我国环境传播事业里重要的动力系统之一。 (二)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人员的良性互动 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人员有多方面的良性互动。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新闻记者对ENGO有多方面的依赖,特别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在环境报道采访阶段的取证阶段,ENGO是环境新闻记者首选的被咨询对象。在“如果遇到环境污染的取证问题,您最有可能咨询的是谁?”的问卷调查里,有58.8%的环境新闻记者选择了ENGO成员,有23.5%的记者选择体制内的科学家/专家,有17.7%的记者选择企业里的科学家/专家。同时,环境新闻记者也把ENGO成员作为对抗来自非正义污染方及其利益相关者压力的重要联合对象。在问及“如果您在报道污染时遇到压力,您最有可能联合”(可多选)的选项中,ENGO以微弱劣势(52.9%)排在其他媒体(58.8%)和公益律师(58.8%)之后,比例居于环境受害者(47.1%)之前。环境新闻记者对ENGO的科学数据之信源的使用也有一定的信任度(可多选),有54.9%的环境新闻记者常使用ENGO的数据,低于政府部门(86.3%)、学术机构(78.4%)与亲身调研(56.9%)的数据,但与国际机构IPCC等部门报告持平,高于国内媒体之信源的29.4%,也高于国外媒体的25.5%。可见环境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ENGO作为科学信源表现出很高的信任度。 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人员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因为ENGO人员也同样需要媒体与环境新闻记者。调查数据显示,当ENGO人员在监督污染事件中遇到阻力时,有93.6%(可多选)的受调查者选择了联合媒体,接下来才是公益律师(53.2%)、受害者(42.6%)与环保部门(19.1%)。在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ENGO也对媒体有相当的依赖。调查问卷显示,ENGO从事环保最主要的形式(可多选)是与大众传媒联合(40.4%),其次是自办网络/纸媒宣传(31.9%)与现场调研与宣讲(31.9%)。 从业界的实践来看,这些良性互动现象有其背后的动因。新闻记者与媒体有着广泛的人脉与影响力,作为中国最早环境新闻记者之一的《中国环境报》熊志红认为环境新闻记者可以为ENGO成员提供特殊的沟通渠道,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引导公众支持与参与是发展壮大ENGO的一条智慧之路。2005年环保联合会的数据显示,79.4%的ENGO被媒体报道宣传过;90%以上的ENGO经常组织公众参与民间环保活动[4](P279)。媒体对于ENGO之所以重要,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这样一个法律专业的ENGO之专业知识性很强,在维权活动过程中与媒体合作既可以向公众大面积普及法律知识,提高ENGO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利用媒体提高ENGO的舆论监督作用,限制污染企业的行为;还有监督政府、司法等职能部门在执法中的行为,达到推动法律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进程[5]。 环境新闻记者之所以也需要ENGO,决定于中国这样的媒介环境,即使像《南方周末》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也不例外。该报前环境新闻记者刘鉴强认为绿媒体的生存环境非常虚弱,若没有强大的资源环境新闻记者很难保障其在媒体中的地位。核心信息源需要强大的关系网,环保局之类的信源对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这样的记者有天然的优势,ENGO就是环境新闻记者的天然盟友。又因为受害者容易过度夸大事实,主管部门更容易封锁消息,比之社会化管理角色的ENGO,媒体记者更容易与ENGO联合(刘海英,2009,P45)。从专业知识、人脉与促进公众参与方面,ENGO相对媒体人都有一定的优势。 二、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主要问题与成因 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现有的环境传播从业者面临着的一些问题,当中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人员会有所同、也会有所不同。从二者问题的共同性来说,其发展皆面临着专业知识欠缺与体制方面的约束;不同点在于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问题更倾向于专业领域,而ENGO则更多体现出体制性困境。 (一)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专业困境与成因 首先是专业知识缺乏的困境。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环境传播从业者当中环境科学知识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样本中环境新闻记者之专业背景里新闻传播学以45.1%的比例占据将近一半的比例,其他文科以31.4%的比例处于第二的位置;文科总计占据环境新闻记者总数之76.5%的比例。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背景的记者仅为3.9%,其他理工科学科背景的比例19.6%。也正是这个原因,样本中有25.5%的记者觉得在业务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采访中专业知识的不足。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大学环境新闻教育领域的缺陷。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有49.0%的环境新闻记者认为其环境方面的科学知识都是在职业生涯而不是大学里面学习到的;31.4%的记者认为这些专业知识主要是向专家学习得来的;仅有15.7%的记者认为环境专业知识主要来自于大学阶段的学习。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环境新闻记者多数都没有接受正规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这和我国大学没有环境新闻教育有关。在西方如美国就有这类针对环境科学与新闻学的交叉学科教育。 在ENGO人员领域也具有类似的困惑。这群从业者中文科背景的比例为42.6%,理科为57.4%。很明显地看出,在ENGO从业者的学科背景中,科学素质明显高于环境新闻记者群体,记者群体里文科背景总计占据76.5%的比例。但ENGO人员里,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背景的比例为12.8%,其他理工科背景的从业者比例为44.6%。在文科背景里,新闻传播学科还是占据着17.0%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ENGO人员是由环境新闻记者转变而来的,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汪永晨后来成了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南华早报》的记者马军后来成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主任,冯永锋由《光明日报》记者变成了自然大学的创始人。这些人多是与新闻传播学、汉语语言文学等相关传统文科背景有关。因此,冯永锋就认为很多批评ENGO人员队伍是一群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对“专业化很强”的环境保护根本没有权利说三道四,越是杰出的ENGO领导者(如汪永晨)就越是容易遭受这些“科学迷信主义者”的攻击[6]。 有一小部分即12.8%比例的ENGO人员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学科背景,并或多或少有媒体人经历。天天喜乐传媒人方玄昌就是一个拥有这样专业背景的ENGO从业者。他是吉林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毕业,在《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等媒体供职并从事环境与气候报道长达10余年,在2012年成为“知识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但像方玄昌这样的环境科学领域的ENGO从业者只是凤毛麟角。调查数据显示,48.9%的ENGO人员认为获取专业知识最好的途径是非大学的职业生涯学习;仅有23.4%的ENGO从业者认为获取专业知识最好途径是正规大学专业学习。因此,从专业背景来看,环境新闻记者与ENGO从业者科学知识获取途径异中有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大学教育中缺少针对环境传播从业者的教育。 其次,环境传播从业者科学数据的取证难。作为环境新闻记者,有45.1%的记者心理上最大的压力来源于采访取证;相对于ENGO人员,这一比例仅为12.8%的比例。ENGO人员更关心个人安全与被批评对象的报复,这种压力人数比例为23.4%。科学与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早在1971年的《布鲁克报告》(BrookeReport)首次官方承认对科学中立的社会支持在消弱,而在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怀疑科学的社会立场以及其中立性[7]。因此,如果能够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拥有多样的新闻信息源,将会对科学报道有积极意义。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记者、ENGO成员都是把我国环保部等政府机构报告/新闻的数据作为科学数据源(可多选)的首选,记者比例达到86.3%,ENGO成员为61.7%。接下去ENGO人员与记者的科学信源使用有所不同,ENGO对于科学信源的选择比例分别是其他环保组织为57.4%,学术机构/学术杂志为46.8%,亲身调研的比例为44.7%,使用央视、新华社等党媒的比例为36.2%;记者的高信源使用比例分别为学术机构/学术杂志78.4%,亲身调研者比例为56.9%,国际机构IPCC等部门报告与ENGO使用比例均为54.9%。可以看出,新闻记者比ENGO人员更注重实地调查。 在实践中,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真正可以选择的科学信源并不多。按照科学信源多样原则,西方科学记者可以咨询至少三类科学家,即企业科学家、独立科学家(如基金)与政府机构的科学家,这里独立科学家在形式上的重要性会更大。在环境新闻记者遇到取证难问题,有58.8%的比例会向非政府等民间专业机构咨询信息,向体制内的科学家咨询者比例为23.5%,有17.7%的比例会咨询企业的科学家。ENGO从业者的咨询对象比例分别为,44.7%的从业者会向非政府等民间专业机构咨询科学数据,34.0%的从业者咨询体制内科学家,有21.3%的人会从媒体上查询相关数据,有14.9%的人会咨询企业里的科学家。因此,非政府组织是环境传播从业者咨询最多的机构,事实上这些机构并不专业,因为在ENGO人员里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背景的比例为12.8%。 最后是从业者比例失调问题。这种失调体现在诸多方面,如男女比例、汉族与少数民族从业者比例等。在记者群体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汉族占92.2%,少数民族仅有7.8%的比例;在ENGO从业者中,汉族人数比例占据97.9%,少数民族比例仅为2.1%。我国民族聚居区面积达60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西部国土面积的90%;西部少数民族人口6625.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3%,我国西部发展与少数民族问题息息相关[8]。事实上由于工业西迁,早在1995年西部某些污染指数已经超过东部,当时东西部化学需氧排放分别演变为43%对57%,二氧化硫变为45%对55%,西部已超过东部某些指标成为环境污染重灾区[9]。我国少数民族环境传播从业者的总体稀少表明西部公众环保传播的缺位。女性比例总体偏少是环境传播从业者的又一比例失衡,女性环境记者的比例仅为33.3%;ENGO从业者的比例仅有10.6%。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环保中有着天然的优势,环境权利、公众参与权等都与妇女解放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女性通过家庭来阻止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效果[10]。 (二)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体制困境与成因 首先是法律问题。ENGO从业者对法律身份问题最为担心。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46.8%的ENGO人员认为心理上最大的压力来源于是外部规制,居压力榜第一位,比居于第二位的个人安全的21.3%高出25.5个百分点;44.7%的ENGO从业者认为制约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法律身份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对2768家ENGO身份调查,发现2768家ENGO中,注册登记率仅为23.3%;另外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专家邓国胜教授的调查数据显示,有52%的ENGO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降低登记注册门槛[11]。名不正则言不顺,ENGO的法律身份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也限制了它社会功能的发挥。 环境新闻记者也面临着体制性问题,由于ENGO法律身份的受限,直接导致很多记者身份的“越位”。我们调查数据显示有34.0%的记者认为心理上最大的压力来源于外部规制,仅次于采访取证的48.9%。在实际采访中,采访取证的压力与外部规制有很大的相关性。如我国虽然实行污染的举证责任倒置,但受害者依然具有举证自身污染损害、污染损害行为的责任,且需要在加害人举证之前完成。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污染受害者这些举证能力受到限制,就需要ENGO人员参加。如果ENGO没有法律身份,就需要有记者身份界入。因此,我国有很多环境新闻记者、ENGO从业者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以此来获得跨界资源发出声音,创办之初的自然之友会员中就有100名记者。在中国,媒体、专家、公众是ENGO最常见的资源整合形式与汇聚力量,如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绿岛召集人张可佳都具有多重身份。新闻记者需要有客观的事实,有中立的立场,因此这种身份的“越位”在实践与理论上都处于一种困境中。 其次为市场困境。我国环境新闻记者目前所服务的雇主多是市场化的媒体,以本地大企业的广告主为主要生存依靠,这是目前市场生存的媒介体制所决定的,导致在传统媒体上环境公共论题往往被“低调处理”[12]。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82.3%的记者认为对当地大企业的环境污染报道遇到的阻力最大;有11.8%的记者认为报道本国非本地环境污染阻力最大;仅有5.9%的记者认为自己的污染报道没有遇到压力。另外,由于传统媒体市场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污染这一类别的新闻生产在记者所服务的媒体压力来自于(可多选)诸多方面,各有58.8%比例的记者选择了环境新闻生产周期长、缺少专业人才这两项;有29.4%的比例选择了领导不重视;有11.8%的比例选择了广告主的压力。典型的例子是“绿色和平”2004年揭露金光集团(APP)在云南非法砍伐事件,APP花费大量的公关费用于当地媒体,当地媒体由于市场压力而改变舆论走向,结果是云南省之内外媒体呈现泾渭分明的舆论格局:外省批评APP的非法毁林,省内主要媒体则宣讲APP在华功劳不簿[4](P.56)。 从ENGO角度来看,由于不面向市场,又缺乏体制上的合法身份,它们的生存压力更大。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4.5%的ENGO人员认为制约他们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来源;比排在第二位的61.7%的比例认为缺少人才的选项高出12.8个百分点。我们调查的数据进一步显示,有51.1%比例的ENGO主要经费来自国内项目(可多选),有40.4%的比例主要经费来自国外捐赠,有31.9%的比例来自国内捐赠。从捐赠角度来看,国外的捐赠比例显然大于国内。刘海英也认为国内的草根ENGO的“化缘”主要来自国外基金会或企业捐赠。已有的数据显示,我国有76.1%的ENGO没有固定经费支持;2005年81.5%的组织所筹集经费在5万元以下,有22.5%的组织基本没有筹到经费;因为经费问题所致,有60%以上ENGO没有办公场所(刘海英,张冬青,2007,第287页)。另外,我国的ENGO生存状况的差异很大,像自然之友等大的ENGO在2008至2010年的时间区间里年均获得500万资金,而小的ENGO仅有4万,这种差异严重束缚了绝大多数的ENGO之发展,只能限于少数几个大的ENGO的社会功能与影响力[13]。 最后,环境传播从业者经济收入总体水平不高,有部分人收入甚至处于较低水平,这又造成了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队伍的不稳定性。我们调查数据显示,新闻记者选择“生活富裕、无衣食之忧”(妻儿3至4人的核心家庭收入在15万元以上或从事环保前家产尚丰厚)的比例仅为33.3%;51.0%的比例选择经济状况“一般”(可满足日常花费,核心家庭收入可达10-15万元);也有15.7%的比例选择“经济拮据”(核心家庭收入在10万以下)。ENGO从业者的情况更糟糕一些,选择“生活富裕、无衣食之忧”的比例仅为4.3%;61.7%的比例选择经济状况“一般”;也有34.0%的比例选择“经济拮据”。环境传播从业者这种经济收入偏低的状况,也可能会对舆论导向产生影响,如可能更同情草根阶层,甚至会有仇富情结,这又与新闻注重事实的专业主义精神相悖。 三、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的职业改善径路 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专业困境与体制约束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总是前进的,传播技术的进步也在加快这一进程。 (一)专业困境的突围逻辑 知识需要融合,突破环境传播专业困境要求跨越环境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藩篱。诸如美国的教育早就意识到环境科学知识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故此美国的大学新闻教育在上个世纪末就尝试走科学知识融合的道路。到2006年,美国有50家以上的大学设有环境科学知识与新闻结合的教育新形式。我国大学目前尚未设置环境新闻教育,但早已经开始做科学知识融合的努力。ENGO组织绿家园从2000年起创立“环境记者沙龙”,每月邀请环境科学方面的专家与记者交流[14],已经走了15年的历程,环境记者沙龙这项教育模式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推广,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开展的“环境记者沙龙”的多次培训。这些努力也在我国大学新闻传播学领域进行着有益的尝试,如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自2010年起设立一年一次的“环境新闻与传播论坛”,邀请环境科学家、传播学者与环境新闻记者进行交流与学习。这些努力对我国环境新闻记者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无疑有推动作用。 利用数据库整合大数据促进专业化是当前环境传播从业者另一条改善的径路。IPE的成功及其经验值得分享与推广。该ENGO成立于2006年,以开发“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数据库而影响我国ENGO走向。其基本原理是一个网络数据库的整合,把各级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按要求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整合起来,100多个地级市非常完整统一的数据都在里面,并有排名系统,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并提供查阅服务[15]。马军认为这些数据会给污染源企业带来压力,市场经济社会企业面对这样的压力会设法减少排污,其实就是公众监督起了作用。马军本人是记者出生,国际新闻专业背景,本无环境科学专业知识,但通过数据库整合而成的大数据达到了专业信息传播的目标,甚至无懈可击。基于这个污染数据库,IPE先后开启了“绿色选择”、“PITI指数评价”[16]等更为专业的项目,旨在推动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倒逼那些污染企业及其监管部门履行环境责任,以推动环境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IPE的成功会对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在专业化方面有风向标的作用。 (二)体制转型与环境传播的嬗变逻辑 体制上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十八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等系列阐述是一个方向性的政策变化。专家认为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很多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协调来解决,承担一部分从政府机构中转移出来的职能。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十八大创新管理的一部分,十八大报告对于整个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安排[17]。前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环保的公众参与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突破口[18]。ENGO与媒体如果能够释放出正能量,即可引导民众理性表达、理性参与,这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有很重大的意义。媒体看好这次体制上的变革,认为十八大“创新社会管理”是在推动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公众都应充分发挥作用,社会和公众的参与程度,依赖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19]。 新闻记者“越位”的回归与国际发展逻辑。环境新闻记者同时具有多重身份,如具有ENGO身份,这种状况被认为与新闻专业主义相悖。汪永晨认为法律还不足以保障社会“肌体”健康运行的时候,媒体人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是推动当前环境保护传播有效运作的机制之一。如果法律法规完善与正常之后,中国媒体人的越位阶段就会过去,这种归位是很多媒体人所期盼的[20]。环境新闻记者以ENGO身份进行社会活动,可以在社会交往中拥有环境伦理正义感和环境道德话语权,从而进一步为新闻采访获得一些优势,媒体的阳光报道与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促进舆论的生成与强化监督的力度。这种舆论的倾向性被外界称之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动机值得反思。然而,即使在环境新闻较为发达的美国,这种“越位”也不是太大问题。其实在环境新闻界,更多的学者与业界人士坚持一种“倾向”的学说。特纳广播公司环境新闻编辑芭芭拉·帕里认为,应该放弃客观报道的传统理念,因为全球环境危机是迫切与紧急的,故此观点与倾向早已不可避免[21]。在芭芭拉看来,环境新闻的倾向性是用来警示世人环境危机的很好途径。持相同观点的《缅因时报》(Maine Time)编辑道格拉斯·鲁克斯(Douglas Rooks)与约翰·卡尔(John Cole)认为,环境新闻不属于客观报道,我们也从来没有许诺要这样做。环境新闻之哲学基理与客观说、平衡说不同,你没有办法把作者的观点与问题分开,记者把倾向性说清楚而不是撒谎,这样做记者是诚实的[22]。 ①数据来源于对我国从事环境新闻报道或与环保报道相关的记者、环保非政府人员的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共98份,其中环境新闻记者51份,环保非政府组织人员47份。调查一方面以上海交通大学“环境保护新闻与传播”三届高端论坛为平台展开;另一方面数据来自于对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媒体人员的零散调研。调研的主要时间点分别为2010年12月、2011年3月与2013年6月。因为我国目前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专门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群体,ENGO从业人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故此样本不是随机的,本文主要侧重于对样本的描述性研究。在此之前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文献中还没有对这一从业人群的统计或描述性研究。标签:数据科学家论文; 大学专业选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职业环境分析论文; 媒体从业人员论文; 科学论文; 环保论文; 新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