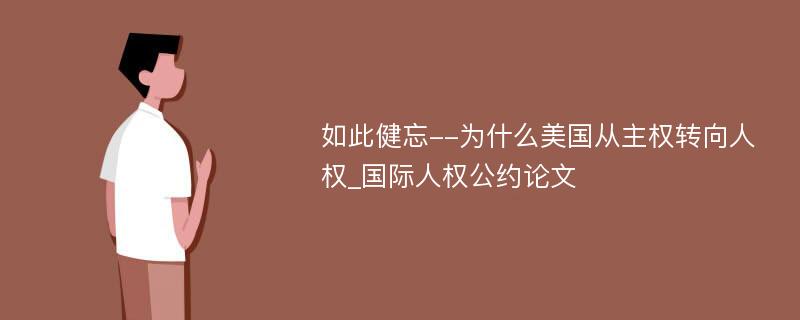
如此健忘——美国缘何从重主权转向重人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健忘论文,人权论文,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挑动一些西方国家多次借人权问题进行反华活动,又屡屡遭到失败。美国在这样做时,似乎淡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自己直到1992年才成为《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参加国,而且至今没有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不是《美洲人权公约》和其他重要的人权条约的参加国。在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后,美国也承担了一些根据条约产生的人权义务,它也是“日内瓦四公约”(指1949年在日内瓦签订的四个公约,即《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之日内瓦公约》)和其他各种规定人权义务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参加国,但是,在批准人权条约(无论是世界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记录非常有限。对于这样一个自诩天生是“人权捏卫者”的国家来说,这似乎十分令人费解,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其原因。
围绕人权的第一次国际政治论战
国际人权宪章的产生同美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际人权事业就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关注。1945年6月签署并于当年10月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为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1946年联合国建立了人权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利诺·罗斯福。1948年6月18日《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后,人权委员会开始按计划草拟《国际人权公约》。公约应对《宣言》中所列举的权利作具体规定,并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上,人权委员会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完成公约的起草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国际人权公约很快成了政治论战的工具。人权委员会在起草公约时遇到的一个主要争论是,是否在同一个公约中,既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条款,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款。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求在同一个公约中包括两组权利,他们认为,若不如此,实际上就贬低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地位。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代表则坚决主张制定两个公约,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能够立即得到实施,而大多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能逐步实现。实际上,政治因素在西方国家的这一观点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它们看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是不可接受的。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美国的影响占了上风,1952年联大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人权委员会起草两份人权公约。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在1953年改变了立场,决定不批准公约。
出尔反尔,不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美国为什么很快从原先支持《国际人权公约》的立场退却,转而对它采取消极态度呢?这与当时美国的国内外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上讲,《国际人权公约》起草之时,冷战已经拉开序幕。在西方国家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全球蔓延,西方正日益受到严重威胁,惟有美国具有能力和意志制止这一威胁。
从美国国内讲,自1948年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从1948年到1960年,即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冷战在国际关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了主导地位。此时,美国国内出现了针对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逆反潮流,其表现形式就是反对美国承担国际人权责任。
二战后初期,种族歧视和各种其他形式的歧视在美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至少并不违法。法律上规定的许多种族歧视出自州法律,其中大多数是在南部各州。种族分校、禁止种族间通婚、在公共服务和设施方面实行种族分离,在美国并不鲜见。杜鲁门政府起初致力于推动国会批准将要问世的国际人权公约,并在国内广为宣传《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绝种族罪公约》)和拟议中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美国的一些民主团体也作出了积极响应。最初以法律诉讼为主要形式的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在此时开始对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提出了挑战。这引起了美国南方种族主义者的担忧,他们担心国际人权条约,特别是《灭绝种族罪公约》,可能被利用来摧毁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政府将凭借这些条约对他们的地方事务进行干涉。这样,南部民主党人同保守的共和党人在国会中联合起来,形成了占优势的保守势力,反对批准国际公约。
保守势力对国内种族制度的担忧与美国社会对冷战的担忧交织在了一起。随着冷战的加剧,反共产主义的保守势力迅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主流。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宣传无异于拆了它自己的台,使它支持批准人权条约的立场变得十分脆弱。
《灭绝种族罪公约》首当其冲。所有反对国际人权条约的主要论点都在反对这个公约时被提出来:(1)条约把低于美国人权标准的条款强加于美国;(2)侵犯美国国内的司法权限,致使主权丧失;(3)导致联邦政府权利扩大,从而侵犯州权;(4)提高共产主义的影响,把美国的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因此,《灭绝种族罪公约》在美国受到了强大的抵制。而且,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为了阻止批准一般的国际人权公约,首先应当击败《灭绝种族罪公约》。
在另一条战线上,1951年9月,出现了美国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布里克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形式上是要求限制总统缔结条约的权力,实际上是与各种利益集团相配合,在宪法上发动一场反对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斗争。这给艾森豪威尔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它当然不愿意以修改宪法为代价来换取参议院对国际人权条约的批准。反对国际人权条约的保守势力达到了目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做出妥协,没有签署任何人权条约。1953年底,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美国不打算批准《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后果对美国的国际人权条约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图以人权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
直到60年代初,美国一直奉行不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政策。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第一次打破了这一僵局。1963年,肯尼迪把三个国际条约——《废止奴隶制和奴隶贩卖补充公约》(以下简称《废奴补充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和《妇女政治权利公约》送交参议院征询意见和要求批准。肯尼迪赞许民权运动,他把这些条约当作对国会的试探气球。但是,参议院直到1967年才就这三个条约举行听证会,而且,这三个条约命运不同:《废奴补充公约》当年就获得批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最终于1975年被参议院一致通过,没有附加任何保留条款,而《废止强迫劳动公约》至今未获批准。60年代中期发生的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和美国的社会结构,使权利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是美国一些人不再像50年代那样激烈反对一切人权条约的重要原因。肯尼迪总统支持民权运动的目标,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全面的《民权法》,取消投票、教育、就业和公共设施各方面的种族歧视。肯尼迪被暗杀后,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7月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国会中保守势力的堤坝被冲开了缺口。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倡导“人权外交”。与此相一致的是,为了表示其政府对促进人权的强烈义务感,他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就签署了三个主要的人权条约:《美洲人权公约》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翌年,卡特把这三个公约连同已经在1966年签署的《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提交参议院征询意见,并要求批准。但在卡特时期,由于被其他一些事件占据了注意力,政府在使条约得到批准方面毫无建树。
1981年里根上台。他的政府对国际人权条约缺乏兴趣,但他在1984年竞选连任的前夕突然决定支持《灭绝种族罪公约》,目的是想吸引始终支持该条约的犹太选民。保守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竭力反对批准《灭绝种族罪公约》,至少要在批准它时附加限制性条款。在附加了保留之后,1988年,争论了长达40年之久的《灭绝种族罪公约》终于获得通过。
1991年,布什政府决定推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3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参加国。另外有五个国家(包括美国)在条约上签了字。布什解释说,该公约所体现的人权原则与美国的人权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批准它有助于美国当前的自由事业,促进世界按美国的人权标准发生进一步的积极变革。由于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支持批准该公约的强大舆论,参议院在附加了一些保留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便于1992年6月批准了该公约,随后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施行立法。这样,在经过40多年的争论和抵制之后,这个国际上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终于于当年9月8日开始在美国生效。
像卡特一样,克林顿赞同国际人权标准,他许诺推动通过有关儿童的国际人权条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也未能兑现。
这样,冷战结束后,美国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频率明显加快,批准条约在国内遇到的阻力大大减小,“承担起在全世界促进人权的领导责任”的舆论在美国形成。
从坚守“主权至上”到鼓吹“人权高于主权”
美国对待国际人权条约的整个过程,从态度僵硬逐渐转变为有所松动;从唯我独尊、自我封闭逐渐转变为要求实现全球普遍一致的人权标准;从被动地消极防卫美国人权逐渐转变为主动地积极向全世界推行西方人权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明显的转折点,它们与美国人权外交的确立和发展历程是一致的。
第一个转折点主要产生于国内因素,以1977年卡特政府把在全球“促进人权”列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为标志。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批准人权条约的理由变得相对简单。“共产主义的威胁”已不再成为反对人权条约的主要理由,相反,人权已经被用来作为在冷战中对抗共产主义势力、尤其是苏联的有用工具。这样,原先所强调的“主权至上”,在观念上逐渐被“人权高于主权”的论点所代替。
第二个转折点主要是由一个国际因素——冷战的结束引起的。冷战因素逐渐减弱,人权更进一步被看作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工具。在美国看来,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不民主的和不尊重人权的,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是民主的和尊重人权的,因此,政治因素仍然在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态度中起作用。
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待国际人权条约的态度来看,还可以作如下归纳:
1.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优越于所有其他国家,美国具有最高的人权标准和最佳的人权保护实践。如果说,战后初期,美国还因自己国内的种族隔离制度而有些理屈的话,那么在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民权革命”之后,美国已确信自己在制度上无懈可击,在人权状况方面与“共产党国家”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美国应当成为其他国家在人权方面的样板。美国的标准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此时主权不应成为推行普遍人权标准的障碍;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却不能因普遍标准而被要求作任何改变,美国国内的司法权限不能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侵犯。美国本身不应受国际条约条款的约束,除非美国法律已包含了这些条款的内容。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始终高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始终被看作是优先的人权。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却不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且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表述。
3.担心州的司法权限被侵蚀和传统的政府制度遭到国际法的破坏,始终是美国消极对待国际人权条约的真实动机。虽然有时扩大联邦权限与维护州权的要求之间的争论与其他政治意图联系在一起,但一般来说,维持州和联邦权力的传统平衡,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反映。正因为此,它过去是,现在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会是美国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主要顾虑。
这样看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权是国内管辖范围内事务”的观点,换言之,“人权是主权范围内事务”的观点,曾是美国抵制国际人权条约的理论依据。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逐渐改变了这一立场。而且它一旦改变了立场,就立即把“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之健忘,常常是令人惊叹的。
标签:国际人权公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