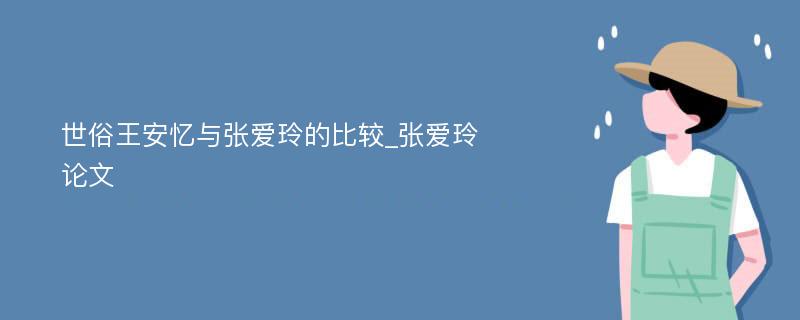
世俗的王安忆——兼与张爱玲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俗论文,王安忆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6-0096-06
2000年初,王安忆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 —《世俗的张爱玲》,其中显示的对张爱玲作品的熟稔和精辟的解析似乎更能证明她是 “张派传人”。尽管王安忆本人曾一再表明自己与她并无多大瓜葛,但“张王比较”毕 竟小有规模,并成为世纪之交文学评论界的一个收获——这一比较在《长恨歌》发表之 后达到沸点,直到她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出现,这两部长篇小说一个质 朴,一个清新,脱尽了《长恨歌》的华美和旖旎,这个时候,人们又觉得她离张爱玲远 了。
一
张王有相似之处,这是毋庸质疑的,“世俗的”这三个字,就可以同时用在王安忆身 上。王安忆对张爱玲最重要的发现,也在于此。读张爱玲的散文时,“我在其中看见的 ,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 喜好。”“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些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 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1](P387)这些话语如果不注 明对象和出处,用在王安忆身上,也不至于引起严重的歧义。《长恨歌》就是典型的“ 世俗的”小说,整部小说其实就是一个接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的连接,它们相 互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并展现着女主人公王琦瑶“结实的生计”和生活的“兴致”,因 此它会被认为是最“张爱玲式”的。
王安忆曾说:“我个人最欣赏张爱玲的就是她的世俗性。”[2](P172)她们都爱对世俗 生活津津乐道,“世俗性”正是她们之间最相似的地方。其实,王安忆看起来似乎比张 爱玲更“世俗”得彻底,张爱玲的小说讲的都是“男女间的小事情”[3](P115),结集 时却命名为的“传奇”——“传奇”这两个字,有不甘平凡的韵味在里面,正是与“小 事情”相悖的。而王安忆的小说没有丝毫的“传奇”因素,更是彻彻底底的“小事情” 。王安忆把生活中的小事情称为“家常”,在许多文章中,可以直接地看到她对“家常 ”的热爱:“《红楼梦》的好,是‘家常’,莎士比亚的好,亦是‘家常’”,“我想 做的就是‘家常’。”[4](P216)散文《台湾的好看》里写到一幅唐人的宫乐图:“写 实的画面,一群操持乐器的宫女围桌面而坐,有拨弦弄管,也有饮茶闲坐,坐姿都很随 便,并不拘礼,和现代的剧场后台无甚两样。”唐朝的宫廷和歌女,本身就是充满了艺 术氛围和传奇性,也是可以好好地点染出其中的悲剧性的,但王安忆要摈弃的正是这一 点,她真正迷醉的是其中的“家常”气氛,因此她评价道:“虽是古时,又是宫中,却 十分日常。好看就在这里。”[5](P234)“家常”这两个字,比“传奇”更为脚踏实地 ,也平凡得多。它与“日常”和“生计”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看得见的人间烟火气息, 是最为平实的人间话语,它贴肌贴肤、丝丝入扣、到处都弥漫着,它合理又和谐地存在 于生活之中,或者它就是生活本身——“‘家常’的东西总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最稔熟的 部分”[4](P217)。“家常”中没有大喜和大悲,它是生活末梢处的细微感受,有时是 一点一滴的细碎的乐趣,有时是朦朦胧胧的浅浅的感伤。与“传奇”相比,“家常”给 人的感觉要温和得多,它是平实、体己、和谐、温暖的,它会让人对生活产生出好感来 。“家常”又是朴素的,即使是上海的舞场,也“其实是听得见隔壁房间里的鼻息声和 咸鲞的气味。”“上海的排场是和寻常日子挤堆在一起,一应华丽都染上了生计的颜色 。”[4](P216)“家常”所追求的不是华丽,而是华丽之下的朴素。
因此,王安忆热衷于描绘最家常的生活、最家常的场景和最家常的人。生活的细枝末 节处,正是最“家常”的地方:“人声嘈杂,楼梯空空地响着跑堂的脚步,窗玻璃布满 了哈气和油烟气”;“透过纱窗,你可看见霓虹灯的粗砺的灯管,还有生了锈的铁支架 ”;“下午四时的太阳,墙上淡淡划了几道树枝的影,有一种闲暇,这闲暇也是‘家常 ’。”[4](P217)《流逝》中一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是家常的,《好婆与李同志》里絮 絮叨叨的张家长李家短是家常的,《“文革”轶事》里兄弟姊妹间的小心眼勾心斗角是 家常的,《逐鹿中街》里的同床异梦和暗地较劲也是家常的。“家常”不是标新立异和 艳光四射,而是可以走入每一个寻常百姓家,与每一个人都有些干系的。《长恨歌》的 好,也好在它的“家常”,小说开篇连续几章浓墨重彩的“弄堂”、“流言”、“闺阁 ”、“鸽子”,正是最最家常的上海的写照。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美中 得了第三名,这个“三小姐”的美也是“家常”的:“照片上的王琦瑶,不是美,而是 好看。……她看起来真叫舒服。她看起来还真叫亲切,能叫得出名字似的。”“好看” 是家常化了的美,有着一股子亲和力,这种美是可以被每个人接受和欣赏的。而她每日 的所作所为、一日三餐,更是再家常不过了:同小姐妹窃窃私语,和父母怄气掉泪,与 友人围炉而坐,炉上炖着鸡汤,油锅哔剥响着,烤年糕片,涮羊肉,下面条,日复一日 的平常岁月。王琦瑶与其说是“上海小姐”,更不如说是一个邻家女孩,她是典型的上 海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她 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 ”王琦瑶是世俗的,世俗性使她同时具备了代表性,她最能代表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她 的魅力和价值也在于此。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家常”,“家常”造就和成全了她, 也成就了这部小说。
王安忆喜欢“家常”,喜欢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喜欢世俗生活的本真形态,颇能与 张爱玲喜欢听“市声”——“非得听见电车响声才睡得着”——媲美,这是她们都“世 俗”的一面。但是,同样的世俗生活来到她们二人的笔下,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却完全不 同。张爱玲无论怎样用词华丽和俏皮,但最后作品的意境总是悲凉的,听到军营里的喇 叭声,即使是“离家不远”,也“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6](P34);而王安忆,看到 鸽群腾上天空,即使是远在他乡,也觉得“那风景之中有了一点肺腑之言,有了一点两 心相知”[7](P10)。说到底,她们还是不一样的。
二
王安忆曾经多次否定自己与张爱玲的“相像”,她郑重地说道:“我和她有许多不一 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8]王安忆将张爱玲的世界观概括为“虚无”,并 且对张“虚无的世界观”和“对世俗生活充满热爱”二者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解释 :
“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 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 ,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8]
对于张爱玲的“世俗”和“虚无”是怎样造就了她最好的小说的,解释同样精辟:
“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 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 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1](P391)
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是出于对悲剧人生的救赎。因为她对世界 的悲剧性的认识,她必须要抓住世俗生活这个救命草,才不至于跌落于虚无的深渊中。 而她的小说也因为这“虚无”的人生观,使“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 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1](P390)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来源于其对具体现实生 活的沉迷和虚无的世界观之间的距离,二者之间遥相对照,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一种强烈 的荒谬感和悲剧感;王安忆也沉迷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但她的世界观则不是虚无的,她 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并不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而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生意义执着 的探求。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写世俗生活的琐事,在张爱玲处,“通篇尽是无聊的”[1](P390)(< 世俗的张爱玲>),但对王安忆而言,世俗生活不仅不无聊、不虚无,而是真正的“市井 之趣”:“市井中人总是高高兴兴的,情绪很好的样子,做人兴趣很浓的样子,内心很 饱满的样子”,“市井生活是没有虚无感的”。[9](P248)她喜欢写“家常”,是因为 她对市井中的人、事和道理都抱有一种认同和理解的态度,这在她的短篇小说中看得尤 为清楚。她的很多短篇小说都称不上有什么故事情节,常常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或 细节,如《小饭店》描述店里一天的人来人往,《酒徒》只是讲一个人如何地爱喝酒, 《小东西》说的是一个美丽的白痴小孩在商场里引起了人们不同的兴趣,《喜宴》仅仅 是描写一场喜宴的始末,王安忆却将这些细节写出一派兴兴头头、过日子的生气。尤其 是《比邻而居》,通篇都描述邻居家通过抽油烟机传来的饭菜香味,这样的细节,王安 忆认认真真、充满兴味地描写出来,如果不是她本人就对日常生活充满兴致,是不能做 到的。不仅如此,她还在小说里对这个特别专注于吃饭的家庭赞扬道:“时间长了,我 对他们还生出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一点不混。”另一篇短篇小 说《聚沙成塔》更能表达她对世俗生活形态的态度:小说的主人公热衷于收集废纸,他 盼望着将废纸换成钱存在储蓄罐里,“这样有一点是一点的积累,无论多么微不足道, 也是看得见,摸得着,是很真实的。他上的就是这个瘾。”如果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孩子 ,这就只是一篇平凡的儿童文学,但“他”却是一个家境殷实的中年男子,就使得这篇 小说带上了不平凡的意蕴:“他的储蓄罐越来越沉了,摇一摇,便发出沉甸甸的响,这 是一种饱满和丰硕的声音,他几乎沉醉了。”在这个短短的故事里,这个成年人以一种 简单和直接的方式领略到了人生的真谛,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我们相信,不仅“他” 沉醉了,王安忆也同样沉醉于这种“饱满和丰硕”的人生之中。正是由于王安忆对平常 人的生活方式充满理解,并发现了平凡生活后面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她的小说才不会像 张爱玲那样苍凉和虚无,而是展现了一种“沉甸甸”的“饱满和丰硕”的人生。这样的 人生当然不再“虚无”,而是充满生气、极具生命力的。
与其说王安忆对世俗生活充满热爱,不如说她真正热爱的是世俗生活背后所隐藏着的 平凡人的智慧和生命力——这就是她称为“市民精神”的东西。对于“市民精神”,她 解释道:“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 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你可以说一般市民的 生活似乎有些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活过来了。”[10](P241)王安忆的人物大多是小人 物,但他们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有的从旧时代跨入新时代(《流逝》、《长恨歌 》等),有的经历了地域性的大跨越(《好婆与李同志》、《叔叔的故事》、《富萍》等 ),更多的是上山下乡又返城的知青(《本次列车终点》等),即使是在“无事”的年代 ,也要经历灵魂的历练(《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等)。但就是在这些作品中, 粗砺的人生背景所衬托出来的,不是时代给人生的巨大的压迫感,而恰恰是足以与荒谬 年代对抗的人的生命力。《流逝》、《“文革”轶事》、《长恨歌》的故事背后都有着 复杂的历史大变革,王安忆所表现的,却是人们日复一日三餐一宿的“家常”生活,这 些人无法把握这个动荡的时代,却可以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 来的智慧和力量,使得他们穿越了时代的层层重压,扛起了人生的重担。因此王安忆不 厌其烦地描写她们如何早晨早早地排队买鸡蛋,如何精打细算搭配一天的伙食,如何精 心剪裁自己喜欢的衣服样式,如何围炉夜话谈笑风生……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说:“持久 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 了人性的美德。”[8]在世俗生活中度过日月的平凡百姓的生活或许是“盲目”的,但 他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体现着生命的韧性和力量,在王安忆 看来,这正是人性中最美的一面。
将“市民精神”表现得最充分的,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生死契阔,与子相悦” 是王安忆和张爱玲都喜欢的诗句,也是她们喜欢拿来写笔下的女性的诗句,但在张爱玲 那里它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 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11]而王安忆却用它来赞美那些既美丽又有力 量的女性:“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 志不渝。”[12](P208)这些女人生活在世俗凡尘中,尽管也会害怕,也会掉泪,但到了 紧要关头,却有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勇气,大难临头时甚至比男性更能气定神闲、 处之泰然。王安忆在小说中对角色的设计是耐人寻味的,男性都几乎清一色的比较软弱 ,女性大都外柔内刚,《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曾是娇生惯养的少奶奶,家被抄后却毅然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代替没主意的丈夫成了全家的主心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怀 上情人康明逊的孩子后,康惧怕世俗的压力不敢承担责任,她便自己生下了孩子并将女 儿抚养成人;《妹头》中妹头一个人跑长途、做生意,而她那个对生活缺乏热情的丈夫 心里永远也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得这样喧腾”。这些女性都是 极其热爱生活的,没有什么能成为她们放弃生活的理由,遇到再大困难她们都能跨过, 她们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典型的市井中人。尽管她们在小说中都是些“庸常之辈”, 但王安忆却愿意将她们看作是“英雄”:“在我看来,妹头就很英雄,当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英雄。她很勇敢,肯实践,很有行动能力。”“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 往前走,不回头,不妥协。……也有可能最终把她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8]
其实,张爱玲笔下也有“飞蛾扑火”式的女性,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为了渺茫的“前途”进入姑母那充满淫逸空气的公馆,自甘堕落为姑母勾引男人的诱饵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离开坟墓一样的娘家,铤而走险与范柳原周旋;《连环 套》中的霓喜更是为了生存将青春和生命作为赌注,投入一个又一个不可靠的男人的怀 中……我们也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也是“勇敢,肯实践,很有行动能力”的,但 她们的“行动”反衬出来的不是生命的力度,而是生命的脆弱和人世的险恶;而王安忆 笔下的女性们的“行动”映衬出来的,却是蓬勃不息的充满韧性的生命力。
因此,“世俗性”只是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相似的表层,内核却是截然不同的。小说 是一个“心灵世界”[13],世界观的不一样,使得她们小说的审美特征、审美效果都截 然不同。正如建房子,材料都是日常生活的一砖一瓦,但因建筑理念的不同,最终出现 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苍凉”和“虚无”是张爱玲所独有的,是作家本人的 对世界和人生独特的认识反映在作品中的结果,她的世界观注定了她的世俗小说其实是 苍凉的传奇。王安忆理解市井人们的生活,欣赏市民精神的力量,她的小说描写着世俗 生活的琐事,却流淌出一种“温暖”和“饱满”的生命的气息。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将世 俗生活和人生观对照起来,她以日常生活的表象为起点,一步一步地挖掘人性的深度和 人生的意义,这些深度和意义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便到达了另一个艺术的高度。
三
张爱玲的世界被称为是一个“死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 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一寸一寸向衰老的路上走,到死为止。”[14](P292)(唐 文标)相比较而言,王安忆的世界则是一个“生世界”:有希望,有青春,有明天,里 面的人物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至死不息。一个生,一个死,一个 冷,一个热,一个苍凉,一个温暖,两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女作家,在各自生存的时代 树立起了各自的名望,成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 固然是世界观的不同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的生成,但同样是“世俗的”作家 ,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世界观呢?客观地说,张与王的孩提和少年时代都不够“顺利”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对比性极强的环境中:保守的父亲(抽鸦片,纳姨太太),新派的母 亲(留洋,离婚);坚强的自己,孱弱的弟弟;旧式的家庭教育,西洋式的学校教育(香 港大学);被父亲拘禁,而后“惊险”的出逃;生活于声色犬马的上海和香港,又亲眼 目睹此二地的战争和离乱……新旧交替的时代,兵荒马乱的世界,分裂的家庭,小小的 敏感的心灵如此戏剧化地切入了这个奇异的乱世,在她心中不断加深着的,是孤独面对 人生时的世事无常、人生奈何的感慨。她享受着世俗人生的小小的乐趣,是因为她太深 刻地感受到人生的荒谬与无聊,她不无俗气地高叫着“出名要趁早呀!”,是因为她思 想里有着“惘惘的威胁”:“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 大的破坏要来。”[15](P186)充满“破坏”的时代重压在一个悲哀的个体的心灵上,她 所能做到的只有抓住手边的世俗生活——她越是沉浸于其中,就越能看到她的痛苦和孤 独。
王安忆同样是经历了巨大“破坏”的人,她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荒谬的20世纪五六十年 代度过的,她目睹过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作为知青她亲身体验过下乡、插队、返城中的 种种滋味。那个年代年轻人特有的热血、激情与无法掌握的命运及荒唐的时代结合在一 起,按理来说,王安忆更有理由产生人生的虚无和荒谬之感。但中国当代文学的事实告 诉我们,荒谬的时代并不一定是虚无产生的温床,开篇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伤痕文 学”和随后的“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给读者提供的不仅不是人生奈何的感慨,而 是对伤痛的哭诉、对历史的反省、对人性的呼唤。王安忆曾不止一次强调过自己是“出 生于50年代的人”,“我们这一代基本是看苏俄文学长大的。我们内心里都有一种热的 东西,都有一种对大众的关怀的人道主义的东西。”[16](P206)这内心的一点“热”, 这一种“对大众的关怀”,就造成了张爱玲和王安忆之间最本质的不同。在张爱玲的笔 下,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都被无情消解,人性的顽愚与现实的虚妄、历史的虚无结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黑暗的、冰冷的“死世界”;然而,在读王安忆的小说时,不管人 物的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我们却总能感觉到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成名作《 雨,沙沙沙》留给我们深刻记忆的,除了雯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呼唤,还有那与 蒙蒙细雨相交织的橙黄色的路边的灯光,谁说这个温暖的灯雨交织的世界不是王安忆心 中那一点“热”的折射呢?《冷土》中一心一意要嫁给城里人的刘以萍,《香港的情与 爱》中与老魏“逢场作戏”的逢佳,《我爱比尔》中爱上外国人的阿三,这些人物如果 来到张爱玲的笔下,就是另一个葛薇龙和白流苏,但在王安忆那里,她们所有的行为都 得到了宽厚的理解:刘以萍是为了实现自己作为城里人的理想,逢佳在假戏中产生了对 老魏的真情,当阿三触到那个象征初恋的“处女蛋”而热泪盈眶时,谁又不会为她掬一 把同情之泪呢?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你总会看到一些“真”和一些“情”,看到一些温 暖的东西,“我从来不是像张爱玲那样看世界的,我要比她温情。”[17](P254)这一切 都是因为她内心中的那一点“热”。
对张爱玲而言,虽然个人的挣扎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但她基本上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她没有外来的教化,她的孤独感和虚无感是在个人与世界的痛苦的对抗中获得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些 充满奇妙才情的“张氏”名言尽管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它们绝对是极其个人化的体验, 是特殊的家庭、时代与一个特定的体验者碰撞到了一起而产生的电光一闪。她的孤独、 绝望与虚无是属于她个人的,并且因为“直指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异化和崩溃,直指人类 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与绝望”,她对世界的体验达到了他人无法比拟的高度,“可以上 升到哲学层面”,“与艾略特、卡夫卡们相类似。”[18](P22)与张爱玲用“我”来言 说自身体验相反,王安忆是用“我们”来进行言说的,很难用“集体主义者”来形容她 ,但她肯定不是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她所生活的时代不允许她这样,她内心的那一点 “热”也不允许她这样。在新时期以伤痕、知青、反思、寻根为主的各种创作潮流中, 王安忆虽然不能算是中坚力量,但各个潮流中都留下了她的身影,从她创作伊始,她就 和其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将自己的声音汇入了时代的大乐章之中。她始终没有 脱离大家关怀的目光,同样,她也始终关注着周围最普通的人们,这就是她所说的心中 “有一种对大众的关怀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正因为此,王安忆对人类的世俗生活充满 着理解和宽容。她的小说中的人物遇上繁华时代就好好享受,命运不济时就躲进小楼自 成一统,这并不是对命运的屈从,而是力求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达成最大限度 的和谐。这是从市民生活中提取出的人生智慧,是平凡人生活真实的写照,不管历史怎 样的变迁,千百年来的民间社会就是这样和谐地发展下来的。人与人、人与现实之间固 然有冲突,但其基石更多的是宽容、理解与和谐,社会也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 王安忆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就是力求表现一个和谐世界的故事:水 乡小镇的秧宝宝寄居在李老师家一年之后,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成长为一个心灵晶 莹剔透的小姑娘,她既活泼又羞怯,既敏感又坚强,她有着和一切小女孩一样的天真、 幼稚,更有着被任何人所珍惜的有情有义、知冷知热。这个美好的生命的形成,并不是 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促成的,而是因为水乡小镇清新自然的风气和人们温暖淳朴的道德 共同滋养,小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促成这个美好生命诞生的契机。概言之, 是因为小镇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和她周遭人们构成了一个“合理”的日常生活的世 界——这个世界“离远了看,便会发现惊人的合理,就是由这合理,达到了和谐平衡的 美。也是由这合理,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了解。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 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女孩如何成长的故事,而是一次 关于人与现实中日常生活关系的探讨。只有人与日常生活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生命也 才能得到完美和回馈。这个水乡小镇虽然也是一个由人们日常生活组成的世俗社会,但 它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和谐的世界,它已具备了审美的高度,这是王安忆的理想世界,这 是王安忆所希望的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是生命最美、最和谐的存在形式。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深刻描写“颓废中的文化”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19], 在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中,她所看到的是灰色人生的悲哀:“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20](P268)就像《传奇》增订 版的封面那样,张爱玲就是屋外那个冷眼旁观着屋里玩骨牌的女人的“鬼魂”似的“现 代人”的影子,她俯视着庸庸碌碌的人类生活,用她悲哀的心灵感受着人生的苍凉。相 比较而言,王安忆的悲观远不如张爱玲的彻底,虽然她也认为:“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 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落的。”[21](P292)但是她 并不允许自己沉溺于悲观、陷落于虚无中,她一直都在试图寻找力量来与悲观抗衡,这 种力量,就是世俗生活中所潜藏着的力量。即使是在生命饱受摧残的“文革”,她所看 到的仍然是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生命力:“比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 头甚至并不像人们原来想像的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 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你可以说一般的市民生活似乎 有些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过来了。”[10](P241)王安忆很欣赏普通老百姓不甘沉沦于 灰色生活,而是在灰色生活中寻找亮色的做法,正是因为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 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们才得以穿越时代的层层重压,在乱世中 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精神力量。近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富萍》很能 体现王安忆对普通人精神力量的赞美。富萍是个老实、内向、木讷的女孩,但内心却有 一股强大的力,她渴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富萍跟随做保姆的“奶奶”从扬州乡下 走到了上海,从繁华的淮海路走到肮渍的闸北河边,她走过了或大或小或贫或富的家家 户户,最后在“梅家桥”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与一个跛腿的青年和他年迈的母亲生活 在一起。富萍最后的选择令人费解,她并没有听从“奶奶”为她安排的看起来不错的婚 姻,而是来到了比她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更为贫穷和肮渍的“梅家桥”。然而,正是在“ 梅家桥”的丈夫和婆婆身边,她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她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人,她也真 正需要他们。“梅家桥”所蕴涵着的优美的平静和醇厚的诗意并不是它本身所具备的, 而是在王安忆与她的人物在粗砺的生活中一点一点地寻找着与之对抗的力量的过程中逐 渐呈现出来的。这一“寻找力量”的过程,就是王安忆拼其所有与悲观对抗的过程。抵 抗悲观,找到乐观,也就找到了力量。在她的一篇演讲中,这一寻找的过程得到了诗意 的象征性的表达: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 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正插在墨肥的泥水中, 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 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 ,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21](P299)
这就是王安忆,她是世俗的,但也是充满力量的。她紧握世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 视人类生活中的悲哀和欢喜,终于有了面对人生的勇气,而不像张爱玲那样将人生撒手 ,坠入虚无。或许她对人生的体验没有达到张爱玲那样的高度,但她毕竟在现实主义的 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结结实实地走到了今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安忆的创作生 命也会有别于张爱玲,张爱玲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传奇》,但王安忆还有希望,在未 来的创作道路中,她有可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收稿日期:2003-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