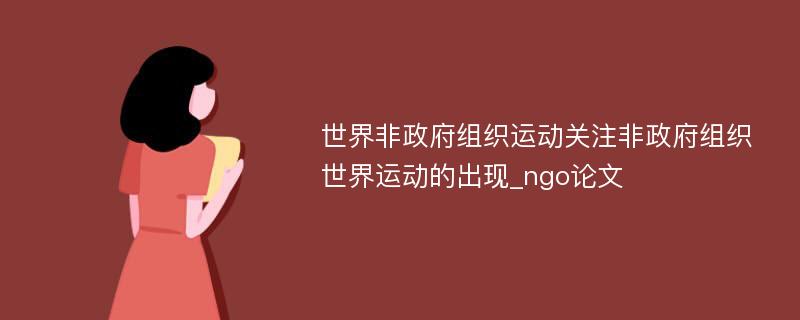
关注蓄势待发的世界非政府组织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蓄势待发论文,组织论文,政府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的西雅图举行部长会议,数万名非政府组织成员冲击了会场,抗议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接着,达沃斯、华盛顿、曼谷、布拉格等地也爆发了类似的,以各类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性示威。学者指出,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反越战运动”以来,世界上发生的范围最为广泛的群众性示威。非政府组织纷纷走向街头,说明了他们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担忧,和对会议斗争手段无效的失望。在政府组织这一层面上,2000年夏秋,联合国分别召开千年非政府组织论坛、千年议长会议和千年首脑会议,形成了非政府组织、议会和政府的“三驾马车”架势。由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膨胀,非政府组织运动的作用已越来越为世界所认识。它们的行为也屡屡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和关注中心。有时,它同“政府”和“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被看作是世界上的“第三种力量”。
非政府组织(英文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什么是NGO,国际上众说纷纭。但综观各方观点,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NGO是指那些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政党性,具有合法性、公益性和带有一定程度的志愿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我国,它们被统称为“社会团体”。
经常同“非政府组织”一词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名词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tey)。公民社会的覆盖面比较宽,包括NGO和跨国公司等。一般认为NGO是公民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成分。
植根于西方政治理论
NGO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确立,使公民们获得了广泛的结社自由,各种民间组织便应运而生。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遂为国际性的NGO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最初的NGO大多同人道主义和宗教事务有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扩大到专业技术领域,如裁军、难民、环保等。
NGO的出现是同西方的政治制衡理论相联系的。按照西方的政治学,国家是统治的主体而社会则是统治的对象。代表国家的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如不予限制,必定走向专制。限制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公民参政,包括建立众多的抗衡性的社会集团。
多年来,世界上存在一种非政府组织运动。这种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新思潮的目标便是“淡化领导阶层的责任和削弱国家观念”,或谓“削弱或破坏国家”(注:James Paul:NGOs,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Policy Making,GFPwebsite,1998,p.2),例如强调人权而不是国权,着重“人的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
不少西方NGO人士对其政府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不信任感。他们称政府为“官僚机构”,认为:政府总是压制人民积极性的,政府官员还有不断扩权的欲望,极易腐败。他们对政党也不屑一顾,因为政党一时台上,一时台下,想的是当官,走的是从政的路。NGO的信念则不同,它们要以自己的清白和公正,为人民执言,同政府树立一个对立面。“非政府组织的天性就是常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新问题和表示公众的不安”,成为“对国家的主要社会抗衡力量”。(注:Chiang Pei-heng: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t the UN,N.Y.Praeger Pub.,1981,p.59)
西方政府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上拖沓不前和无能,也为NGO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对于国家丧失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从民间社会的发展得到补偿。”一位非洲学者把这些变化称为“悄悄的革命”。(注:Robert W.Gox::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Cambridge Univ.Press,1996,p.534)
“非政府”不等于“反政府”。“非政府”仅指“不为政府所建立或控制”,但抗衡政府的思想很容易使NGO同政府处于对立。不讲分寸、不谋妥协、不知策略常使它们同政府的关系激化。它们对不同性质的政权不加区别,更常使它们的反派角色走入误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和人民也存在矛盾,但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声誉仍是公民的义务。西方NGO相信的是公开压力。它们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机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官方背景,如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被发展中国家称为“西方国家的别动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部分NGO,或由于沦为外国势力工具,或因为以极端手段经常发难,被视作非法组织。
一支庞大的队伍
如果把国际性和国内性的都计算在内,世界的NGO数字可以达到百万。的确,二战之后,国际性NGO得到很大发展。到了70年代末,它已增加到大约3000个。如今大约有近3万个。
全世界各国的国内性NGO的发展更是迅猛异常。从1987年到1994年,法国就诞生了5.4万个新的NGO。在同一时期里,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智利也发展了2.7万个。(注:《联合国高中教程》,联合国出版社,1995,p.17)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NGO的数量也直线上升。1948年仅有41个,1968年达到337个,目前有1350个。同联合国新闻部有合作关系的NGO也由1968年的200个发展到现在的1550个。(注:联合国文件,A/53/170kgn,1998,p.3)
NGO除参加联合国的许多重要世界性会议外,并同时举行规模宏大的NGO论坛。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召开时,近2万名NGO人士举行了非政府组织论坛。1995年,来北京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的NGO的人数超过3万。
为了加强国际联络和进行游说,西方重要的NGO都在国外派驻人员。日内瓦的NGO常驻人员多达2000余人,与各国常驻日内瓦的外交官人数相当。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情况亦大体相同。
NGO不但取得了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权利,而且还争得了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甚至最后文件及决议的起草权利。90年代以来的历次重要全球性会议的最后文件和行动纲领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NGO的呼声和要求,特别是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人权保护、改革联合国、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等都是非政府组织所长期倡导的。
NGO中藏龙卧虎,各方面的人才和专家众多。联合国倡导和采用的许多思想、新概念和新举措中,不少首先出自NGO。有的则是在NGO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绿色和平运动举世闻名,在一些国家甚至已演变为绿党。近年来,在推动签署全面禁止地雷公约和建立国际军事法庭方面,NGO发挥的作用是世所公认的。
NGO在全球显著壮大,其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能力也相应扩大。例如,1992年,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估计超过80亿美元,比整个联合国系统提供的还多。(注:James Paul:NGOs,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Policy Making,GFP website,1998,p.2)在发达国家政府“援助疲劳症”日益严重的情况下,NGO的资金优势日趋明显。它们已成为第二大发展援助来源。
NGO虽然在联合国中没有投票权,但它们总能充分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和进出联合国大厦的便利,大搞走廊外交,巧妙地运用出版专题报纸、改变会议议程、充当项目执行人、挤进工作组、为秘书处捉刀、转入秘书处任职等手段施加影响。为使工作更加有效,它们往往组成联合体,将资源集中起来和协调彼此的游说工作。实例就是: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安理会工作组”,以推动NGO和安理会之间的对话,和追踪安理会的活动。
NGO善于做细致的调研、做敏锐的分析和进行巧妙的游说。因此,联合国秘书处人员便常找他们索要有创新的主意和材料。外交官们也寻求它们的支持。在许多国家中,它们同基层群众的联系密切程度甚至超过政党和政府。某些政府从NGO那里获得的信息比本国驻外大使馆获得的还多。(注:约翰·汉费莱:《国际人权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p.55)
NGO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可小看。例如二战以来,世界上反对核试验、反对生化武器、反对武器输出、反对军事基地等的群众性运动此起彼伏,演出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的剧幕,对唤起群众的反战觉悟,约束有关政府的扩军备战,和牵制国际上的军备竞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就是在美国民众的反战运动中倒台的。
东西方NGO存在明显差距
在一国一票的联合国系统,发展中国家占数量上的明显优势,曾被西方咒骂为“多数暴政”,而在民间多边外交舞台上的情况则很不一样。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原因,发展中国家的NGO起步晚,财力和物力有限,因此有能力经常、广泛参加联合国会议和活动的NGO很少。在同联合国新闻部建立正式联系的1550个NGO中,只有251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联大报告,A/53/170号,1988)由于西方NGO大量介入联合国事务,西方在联合国系统中的数量劣势便得到很大的弥补。
西方国家的NGO专门人才多,对国际问题和联合国事务了解深,能经常不断地提出有系统理论的新建议和新思路,并且有条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在这些方面,发展中国家的NGO也相形见绌。
西方NGO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明显优势,使联合国和多边舞台更多地反映了西方的立场和观点。这正是西方国家十分重视NGO在多边外交中的作用的重要原因。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分别占美国、加拿大、瑞典NGO活动经费的66%、76%和85%。(注:NGO's Status and Donors,Macmillan Press Ltd,1997,p.7)
联合国秘书长也在大力呼吁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参与联合国事务,以改变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从我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在对世界NGO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我国政府也似应大力支持我国的NGO积极跻身于世界非政府运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NGO的合作和交流,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特别是联合国中的声音和整体力量。
同政府相比,占有某些优势
NGO考虑问题的角度同政府不同,一般更强调公益性和公正性,较多地反映国际社会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许多严肃的NGO成员还带有一定的志愿性质,不太崇尚物质利益,具有事业和献身精神。凡是与NGO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不管是活跃在联合国走廊上的说客,还是忙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都能尽心尽职,工作效率比较高。
绝大多数NGO都不谋求执政。这种非政党性质使非政府组织免受变化无常的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能长期地、始终如一地追求相对单一的主张和目标。“非政府组织往往是革新者,而政府趋于埋头于日常事务和维持现状。非政府组织能集中关注世界性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价值,而政府主要是应付事变和着眼于下次选举。”(注:John Sankey in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London,1996,p.270)许多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集中了许多本行业的专家,人员比较稳定,有许多人长期,甚至一辈子,研究某一问题,容易提出有前瞻性的看法,例如建立有“非政府行为者”参加的联合国“人民大会”、撤消经社理事会代之以经济安全理事会等。相形之下,外交官的岗位、专业变动频繁,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时常不是NGO人士的对手。
同政府比较,NGO在组织体制、机构以及活动方式上灵活性更大。它们信息灵通,对问题反应迅速。许多情况下,联合国正是通过NGO来了解战乱地区的人权和难民状况。联合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时,NGO经常因能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而成为项目的承包者,成为联合国或多边机构的重要合作伙伴。以世界银行为例,1997年批准的援助项目,有47%是由NGO承包或参与的。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各国政府难以达成一致,造成许多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NGO,特别是国际性组织,是以解决某一突出问题而存在的。它受国家利益的约束相对为少,敢于提出超越国家利益的大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解决对峙的国家利益关系的滞后手段客观上也为NGO提供了庞大的活动空间。
许多观察家认为,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会议中,它们是新闻报导中最色泽斑谰、最活跃和最有想象力的与会者。关于它们能量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
“不论大会小会发言、评论或讨论,还是会间休息、会下交流,甚至晚上娱乐活动时间,出头露面最多、接触交流最频繁的,正是那些没有官方头衔、不拿政府薪水、热心公益事业的反核活动分子,‘保护少数’活动分子。他(她)们视角之独特、议论之有力、能量之大、影响之广,非我们这些习惯于国内状况的人所易于理解。”(注:谢启美等编:《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王逸舟文,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p.212)
当然,NGO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也常常受到质疑。有的NGO主张过于激进和理想化,某些组织又热衷于意识形态攻击,以致失去群众基础。
同政府的微妙关系
大体上,凡涉及国际问题时,因为民族利益一致,NGO同本国政府比较容易取得共同语言,但遇到国内问题时,NGO因为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特殊利益,看法常常同政府相左。西方的NGO对政府的批评不少,但通常都是小骂大帮忙,不涉及根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问题。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NGO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于冲突。
西方NGO同政府携手合作并不少见。1994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注册的390个美国NGO中,政府资助占它们支出额的24.4%。澳大利亚的“海外项目非政府组织联盟”1993年度开支的40%来自政府。结果,连联合国难民署也感到吃惊,有关政府不是把人道主义援款交给国际机构,而是本国的NGO,致使过去发生大规模紧急状况时进行协调和合作的体系遭到破坏。这种为政府执行项目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担心NGO会丧失独立性,成为政府的附属品。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NGO也在不断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NGO通常以南北利益划线。但面对北强南弱,霸权横行的严峻国际形势,政府更需考虑国家安全。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便要保持国内的安定团结。当它们成为西方的“以NGO抗衡政府”理论的扩展对象时,必然提高警惕。但这一切并不总是能得到本国NGO的理解。大体上说,从事发展事业及援助型的非政府组织比较容易和政府相处,政治性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则相对难以协调。(注:范士明:《国家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浅析》,《现代国际关系》,1998-3,p.36)
大幅度介入联合国事务
NGO介入联合国事务的程度已有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的世界环发大会上,NGO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后NGO很想乘胜扩大成果,打破NGO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经社理事会的传统。但不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对NGO参与联合国事务大开绿灯,而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不同的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例如,欧盟即强调应放开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限制,而许多77国集团的国家则对NGO对政府的批评和攻击十分敏感。另方面,77国集团力图把发展中国家的NGO带进所有同发展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而欧盟则要把它们限制在经社理事会的范畴内。(注:Peter Willets: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NGO Movement,1996,p.18)美、日两国对NGO参与联大活动采取了特别强硬的路线。甚至有人说,是否在联大给予NGO某种正式的磋商地位,斗争是在美国和77国集团之间展开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口头上最坚决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政府(美国和欧盟)却最强硬地坚持把非政府组织从改革联合国的讨论和联合国的高层机构中排除出去。”(注:James Paul:NGOs,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Policy Making,GPF website,1998,p.5)
按照联合国通过的环保《21世纪议程》的要求,在包括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中,NGO“在政策规划、做出决定、执行决定和评估结果”上都应发挥作用。许多NGO提出,应给予它们在联大、各主要委员会、特别联大甚至安理会正式的咨商地位。有人担心,如此下去联合国会变成国际红十字会那样的“混种组织”——政府和NGO享有同等的一票。
NGO过大的“雄心”引起了政府的警惕。固然NGO在某些方面可弥补政府的不足,并配合政府行事,但对NGO企图在决策上,特别是有关安全问题上,同政府分一杯羹的想法后者却难以苟同。NGO显然已不满足于多年来已取得的经社领域的咨商地位。有人认为,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国家、市场、公民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
90年代上半期,NGO同联合国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一个“蜜月”,但后半期趋势下滑。近来,NGO纷纷反映联合国秘书处收紧了对它们参与联合国活动的限制。当前,NGO步步进逼,强调联合国是“人民的联合国”,还以秘书长安南曾称NGO是联合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为理由,要求进一步“开禁”。去年6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NGO千年论坛,NGO要求列席安理会会议、要求进入所有联合国机构和会议,并给予随后成立的“全球公民社会论坛”以联合国观察员地位等。这一趋势值得关注。
中国的NGO现状
我国是一个NGO大国,迄今全国性社会团体仍有1800多个,在各地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县级以上的社团约16.5万个。近年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助残、捐资助学、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消费者利益、提高环保意识、职业培训、协助下岗人员再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国的NGO,特别是外向型的组织,不但数量少,而且刚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已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获得咨商地位的1350多个NGO中,迄今中国只有全国妇联、残联、人权研究会、中国联合国协会四家,而且它们的咨商地位获得的时间不长,工作局面还有待打开。1995年的北京世妇会,仅美国就来了500个NGO,而我国作为东道主只派出22个NGO与会。相比之下,我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NGO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声音非常微弱。
要解决中国NGO积极参与国际民间多边活动还需调整某些认识。
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为此,对于国外NGO在运作上的独立性,多数人往往难以理解。我们对西方利用NGO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性较高,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却常常忽略西方NGO抗衡本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也有促进世界和平、加强环保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西方NGO在世界NGO运动中占有主导地位。如果我们不能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它们,团结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在融入这个运动时就不能使自己置身其主流之中,就会同多数NGO的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
二、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代里,中国的工、青、妇等人民团体都是党和政府团结、教育、动员群众的渠道。如今,要同世界非政府组织运动接轨,如它们继续保持一副官方的身份,就同公认的NGO身份不符,会与国外的同僚格格不入,难以开展工作。好在中央现在十分强调完善国内的民主监督机制,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此问题当不难解决。
三、由于对境外的NGO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长期来我国对国际NGO的宣传报导不多,结果群众对它不仅陌生,甚至有相当的误解。事实证明,1995年北京来了三万多外国NGO人士,包括同性恋组织等,并没有能对我国社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我国群众更需要对世界NGO运动有正确和全面的了解。
当今的外交是总体外交。我国在双边外交中较早注意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比如外交学会、对外友协等社会团体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多边领域,民间外交却相对滞后。因此,应当鼓励有涉外能力和组织机制健全的中国NGO到联合国经社会去申请咨商地位,加强中国在世界及联合国NGO运动中的声音,同时也要放手让我国的NGO多到民间多边外交舞台上去锻炼和学习,通过参与加强自我,为这一世界性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一波澜壮阔,代表政府外的另一种声音的民间运动正随全球化的进展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