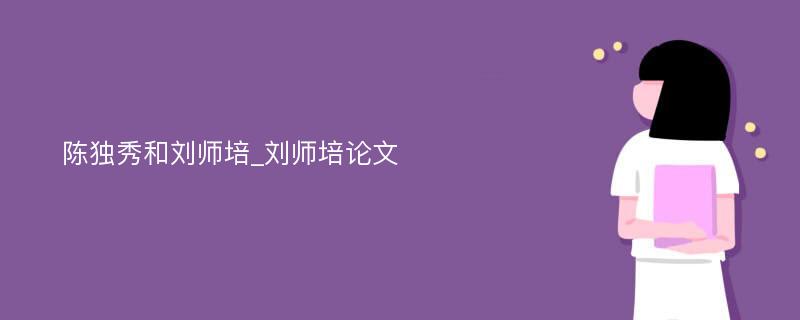
陈独秀与刘师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1)01-0051-05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与刘师培有过一段不浅的交谊,尽管它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颇有波折,却从未中断过。作为横跨政、学两界的知名人物,他们的交谊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时局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提供了一个思考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案例。
一
从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史实来看,1903~1907年是他们友谊的第一阶段,彼此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论学挚友。
1903年夏,陈独秀因在安庆举行爱国演说会而遭清政府通缉,遂逃至上海,与章士钊同住(注:据章士钊所记,“是年(1903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见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7号,1926年12月25日。)。随之刘师培亦由家乡扬州来上海投奔章士钊,结识了陈独秀(注:章士钊曾回忆:“申叔(刘师培)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见章士钊《孤桐杂记》。亦可参见章士钊《刘申叔论古文》,《柳文指要》下册,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851页。)。此时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共同主编。该报既为继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立,论调不得不稍“舒缓”,不象《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在于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注: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因此发行未久,即风行一时,人称《苏报》第二。刘师培曾在该报上发表《黄帝纪年论》、《王船山史说申义》等文(注:章士钊说《王船山史说申义》是他的作品,见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2页。因该文发表时无署名,难以稽考。现从钱玄同说(钱将该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仍认作刘师培作品。)和诗《读王船山先生遗书》、《杂咏》。这些诗文力倡排满兴汉,在当时的革命派中影响甚大。作为报纸主编和革命志士,陈独秀以编发这些诗文的方式表明对刘氏主张的认同与赞赏,两人的友谊也由此深厚起来。
1903年12月初,《国民日日报》停刊。年底,陈独秀返抵安庆。1904年1月,他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内容以“开风气,倡革命”为主(注:安徽省政协文史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沈寂:《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安徽史学通讯》总第14号,1959年第6期。)。同年暑假后,他和房秩五皆去芜湖安徽公学任教,遂将编辑部迁至芜湖(注: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另有一说认为陈独秀于1904年暑期独自来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楼上,直到1905年才到安徽公学任教。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9页。)。此时,刘师培仍留在上海宣传革命,除为报刊撰稿和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外,还与林獬接替蔡元培、汪允宗编辑《警钟日报》(注: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1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4页。)。他和陈独秀虽不在一处,但始终关注陈的动向,曾对蔡元培称赏陈独秀,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注:《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他与陈独秀再度见面大约是在1904年11月,当时陈应章士钊之招来上海,参加革命组织暗杀团(注:参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66页。)。此前刘师培已加入了这个组织。这次两人再度携手,试制炸药以图暗杀清廷顽固派,虽很快便因行动失败而分手(陈独秀在上海仅住月余即回芜湖),但友谊无疑加深了。
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查封,作为主笔的刘师培亦被通缉,刘只好逃至浙江嘉兴,匿居半年之久。这年秋天,他应陈独秀之邀赴芜湖,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任教,化名“金少甫”(注: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直至1907年初,两人共事一年有余。
安徽公学由名士李光炯、卢仲农等人创办,以传播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该校任教的,皆为当时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除陈独秀、刘师培外,还有陶成章、柏文蔚、苏曼殊、谢无量等。陈独秀出任国文教员,除在课堂上讲说革命道理外,还与柏文蔚及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会长,对推进该会的成长和在新军中扩大影响起了较大作用。刘师培在安徽公学讲授历史、伦理课,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反清革命,并以当地光复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学生中发展新会员,还组织名为“黄氏学校”的秘密团体,介绍李光炯、柏文蔚等人加入,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此外,陈独秀与刘师培还共同发行一白话报(注: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1页。),以开启民智,鼓动革命。
1906年暑假,陈独秀偕苏曼殊东游日本,8月下旬(处暑后)回到芜湖,到张通典主持的皖江中学任教(注:参见《苏曼殊致刘三信》(1906年9月13日),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1册,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331页。)。该校也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陈独秀、刘师培在这里仍继续他们的事业。1907年2月,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声方捉拿(注:参见马君武:《孙总理》,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在国内很难立足,加之章太炎又发出东渡邀请,遂偕妻何震、姻亲汪公权及苏曼殊东渡日本。抵东京后,与章太炎同住在《民报》社,得以朝夕晤谈(注:参见柳亚子:《苏玄瑛正传》,《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随之陈独秀亦因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不得不离国东去,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注: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74页。)。
在日本,刘师培加入了同盟会、亚洲和亲会等团体,并在1907年6月通过何震创办《天义报》、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始终活跃于政治舞台。而陈独秀此时却与政治有所疏离,他不肯参加同盟会,只加入了刘师培参与发起的以反帝为宗旨的亚洲和亲会。他虽较少参与政治活动,但和刘师培过从甚密,一同切磋中西学问。他常去《民报》社找刘师培,与刘及章太炎、钱玄同、苏曼殊等探讨传统汉学、西方文学和古体诗的写作,并参与议建梵文书藏。(注:“(苏曼殊)为梵学会讲师,交游波罗门忧国之士,揭其所有旧藏梵本,与桂伯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未成。”见柳亚子《苏玄瑛新传》,《苏曼殊全集》第1册,第4页。)苏曼殊著《梵文典》,陈在上面题诗,刘师培则为之作序。刘以“国学大师”著称,此时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可见其学术地位。他幼承家学,于小学(语言文字学)、经学无所不通,陈独秀与他及章太炎时相过从,自然于学问上受益非浅。陈后来在小学上多有建树,发表《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等著作,虽自有师承,但与刘师培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可以说,两人不仅是革命同志,亦是论学挚友。
二
1907年底,刘师培回国,除与老朋友相会外,还帮助章太炎向清两江总督端方谋款。此时章太炎因和孙中山矛盾日深,对同盟会也日益不满,准备去印度出家为僧,但缺乏路费,遂通过刘师培夫妇与端方联系谋款,为此先后五次致书二人。端方要章太炎去福州鼓山或普陀等地出家,欲把章控制在国内,章坚拒之,事遂不成。刘师培却由此落入端方圈套,加之对革命失望,对孙中山与同盟会不满,以及其它一些因素,遂向端方自首,作《与端方书》,提出十条“弭乱之策”以镇压革命党人(注:《刘师培与端方书》,《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133页;杨天石、王学庄:《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曾业英:《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908年2月,刘师培与何震回到日本东京,表面上仍以革命党人身份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不久他们与章太炎因事吵翻,还波及苏曼殊。“申叔把曼殊认作傻子,他们夫妇和端方的关系,都不避曼殊面谈讲着。曼殊听了,却把来告诉仲甫。”(注: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苏曼殊全集》第5册,附录下第21页。)闻知刘师培的言行,陈独秀失望之极,开始疏远刘,两人之交谊走了下坡路。
1908年11月,刘师培夫妇回国,不久投入端方幕中,先在南京,后随改任直隶总督的端方去天津。1909年秋,陈独秀回国,居杭州,曾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两人虽不在一地,且因政见不同而关系疏远,但友谊并未中绝,还是彼此牵记,书信往来。刘师培曾有一诗记他收到陈独秀信的心情:“天南尺素书,中有瑶华辞。旧好见肝鬲,崇情凛箴规。……秋芳纫荃心,春荣镌留荑。愧无双玉盘,酬子琅玕贻。”(注:刘师培:《得陈仲甫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915页。)1911年底,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刘师培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闻讯后即于1912年初与李光炯等人致电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注:《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实际上陈独秀致电时刘师培已被释,并应老友谢无量之请去成都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尽管因信息不畅使得此举劳而无功,但亦可见陈独秀对朋友的拳拳之情。1913年夏秋之际,刘师培夫妇离川赴沪,陈独秀也恰于此时因反袁失败逃至上海,两人得以在分别5年后见面,“独秀问他们怎么打算,他太太嚣张的说,要北上找‘袁项城’,使独秀不便说下去。”(注: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龙坡杂文》,台湾洪范书店1988年版,第162~163页。)此后刘师培果然北上,先至太原阎锡山处,不久在阎推荐下,到北京投靠袁世凯,1915年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直到1916年6月袁死后,才被迫移居天津。与此同时,陈独秀仍坚持他的反袁民主立场,先是在1914年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宣传民主,反对专制;1915年归国后,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引发新文化运动。刘、陈二人的政治立场不仅相距极远,而且恰为对立面,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几乎没什么来往,友谊跌至低谷。
三
1917~1919年间,陈独秀与刘师培再度共事,这次是同在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任教。两人虽在文化见解上差异甚大,但道不同仍相与谋,友谊进入新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就职后,将《新青年》迁至北京。不久陈向蔡元培推荐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注: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
在北大,刘师培任中国文学门教授,为一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课,为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两门课(注:《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同时做国文研究所“文”与“文学史”两个方向的指导教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注: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8页。)另外,当由国史馆改制而成的国史编纂处归并北大后,他又被聘为国史纂辑员,而陈独秀则以文科学长兼任纂辑股主任。不久两人又共同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并在1918年6月1日当选为该会评议员(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3日。)。
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力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与此同时,蔡元培校长本着“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一些所谓旧派人物也被延揽在校讲授他们的思想与学说。在这方面,陈独秀亦有蔡元培之风,尽管鼓吹新文学不遗余力,但在校内对两派教授,“则一视同仁,不作左右袒。”(注: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适)、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秀刚(侃)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的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时而语。”(注:转引自杜学文:《从刘师培的另一面引起的话题》,《黄河》1999年第6期。)可见陈独秀对刘师培等人的学识是相当认可的,并不因思想观点的不同而有所歧视。
在刘师培这边,虽所秉持之文学观念(以骈文为文体之正宗)与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截然相异,但并非象林纾等顽固派人士那样攻击陈之主张,而且在守旧师生拥戴下于1919年1月出任《国故》月刊总编后,仍未对新文化加以指责,只是本着其一贯立场,“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注:《本社记事录》,《国故》第1期,1919年3月20日。),专门发表研究古典学术之作。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称陈独秀、刘师培分别为新派、旧派首领,两派各组织了《新潮》、《国故》杂志。“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急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这篇报道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4日。)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这就象他与陈独秀的关系,道不同仍相与谋,而且私底下,“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注: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当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刘师培迅即与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注: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02页。),此亦可见二人之关系。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公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注: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1页。)。翌年3月,陈独秀又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将其灵柩送回扬州安葬。而且“申叔死后,他的太太何震发了神经病,时到北大门前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后来由独秀安排,请申叔的弟子刘叔雅(文典)将她送回扬州。”(注: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这样,从1903年相识到1919年刘师培去世,十六年来陈刘之间的友谊尽管中经波折,亦可谓善始善终。
四
综观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历程,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同有异,其交谊在不同时期或深或浅,即与此息息相关。作为横跨政、学两界的知名人物,影响双方人生轨迹和与之相关的交谊程度的基本因素显然在政治与学术。
就政治而言,1903~1907年间,共同的排满革命立场自然是陈独秀与刘师培交谊甚笃的基础;1908年后两人逐渐疏远,也是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所致。目前虽无陈独秀谴责刘师培变节和襄助袁世凯的直接证据(注:1923年9月8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39期上发表《章炳麟与民国》,其中有指斥刘师培拥袁称帝的内容,但已事过境迁。),但陈一直坚持革命反袁立场,便足以证明他在政治上走的是与刘师培对立的另一条路。在辛亥革命前后那种必须判明黑与白的历史情境下,政治上的不同路者是不大容易保全个人私谊的。
但陈独秀毕竟保全了与刘师培的友谊,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因素——学术。1907~1909年陈独秀在日本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对刘师培等人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兴趣也不大,却热衷学问,不时与刘师培探讨汉学。陈独秀为学相当早慧,于小学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反对者认为他学力不够,蔡元培便是以“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为由,“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注: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8月。)。而刘师培以经学名世,小学造诣极深,不能不引发陈独秀的钦敬之情。陈独秀在刘师培政治上失节之时未断绝交往,且在其失意之时以北大教职相聘,恰恰表明陈对其学术才华的看重;两人在北大时“互相尊重,绝无间言”,正是学术上相知甚深的表现。
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以贯之。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恰可为政治与学术的这种特质作佐证,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当然,陈独秀的为人处事态度对保持两人的友谊也起了一定作用。表面上,陈孤傲自许,为文“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注:《陈独秀答胡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他为人并不偏激,无门户之见,在处理政治、学术问题时,往往对事不对人,所以对刘师培这样有较多过失的朋友“颇存宽容”(注:参见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125页;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不过,根本上说,维系两人友谊的,一定时期是共同的政治抱负,但终究靠的是学术上的旨趣一致和相知相佩。
标签:刘师培论文; 陈独秀论文; 苏曼殊全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章太炎论文; 苏曼殊论文; 章士钊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