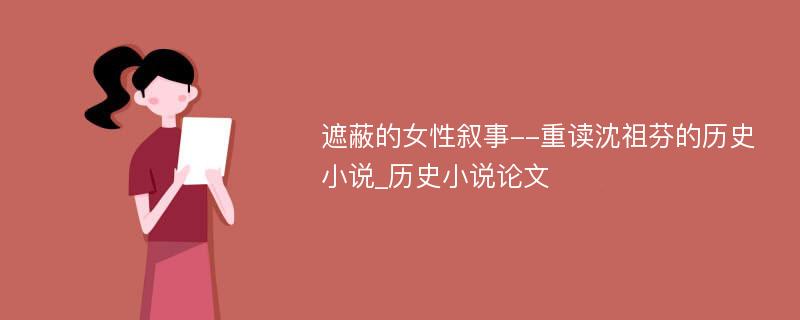
被遮蔽的女性叙事——重读沈祖棻历史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女性论文,沈祖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3-0209-04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时代精神都会以不同方式洇渗到文学中去,思潮的叠新变革往往蕴含着某个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最高旨意,社会思潮的嬗变与关注自身命运的女作家们创作中的人文精神或是强力或是潜在地合拍。女性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被某种价值观念渗透着的话语叙事,通过叙事中那些“说出来的和被掩盖的”、“讲述的和为什么讲述的”话语以及作家主体在特定历史中的特质,并予以挖掘和还原,能够更加贴近现代女性的精神本质。福柯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沈祖棻创作的历史小说带着明显的被大时代遮蔽的元素(讲述神话的年代):战争的风云、家国一体的政治想象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淹没。她试图凭借幻想和超越的勇气,来建立一个提升女性本真的世界(神话所讲述的年代),以期用话语的表达来建构女性的信心。沈祖棻的作品曾“被誉为富有奔放的热情和飞腾的想象”,若是少了对美好的期盼,真不知她如何度过那“不用艰难坎坷四字是无以形容的”一辈子。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有幸福的少女时代,志同道合的程千帆先生又给了她美满的姻缘,怎奈社会时代逼迫她“历尽新婚垂老别”,中国的风云变幻她几乎无一逃过,大革命、抗战、内战、“反左”、“文革”。她本来梦想“环绕着屋子的是寒冷的风雨,但窗子里面却关住了春天”,这在“有斜阳处有春愁”的华夏何以实现!这经历练就了她如刃的笔:颠沛流离、悲欣交集却真情不舍、初衷不改。“寒冷的风雨”塑造了她的刚强,“窗子里的春天”又滋生了她的柔媚。沈祖棻历史叙事中呈现出的沉思、梦想、忧患……把对可能性的瞻望转化为对女性本体的寻求与观照。
历史的是对过往事实的记载,它应该具备镜像式的历史感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春秋笔法。然而事实上,参照某种权力话语或利益集团的需要,历史常在某一横断面上被切割、替换或者改写,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的“虚构”。历史小说的书写方式通常是在社会史和政治史中铺陈的,在时间的线性链条上寻找环环相扣的偶然与必然。正如乔伊斯所称的“父亲的时间,母亲的种族”,男人创造并主宰着历史,历史的叙述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女人则被压在了历史感知的最深处。女人因为在历史发生和记录过程中的空白和缺失,话语权留给了她们阅读和诠释的不同策略。人不能没有历史,如果女人的话语权力被占有,她就只能改写已然的历史。也就是说,女性作家对历史的表述并非是对存在的历史客体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完完全全是对历史的女性解读,是赋予历史的性别新生。沈祖棻的历史小说试图把已然成文的被统治结构所压抑掩盖的事实加以全新的阐释与表达,她写的历史虽然注重典型性,但却常取其“日常”的一面,侧重的不是历史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是人的内涵。她不沿袭男性的写作传统去写政治史,而是写个人生活史、文化风尚史、人性心理史。“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1]她写出的历史是通过女性的视角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与评说,是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写出的不同的历史,她更看重的是“女人经历的历史是怎样的”,更尊重女人的体验和感悟,去做女性的表述。
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是父权制的,由土地和机器决定的生产模式一步步助推男性走向统治者的神坛。社会的文化秩序,审美思维都是按照男性的需要和模式进行再生产的,其功能指向也就固然是男性化的。男人是神,是绝对的权威,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女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就被废黜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的态度一直在演变,从而也引起了女人命运的演变。”[2]男人和女人如何被期待获得和行使权力已成为陈规,男人的统治和女人的被统治就这样被冠冕堂皇地固定在了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上。历来的文本框架中男性都占据着绝对中心的势力场,女人的言说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诗经》自有出自女性之手的佳作,慨叹弃妇的命运也讴歌女性的价值;汉代的蔡琰、班昭,晋代的左芬,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元代的郑允端,明代的柳如是,清代的蔡琬、周淑履,都留下为人称道的作品。但正如玛丽·雅各布斯所,说的“她们作品中关于性别的方面受到压抑或边缘化了”[3]。女人在话语叙事中不过是被书写的男权文化模式下的符号图解,“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太男性化,或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根本的品质”[4]。她们对男人的书写多取材于男欢女爱、弃妇忧怨、寡居之悲和离别之恨。从大禹治水时期涂山女唱出的“候人兮猗!”到汉高祖时期戚夫人的《永巷歌》,对男人的思念、期待、爱恨交织和对女人的自怜自爱却始终停留在哀而不怨、怒而不伤的阶段,雍容大度地拥护着心中的“神”。“她最初想通过爱情进一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进一步证实她的人格,但这里她也包括了她的未来,为了证实她的未来是正当的,她把未来交给了一个拥有一切价值的人来掌握。这样她便放弃了她的超越,让这种超越依附于身为主要者的那个人的超越,让她自己成为他的附庸和奴隶。”[5]与经济依附相比,爱情依附更具隐蔽性,也就更加顽固。男人在女人心目当中是托付了生命的对象物,旧时代的书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不可选择性,对男性形象的忤逆是不可实践的也是无法成功的。
现代以降,“男人”的内涵被极大丰富乃至多面化了,改写的意识和诉求已成为改写的实际行动。秋瑾率先对男人发难:“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回首神州堪一恸,中华偌大竟无人!”就像当代女诗人海男说的:给男人命名的显然是女人。真正意义上浮出“女性”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启蒙带动了“女性”意识的苏醒,女人处于压迫的最底层,巨石被骤然掀开,她们尽管是受着男人的引导,却异常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你不可改变我”代替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沈祖棻在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另辟蹊径,引领着性别话题远离现实表象走进历史,写他们在变动时代中无力把握和拯救命运的苦闷,“酿得深愁成浅笑”,以淡墨染出浓彩,塑造出虽是传统的,却具备现代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体。
沈祖棻将笔下的男人从“神”、“英雄”回归了“人”本身的民间性,写他们的软弱无助,他们反抗的不彻底,他们交织着生与死、有限与无限、停留与克服的人生困惑。不论是唐明皇还是司马相如都是失去了生命的安慰并且要靠女人的付出来完成己任的,在相同的人生背景与各自的具体情境中他们显出了男人本性中的自私与羸弱。男人需要女人来拯救,女人在某些环节上优于男人,甚至比他们更理智、更刚强。沈祖棻在《马嵬驿》中改写了杨玉环,她的一切罪过都因她是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人。杨玉环本来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从寿王妃到杨贵妃,她也在心里存着“另一个世界的梦”。可惜梦只能是梦,要以失去生命的代价换得梦醒,原以为她和皇上之间的爱是“没有权势的压迫,没有虚荣的引诱,更不是享乐的要求;没有目的,没有条件,是心与心的结合,灵魂与灵魂的拥抱,生命与生命的交融”,可到头来“在你的国家的责任、皇帝的宝座的面前,一个弱女子显得多么渺小啊!”“你既然将一切抛弃了……我不死又做什么呢?”这一诘问问出了多少代女人压在心底的苦痛和冤屈。杨玉环一直以为有爱在支撑,但这爱真的是比命还重要吗?现代社会初始倡导的爱情是生长在封建废墟上的玫瑰,因沃土肥料的缺失美丽却不会持久。20年代的爱情是作为反封建的武器而存在的,被剥夺了数千年的爱的权利的失而复得让现代女性们激动得手足无措,她们并不应该爱上谁,她们应该爱的是爱情本身。沈祖棻却在30年代“革命+恋爱”的大背景下清醒地写出了杨玉环生为女人的可叹,在对历史的深思追问中体现对女人本性的发掘。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则是这一原则所排斥的对立面,是人的“另一种”,在男性第一的原则中主要具有“反面价值[6]”。杨贵妃就只能是祸水,只能带着她做为一个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反思和觉醒自缢而终。玄宗皇帝并不想死,他只是希望杨贵妃的死能保住他的皇权。杨贵妃所痛苦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她深爱的男人的怯懦与背弃,因为这个男人“毁灭了我对于爱情的信仰、一切崇高的理想和美丽的人生”。当她终于“含着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轻蔑”离去之际,她的光芒已经掩盖了玄宗皇帝。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在她无法掌权的社会里独有的生命恐惧和精神苦难,揭示给人是达到男权批判境地的文化揭秘。沈祖棻的书写在此高度上体现了“一种全体意识”,杨贵妃自戕的结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谎言的男性世界,昭示着所有女人受压迫的历史。沈祖棻在此借着玉环的口“抹去了男性统治的权力、逻辑理性的权力,而这恰恰是男性最出色的权力了”。[7]
沈祖棻仅有的几部历史小说《辩才禅师》、《茂陵的雨夜》、《马嵬驿》、《苏丞相的悲哀》等都在促使历史的书写从民族/国家叙事的主流模式中脱离出来,确立以个体/女性叙述为侧重点的言说,内心世界为民族国家所感却仍保持着独立性。对于“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探索是沈祖棻在时代的多事之秋中建构的纯美的精神世界的思想中轴。
叙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文本的问题,文本总是要依靠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展开,依靠某类气质的语言去承载。“视角”意为从一个特定的观察点或角度切入文本,是表述所采取的位置(Perspective),也是研究者进入文本意义的方式之一。与沈祖棻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历史叙事(鲁迅、郭沫若等)往往擅长营造文本世界,但自身处于世界之外,他还是“他”,不易为之所动,注重的是展示(Showing);而女性作家则倾向于走进自己所设计的世界中去,慷慨坦白地写出实实在在的“她”,注重的是讲述(Telling)。如果说男性作家描写女性题材的小说尚需“情感换位”的过程,那么女作家就是明白无误的“言为心声”和“现身说法”了。胡云翼先生说,无论文人怎样努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在男人那里,即使是最特异的见解也一样打着社会既定话语的烙印,而女人的视角则可触到无法触及的深处。男性的人称选择、表述方式遵循一定之规,或与既定逻辑相同或与之相悖,女作家只有跳出这个圈子才能找出自己的书写经验,所以“视角”是她们特异表述出的既定语言无法阐明的内觉,对于她们来说具有返回自身和塑造自我的意义。20世纪初,女性写作刚刚如出水芙蓉般争奇斗妍,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采用的是“我”的人称视角,既可以营造真实的叙事效果又可以抒发强烈的主观情感。似乎只有这样,文化传承对她们来说才能是空白,而且至少在接受者那里,形成“我”无可动摇的中心位置。视角的选择影响到表述者态度、情感的传达以及接受者所获信息量的大小,和同时期的女作家(冰心、丁玲等)不同,沈祖棻虽然更擅长使用第三人称,但作者、叙述者、人物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全知者被认同到“她”中去。这种视角选择是迄今为止发展得最成熟、被运用得最普遍的结构模式,从《诗经》中的弃妇诗篇到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是将视角认同溶解于“她”的观点。说的是“她”,其实作者也就是“她”,叙述时不会受到角度的限制。
在沈祖棻女性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两篇作品《茂陵的雨夜》、《马嵬驿》中,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声音经常性地与“她”的心理或话语独白重合,这种视角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它标志着中国的女性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叛逆与解构。《茂陵的雨夜》以卓文君的内视角写出,男性缺席。作者成功地假定了一个不在场的参照体系——伦理文化规定的世俗印象,然后再将这一印象内化为主人公的行为目标,即使自己明知虚伪做作、恼恨万分也难以将其抹去,甚至要实现快意的复仇。作者叙写历史人物在追求浪漫人生时遭遇的个体抵抗,着意于个体的积极生存与这种生存的不可能实现间的矛盾,从而使这篇小说获得了同类主题作品中一个似轻实重的高度;《马嵬驿》用相当的篇幅写杨玉环的美,转换了视角,把女人抛远的目光收回,将女人身体作为表达:我的身体是我的,不是你的或者他的。男人的标准和尺度在此是理性的,也几乎就是先验的,所以要想搞清楚女人的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只有通过女人以自身的视角才能实现。
杜夫海纳曾说存在就是被叙述,意为话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一种风格化的叙事效果,是叙述人的文字渗透到事物、人物和事件的存在方式之中的体现。写作是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记录,女性写出了自己的话语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存权和自由意志,“拥有一种声音,就意味着拥有一种生活”。但是人类的话语场是以男人的权威确立的,女人不具备话语权力,她从写作的初始便在使用男性既定话语规范与打破这一规范间挣扎。沈祖棻将“女”字突显意味着把语言本身(男女共有)从语言(男性话语)中断裂出来,这是一种作为存在的拒绝和反叛。历经岁月感受的沈祖棻在一定意义上将历史的背景元素置放于主体心态元素之后,她笔下的历史与男性的一以贯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是不同的,而是一种非时间化的拼接。她在捕捉每一次心跳,感受每一种情绪,将历史的点点滴滴叠加起来,并不讲究男性所倾向的有一定的长度,错杂的内涵及跌宕的情节。沈祖棻以历史写作者的身份显示了人物的话语欲望,呈现出的既是她们的自我吐露又代表一种深刻的共性体验。她笔下的女人大多有自觉不自觉地突破自己的言行举止的渴求,从而使本身的行为跳出社会身份的约束,人格规范与自我意识的冲突都会使人物带有突围的痕迹。从沈祖棻对历史的叙述视角可以看出,女性不论是叙述人还是主人公,她在自身确定的秩序中都实现了自我设计,实现了女性对自身意义的现代命名与界定。
肖沃尔特概括女性写作发展的三个递进性的阶段:“首先是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力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动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8]那么,出于某种局限,沈祖棻的历史叙事只是在第一、第二阶段的过渡,尚存有一定限度。沈祖棻的历史小说多创作于30年代中期,创作时间不长、为数不多。当时的集体话语被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浓雾笼罩。沈祖棻的“历史”当属女性宏大叙事背景笼罩下的一个声部,虽然同样叙述民族精神、人伦亲情,但叙和述相比,她更重后者。这种述说把女人当成主人公,让她们占据历史,注重女性主体性的凸显,却对周围环境施予的压力漠然。她们无论在30年代的语境还是在还原历史的语境中都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所以这“战争”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注定是女人的乌托邦设想。沈祖棻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叛和突围,但她达不到颠覆的高度,只能找出历史某一时期叙述的漏洞,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条件大致允许的反抗。她写中国传统的故事,情境和心理为小说营造了情绪化的世界,但故事的情节链却并不光滑可触;她写心理,而没有像现代派“由意识的本体出发,经过详细而缜密的构思,将内在的感觉变为意象的线条”,所以在遣词造句方面还是酣畅有余,韵味不足;她的小说色调暗淡重于明快,过多地写女人的艰难不易、却忽略了生为女人的欢娱和自足,对女性美的人文色彩表现乏力。虽然在以男人为标尺的世界里,女人天生就是暗淡的,况且她在暗淡、无奈之中仍隐含超越,有着峰回路转之后的柳暗花明。但总的来说,沈祖棻并没有去表现主体实现的可能,而钟情于主体在困局中的无奈。
女人对世界的认知始终处于有限的了解和理想化的理解之中,欲说还休的困惑因之无法避免。一次次的历史转折与蜕变带给整个民族像空气一样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困惑。生存其中的沈祖棻则更多更深地感受到这种普遍的精神存在,因她要对世界和自身进行双重认知,要在“人”的解放背景下寻求“女性的发现”。诗人和学者的身份使她更加困惑于理性憧憬与现实存在的距离、困惑于由旧的被打碎而带来的新的选择,困惑于观念林立的无法判断。对历史权力的破坏固然只是女性为自身争得席位的手段之一,但她的历史小说在深度广度上并未形成应有的势力场。这无疑是所有女性作家受制于男性话语控制的事实,在不使女人游转于边缘之地时,沈祖棻本人的历史叙事却被遮蔽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她“用情丝和思绪系上灵活的笔尖,去做灯光照亮每个灵魂的暗隅”。“不仅用她的感乱伤离的歌,迎春祝捷的酒,而且用她的少女的梦,少妇的泪,母亲和祖国的心,教师和学者的口和笔”书写历史人生,她依然在精神追寻中承受着命运的播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