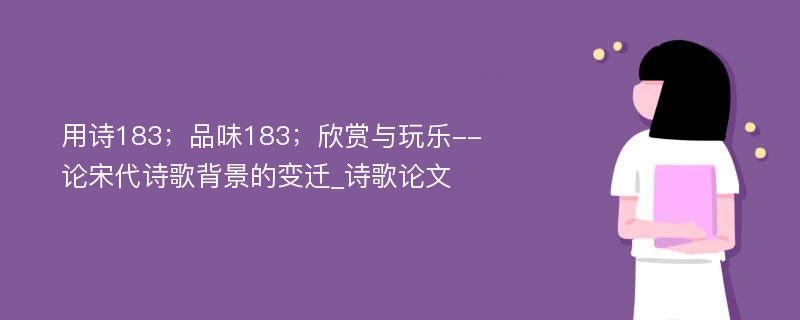
用诗#183;品味#183;赏玩——论宋代诗学背景之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宋代论文,背景论文,用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06-0066-04
如何理解宋代诗学大不同于前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具体诗论去把握诗学精神的转换。这一点,相信是学界共识。但在具体做法上,以笔者有限的涉猎范围看,发现一般的研究著述还有明显偏差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一是从“诗分唐宋”观出发,宋代诗学转向往往被理解为具体的鉴赏论、创作论的不同,由此很难越出“以意为主”的视野。二是过多地强调道学的影响,于是“以理为主”又成为宋代诗学的一道底线。其实,无论“以意为主”或“以理为主”,都是过于具体的诗论,不足以充当宋代诗学的精神背景。再则,如果我们以道学为诗学研究的出发点,为宋代诗学的底色,其实是大有疑问的。哲学之论究竟如何转化为文学之论的?对社会、人事的洞见,哲学之论永远先于文学之论吗?我在这里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只是力图既脱离具体诗论,又不滑入形而上高论,来描摹一下宋代诗学的背景。
这需要一种反思性追问:种种诗论何以产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的立场、态度、情境……亦即背景上生发而来?纵观自先秦至宋代的诗学发展,我将不同时期的诗学背景依次描述为用诗的立场,品味的态度,赏玩的精神。宋代诗学正是依其赏玩精神显示出自身的风貌,并成为传统诗学的、也许是一个主流的倾向。
先秦两汉诗学的用诗立场是我们熟悉的,但为了在比较中凸显宋代诗学的转向,仍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范文子言“诗以言志”,可它并不是说诗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志意的,它只是说朝聘会盟场合的外交官们,庙堂朝廷之上的公卿大夫们,可以用诗来委婉、细腻、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提出自己的建议,反映自己的意见等。《左传》中大量“赋诗言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代,在不同的场合熟练地以诗来表达自己或领会别人用诗的表达,对一个当政的贵族、或对一个企图走上仕途的“士”来说,应该是基本的素质要求。所以孔子才感叹:“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这实在是没有一点夸张。既然在任何政治、外交场合都可以随机地引用诗,冲破诗之本义束缚也是势所必然了。“断章取义”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用诗方式。尽管有孟子提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可理论归理论,他自己所为,不过是先秦时代“断章取义”用诗的又一例子罢了。(注:《孟子》[M]一书,共引用诗三十余处,其中不乏断章取义,以为自己论证目的服务。)这种用诗的风气,合乎逻辑地会有“诗无达诂”的结论。“诗无达诂”虽是汉人的说法,[1]但可以将其看作“断章取义”的逻辑结果而不是汉代诗学的主要论点。很明显,无论齐、鲁、韩、毛哪一家,既奉《诗》为经又严守师法,决不至于承认“诗无达诂”。况且,四家诗虽说法各有异,在基本立场上却是一致的。清人程廷祚《诗论》概括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四家均是经学诗学,这是汉代用诗不同于先秦用诗的地方。
如果说,贯穿先秦两汉诗学发展的是一种不变的用诗立场的话,魏晋六朝直至隋唐诗学的发展,则愈益显示出品味的态度取向——我在这里将其定义为论者总是处在与诗歌作品的水乳交融的一体状态中,甚至是在陶醉中去品评诗歌的“滋味”。本时期钟嵘、司空图的两部《诗品》,是颇具代表性的诗学著作。我们不去辨析它们的概念,让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也去“品味”作者不得不如此说的由衷之情。钟嵘《诗品序》大段有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作者于人情、诗情的一种醉心,洋溢在字里行间。司空图同样如此,他言简意赅地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论诸者首先要沉浸于诗的情味中,然后才有言说的可能。与此相符合,他自己将唐代诗学建构的审美对象——境,一一细分出24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将钟嵘提出的“滋味”细细分为24种,不可谓不明辨,然而不是“慎思”的结果,只是一味地“品”。什么“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二十四诗品》)。他让读者完全地融于诗情当中去“品”。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认识是,六朝乃至隋唐是一个“尚情”的时代。正是如此,具体化为诗学背景,它就成为一种品味的态度取向。
从尚情的角度定义“品味”,从功用的立场阐说“用诗”,并把它们当作宋以前诗学发展的两个背景,我想,是不会有太多疑问的。这样,我们对宋代诗学转向的思考,就应该紧紧追踪其如何对立、偏离传统的诗学背景的。于是,我们可以沿着两条线索——非功用和情感超脱,去考察宋代诗论,并由此达到对宋代诗学赏玩精神的把握。
先谈非功用。先秦两汉的“用诗”,最终集中体现为“美刺”诗学,宋代诗学的非功用转向,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反对“美刺”说。一般的文学史,由于渲染“文学自觉”而给人印象,似乎魏晋已开始反对汉儒的“美刺”诗说,这是不确的。为了充分理解宋代的“第一”,从而真正彰显宋代诗学的非功用转向,我们还需回到六朝稍辨析。六朝诗歌创作,固然是“缘情绮靡”,“声色大开”,好像在无声地反对“美刺”诗说。但创作内容不等于诗学观念。诗歌从来都是“缘情”而作。《诗经》的作者早已有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啸歌伤怀,念彼硕人”。[3]屈原也有自诉:“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结微情以陈词分,矫以遗夫美人”。[4]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社会普遍的用诗立场。其实,如果仅就创作内容而言,诗歌(文学)创作从来也没有成为普遍地上“谏书”(白居易最多只能算勉强的例外)。汉代以前如此,汉代以后如此,甚至汉代也是如此。汉大赋“曲终”的“奏雅”,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罢了,所以才会有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武帝好神仙,帝反“飘飘有凌云之气”(《史记·司马相如传》)。那么,将陆机的“缘情”说看作是诗论,它难道不是在反对政教功用的“美刺”说吗?这也是似是而非。“美刺”是用诗的看法,“缘情”是一种诗歌发生论,严格地说,两者并不矛盾。诗歌怎么来的是一回事,它有什么作用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毋宁说,六朝人只是尽情地写诗,尽情地品诗,至于诗是否有政教功能,他存而不论,而不是反对。当然,从政教功能出发,会引申出对创作的限制——“止乎礼义”,这确实对立于六朝的尚情精神,但也仅是一种引申的对立,而不是用诗的立场和品味的态度的对立。这一点,在唐代表现得更清楚。文学史上公认唐人是沿着六朝人开创的诗歌创作之路,日益达到了完美的高峰。可偏偏是唐人对六朝诗歌指责最为激烈。这是耐人寻味的,它再次说明,一方面,创作内容不等于诗学观念;另一方面,“缘情”的观点不碍于“美刺”的事业。白居易等人的诗说固不必论,即以李白这样纵情高歌的诗人,都会时而发出古板、正统的见解:“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第一)。《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整个是一个下降通道。六朝“绮丽”之所以不足珍,就是因为离“大雅”之“正声”愈来愈远。这里体现的就是尊《诗》为经的汉代诗学,自然隐含着对汉儒以“美刺”释《诗》之微言大义的赞同。
宋人首先开始否定“美刺”说。如黄庭坚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5]并讥评当时的注杜诗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6]梅尧臣也通过称赞林逋的诗:“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至乎静正,不主乎刺讥”,[7]来表明自己不屑于“美刺”诗说。这种认识逐渐扩大开来,到了南宋,颠覆《诗经》本身的“美刺”大义,也是顺理成章了。我们并不需要处处从“理”,“心”的哲学层面上去寻找宋学取代汉学的依据,就《诗经》而言,非功用的宋代诗学精神流风所及,朱熹完全可以很自然地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一般,其间也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8]
准确一点说,宋人否定“美刺”,是否定诗的政教功用,他们是否也否定诗的抒情功用呢?在一个“品味”的诗学时代,抒情是相当被看重的,就象针嵘对“诗可以怨”的理解那样,“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没有比诗歌能更好地抒情,从而安抚、镇静愁怨的人们的了。宋人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点,也否认不了,因为抒情功用源于诗歌创作的基本事实——缘情而发。无论是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还是黄庭坚的“诗者,人之情性也”等等,都是对传统的抒情诗论的承认和继承。类似的言论在宋代诗论中并不少见,但就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观点产生了。苏轼引述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9]当代的文学史著作,很重视这句话,认为它是在道学氛围中的对文学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我仅仅关注这个“文学自身价值”。实际上,在我看来,它也许是文论史上第一次如此鲜明地肯定了文艺作品的客观自足性。这种自足性,不仅意味着非政教功用性,甚至作品的抒情功用,其实也是作品同作者(也有读者)的关系,都被悬搁了起来。文学作品终于能以客体的面目,拉开了同主体的距离,为接受主体的认识作好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诗学相对于“品味”时代的诗学转向,不是否认情,而是对情的超脱。我们已转到了情感超脱这条线索。
比较直接地谈论诗歌作品的客体性质,如欧阳修的“精金美玉”之论那样,在宋代并不多见。但宋人喜谈的“意”、“理”、“法”等,其实都含有不言而喻的情感超脱的立论前提。唐人皎然可以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我们当然理解,这是对最好的诗歌的礼赞,更能体会,这恰是皎然本人浑然沉浸于诗情中的自白。刘禹锡说“境生象外”,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也可作如是观。反观宋人如黄庭坚,偏偏要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10]皎然等人“不睹文字”,黄庭坚却看到了“每一个字”,个中原由无它,正是显示出宋代诗学的情感超脱相对于品味态度的转向。由此我们必须深悟,宋人诗论之所以能倡“理”,是因为论者与作品之间已先在地具有理性考察所必需的距离了。
我们的理解并不就此结束,我们仍然要追问,非(政教)功用和情感超脱,又意味着什么?一个简要的回答就是:非功用体现了由来已久的诗的重要地位的终结。情感超脱又显示了独特的中国传统诗学认识模式建构的完成。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人们的喜爱暂且不论,这种重要地位依靠两点保证:一是先秦时代,诗歌具有事实上的重要性。一个熟读“诗三百”的人,内可以“授之以政”,外可以“使于四方”(孔子语,见《子路》,)而且确实能通过诗的唱答,来完成外交活动。放眼世界诗歌史,也许都找不到第二处如此令人称奇的“用诗”了。后代不再如此“用诗”,诗也就丧失了事实上的重要。但是汉儒尊《诗》为经,把诗同先王之道联系起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这样,诗的重要地位并没有随着不再“用诗”而消失,它又获得了另一个支撑点——形而上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一种“想象”的重要性,但它作为经学,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例如,我们可以设问,为什么选拔国家官员的科举制度竟然以诗赋取士?因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经学”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大序》),诗是最好的政教工具。自然,这只能是一种政治想象,人们不可能,至少不可能经常地、普遍地把诗写成“谏书”,写成“对策”。实际上,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朝廷已意识到以诗赋取士的不足,对科举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到宋代,范仲淹就愤激地说:“国家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因,乏人如此,将何以救”?[11]诗人已被排除在“有才有识者”以外了。这显然不是范仲淹一人的看法,因为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开始,殿试进士,就取消传统的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取士。其后虽有反复,但至高宗建炎二年(1128),再次规定殿试试策,终南宋之世,不复更改。这样看来,相比于前朝,诗歌在宋代是真正“沦落”了。理学家对“美刺”诗说的抨击,既是对这个“沦落”的历史注解,也是对诗歌凭附的那种“想象”的重要性的最终剔除。
那么,诗歌地位究竟下降到什么程度呢?程颐曾经很不屑地评论杜甫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又说:“《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12]理学家的态度自不必论,但是,从功用的角度看,诗(文)为“玩物”、“末事”,却也是真实。不独理学家这样认为,纯粹的诗人也意识到这点,这是宋代诗学的大背景。黄庭坚就说:“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13]“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10]和理学家相比,认定的是同一事实,不同的是态度。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诗歌以及纯文学,正是在“闲言语”,“玩物”,“末事”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它不需要靠外在的功用目的为自己赢得声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诗歌地位的下降,不啻是认识诗歌自身的有益机缘。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谓赏玩精神的内涵之一。
这个“内涵之一”也只是说明诗歌在时代意识中的地位,究竟诗论家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把握诗歌?这是赏玩精神的另一个内涵,即宋代诗学的认识模式问题。我们须返回到情感超脱线索中去探寻之。
情感超脱拉开了论者同作品之间的距离,诗歌作品有了客体的物的性质。(这一点,同诗歌地位的下降也有相通之处。)比如,黄庭坚有言曰:“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14]作诗如同百工制物一样,总需要某种技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完成,于是,宋人,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穷究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立意、布局等等。这是我们熟悉的宋代诗学的理性的认识眼光。有论者谓宋代诗学的这个特色颇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文学的“内部”研究等等,说“类似”是可以的,但不能当真。因为,宋代诗学的这种理性,并非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在主客观对立的认识框架下,对客体采取的始终如一的冷冰冰的科学理性,科学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职业“科学家”,黄庭坚等人首先是诗人,他们只是“论诗”,不可能像西方的一些学者那样去“科学地”研究诗。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宋代诗学的认识模式很重要。让我们作一个合理的推测,比如,我们不能想象,作为诗人的黄庭坚等体会不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带给读者的那种“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艺术境界,或者,无法领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体现出来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般的“诗家之景”,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黄庭坚等大谈古人、尤其是杜甫的诗的“用意”、“法”等等,只能看作是对于诗的“已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认识,而这既是宋代诗学超出前人的地方,也是何以超越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小例提示之。针对前引陶渊明诗句,苏轼曾评价:“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15]显然,苏轼完全体会到了“见”字的情味,此谓“入乎其内”;当他以“境与意会”的特征,将“见”与俗本“望”字区分开来的时候,他已经“出乎其外”地去认识说明“诗法”了。可见,宋代诗学的理性,是一种“已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理性。不过,这还不完全等于宋代诗学的认识模式。仍以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例。“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故学者要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16]正法眼,是佛家用语,指识得“真相”的能力,用在这里其实就是通常说的“悟”字。所以,曾季狸《艇斋诗话》总结江西诗派诸人云:“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之非悟入不可”。[17]一个“悟入”,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涣然冰释,论者再一次地融入到作品中去了,不过,比起开始的沉醉于诗的“滋味”中,这一次的“悟入”也可说是“理性的直觉”了,是对“法”、“意”、“理”的真正洞识。这样,所谓赏玩精神的另外一个内涵——宋代诗学的认识模式,就可以概括为:(对诗)“已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再入乎其内”,如此反复不已,把玩不已,因为“诗道”非能穷尽,即使对一首小诗。
诗的地位日渐沦落,成为体现文人士大夫雅趣的“玩物”,文人士大夫又在“把玩不已”中去认识这个“玩物”,这当然不是宋代诗学的全部,却是极富特色的部分。这也不自宋代始,但在宋代终成气候。这就是本文以“赏玩精神”所要揭示的宋代诗学的新面貌。
收稿日期:2001-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