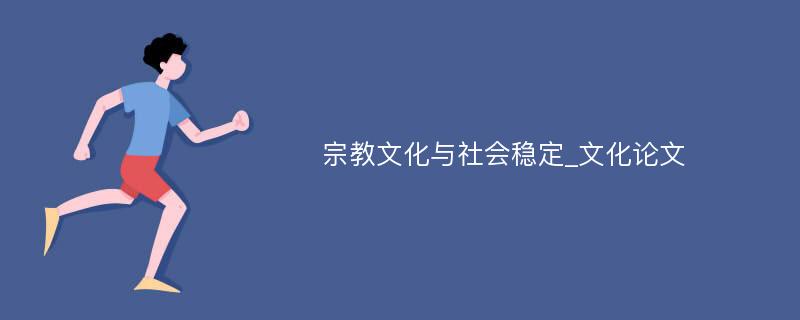
宗教文化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文化与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宗教文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发挥心理调节和群体整合功能而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宗教的核心是克制欲望而达到善的彼岸并奉行信仰至上的原则,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往往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渊薮。“邪教”更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关键词:宗教 文化 社会稳定
文化是人类生存所独具的认识和活动方式,它植根于人类同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标识着人与自然分离的程度和水平。由于人的缘故,自然演化出文化;由于文化的缘故,人类获得了真正的人的本质。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历史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宗教反映着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外部的或内部的)异己力量时的无能为力(社会的和个人的、实践的和认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无能为力),是在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和活动方式。或者说,是人类试图在幻想中理解和克服这种客观的无能为力处境的一种努力,一种模式,一种结果,也是人类力求认识和把握自己这种主观的自我意识的一种残缺或是一种残缺的自我意识。
因此,宗教是维系着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态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仅对世界具有认识和说明作用,是一种特殊的观念解释模式,为人类提供了一整套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评价,而且是对待生活的一种人生观,它赋予了个人与群体的生活一种意义和目的,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系统,对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具体而言,宗教在现实中具有各种解释和实践功能,它与社会稳定的特殊联系便是其中之一。从历史上看,宗教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但无论怎样,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宗教学家,都承认宗教的起源同社会的需要具有一定的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的功能,构成了其在历史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在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看来,宗教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神圣乃是社会统一体的象征,因而它在根本上是适应维系社会统一和稳定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所以,维持社会稳定是宗教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具体发挥作用:
一是心理调节。在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中,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心理接受和承受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虽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但它通过把现实的一切纳入信仰的解释模式之中,给予虚幻的反映和合理性说明,从而使一切矛盾和不合理被臆想地解决了:现实压迫被“精神自由”所克服;社会的不平等在“天国的平等”中被补足;阶级的仇恨在“上帝的怀抱”中化为兄弟情谊;社会中的罪恶与不公正被“末日审判”和“来世报应”所抵消;死亡意味着永生;贫困可换来安宁;饥饿使灵魂净化;失败是上帝的考验。这就是宗教作为“精神鸦片”的心理麻醉和慰藉功能,它以超现实的方式增强了人的心理接受和承受能力,提高了人应付各种现实问题的心理强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稳定消除了心理隐患。“战争与不公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伴随各种文明而产生的两种社会弊端。这种致命的社会弊端,有可能使文明社会的生机枯竭,不过在一定的时间内,宗教却是使这一社会维持下去的精神力量。”[①]
二是群体整合。宗教具有使社会结成整体,并稳定和维护这个整体的作用。一方面,宗教通过神话为社会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起源论,使其被神圣化,强化了社会对其成员的神圣感和首要性,增强了成员对其群体的崇敬感和依赖感;另一方面,它通过共同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共同的目的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实现了社会意识的统一。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它使社会沟通成为心灵沟通,把所有个别情感融合成一种共同情感”[②]。另外,宗教还通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统一了人们的行为,集中了社会的力量,实现了群体活动的基本一致。这些都巩固和加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密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团结,提高了他们与社会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在宗教的群体整合功能中,宗教道德,对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十分突出。宗教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人的行为的调节器,它主要从道德方面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矛盾进行调整。宗教与道德,共存于同一社会体系中,共生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的情况。道德用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的需要;宗教则用神的意志和天命的安排来神化以现存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道德为宗教教义信条体系提供了部分社会内容,宗教则为道德准则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一方面,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把恪守宗教关于道德的诫命作为取悦神宠和来世进入天堂的标准;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给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之行为当与不当、德与不德、差与不差的普遍准则,由此而形成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道德宗教化与宗教道德化的现象。
在宗教文化中,宗教被奉为全部道德的源泉,一切道德的基础、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都是从神的召示引伸而出。按照他们的说法,正是由于宗教信奉作为赏善罚恶之正义主宰的神的存在,规定了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天堂地狱、来世报偿等教义信条,这才促使世人去恶向善,并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神圣的保证,为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净化奠定可靠的基础;如果没有宗教的那套教义信条,人们的行为就会无所顾忌,社会上必然出现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局面。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将社会稳定完全依附于宗教道德的说法带有明显的虚妄性,有悖于人类历史,但宗教道德对于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却不能忽视。
各种宗教往往把社会生活中的世俗道德都同宗教道德等同起来,把世俗道德宣布为神圣诫命,成为宗教教义和宗教信条的一部分。佛教、道教的“五戒”、“十善”,犹太教、基督教的“十戒”,以及伊斯兰教的关于道德的训诫和教法规定,都含有许多现实的内容。基督教“不可杀人,不可偷窃”的道德规范,反映了人与社会普遍的道德观念;伊斯兰的宗教文化突出强调个人行为的善恶,以真主的末日审判和赏善罚恶来保证人的道德生活,任何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无善不报,无恶不罚,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真主的审判,任何行为都因其善恶的性质和程度而得到相应的报偿;佛教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作为道德基础,表现为对社会一切人都机会均等。大乘佛教“主张宇宙和其它一切生命都跟自我之间的调和与融合,主张在这里才有人生的理想和幸福,其实践就是表现在由慈悲而产生的利他,通过这一高尚的理念把欲望克制下去。”[③]克制欲望,以利他为出发点,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不能仅看作是宗教的信条,应该认识到它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所有这些,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劝善止恶,弘扬道德伦理,确立和稳定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确保私有财产不被盗窃和不受侵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宗教通过将道德规范神圣化,宣布为神圣诫命和死后奖罚的标准,这就必然强化了道德的权威性和人们的服从心理,使道德更具约束力,从而也更加增强了道德对社会稳定的维系作用。
无论怎样,宗教总是以一种虚幻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宗教在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相反的作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是社会稳定的维系力量;在另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同样会成为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宗教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克制肉欲而达到“善”的彼岸。各种宗教一般都把罪恶的根源归结为物质的诱惑和肉体的欲求,宣扬物质和肉体是罪恶之源,认为只有通过禁欲和修行才能使灵魂获得拯救,从而倡导奉行违反人道原则的禁欲主义。但是,克制作为生物本能的肉体欲望,放弃对生存所必须的物质需要的追求,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它本身就是违背自然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强行做到了这一点,不仅有违于人性,而且在许多时候是使外向欲求的心理能量不能外泄,而被压抑在潜意识内部,成为一种没有目的和方向的冲动。它不仅常常成为人的一些心理和生理疾病的根源,有可能导致变态心理和行为,而且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在适应的社会条件下会产生非理智的疯狂举动。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的所作所为,以及近代出现的反禁欲主义的宗教改革运动,不能不说与此有相当的关联。
其次,宗教奉行信仰至上的原则,信仰决定着信教者的意识和行为。为了信仰,他们可以付出一切,也可以从事一切。因此,对神的绝对信仰必然降低对人应负的道德义务感,对神的绝对肯定必然包含对人的否定,对神的绝对服从必然意味着对人的抛弃。美国学者威廉·詹姆士在其《宗教之经验种种》一书中揭示了宗教的此种性质,他认为,“对上帝的过份虔诚会导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视为理想,把对神的牺牲和谄媚看成是美德。”他进而指出:“一个太窄的心灵只有可容一种感情之地,在爱上帝的感情占有了这颗心时,这种感情就把一切爱人类,并为人类效用的心除掉了。”[④]在宗教信徒们看来,只要是出于对神的信仰,就属于宗教美德,理应得到上帝的奖赏。许多宗教都有爱惜生命不可杀人的戒律,但为了表示对神的崇敬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可以把杀人弑亲作为对神的献礼。宗教的信仰能导致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尽管从其情感自身而言可能是纯洁的、美好的,但它作为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往往漠视一切规范和秩序,无所不为,因而常常成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古今中外历史上,莫不具备此类事例。
再次,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排他性,往往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渊薮。在各种宗教文化中所信奉的神,本质上都具有否定和排斥其它宗教的排他性,他们总是宣扬自己信仰的神才是至高无尚、唯一无二的,自己信仰的教义才是真正的昭示和绝对真理。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他性。各种不同的宗教,甚至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教派,它们所信奉的神的神性和教义。不但互有差异而且常常彼此对立,这就决定了他们总是不可调和,更不能互相承认。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宗教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不同宗教的歧视与迫害。基督教高唱上帝爱大家,一切罪过都可以赦免,可是耶稣对不信其教者从没有表现出半点宽容赦免的姿态。如“十字军”东征使阿拉伯世界血流成河;布鲁诺因信奉科学而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就是明证。信奉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之间长期纷争不已,从古至今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不仅不同宗教之间存在强烈的排他性,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之间往往也互不相容争斗不已。佛教高唱慈悲平等,忍辱无争,可谓人道之至,而其内部各宗派间却常常因一经、一偈的不同理解而互相仇视,甚至置对方死地而后快。基督教在实行宗教改革后,新旧两派都把对方视为异端,新旧两派的斗争曾一度在欧洲大地上广泛展开,甚至兵戎相见。伊斯兰内部的教派争斗更为激烈,什叶派与逊尼派多年来就犹若水火,两不相容,这种血肉相残的斗争在今天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仍在继续。历史和当代世界上连绵不断、层出不穷的宗教战争和教派斗争,也许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民族等方面的原因,不能笼统的归咎于神和宗教的排他性,但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兵灾战火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苦难,却不能忽视。
第四,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功能。不仅统治阶级利用它麻醉被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往往也把宗教作为反抗统治阶级的武器。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历史中,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整个国家机器都腐朽不堪,贪官污吏肆虐横行,百姓民不聊生的时候,人民群众要想推翻统治阶级,往往需要罩上另一道神秘光环,披上另外一层宗教外衣,打出另外一种鲜明的宗教旗号。恩格斯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之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⑤]在宗教文化占据思想领域的条件下,只有借用诉诸民众感情的宗教观念,运用民众最为熟念的宗教语言,才能“揭竿而起,从者如云”,掀起巨大的狂潮波澜,给原有的统治秩序以强烈的震撼冲击。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运用神秘的宗教语言进行动员,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则是针对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之风弥漫朝野的状况,以“太平道”的教派活动为手段,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宗教口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编造“石人谶语”与陈胜、吴广制造“丹书”、“狐鸣”异曲同工,而利用白莲教宣扬“明王出世”和“弥勒下生”,又与张角运用“太平道”和方腊利用明教起事一脉相承。至于中国最大的一次利用宗教而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则更是利用上帝的神圣权威去打倒君王的神圣权威,利用宗教手段去达到政治斗争目的。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数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满的人也会借助宗教的外衣和旗号,从事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受某些外国势力支持的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就曾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五,在现代社会,宗教成为许多人寄托精神的急功近利的工具,也是少数人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的特殊手段,因而许多实为“邪教”的五花八门的现代宗教,不断出笼,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化,生活的紧张不安,工作的沉重压力,人际关系的疏远陌生,价值观念的多元冲突,使得人们精神混乱空虚,情绪狂燥不安,渴望得到内心平静和心灵交流,急需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对传统和现实的失望以及现代人急功近利的特性,使许多人纷纷投向各种新型宗教,力图在各种新奇的宗教信仰中寻求慰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趁机大肆标新立异,创立形形色色的现代宗教。这些现代派宗教宣扬世界行将毁灭,新救世主将莅临人间,信教者才能获得主的拯救而进入一个平和宽畅的天堂。它们往往思想偏激,情绪狂热,甚至诉诸暴力,以破坏和毁灭渲泄其压力与苦闷,并以此惩诫不信教的“执迷不悟者”,用损害他人或虐待自己,甚至集体自杀来迎接主的降临。8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圣殿教”教徒900余人集体自杀事件,以及近期在日本制造东京地铁事件,致使无辜者中毒伤亡达数百人的“奥姆真理教”,都属于这类新崛起的宗教组织的代表。这些现代派的宗教团体除少数于世无害外,大部分具有邪教的性质,它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或多或少地威胁着广大民众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对于维系社会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鼓励人们抑恶扬善,无疑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我们应该科学的、实事求是地正视它的存在,我们不能赞同宗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的说法,但也不应忽视宗教文化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持社会的正常稳定,不仅必须健全科学、民主的政治和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道德基础,通过人的道德自省,人人的内心世界产生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约束的力量。这必然应该包括利用宗教文化的社会稳定功能。我们对宗教文化中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的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坚决予以摒弃,而对宗教文化中鼓励人们利他向善、劝戒人们不要纵欲等有利于优化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健康和谐的人事关系,对社会稳定有着某种积极作用的内容则应予以适可而止的肯定。
注释:
① ③《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公司版第363页、第395页。
②(英)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版第198页。
④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第63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