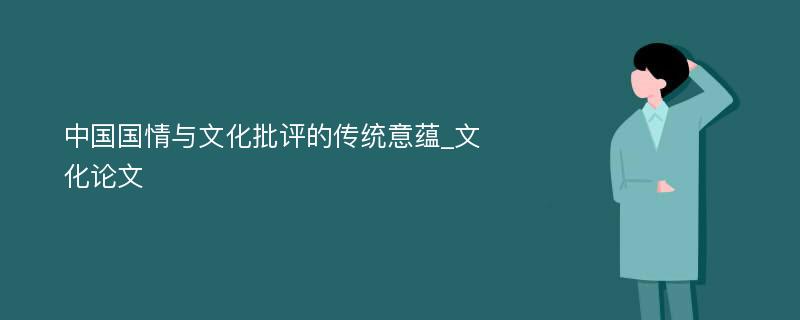
文化批评的中国境遇与传统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境遇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视角介入文学批评早已有之,但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是指由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催生的各种反对形式批评的文化批评理论,这些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输入中国,一时出现了众多理论话语齐声喧哗的局面。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这种理论:来源于西方理论资源的文化批评符不符合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理论过剩”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不能深入文学内部的“不及物”的批评模式?
文化批评的西方语境
反思是必要的,没有反思就没有理论上的进步。每一种理论都有它得以生成的土壤,也都有它适用的界限。伊格尔顿认为,“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出自美国,或者至少在那里迅速扎下了根,并且反映了这个国家某些最棘手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对中国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非常地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所造成的一种时间扭曲,“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①言下之意很明确: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其实是西方理论殖民的表征,中国目前面临的是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后现代性的问题。按照伊格尔顿的逻辑,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前的文化语境完全是错位的。但是仅仅以历史发展的分期来限定理论的适用空间显然过于武断,只有回溯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历史语境才可能真正明确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
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阿多诺为什么要批判大众文化?因为他信奉现代主义的激进美学,认为大众文化是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为什么经常谈到传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那是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他想通过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建立一种共同文化,一种理想社会。杰姆逊为什么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有时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伊格尔顿为什么要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他认为这是激进的政治变革的准备。即便是被伊格尔顿嘲讽的“在政治上含混不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也还想着通过身体、身份、种族、性别、非同一性等等去反抗资本主义的体制化。文化批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就在于传统的文学批评遭遇了“意义危机”:文学本来是一种贴近人类具体生活经验的人文现象,如果文学批评只能在语言符号、形式结构、审美乌托邦里打转转而无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的话,那么这种文学批评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人觉得这样一种沉重的社会担当是文学批评的不可承受之“重”,然而回顾历史,文学批评的最初形态不都具有这一特点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批评只不过是“把文学批评唤回,使其回归它已离弃的古道”②。正是因为文化批评强调批评的现实意义,所以它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十分宽容的:“研究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试图去做什么,以及置身于何种境况……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有助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而创造‘更好的人’,就都可以接受。”③因此,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如果有必要,文化批评也会去解读文学经典;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也不是强调只能从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如果条件合适,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一言以蔽之,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强调社会批判的批评策略。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在文化批评理论兴起之前的几十年里,形式批评和被自由主义理论浸透的人文主义批评,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学术机构。这种批评方法非常反感文学与社会政治的牵连。因此,文化批评的现实关怀也是西方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矫正。
文化批评的中国境遇
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化批评在西方语境中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批评策略,它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可循。然而它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别人强调的是现实关怀,我们强调的是理论特征。按照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一种理论必然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有明晰的方法界限。于是在有些研究者那里,文化批评被理解为针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活动,文学批评被排除在文化批评之外。在有些研究者那里,文化批评被理解为对文学的“文化”批评,是借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理论资源,来解读文学现象的“批判话语”,传统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好像是绝然不同的。我们以“划界”的思维方式理解西方“越界”的理论追求,误读不可避免,由此而产生拒斥的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历程确实不同于西方,两者的道路甚至是绝然相反的:他们是现实关怀不足,我们是现实的束缚太重。由此看来,文化批评引入中国确实有水土不服的风险。但中国同样也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知识分子去认真面对,如文化身份的认同,底层状态的书写,消费主义的盛行,宏大叙事的消解,女性权力的诉求等等。文学批评能够对此沉默不语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当然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而来,想要闭门不纳都已经来不及了。
文化批评理论化色彩颇受诟病。很多人抱怨一些文化批评的术语玄奥虚空,大而无当,认为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批评实践中完全是语言游戏,生搬硬套。在他们眼中,文化批评是一种“空谈”的批评。这种观点与前些年一些学者忧心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心理极其相似。在他们看来,用西方的理论资源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一种学术上的崇洋媚外和妄自菲薄。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比较陈旧的语言观:语言无非就是表达意思的工具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语言阐述同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把西方理论翻译成为中文的时候,这些理论就已经中国化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西方理论称之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运用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得出的结论也许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话语给出,但是得出这些结论的思维过程可能与中国传统理论大相径庭。试想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与中国传统的“中庸”观念能够画等号吗?我们经常说,文学作品本身与用另一种语言转述的文学作品是不能画等号的。其实对文学批评来说也是一样,文学批评的论述过程也绝不应该简化为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转述的批评结论。
还有一些批评者固执地坚持作者文本和作者意图的优先性,担心批评者的意义生产湮没了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在他们眼中,文学批评从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次生文本,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只要文学批评稍微越出传统的阅读习惯,他们便怀疑这是一种过度阐释。难道批评就得如此谨小慎微吗?能够生产出意义的文学批评对于其读者而言是一种幸运而不是灾难。
以上这两种批评都指向文学批评理论的具体运用。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过剩”的指责有时也指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本身。这两种指向虽然外表相似,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批评者认为中国当代批评理论是“引进”过剩,暗示的则是一种理论的贫乏与饥渴。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好好消化西方的理论,进而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理论。这些学者其实是在呼唤中国化的文学理论的激情爆发,他们的这种意识应该受到肯定。
理论是一种反思的话语,虽然西方理论繁荣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理论本身将始终伴随人类走向未来。伊格尔顿说,“敌视理论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④,此言一语中的。从根本上讲,指责文化批评实践“理论过剩”的批评者只是更欣赏、更习惯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然而,今天文学批评的读者已经不是过去的读者,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课堂上不停地重复传统的阅读模式,学生们也会产生审美疲劳之感。而且对中文系的学生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审美的乌托邦,还有知识信息的传播和思维方式的磨炼。即便是普通读者,转换文学欣赏的思路与角度有时也是必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不能画地为牢,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不一定非得局限在“创造性”、“想象性”的牢笼之中。事实上,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涵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我们为什么要奉之为永恒的真理?“文学”概念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存在纯粹的“文学”,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的传统意蕴
文化批评的兴起必然会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发生矛盾,不仅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如此。英国的现代文学批评一直强调对文学内容的再现式地阅读,当西方上世纪60年代各种“文学理论”兴起的时候,英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只是谨慎地输入了结构主义方法,而排斥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等“爆发性”的理论。当文学的文化批评在中国兴起的时候,自然也会遭到一些抵制。经常会出现的疑问是:如果对文学的文化批评都要考虑现实问题,那么这还是“文学”批评吗?社会学、经济学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不是比文学更直接、更有效吗?文化批评对此的回答是:文学意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融为一体,社会的变革必然是以日常生活感受的更新为基础的,而文化批评正是促使人们日常生活感受更新的一种动力。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文学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更具有基础性。
但是文化批评的现实关怀并不意味着它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绝然对立,文化批评并非仅仅只是对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把传统上所谓文学的“审美价值”完全抛开,把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经验完全弃置一旁。与其他文学理论一样,文化批评理论同样是对阅读经验的总结和对阅读规律的提升,文化批评同样需要建立在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也许有些人看到斯皮瓦克把《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判定为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时,会觉得这是一种过度阐释。但是斯皮瓦克有充分的、有力的文本材料来支撑这一观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仅仅表现为露骨的殖民主义言论,而是更为普遍地显现为无意识的话语和隐而不现的神话。伊格尔顿对理查逊的小说《克拉莉莎》的意识形态批评同样建立在严格的人物分析的基础之上:“克拉莉莎·哈洛威比任何人都更加唯父权制之命是从,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为资产阶级的忠贞道德辩护”,但是“小说越是肯定这些价值,哈洛威一家就暴露得越发彻底;克拉莉莎越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柔弱温顺,对那些置她于死地的人所作的批判就越发彻底”⑤。在很多情况下,文化批评只是比传统文学批评多了一点阅读的自醒意识和批判意识,他们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它们之间的差异,研究者们大可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即便是对作品的价值判断上,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也有广泛的一致。传统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批评所探寻的社会现实关怀往往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文本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关系越是复杂、深刻,就越是具有传统文学批评所谓的美学价值,同时也获得越有力的意识形态批判力量。在一些文化批评家看来,文学作品写得好不好“不止是‘风格’问题,它还意味着具备一种能自由支配的思想能力,能透视人们在某种场合下所经验到的现实情形。”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所描写的普拉西多海湾的景色在艺术上显得极为精湛,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艺术上的成功与康拉德极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有关。因为康拉德这种极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与当时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使他获得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从而获得一种深刻的思想体验。“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出来。”⑥因此,虽然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的角度不同,但它们的结论极有可能是相似的。
总之,尽管文化批评有其特殊的批评角度和价值标准,但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批评一样,文化批评只有与批评者的文学阅读经验相呼应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有太多疑问。眼下,文化界强调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感受性、审美性的呼声一再响起,其理论背景具有多重性。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想纠正当下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一些偏失之处,诸如学院批评的机械僵硬、曲高和寡,媒体批评的浮躁与功利以及一些所谓“酷评”的简单粗暴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缘于企图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而确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化身份的理论诉求。
当然,诗意的栖居仍然寄托着当代中国人的自由梦想。然而,任何精神的追求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都将变成空中楼阁。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作为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穿越最为野蛮的历史阶段。我想,文学批评也可以两个向度:一个指向理想,一个指向现实。批判的文化批评和诗意的传统文学批评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注释:
①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页。
②③④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第264页,“序言”第2页。
⑤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⑥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