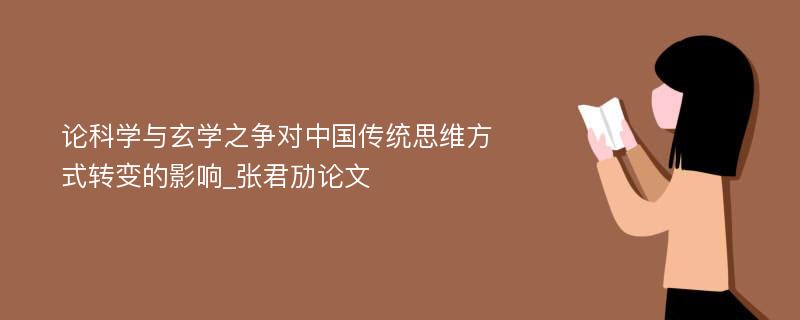
论“科玄之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和对立是20世纪世界性的哲学课题。发生于五四时期的“科玄之争”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实质上也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和冲突,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争论是在东西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轨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
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有控系统,这一系统的显著特征是,它导致了中国人有机的、连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重直觉、综合,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的特点,但由于没有实证科学作基础,往往引导人们去进行空洞、无益、脱离实际而又不能产生具体成果的思辨。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避免陷入机械论,却不能引导人们走向近代科学,因为它主要不是科学思维,而是玄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才逐渐发生转换。
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大开,中国人固守的传统观念开始解体。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魏源等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方文明之所以高,在于“技”,故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只流于浅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洋务派继魏源等人之后,强调实业兴国,然而,和魏源一样,“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他们那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并未发生根本动摇。随着维新派的崛起,西方文明的本质才为更多的人所逐渐认识,他们中有不少人曾直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洗礼(如严复),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西方文明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以什么方式来把握必然之理和因果关系,即在于思维方式。但在严复那里,这种想法还是模糊的、缺乏具体的环节。到了五四前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丧失了其威摄力,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衰败的症结所在。于是,一场重建思维方式、价值信仰体系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科玄之争实质上就是以思维方式为轴心而展开的。
二
科玄之争中的科学派将科学作为重建新的观念体系的轴心。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但具有可信的,而且具有普遍的品格,科学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主体行为,最终都被诉诸科学的解释,一切都须按科学原则行事,一切都须以科学原则加以裁决。
玄学派就是抓住科学派所主张的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而展开攻击的。论战是从张君劢在《清华周报》上发表的演讲开始的。他说:“我对于我们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希望也、要求也,是谓之人生观”,其特点是“曰主观的、曰真觉的、曰系统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因此,人生观就是“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1〕他还列举了九项人生观问题, 认为人们对于这九项问题都有不同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没有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人生是没有因果规律可循的,“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皆其自身良心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故曰直觉的也。”〔2〕张君劢对科学派所鼓吹的“科学万能”非常不满,他主张“意志自由”,认为“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人生之总动力,为生之冲动。就心理言之,则为顷刻万变之自觉性,就时间言之,则为不断之绵延。……此‘生之冲动’,人各得其一部,故一人则有一个之个性,因个性之异而各人之人生观因而异之。”〔3〕科玄之争的本质在他看来“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自由意志问题是矣。”〔4〕在这里, 张君劢提出了与科学派相对立的看法:人生是“生之冲动”,是自由意志,并非科学所能把握。所谓“生之冲动”,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那里,叫做“生命之流”,它是不受任何因果规律限制的,是绝对自由的。生物的进化就是“生命之流”或生命冲动的不断更新和创造。张君劢承袭柏格森的观点,主张“生之冲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动力,而这种发展又是“顷刻万变,过而不留”,“故绝对无可量度,无因果可求。 ”〔5〕这样,张君劢就将科学与人生观完全割裂开来。由于张君劢受西方哲学家影响很深,他力主科学不能越出其自身的界限。“科学之大原则,曰有因果,既以求因果为归束,故视此世界为一切具在,而于此一切具在中求其因果之相生。”〔6〕科学只研究具体的客观对象, 不能研究经验以外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虽然看起来像是与中国传统的玄学思维方式不同,其实这是在为传统思维方式作辩护:科学不能研究的领域,只能由玄学来完成。于是玄学思维模式可以大显身手了。张君劢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他说:“其实我所持者,即仅理智主义论调,是因为欧美留学时受欧美反理智主义哲学之洗礼”。〔7〕然而,他忽视了, 西欧理智主义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尤其黑格尔的理智主义完全排斥感性,故使许多西方现代哲学家起而攻之,形成了反理智主义运动。张君劢依照西方学者的论调在中国大谈反理智主义,反对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而人类思维又不可或缺的东西,反而阻碍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转换,更加强了传统思维方式的抵抗力。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是个马赫主义者,主张“存疑主义的唯心论”。他认为关于世界为何物,人生是什么这些问题是“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应该“存而不论”,而“玄学家吃饭的家伙就是存疑的唯心主义所以为不可知的。”〔8〕他指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 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9〕在这里, “科学方法万能”指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即是指科学的实证性,又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将科学方法看成是万能的、普遍有效的,实际上已将科学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涵盖而极广的思维方式。科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胡适则大声疾呼“拿证据来”,这种提法也是有实证精神,与中国的经学传统是迥然不同的,明显包含有转换思维方式的时代意向。
但是,科学派并没有将人生观拒斥为形而上学,他们将科学看作是绝对行之有效的准则,要求以科学来裁决人生问题。胡适将科学精神引进人生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10〕科学一旦被运用于人生观,即具体化为一种讲究功用的人生态度。而科学作为人生观的基础,是以因果关系为其基本原理的。“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11〕因果大法支配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也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精神现象。而这种普遍大法却又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单一的因果律,表现为一种单向的决定。在因果大法的支配下,人的自由也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于是就形成了“那具体的、纯物质的、纯机构的人生观。”〔12〕可以看出,因果大法与人的自由被绝对对立起来,因果必然性表现为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这样,科学派就由反对意志主义思潮走向忽视人的自由的偏差。他们一开始强调西方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近代机械论思想)旨在冲破中国传统的那种注经式的独断论思维模式以及“天人合一”的玄学思维方式,但由于他们极力高扬机械论思维模式,最终陷入了科学独断主义。
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看到了科学派对于人生的理解是“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确有见于科学主义者对于人生片面化之弊,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张君劢等人将科学与人生观割裂从而给科学主义者留下了把柄之误,故而主张“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13〕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爱与美”。梁启超到过欧洲,对西方的科学万能之梦有所评论,在《欧游心影录》中,他说:科学把一切内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是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根据实验心理说,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是一种物质,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自由,也就无所谓善恶的责任。梁启超敏锐地抓住了人的自由这一问题反对科学主义者,但他对“爱和美”这些非理智所能解决的问题也无所适从,只能称之为“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投入了玄学思维方式的怀抱中。
玄学派对于科学者的攻击,暴露了科学派将科学方法绝对化的片面性,而玄学派等人到宋明理学那里去寻求解决人生问题的真谛,却也同样暴露了固守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管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没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没有触及到社会历史领域。但是在强调科学作为人生观基础这个问题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与科学派的观点相仿。陈独秀认为,张君劢对于人生观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他在逐一批判了张君劢的九项人生观之后明确指出:“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理论说明,找不出哪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14〕所有人生观都要“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规律的科学所支配。”〔15〕在这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将科学看作是人生观的基础。但与科学派不同的是,在他们看来,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涵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史观。”〔16〕陈独秀批判了玄学派意志自由、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指出一切情感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环境;同时他也用唯物史观批判了丁文江等科学派的唯心主义,指出科学派离开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历史现象,结果也只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坑。
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代表人物瞿秋白写了《自由与必然世界》一文,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驳斥了张君劢的唯心主义意志自由论。他指出,所谓必然就是指自我和社会的必然因果律,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换言之,人的自由总是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根本没有的。瞿秋白和陈独秀一样将唯物史观抬高到思维方式的高度,强调历史规律性对于主体行为的制约,这比科学派前进了一步。科学派只看到自然规律对主体的限定,而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对于主体的规定。所以,作为思维方式,唯物史观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既克服了玄学派直觉主义思想方法,也克服了科学派忽视人类历史的独断论错误。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象科学主义者一样,在因果大法的制约下,没有很好地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从瞿秋白的如下论述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点:“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17〕在这里,偶然性被归结为一种主观因素。其实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基础,偶然性给主体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否定了偶然性也就勾销了人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人完全为必然性所支配,如是则像科学主义者一样陷入了独断论思维方式之中。
三
在传统的观念体系分崩离析之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力图确立一种高度统一的新的观念体系,但是这种新的观念体系不可能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产生出来,它必然来自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它首先表现在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上,科玄之争的本质即在于此。
如前所述,严复等维新志士已开始将科学与把握必然之理及因果关系的方式联系起来。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联系由于缺乏具体的环节而带有比较抽象模糊的特点。科学派则进一步将科学明确地规定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被称为“科学的精神”,即凡立一说,须有证据,方可下判断,不盲从他人的结论,旨在将人们的注重点从传统的六经转向事实界,并把主体理性从经传圣训之中解脱出来。这种注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包含有转换思维模式的意向。科学派强调实证、排斥玄空,对于消除玄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科学派认为,科学活动是一种理智的操作,主张以因果原则来解释主体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将主体纳入理智的框架之中,以理智为主体的唯一品格。正是在这一点上,丁文江将“主体”比作一种思维的机器,”我的思想工具是同常人一类的机器,机器的效果虽然不一样,性质却是相同的。”〔18〕对于现象和自我的这种理解确乎有十分明显的唯智论或机械论的倾向,这是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果,的确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缺少,对传统思维方式走向现代有很大影响。然而这种理解却丢掉了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也抹杀了传统思维方式中优越的一面。
我们认为,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不仅具有理智的品格,还具有情感、意志的品格,本质上表现为知、情、意的统一。人的行为,特别是道德行为,固然要受到理智的支配,但同时又往往出于意志的自主选择,后者则赋予这种行为以自愿的特性。西方哲学则对后者进行了较多的考察。玄学派正是在这一点上吸取了西方柏格森的意志自由主义并且与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相结合,力图重建新的价值观念。“吾则以为格氏有言有与理学呈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复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摈弃之。”〔19〕他们从柏格森那里找到了弘扬宋明理学的借口,“尤觉内生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20〕玄学派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其实是恢复传统理学的价值观念。张君劢说:“若其人生观,则涵育于中庸之说,既无机械观,目的观,亦无所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如是,东西相形,若其中亦自可以安心立命者”,“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21〕可见,玄学派试图以中国传统的非理智主义思维方式来重建价值信仰体系。然而在中国正统派儒学那里,特别是在宋明理学那里,只需“重心在内”、“复性”、“无对”就可获得自由。他们较多地考察了伦理学上的自愿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修养),而较少考察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问题。玄学派从柏格森那里吸取了人的主体活动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观点,却抛弃了柏格森主义大力提供的自愿原则。需要提出的是,虽然玄学派最终陷入玄学思维模式中,但却对科学派的机械论思维方式进行了有力批判。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派、玄学派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处理好人的自由问题,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新型的价值信仰体系,这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有关。然而他们都对思维方式的不同侧面作了探究,这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转轨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创造性的融合东西方思维方式,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注释:
〔1〕〔5〕〔19〕〔20〕〔21〕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签丁在君》,载《科学下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2〕张君劢:《人生观》,载《人生观之论战》,泰东图书馆, 1923年版。
〔3〕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 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6〕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载《人生观之论战》, 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7〕张君劢:《〈思想与社会〉序》,载《知识与文化》, 商务印书馆,1946年3月重庆初版。
〔8〕〔9〕〔18〕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10〕〔11〕〔1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13〕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四十卷。
〔14〕〔15〕〔16〕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17〕瞿秋白:《自由与必然世界》,载《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2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