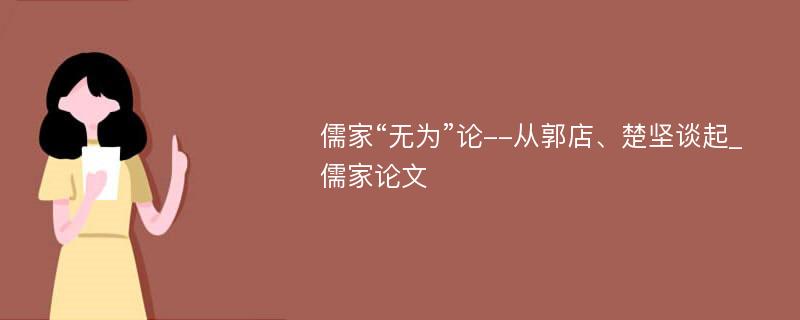
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开去论文,郭店楚简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凡繙经绎史及相关学科者不能不注重出土文物——“历史一”。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要求以考古材料来印证书籍文献;到饶宗颐等人则又有加,提出“三重证据法”,将出土文物分为“有字”和“无字”两种,认为不应忽视后者。我们知道,研究方法的改进、理论视角的变换等,都可能对以往的一些“成论”带来冲击;而出土实物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则可能从根基上修正或改写以往的学术史,有价值文物的发现促进科学研究的进步乃至“革命”。若没有王懿荣1899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发现甲骨文,带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划时代发展,大概就难有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7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汉帛书(1973)、睡虎地秦简(1975)、曾侯乙墓战国初期简(1978)以及近年尹湾汉墓简牍(1993)、荆门郭店战国中晚期楚简(1993)等等的发现,对典章、律法、官制、学术等研究颇具价值,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面世以来,由于楚简中的儒道典籍学术价值很高,许多学者投入了研究。庞朴先生发表《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第9期)等文章, 说郭店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还说这可能提供儒道两家关系的“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大信息”,确有振聋发聩之益。他还列举了儒家反对“有为”的材料,又说“不过在竹简儒书中还未发现提倡无为的话。这些有同有异之处,大概便是当时儒道的界限所在。”
儒道关系历来是学术思想史的复杂问题,而且在许多论题上两家的界限也不大容易厘清。但是,无论如何“无为”都是道家学说的典型“话语”,以此作为道家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很有道理。庞先生即以此作为儒道两家的分界,并进一步把关键点定在反对“有为”与提倡“无为”的差距上。他列举了简书中“父孝子爱,非有为也。”(《语丛三》)“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为也,弗得之矣。人心不能以为也,可知也”(《性自命出》)等材料,说明儒家一般地反对有为。另外,简书中有关儒道联系,我还看到如《语丛一》的1号简和104号简都有“凡物由望(裘锡圭先生按:疑当读为亡、无)生”等,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老子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不过,此次整理出的简书中的确没有儒书使用“无为”的话语,(不知被盗楚简中是否有),但文献材料则不然,先来看儒家经典集成“十三经”之例——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周易·系辞上》
有兔,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毛诗·王风·兔》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优枕。《毛诗·陈风·泽陂》
天方之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毛诗·大雅·板》
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礼记·礼运》
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礼记·中庸》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左传·成公二年》
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尽心上》
这些材料中的“无为”虽用法和意思并不都一样,但不乏类似道家“无为”的内容。类似意思还有如《孟子·离娄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样的思想主张先秦以降亦为“后儒”所承续发展。比较重要的如汉初陆贾作《新语》专设《无为》篇,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西汉时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列为学官地位很高,韩诗一派由韩婴创立,其主要著作是《韩诗外传》。该书有“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韩诗外传》卷三第一章)“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同上,卷五第二十七章)此书还明确记述孔子有类似道家的主张,“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同上,卷三第三十章)先前《荀子·宥坐》就有“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儒道如此这般的类似可否从学术渊源上去探寻呢?大家知道,各种典籍不乏孔子学于老聃的记述,如《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再如《孔子家语》。既然儒家典籍都不避讳其宗师曾向老子学习,是否也说明儒道“和平共处”或相互影响呢?尽管我们不一定能确信“孔子问礼于老聃”之史实,倒是太史公关于道家博采众家之长的说法更值得注意。
儒家的“无为”主张不仅是学术思想,也用于为政实践。《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述当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结果“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又如《史记·曹相国世家》讲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可见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之首,即肯定“无为”之治。到唐代,名臣魏征以直谏唐太宗而为古今称道,他曾上疏要求为政者“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贞观政要·慎终》)不过,有人会从“无为”的内涵去区分儒道之别,如宋代大儒朱熹。他说:“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说明朱子肯定儒道两家都主张“无为”,仅内涵不同罢了。后人对“无为”也有各种释义,如无所作为(non—action)、不做事(do nothing)、 不活动(inactivity)、没有行动(without action )、 无意识的行动(without conciousness wilful action)等等。李约瑟教授在《科学思想史》中对“无为”作界定——“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contrary to Nature)。 不能否认儒道两家的“无为”大概确能具体分析出一些不同,但同样不容否认其相同、特别是基本涵义相同内容的存在。我看大抵可以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及二者的关联中,来看儒道两家的“无为”说,特别是基本涵义相似的主张和思想。
自然方面——不妨以“水”的“行为”来阐释“无为”。据说古代君子见大水必观。孔子观“东流之水”,子贡问其故,答:“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水的特性最重要的便是“无为”,即柔弱、顺从、不争、不为(不有意去做什么),但顺乎物性自然而然,向下流去,不可阻挡。即孟子所谓“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老子则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同上,第四十三章)这样的“无为”特性被扩展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道”。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淮南子》表述为:“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水下流。不争先。”“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淮南子·原道训》)“若吾所谓无为者……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淮南子·修务训》)各家文献中多有相似的说法。 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Alian ,
现为美国Dartmouth College 教授)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本喻》中概述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其自然而然地流尚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英文中“本性”、“自然”、 “天理”、 “造化”等都是“nature”,从这里反观“水”之于“无为”,恰道出“水”本身体现了宇宙本性自然之道,这也就是“无为”之道。上述研究运用了西方哲学“隐喻认知论”的方法,隐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一种文化的形态和特质,即一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将附着于此文化中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中。换言之,概念范畴或称话语的使用,是一定的文化特质或思想观念的体现。“无为”正是中国文化特质的一种体现,这在社会方面将得到进一步证明——
德治是儒家典型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前述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有人认为《论语》中此段是后人加的,但历代大儒不乏对此注疏诠证,被认为是“德政”枢要,因而不失其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意义)与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恐怕正是理解儒道两家“无为”说之关键。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解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引程颐等人之注“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繁),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四书集注·论语》)以上曾述此思想为汉唐之儒所承,再往后,还有“无为则所行事简。”(《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上》)儒生对此很重视,朱熹的门生就认真探讨过,例如他们问“无为而天下归之”的说法,朱子解释说:“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学生问“如何无为?”他答:“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又说:“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为政以德、以简御繁、不生事扰民;一是个人静心修德、依本分做事、民众自然被感化。这样就达到“无为而治”或“无为而无不为”——这不正是道家所主张的吗?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庄子进一步阐述:“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庄子·天道》)“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郭象《庄子注》说“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要点。”朱熹还将“无为”释为“理”:“圣人所谓‘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个“当然之理”或许就像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而然、无执着、无勉强,正己立德以达无为,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而万物化”(《庄子·天地》)。
为什么儒道两家都有“无为”之说?李约瑟认为“无为”是中国思想的根本观念,最深沉根源之一,可能在于原始农民生活的无政府性,无干涉就昌盛。儒道都不主张“生事”,儒家主张以“道德”(反是道家作《道德经》!)修、齐、治、平,但其最高理念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界有相通之理,无论“天人感应”还是“理一分殊”。这样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之统一,在道家那里就表现为“道法自然”。晋王弼《老子注》释“无为”为“顺自然也”,至今亦多作此解。这样的思想与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靠天吃饭”的生存实践分不开,也同当时争霸战乱造成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有关,还有生产与生活的观察形成了人们对自然或社会一些规律性认识的经验,这些恐怕就是“无为”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的要素。“无为”就是要依自然和社会的本来而不强行,不违反物性,自然如此(so of them selves), 取法于自然之道本身的运行,虽无所作为却能完成一切,否则只能劳而无功。当然,对儒道两家“无为”说还需深入研究。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儒道两家是否经历一个从早期的“和平共处”到后来的“分道扬镳”,到再后来的“三教合流”?郭店楚简的出土与上述文献记载到底说明什么?有待方家指教。不过,上述论点若可成立,是否涉及“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也主张“无为”,那么以往“定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定式有否重新认识的必要?更令人疑惑的是:如果连“无为”都成了几家所共有(其他学派也有“无为”之说此处不赘),那么还有什么能用来界定或区分诸子百家呢?
《庄子·天下》认为“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荀子·解蔽》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他还作《非十二子》但没提老庄。《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到司马谈(?—前110 )论“六家之要指”,提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迁作《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但他将老子与韩非子共同立传,(《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列合传以共性为基点,说明至少到汉武帝时各家各派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将后人看来最无作为的道家之祖与最要入世成事的法家集大成者立合传是为证。到西汉末刘歆《七略·诸子略》将诸子百家总括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除小说家),这也就是先秦至汉初的“九流十家”。班固有“诸子皆出六经”说,认为诸子百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总之,各家学派恐怕从最初就很难完全分开,无论是一家兼采诸家之长,还是各家相互并存互相汲取;是从初时的“和平共处”到后来的“分道扬镳”,抑或再从“分道”趋向“合流”,但代表某一家某一派思想最典型的概念总还是该有不同的——然而,本文的论述标明了疑惑。
另外,再一个疑惑是:出土的实物中按今人看来的不同学派的材料为什么会不止一处地埋在一起?郭店楚简中既有《老子》、《太一生水》;也有《唐虞之道》、《尊德义》;马王堆汉帛书《老子》甲本后有四篇佚书,整理者题了篇名:《五行》、《九主》、《明君》、《德圣》,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德圣》“其文句多受道家影响。”(《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载《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325 页)仅从这两处(自战国至汉代)就可以看到儒道典籍依然杂陈,更不必说后代的几教合流或一位撰主同时尊儒、崇道又拜佛了。
今人的研究多习惯基于不同的“家”或“派”,这是否是值得重新检讨的思维定式?本文仅提出个人多年来一些认识或疑惑,观点也不成熟或可能有悖常识,仅作为本人所谓“学术研究史”(认为跨世纪学术深进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提出,特请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