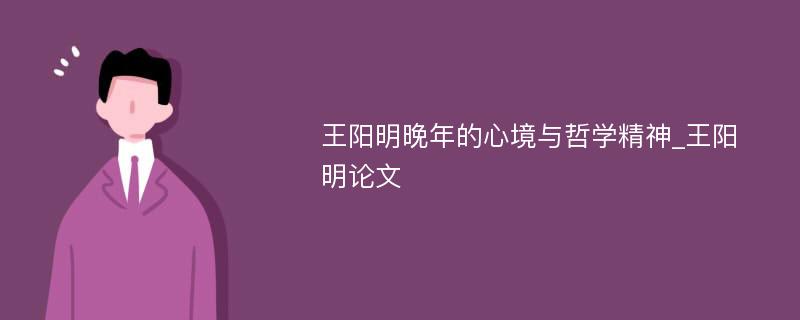
王阳明晚年心境与哲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心境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阳明的学说是其全部人生体验的结晶和升华。若要把握阳明哲学的精神需从对其人生体验的理解入手。本文一方面着力揭示阳明晚年洒落而沉痛的心境,为理解阳明哲学打通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对作为其哲学的血脉和灵魂的基本范畴和命题的分析,发掘阳明哲学的真实意蕴。从总体上讲,阳明哲学立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但又要根除人的现实的感性冲动,以此彰现人性的伟大与崇高。阳明哲学的现实意义主要不在于它解决问题的方略,而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展示的哲学创造的基础。
王阳明一再强调,他的学说是从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中得来,是个人经验的结晶和升华。确实,虽然阳明“心学”有其思想史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但是包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感觉、情感等在内的生存体验才是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对王阳明哲学的解释,必须建基于对王阳明生存体验的理解。如果没有对其生存体验的理解,就难以揭示其思想的内在结构和丰富的复杂性。
生存体验的理性化表现是思想;它的感性形式的情绪化表现是心境。思想在特定的心境下产生,心境决定了思想的限域和可能的解释;而心境也通由思想表现出来,并借以保存下来。因此,对思想的解释,如果这种解释不是在一堆语言的废墟上去重构所谓原创者的思想而事实上是论证预定的解释框架的合法性的话,必然要关注思想产生时思想者的心境。本文探索的方向,就是在关注王阳明晚年心境的前提下,寻绎王阳明晚年哲学的意蕴。
一、心境
王阳明龙场悟道,开始形成自己的学说观点,成熟的标志是致良知宗旨的确立。据王阳明自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王阳明全集》,下引简称《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5页)因此,他晚年将他一生的学说概括为“致良知”三字。但是,自龙场时起直到平定朱宸濠乱和经张、许之难,王阳明为什么都“点此二字不出”呢?
王阳明正德十五年在虔论致知时曾说:“我亦近年来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子欠缺。”(《传习录下》,《全集》第92页)王阳明此前没有点出良知二字的根本原因就是尚未“体贴出来如此分明”。这表明,王阳明是以自己的体证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学说。他强调“诚诸其身”、“于事上磨练”等大抵也基于此。王阳明认为圣学不明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未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体认,“大抵此学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尝诚诸其身。譬之谈饮说食,何由见得醉饱之实乎!仆自近年来实见得此学,真有俟百世而不惑者。”(《与席元山》,《全集》第180页)唯有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思考、去体会,才能验证某种思想的真理性,才能倡明某种具有真理性的思想。对王阳明而言,验证某种思想的真理性或倡明某种具有真理性的思想,目的都不在于这种思想本身是否为实在性的真理,而在于探明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如草木之有根,畅茂条达,自有所不容已”(《寄邹谦之》三,《全集》第204页)。因此,可以说王阳明提出良知说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问题。
王阳明经宸濠之乱和忠、泰之变,证得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遂“揭致良知之教”。归越之后,专以致良知教学者,他自身也仍然用全副身心去验证良知之说的真理性。经丧父、丧妻之痛,愈信良知,“比遭家难,功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寄邹谦之》,《全集》第201页)此际,王阳明的心境也与往日不同。
嘉靖二年,王阳明自述:“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得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谱》,《全集》第1287页)王阳明以狂者自况,道出了他那时的心境。王阳明所谓狂者,以曾点为原型,其志向、意趣、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有以下特征:一是狂者“志存古人”,不与俗谐,追求真正的忠信廉洁,而不是以所谓的忠信廉洁邀名于当世;二是狂者有“一切俗缘皆非性体”的洞见,故能豁然脱落,而不致于沉溺富贵声利之场;三是狂者因能超脱俗染,故能“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不为当下的处境所限,“无入而不自得”;四是狂者“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但无为善去恶之实功,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五是狂者“轻灭世故,阔略伦物”,故尚未入于圣人之道。就强调狂者为“未得于道”而言,王阳明以狂者自许,没有丝毫自傲的成份,有的是对自己学说的自信。这种自信,就是认为自己已道出了“圣门正法眼藏”。在对自己学说的自信和依自己学说而践行的过程中,王阳明勘破了世间的毁誉及富贵名利等等,洒落超然,恬然自适。但他对不能“轻灭世故,阔略伦物”的强调,又透露出他对生民的关切。可以说王阳明晚年的心境是洒落中有沉痛,沉痛之际也有洒落。所谓洒落,不是旷荡放逸,而是不以自己的困窘处境和外在的毁誉为意;所谓沉痛,也不是对自己境遇的悲伤,而是对民生疾苦的恻隐。其嘉靖三年的两首诗作,完整地烘托出这种心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全集》第786页)
夜坐
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
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贤。
(《全集》第787页)
在“幽意自随流水春”而又要扫青天旧尘的超然自得和沉痛中,在别离筵散又要驰驱军旅之际,缘其高足王畿、钱宽之辩论,王阳明订立了四句学问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年谱》,《全集》第1307页)这“四句教”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精髓。如果依王阳明自己的认定,“平生所学,只是致良知三字”,那么“四句教”是致良知学说的系统概括。
二、良知
“四句教”的基本范畴是心、意、知、物;基本问题是本体和功夫。基本问题是骨架,基本范畴是血脉和灵魂。因此,对王阳明晚年哲学思想的探究,当以基本范畴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
王阳明在确立致良知为学问宗旨之前,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与陆九渊的观点有一脉相通之意。王阳明对“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解说,意在指明不能在心外求理,即道德的根源不在道德行为的对象上,人修身作圣应以修心为本。但是,王阳明在强调心与理是一个,让人“不去袭义于义”时,对心即理的分疏并没有象提出致良知后那样清楚,依“心即理”、“心外无理”去践行,修心也会产生在心上求天理的“理障”。这样一来,“心即理”、“心外无理”作为知行合一论的本体根据就有问题,如其弟子陈九川所言,“难寻个稳当快乐处”。王阳明在拈出良知二字后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传习录下》,《全集》第92页),但如果没有致良知这个“诀窍”,“理障”问题恐难解决。良知学说的提出,才解决了“理障”问题。
在良知说提出之后,心与理的问题变成涉及心、良知、理三者的问题。王阳明指出:“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答舒国用》,《全集》第190页)又谓“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全集》第47页)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又是心的虚灵明觉。王阳明认心的虚灵明觉为良知,又以心的本体为良知,则本体即所谓虚灵明觉。因此,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同样可以理解为良知是天理的本体。心与理在本体上是统一的,理出于心之良知,故可以说“心即理”。王阳明论证说:“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纵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同上书,第45页)心与理在良知上获得了本真的统一,修心成圣不是在心上求天理,而是致良知,故无“理障”而稳当快乐。
良知是心的虚灵明觉,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就是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传习录中》,《全集》第47页),良知是意之体。所谓“应感而动”,就是应外物所感而发动。就此而言,良知相当于“未发”,意相当于“已发”。意之体是良知,所以可以说无未发、已发;意是良知之发动,所以也可以说有未发、已发。其实,在良知说提出之后,未发、已发问题在阳明哲学中已不是重要问题。意是十分重要的中介性范畴,旨在解决是非善恶的问题。意是良知“应物起念处”,念有善念、恶念,故有善有恶、有是有非;而正因意是良知所发,所以“凡意念所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大学问》,《全集》第971页)良知是意之体,而又察知、监控着意,是意的内在评价、督导系统。此即所谓虚灵明觉。虚灵即良知本不动;明觉或昭明灵觉即良知能照察是非善恶。在照察的意义上讲,良知是“是非之心”。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传习录下》,《全集》第107页)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只是说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而能分辨好恶,并不是说良知还好善恶恶。换言之,良知只是道德理性原则,而不是道德情感原则。王阳明一直用“照”、“觉”等说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关键就在这里。知善知恶也是良知的发用,而不是良知本体。“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同上书,第109页)良知正如太阳一般,根本上无知也无善恶,知善知恶只是它的发用。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良知本体无善无恶,王阳明自己的解释是:“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疫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年谱》,《全集》第1306页)就此而言,良知本体无善无恶不能说良知是道德意义上的至善。但也不能说良知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至善。《传习录》收有与此几乎相同的两段话:“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曜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也。”(《全集》第70页)还有一段:“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之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同上书,第106页)因此,所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指示“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同上)。所以,人的良知才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而“人心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同上书,第95-96页)。从境界上讲,“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是虚实相生,有无相生的境界。这一境界是伦理的,因为它并不放弃对天地万物的关怀,特别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这是本;这一境界又是超伦理的,因为它“廓然与太虚同体”,彰现的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这一高超莹洁而又壮阔幽深的境界,源于伦理而又超越了伦理,在善恶之彼岸。在王阳明眼中,这一境界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愚夫愚妇都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
三、致良知
王阳明指出每个人都有良知,从圣贤到愚夫愚妇,良知都相同。“心之良知是谓圣。”(《书魏师孟卷》,《全集》第280页)每一个人都有不会泯灭的圣根,都可以成为圣人。从本根上讲,“满街都是圣人”。每个人是否是圣人,也不是依外在的判断,而是以自己的良知为准则。从人—我关系上讲,他人并不能说我是否是圣人,我也不能说他人是否是圣人。对他人的评价,如果以他人本根上有良知为准则,就只能承认他人是圣人。因此,从现实上讲,也是“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传习录下》,《全集》第116页)。王阳明点出每个人“胸中原是个圣人”和“满街都是圣人”,其用意一是强调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学并不高远玄妙,而是坦坦平平,人人可学、可至;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担当起卫道、弘道的使命;三是要剖破人“终年为外好高之病”,让人“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同上书,第117页)。但是,他维护孔孟尧舜之道即“破心中贼”之心越急切,为这种道德的解体打下的基础就越坚实。
人先天具有的良知就是天理,人以自己的良知为准则,依良知行就能直跻圣位。这种推论,从根本上讲是将外在的社会评价系统或者说社会性的道德规范内在化和先验化,以维护其至上性和普遍性;但同时也割断了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自我内在的先验道德规范之间现实性的关联。王阳明将自我评价、自我认同和自我内在的先验道德规范置于本体地位。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的社会认同、社会评价、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他自己对毁谤的态度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毁谤自外来的,虽圣贤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著。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同上书,第103页)一个笃于自修的人以自我认同为本而不求社会认同;社会评价对于一个笃于自修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进而也可以说社会评价的标准即社会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于一个笃于自修的人没有任何价值。这样一来,王阳明就为个体的反叛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希望人人成圣,但又指明了只要你认为成为魔鬼很快乐你也不妨去做;他希望世人遵从某种神圣的法则,但又指明了世间并没有神圣的东西,唯有你自己才是最神圣的。
在否定了社会认同、社会评价和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之际,王阳明强调人要依良知去实实在在地自修。“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誉,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个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不能动。”(《传习录下》,《全集》第101页)“依此良知,忍耐去做”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全集》第972页)“物者,事也”和“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表明王阳明在讲格物时所指陈的物,不是指与人的意念无关的客观事物,而是指人的意念所关注的和在人的意念之中的社会事务和自然物。无论是对事亲、读书等事务,还是对草木瓦石等自然物,王阳明都是从与人(心、意)的相关性上来理解。这一相关性的理解即“无心外之物”包含两个向度,一是心—物、一是物—心。从心—物向度,意之所在或意之所用便是物,物是指人的意识活动的不同方面和展开;从物—心向度,物是客观事物,但客观事物只有与心相关才有存在的意义[1];换言之,物的物性即物之所以为物不在物本身而在于人心。按照这种理解,无论怎么看,则物都不在心外,故“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答季明德》,《全集》第214页)。格物就是在意念着处依良知的觉照为善去恶。
致知与格物是一体两面,“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传习录中》,《全集》第45页)因此,致良知不是认识事物,不是从事物上求理,而是在事物上磨炼,去除意之不善而于归善,最终达到此心之全体流行无碍的境界。
致良知不是认识外物以扩充知识,因而知识技能对人的成圣无关紧要。“圣人之学,……唯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传习录中》,《全集》第81页)有关礼乐名物、草木鸟兽之类的知识,是不必知或不必尽知的,因为此类知识之知不是根本的知,根本的知是知天理;训诂、记诵、词章之类的学,也是不必学或不必尽学的,因为此类学问之学不是根本的学,根本的学是充拓良知而复心体。克尽己私而复心体之同然须用实功,“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同上书,第71页),读书、举业、簿书狱讼无非磨炼之地。王阳明以成德作圣为本而以知识学问为末的知识论,最终导致王门后学空谈心性;但王阳明其实是强调实践、实功的,他的态度抽象地说是否定实践出真知,肯定以实践证真知,在证真知的主导下去实践。
致良知的极至是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境界。怎么才称得上达到这一境界呢?“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末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下》,《全集》第108页)此就克己而言,是“为己”的根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为己”,也不是“为己之学”的全部;真正的为己功夫还要“亲民”,由亲吾之父兄始推及亲人之父兄,而至“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全集》第969页);真正的“为己之学”,也是“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心体之同然”(《传习录中》,《全集》第54页)。根除生死念而救斯民之陷溺,是逍遥?还是拯救?是安乐为本?还是忧患为宗?
人以必死的血肉之躯致良知,但要彻底抛开生死之念,根除一切感性的冲动;现实感性的自由与欢乐在此没有一点位置。虽然王阳明认为顺自然流行的七情是良知之用,但他肯定的是无“指著方所”的纯粹的七情,而不是现实的感性冲动。在根除一切感性冲动之际,又要救民于陷溺,使斯民不“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坠于夷狄禽兽”。两者完完全全地胶合在一起。无论是视其为以安乐为宗,还是当其以忧患为旨;无论是指其为无视人的苦难和不幸的逍遥也好,还是认其为要解救和铲除人类心灵苦难的拯救也罢;都无可无不可。关键的问题是:铲除了人的感性冲动,不管物质生活的困窘,人果真能彰现人性的崇高与伟大吗?
王阳明曾言:“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传习录下》,《全集》第113页)这也可以看成一条哲学解释的原则,他对经典以及前人学说的解释,其实也是遵从了这一原则。虽然从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来看,因为经历、体验、心境不能重复,“得他许多苦心处”事实上不太可能,正如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解释也不能说是得到了朱子的“许多苦心处”。但是,这一原则仍有其合理性,即不能把古人的思想与古人的经历、体验、心境、人格分割开来。因此,虽然传统的生命在解释者手中,但是如果要真正承续传统的慧命,就不能随意用某种外来、外在的框架来解释古人的思想,而必须在尽可能关注古人的经历、体验、心境、人格的前提下,从他所用的基本范畴(语词)入手,才能大体不背古人立言宗旨,而开出传统的新生命。显然,对阳明哲学即应如此。
注释:
[1]参见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