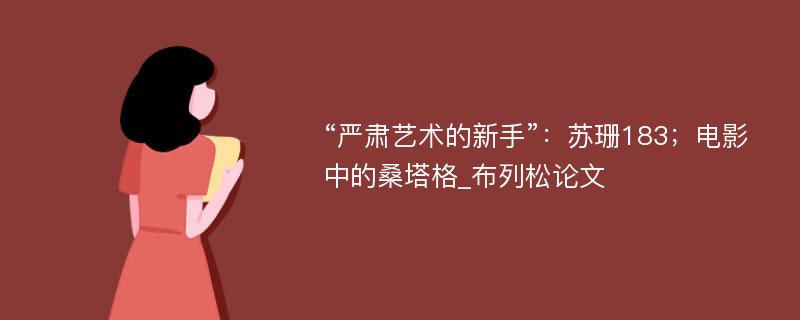
“严肃艺术的一个新来者”:苏珊#183;桑塔格论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肃论文,艺术论文,电影论文,新来者论文,桑塔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是一位研究兴趣广泛的文坛多面手,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被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她在20世纪50、60年代浸润于巴黎的文化界,而对电影的痴迷使她“早就开始每年在那儿过暑假,每天都光顾电影资料馆”[1]308。为了积累写作电影评论的素材,她甚至每天都要看一部、有时是两部或者三部电影。这位勤勉的电影爱好者释放出的批评能量成就了她一篇篇不乏精彩论述的电影论文,分别收录在《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1969)、《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1980)和《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等论文集里。从这些论文的时间跨度我们可以看出,电影是桑塔格颇为钟爱的题材,从她崭露头角的青年时代一直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时光里,她一直坚守着这份热爱之情,保持着将各种感悟和思考诉诸笔墨的热情。 一、兼收并蓄:电影与小说和戏剧的关系 桑塔格非常认可电影的包容性,称其为一种“泛艺术(Pan-art)”,能够“利用、融合、囊括几乎任何其他艺术: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刻、舞蹈、音乐、建筑”[2]245。她在不同时期的论文里主要探讨了电影与小说和戏剧的关系。 (一)电影与小说 1961年桑塔格发表了《关于小说和电影的一则札记》(A Note on Novels and Films),文章虽然不长,但是还是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她对二者关系的分析。她另辟蹊径地将电影与小说的两位影响深远的开拓性人物进行比较:前者是美国导演D·W·格里菲斯(D.W.Griffith,1875-1948),后者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桑塔格发现,格里菲斯与理查逊“都是天才的创新者;都有着极为粗俗甚至是浅薄的才智;两个人的作品都充斥着对性和暴力的狂热的说教,而性和暴力的能量来自于受压抑的肉欲”[2]242。除此之外,两人至少还有三个共同之处:在说教上的无趣,在刻画女性情感方面的细致以及展现出的世界相对于现代趣味而言显得令人反感。桑塔格其实无意于深入挖掘格里菲斯和理查逊的渊源,她意图要表明的是尽管无法将伟大的电影导演和小说家一一对上号,但是在短短几十年的电影史(桑塔格写作此文时是20世纪50年代)上确实涌现出了可以与小说界的大师们比肩而立的电影导演们。既然电影与小说的创作者有众多的共同点,那么这两种形式具有相通之处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她进而指出,她固然不会简单地把电影比作小说,不过它们在展示观看的角度时都置观众(读者)于导演(作家)的控制之中。也就是说,观众(读者)在与作品面对面时无法选择自己的视角:观众的目光跟着摄影机的角度移动或静止,读者则随着作家的引导,阅读的是“一些经过选择的与作家的观念相关的思想和描写……按顺序逐一阅读”[2]24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也意识到了电影的这个特质,即“观者的眼睛必须认同摄影机镜头,看到的只是演出本身”[3]79。 就文学类型而言,电影是否仅与小说有类比的可能性?对此桑塔格亦专门予以了解释。她评价爱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1898-1948)、黑泽明(Akira Kurosawa,1910-1998)等人的名作体现了把电影作为史诗的观念,而法国20世纪20年代的不少先锋派的短片也能与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等人的诗作相媲美。换言之,电影也有诗歌的血脉,只不过其“主导性的传统还是侧重于那种多少带有小说风格的情节和思想的展开,采用的高度个性化的人物也是处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场景之中”[2]244。桑塔格特别指出,在电影与小说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意味着可以据此将电影划为“文学性的”(Literary)和“视觉性的”(Visual)两个类别。她谨慎地建议,不妨将电影区分为“分析性的”(Analytic)和“描述性的”(Descriptive)或曰“说明性的”(Expository),前者适用于心理电影,主要揭示人物的动机,而后者则可用于反心理电影,人物并不是中心,处理的是感觉与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类可见于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和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等导演的电影,第二类以罗贝尔·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01-1999)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等导演的作品为代表。桑塔格试图在电影的这种分类上将其反向作用于小说,认为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第一类,而司汤达属于第二类。不过遗憾的是,她没有就此展开论述。 在桑塔格看来,电影自诞生之初便与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在《从小说到电影:法斯宾德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Novel into Film:Fassbinder's Berlin Alexanderplatz,1983)一文中,她忍不住为电影叫屈:“改编小说是最可敬的一项电影工作,而一本声称改编于电影的小说看起来却是理所当然地粗俗不堪。”[4]123早期受到欢迎的电影往往都是来自对小说的成功改编,至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电影观众数量的激增,银幕上的改编之作也达到了巅峰。电影在借助小说的力量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自然而然地被当成是小说的副产品,不得不接受人们的比较和评判:它是否忠实而充分地再现了原著的内容?就在这样的质疑中,电影被动地沦为了小说的附庸,“电影的本质,姑且不论电影的质量高低,似乎就是把优秀的原著删减、稀释、简化”[4]124。人们对电影的求全责备使得改编文学经典作品的难度愈来愈大,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包括戈达尔在内的导演选择了通俗的文学样式作为改编的对象,如犯罪小说、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等等。桑塔格感叹“经典作品似乎遭受了诅咒:电影的营养来自低俗小说而非来自文学成了至理名言”[4]124。 除了忠实的问题,另一个制约电影向小说取材的是小说的篇幅问题。电影要做到恰如其分地符合小说的长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桑塔格对电影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案例进行了研究,那就是德国新电影的领军人物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6-1982)拍摄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80)。该片是根据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1878-1957)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整部影片长达15小时21分钟。桑塔格分析这部非同寻常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具备了如下条件:其一,导演获得了授权,而有着同样雄心壮志的另一个导演史托洛海姆(Eric von Stroheim,1885-1957)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先于法斯宾德根据一个类似的小说制作了一部片长为十个小时的影片,但是因为打破了电影的常规而被迫将其剪辑成2小时45分钟。桑塔格认为“对片长不加限制并不能确保将一部好小说成功地改拍成一部好电影。但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却可能是必要条件。”[4]125其二,法斯宾德这部长度惊人的影片有传播的渠道:通过电视分集播出。当然,它不是电视连续剧,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分集”,只是在时间上予以了分割,便于观众观看。除了上述两个客观条件之外,桑塔格还具体分析了法斯宾德成功的主观原因:融合了小说和戏剧的元素,有助于贴近原著;对原著进行合理的改动,使叙事更紧凑;起用演员非常得当,表现力感人至深。桑塔格肯定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成就,赞叹其“片长超过任何其他影片且极具戏剧效果,电影这种综合性艺术终于获得了长篇小说那样的舒展自由的形式和不断累积的力量。”[4]131 (二)电影与戏剧 1966年桑塔格的《戏剧与电影》(Theatre and Film)一文如其标题所示,专门研究了戏剧与电影的关系。她开篇就提出了两个疑问:“戏剧与电影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是不可调节的矛盾?是否真的存在着纯粹的‘戏剧’元素和纯粹的‘电影’元素,而两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呢?”[5]99桑塔格表明,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萧伯纳就曾经态度坚决地表示无法接受自己的戏剧被拍成电影,在他眼里,电影毫无姿态和立场可言,其“目标群体汇集美国百万富翁和中国苦力,大城市的家庭女教师和矿区酒吧女招待,因为电影不得不到处放映,取悦于每个人”[6]47-48。电影与戏剧的对立首先体现在前者是对后者的突破上,也就是从静态转变为动态的表现方式。剧场中的观众只能从其固定的位置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如此一来,不同座位上的观众由于视角的有限性看到的也就有所不同,而电影则借助移动的镜头,让坐在不同位置上的观众看到同样的画面。其次,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媒介,“可以对任何其他的表演艺术进行记录、压缩,并通过自身特有的转录形式表现出来”[5]100,而戏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电影还有一个“典型的非戏剧功能就是制造幻象、虚拟幻象”[5]101,传统的戏剧舞台同样无法完成这种工作。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就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反对电影与戏剧之间的相互渗透,主张二者各自为政,保持独立性。桑塔格虽然认可帕诺夫斯基在探讨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上做出的贡献,但是批评其论断过于简单化,因为“就算一部电影对话正式、繁复,机位相对固定,或仅仅在室内拍摄,也不能说它就是戏剧化的——不管它是不是改编自戏剧;与之相反,电影公认的‘本质’也不是必须大范围调动镜头或是让声音从属于影像。”[5]106在她看来,电影与戏剧固然在呈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相反,一部电影完全可以表现出戏剧的一般特征而无损于其成为杰作,比如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1903-1963)就能够用几乎静止的镜头做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桑塔格还反驳了阿拉达斯·尼柯尔(Allardyce Nicoll,1894-1976)的观点,这位评论家称电影与戏剧的区别在于使用演员的不同——电影观众会将电影演员与角色当成同一个人,从而把电影看成是真实的,而剧场观众在观看表演时就已经预设了演员与角色的不一致,接受戏剧作品中各种不真实的成分,而纯粹的戏剧,只是一些传统的技巧而已。桑塔格反问道:“难道戏剧就不能将表现真实生活和尊重传统技巧融合起来吗?”[5]107 桑塔格不赞同武断地将电影与戏剧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认为它们之间其实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不过按照电影发展的速度和趋势,戏剧似乎处于被动地接受电影渗透的地位,例如:“表现主义电影”(expressionist film)的成功经验被表现主义戏剧所吸收;电影的“渐明”(Iris-in)技术启发了戏剧舞台采用聚焦的照明手段来突出单个演员或场景;电影快速切换镜头的视觉效果催生了旋转舞台的设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与电影的竞争中,戏剧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在观众的人数上处于下风。帕诺夫斯基宣称:“电影,而且唯有电影,公允地对世界进行唯物主义的阐释,这种阐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渗入到了当代文明之中。”[7]71尽管如此,电影并不能取代戏剧的位置,因为后者同样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甚至能够将电影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而且它还是众多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作曲家“选择艺术至高形式时的首选”[5]120。 电影毕竟不等同于戏剧,因此讨论二者的差别仍然是必要的。桑塔格总结道:“如果电影与戏剧之间存在着某个最简单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就是两者对空间的利用方式的不同。戏剧总是存在于一个符合逻辑的、连续的空间里;而电影(通过剪辑基本元素——镜头)则可以表现在非逻辑的或非连续的空间之中。”[5]108换句话说,戏剧表演的现场性使得演员的空间定位非此即彼:要么在要么就不在观众的视野中,他们的出场和退场按照情节的发展有其空间的逻辑性。相比之下,电影的空间感则可以在镜头的转换或者并置中变得多维化,演员在银幕上出现或者消失也比在舞台上要灵活得多——拍摄时摄影机的移动和剪辑时的取舍能够让电影中的人物在不同的空间里穿梭自如。不过本雅明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电影演员较之于戏剧演员的局限性,首先,“戏剧舞台上,在观众面前展现演技的终究是演员本人,而电影演员则需要依靠一整套的机械作为中介”[3]71,其次,“电影演员不能像舞台演员那般在演出过程中依观众的反应来调整他的演出”[3]72。本雅明的分析自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桑塔格论述的重点在于戏剧与电影其实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出现戏剧电影化或者电影戏剧化的情况。 二、从布列松到戈达尔:电影的形式主义美学 1996年,在为《反对阐释》的西班牙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桑塔格称自己“对戈达尔和布勒松的影片印象尤为深刻”[1]308,这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她对二者电影风格的评论组成了其电影观的重要内容。桑塔格认为在电影导演中,罗贝尔·布列松是反思形式的大师,而另一位她推崇的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作品的精神核心,是其中刻意反思的特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身性的特质”[8]151。 桑塔格将电影的反思性与形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认识到在“反思性的艺术中,艺术作品的形式以突出的方式呈现出来。”[9]179乍看上去,这令人费解:倘若艺术作品流于形式,如何引起观者的反思?桑塔格显然不会止步于此,她继而解释道:“观众对形式保持警觉,其功效在于拖延或者延宕他们的情感……对形式的警觉,同时起到两种作用:它提供一种不依赖于‘内容’的感官愉悦,此外,它还诱导人们使用理智。”[9]179由此可见,桑塔格倡导形式的重要性是希望人们在接触艺术作品时要避免不假思索地投入到其内容之中,不加选择地认同和吸收内容,而“反思的艺术实际上是对观众施加某种节制的艺术——延缓其轻易获得的满足感。甚至乏味也可成为这类节制的可用手段。”[9]180因此,桑塔格主张在电影中引入布莱希特在戏剧中采用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而这也可以看成是她打破电影与戏剧对立关系的一次学术尝试。布莱希特在《中国表演中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s in Chinese Acting)一文中指出德国戏剧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的间离效果,这样做能“阻止观众简单地认同剧中的人物。接受或者抵触表演者的行动和语言应该在观众的意识层面展开,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在潜意识层面展开”[10]91。 (一)布列松的间离之道 当桑塔格将目光转向电影界时,她发现布列松其实也深谙间离之道,称得上是电影界的布莱希特。她为布列松在评论界受到冷遇鸣不平,分析“布勒松之所以大体上没有获得与其成就相符的地位,原因在于他的艺术所属的那种反思的或沉思的传统,并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尤其在英国和美国,布勒松的电影经常被说成是冷漠的、超然的、太知识分子化的、抽象的”[9]179。桑塔格呼吁人们“得去理解有关此类冷漠的美学,即发现冷漠的美感”[9]179。我们不妨来理清一下这几个概念——冷漠的美学(Aesthetics of coldness)、间离效果、反思和形式的逻辑关系:“冷漠的美学”即以布列松的作品为主要代表所反映出的电影美学,其特征最终指向的是间离效果,其目的是激起观众的反思,而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对形式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完善。可以说,冷漠的美学是桑塔格为区分电影与戏剧的批评话语而造出的一个术语,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 王秋海指出:“综观桑塔格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最具感召力和总结性的一句口号式的表述便是‘反对阐释’。”[11]54这个论断似乎尤其适用于桑塔格的电影观。在她那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反对阐释》中,桑塔格为电影暂时躲过了各种刻意为之的阐释而庆幸:“电影之所以尚未被阐释者所侵占,其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还是新鲜事。也多亏这么一个幸运的巧合,即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只不过是一些影片;换句话说,电影被认为是与高级文化格格不入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被大多数才智之士所忽视。”[12]11-12这里包含了“反对阐释”的一个悖论:电影因其大众性(此处的大众性多多少少会让人联想起“低俗性”)以及是艺术的一个新生门类而免于遭受批评界的过度阐释,但阐释的匮乏反过来又表明了电影在批评界立足不稳以及关注度不高的状态。法国电影理论家亚历山大·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早在1948年就写道:“今日之电影已然展现了新的风貌……在哪些影片里能发现这种新的美感?正是在那些被批评家所忽视的影片里。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的《游戏的规则》、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的电影、以及布列松的《布洛涅森林的妇人们》,所有这些为电影崭新的未来奠定了基础的影片在批评家眼里视而不见,这并不是什么巧合。”[13]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电影的命运与当时相比似乎也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撇开那些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粗制滥造之作不谈,即便是在口碑和票房上都大获成功的影片也仍然不能像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文艺形式的经典作品那样会成为研究者永不枯竭的题材,往往都是昙花一现,只是在各大影院上线的前后引起一番讨论,不久之后就归于沉寂。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桑塔格一方面为电影抵制了阐释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却建议道:“对那些想分析电影的人来说,电影中也常常存在某种需要加以把握的内容之外的东西。因为电影不像小说,它拥有一套形式词汇,即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关摄影机的运动、剪辑和画面的构成那样一套详尽、复杂并且大可商榷的技术。”[12]12如果仔细阅读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我们便会理解她这个看似自我矛盾,实则顺理成章的态度。她所反感的阐释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12]5,也就是为了阐释而阐释,并且一定要找出条条框框来限定阐释,如此一来就失去了对阐释对象的真正的感受力。 通过考察布列东的电影,桑塔格试图为“想分析电影的人”提供一种阐释的路径。她切入的那个点正是她高调宣扬的“形式”,而布列松创造了一种完美地表达他想表述的内容的形式。在桑塔格的笔下,布列松的电影风格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将电影作为语言,实现形式的突破。桑塔格援引了阿斯楚克的一段话来说明电影作为语言的具体含义:“说它是语言,我指的是这么一种形式,艺术家能够以它并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无论这些思想如何抽象,或能够传达他的困惑,像在当代的文章或小说中那样”[9]181。在布列松的电影里,所谓形式,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视觉形式,而主要是叙事形式,因为布列松对叙事体验(narrative experience)的看重远胜于造型体验(plastic experience)。为了达到理想的叙事效果,布列松努力打造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电影语言,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多余的或者早于场景的叙事。多余的叙事是指在展现了场景之后对场景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中断观众对情节的直接的想象性的参与”[9]183;早于场景的叙述则是指在场景开始之前,先行解释了即将发生的事,其目的是消除悬念,以挑战传统的叙事方法。 第二,在表演中反对情感投入。这一点与布莱希特亦有相似之处。布莱希特希望演员能做到不与其表演的角色认同,他非常欣赏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表演者会表现出自己意识到是被观看着的,会自我审视,“因此,当他在表演一片云彩时,比如在展示云彩的突然出现、柔软且强劲的增长、快速而又逐步的变化时,他会不时地看看观众,好像在说:‘是这样的吧?’与此同时,他还会看看自己的胳膊和腿,比划比划,检查检查,最终也许还要示意确实如此。”[10]92这样一来,表演者便在一定意义上与所表演的对象分离开来,观众也由此产生一种疏离感。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布列松启用了非专业的演员,让他们用尽可能少的表情来说出各自的台词。这些演员由于与角色气质的契合,基本上都在没有花哨的表演技巧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演出,倒是那些为角色所感染而按捺不住地投入情感的演员削弱了影片的表现力。 也许人们不禁会问:布列松的电影形式尽力地节制情感,这是否意味着观众自始至终都会由于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而保持无动于衷?桑塔格的答案是:“艺术中情感力量的最大源泉终究不在于任何特别的题材,无论这种题材如何充满激情,如何普遍。它在于形式。通过对形式保持警觉而疏离和延宕情感,最终使得情感变得更为强烈、更为强化。”[9]181克制情感其实是为了退后一步进行反思,桑塔格期望的是人们在反思之后爆发出更大能量,而这种能量带着清醒思考后的智慧光芒,其震撼度会远远大于在人们在观看一部影片时仅限于现场的感动之情。 (二)戈达尔的杂糅之道 桑塔格认为在电影中贯彻反思性的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导演,那就是戈达尔。从某种程度上讲,桑塔格将戈达尔的地位置于更高之处,虽然“戈达尔与布列松同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艺术家,而让戈达尔不同于布列松,进一步升华为文化英雄的特质正是他无尽的活力、冒险的精神以及他在驾驭电影——这样一种大众的、正在迅速商业化的艺术时,所表现出的离奇个性。”[8]149-150她在《反对阐释》和《激进意志的样式》两部文集里各收入了一篇论戈达尔的文章:《戈达尔的〈随心所欲〉》(Godard's Vivre Sa Vie,1964)和《戈达尔》(Godard,1968)。我们从篇名也能看出,前者是对戈达尔某一部影片的具体解读,后者则是对他整个创作的宏观评述,但无论如何,将这两篇相距不过四年的文章合在一起来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桑塔格对这位“文化英雄”的电影风格的分析。桑塔格盛赞戈达尔“不仅是一个睿智的偶像颠覆者,更是有意识地要‘摧毁’电影本身。也许他不是第一个要摧毁电影的人,却绝对最持之以恒、最才华横溢、最懂得应时而动”[8]150。当然,所谓的“摧毁”实则是一种与传统决裂的姿态,在这一点上,戈达尔比布列松更加坚决,更加执着。 在桑塔格看来,“戈达尔作品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其中大胆的杂糅(hybridization)”[8]150。文学、戏剧、绘画、电视等方面已有的技巧都能被戈达尔随心所欲、灵活自如地加以运用。如果说布列松主要是通过个性化的叙事和极力克制的表演来达到间离效果以推进电影的反思性的话,那么戈达尔为此做出的尝试要多得多,至少他试验的成果数量也要远远超过布列松。那么,戈达尔主要在哪些方面展开了他的杂糅试验? 第一,视角的多样化。在戈达尔之前,电影的拍摄美学法则要求视角必须固定,一部影片从头到尾要么是第一人称叙述,要么就是第三人称叙述。戈达尔对这个法则不以为然,他天马行空地变换视角,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中来回切换,当他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时,“并不是出于一己的投机,而正是应合了已然确立了的艺术潮流——在作品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认知”[8]152。戈达尔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不是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桑塔格以《阿尔法城》(Alpha ville,1965)为例,指出该部影片在开场时就出现了三个不同角度的第一人称叙述:作为导演的戈达尔本人以及影片中的两个角色。导演的干预是桑塔格比较欣赏的表现形式,认为“在影片中采用导演的第一人称视角有其特有的优势:既能给予导演更多的自由,又能促进更严谨的叙事形式的形成。”[8]171桑塔格更看重的是当导演根本不是作为片中的人物而是用画外音、旁白等参与叙述时,应该成为一个既要置身于电影之外,又要对作品负责的思考者。或许只是为了突出戈达尔电影视角的创新性,也或许他的第三人称叙述相较于传统的方式而言没有太多的变化,桑塔格在特别介绍了他在第一人称叙述上的一大特色之后并没有继续讨论第三人称叙述的问题,不过她极为肯定的是,戈达尔在启动两种叙述模式时使得影片更具有层次感,会出现“两种并存的时间尺度,前一种标志着影片故事的发展进程,而后一种标志着叙述者对影片内容的思考过程,从而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也得以自由地贯通”[8]169。 第二,电影手段与其他手段的融合。受好莱坞音乐剧的启发,戈达尔在一些影片中会用歌曲与舞蹈表演等来打断故事的进程,不过他受布莱希特的影响更为明显,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让剧中人物直接表达对于电影艺术的主张,二是将完整的影片叙述分解为若干小片段,类似于戏剧的场景安排。不过戈达尔显然不是一个只借鉴不创新的艺术家,为了打乱影片的叙事顺序,他有时候会综合视觉和听觉的技巧将戏剧与电影的各种手段进行大杂烩式的处理,而“最能反映戈达尔导演风格的电影元素,就是招牌式的快速切换、不匹配的画面、闪动的镜头、顺光拍摄与逆光拍摄的交替,以及用(符号、绘画、广告牌、明信片、海报等)预制的视觉载体引导相应的电影情节,还有不连续的背景音乐”[8]165。这样做也是抵制观众的情感投入,比如在《随心所欲》的片头,戈达尔将听与看分离,在昏暗的画面中,观众只能听到谈话声,而无法看清人物的相貌,“观众不被准许去观看,去投入情感”[14]203。 第三,雅俗共赏的文化元素。戈达尔相信“任何文化素材都可以被电影物质化”[8]154,因此他一方面倡导平实的文学品味,喜欢将情节丰富的低俗小说作为自己电影的灵感源泉,另一方面又在电影中大量地插入文学“文本”和其他文化形式,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毛泽东语录、某些学术著作的段落等,还有其他导演的电影也会在戈达尔的“引用”之列。这仍然是戈达尔控制情感强度拉开观众与情节之间的距离的一个措施,因为“视觉元素易于直接地表现情感,而通过语言元素(包括符号、文本、故事、话语、诵读、采访在内)所表现的情感在强度上则要弱得多,所以戈达尔在影片中安排了大量的或看得见,或听得见的语言元素;这样一来,当观众被电影画面带入情节的同时,批判性的语言又让他们清醒地置身事外。”[8]185在戈达尔的《随心所欲》中,桑塔格观察到该片十二个插曲中就有十个使用了这样的方式,有时候剧中人言谈的深度甚至超出了他们自身应有的水平。桑塔格欣赏戈达尔“从人所共知的庸俗素材入手,不避市井谬传、巧妙利用情色,在以商业化元素吸引观众的同时,也获得了探索纯粹电影的空间”[8]160。这个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桑塔格自己。从桑塔格本人的创作,尤其是后期的小说创作来看,她也乐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既能吸引大批的读者也能探索纯粹文学的空间,《火山恋人》(The Volcano Lover,1992)和《在美国》(In America,2000)也确实达到了她的期望,在商业上和文学样式的探讨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从布列松到戈达尔,桑塔格想要热切表达的是“一切艺术皆趋向形式……在伟大的艺术中……是形式才使艺术作品收尾”[14]198。不难看出,布列松的“间离”也好,戈达尔的“杂糅”也好,这两个在她眼中非常伟大的电影导演都在贯彻电影的形式主义美学,他们殊途同归的那个终点就是去推动接触电影的人(包括他们自己)从内容的羁绊中抽身而出,站在较高处进行反思,电影的地位也能由此拔高,成为一个更具智性的大众化媒介。 三、里芬斯塔尔之争:电影与法西斯美学 桑塔格不是一个固守己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她经常会根据认识的加深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也落下了不少诟病。在桑塔格的电影评论中,她对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的看法就非常耐人寻味。从1965年的《论风格》(On Style)到1974年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我们很难想象她对同一个电影导演的态度会在十年间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卡尔·罗利森讥讽地解释说“里芬斯塔尔渐长的声誉要求桑塔格推翻她自己早期的评语,因为在1964年(《论风格》写于1964年)看上去大胆的话语到了1975年就变得平淡无奇了”[15]135。他的言下之意乃是桑塔格一直是一个标新立异、爱唱反调的人,当她发现自己的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她就开始摇身一变,推出一个新的观点。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这里有必要对里芬斯塔尔其人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她多才多艺,是舞蹈家、摄影师、电影演员和导演,备受希特勒的赏识,是他眼中“完美的德国女人”。在希特勒的大力支持下,她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1935)和《奥林匹亚》(The Olympiad,1938),前者展现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后者记录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从拍摄的技巧而言,这两部影片的确标志着一个天才女导演的巅峰时刻,但是由于影片题材的特殊性,里芬斯塔尔在第三帝国倒台后数度入狱,罪名主要是参与了纳粹活动,为纳粹摇旗呐喊,极力美化希特勒和他的纳粹统治。 在《论风格》中,桑塔格为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辩护道: 把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纳粹的宣传。其中存在着纳粹宣传,但也存在着我们难以割舍的别的东西。这是因为,里芬斯塔尔这两部影片(在纳粹艺术家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展现了灵气、优美和感性的复杂动态,超越了宣传甚至报道的范畴……通过作为电影制作人的里芬斯塔尔的天才,“内容”……我们即便假设这违背了她的意图,开始扮演起纯粹形式的角色。[16]25-26 这段话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桑塔格在60年代颇具标志性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她几乎是急切地、一厢情愿地把里芬斯塔尔归类为形式主义者。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内容自然也可以转化为形式,成为形式的表现方式。王秋海的评论十分中肯:“早期的桑塔格试图创造出一个艺术形式的心理空间,完全摒弃作品中的历史性和作品背景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悬置’思想和内容抛弃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但却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自我循环怪圈,因为她对艺术形式的无节制强调又使她回到了将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的悖论之中。”[11]107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桑塔格在褒扬里芬斯塔尔时措辞还是相当谨慎的,并没有否定其作品的纳粹宣传成分,只是提醒人们要看到纳粹之外的东西,也就是里芬斯塔尔对电影美学所作出的贡献。她特意强调人们在里芬斯塔尔的电影里看到的是带着引号的希特勒和1936年的奥运会,是作为艺术呈现出来的形象。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74年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桑塔格话锋一转,称尽管《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无疑是一流的影片(它们或许是迄今为止两部最伟大的纪录片),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们在电影史上并非真正重要”[17]95。其实,这样仍然包含着正面词汇的表述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里并不多见,该文更多的是对里芬斯塔尔所言所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在第一段桑塔格就直截了当地斥责里芬斯塔尔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The Last of the Nuba)的介绍文字与事实出入太大,“充斥着令人感到不安的谎言”[17]74。桑塔格通过细致的文献工作和考证,驳斥了这位德国导演力图撇清与纳粹关系的种种不实之词。诚然,桑塔格的“急转弯”有其自身的原因,其“形式主义美学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已有所转向,逐步意识到文学艺术作品不可能完全与历史及现实割裂开来,而且它们必然是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为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服务”[11]110,但真正促使她重新评价里芬斯塔尔的却是她对法西斯美学的警惕,而在她看来,后者的作品恰恰就是法西斯美学的具体阐发。 本雅明曾极为反感地写道:“法西斯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将美学引入政治生活里。法西斯主义者将首领崇拜强加给民众,如此来压榨百姓,正好比施压于设备器材,强迫实现仪式价值的生产服务。”[3]98桑塔格显然赞同这个观点,她补充道:“法西斯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为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17]91无论是在《意志的胜利》里还是在《奥林匹亚》里,里芬斯塔尔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上述表现手法,突出了希特勒的“神圣”地位和民众对他的极度痴迷和崇拜。尤其是在《意志的胜利》的开头,希特勒乘坐的飞机穿越阴霾,从云端降落至欢腾的群众面前。随着希特勒走下飞机,里芬斯塔尔完成了一个大大的隐喻:希特勒就是天神下凡,为万众带来了欢乐和光明。 里芬斯塔尔为纳粹所累,其电影生涯遭到了重创。1984年,在82岁高龄的时候,她开始撰写回忆录,“目的是想澄清误会,消除成见”[18]599,极力解释自己与纳粹不存在同路人或同情者的关系,她所关注的不是政治因素或意识形态,而是纯粹的美感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在回忆录里里芬斯塔尔写到了自己如何勇敢地突破戈培尔设置的种种障碍,又如何大无畏地在希特勒面前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屈服于后者的政治意图。其实,在桑塔格写作《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之前,里芬斯塔尔就已经在很多场合表述了类似的言辞,但是桑塔格一一予以了反驳,并坚持认为“里芬斯塔尔是惟一一位完全吻合于纳粹时代、其作品不仅在第三帝国时期,而且在其垮台三十年后依然一直系统地阐明法西斯美学的诸多主题的重要艺术家”[17]90。这也确实是里芬斯塔尔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她如何强调其个人的主观意愿并不受到纳粹的影响,她的影片所展现的也仍然是纳粹想要传达的东西,即“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17]91。正如电影评论家和纪录片研究者林旭东所言,她的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即兴采访,更不是漫不经心拍下的一般印象,它是一个经过严密推敲、精心编织起来的政治图腾,它是气焰嚣张的,但确实是直言不讳的。因为里芬斯塔尔对自己所鼓吹的东西确信不疑,惟其如此,她才会以赤裸裸的方式供认了一个民族的歇斯底里,也许正是它的过于露骨使它成为一种罪恶的见证”[19]81。如果没有对纳粹精神的精准把握,即便她尽心尽力地对拍摄角度加以选择和调整并在电影的后期制作中废寝忘食地进行剪辑工作,《意志的胜利》也未必会成为纳粹的完美宣传品,吸引着无数的德国青年踊跃地加入到纳粹的队伍之中。 桑塔格不惜冒着自相矛盾和思想摇摆不定的指责对里芬斯塔尔大加鞭挞,这种“反常”的举动其实在时间节点上有一个导火索。在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中,女权主义者就开始把里芬斯塔尔树立为一个文化偶像。1973年的纽约电影节上出现了一幅将里芬斯塔尔作为主角之一的宣传画;1974年,在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镇(Telluride)举办了第一届特柳赖德电影节,里芬斯塔尔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受到了影迷的追捧;也正是这一年,她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出版,她“一跃而成为一座文化丰碑”[17]84。在愈演愈烈的里芬斯塔尔热中,桑塔格按捺不住,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她敏锐地观察到在里芬斯塔尔声誉日隆的背后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人们在认可那些反映着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作品时所产生的对法西斯主义的迷恋之情。桑塔格承认里芬斯塔尔未必是有意地宣扬法西斯美学,但是当她和她的拥护者打着美的旗号进行辩护时,他们没有料到人们心底燃烧的法西斯欲望远远超过了预想的程度,也就是说,在追捧者中间,并非人人都是冲着她的作品给予人的美感,相反,更大一部分人是为其中的法西斯主义特质所吸引。桑塔格认为,如果把里芬斯塔尔置于高雅文化的圈子,其艺术表现力仅为少数人所理解和欣赏,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当她走向大众,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在高雅文化中可以被接受的,到了大众文化里就不能被接受,只提出无关紧要的道德问题作为少数人的一种特质的那些趣味,一旦确立下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便蜕变为一个让人腐败的因素”[17]98。桑塔格担忧地看到,人们对法西斯主义愈来愈浓厚的兴趣中一部分是好奇心使然,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对于恐怖和非理性的着迷,而连接这两种兴趣动因的是法西斯主义明显的性吸引,它满足了人们的性幻想,尤其是男同性恋和施虐受虐狂的性幻想。与纳粹党卫军的装备相似或一致的皮鞭、皮靴、重型摩托车等已经成为追求离经叛道的性体验的人们心醉神迷的性意象和炙手可热的性用品。 与《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起出现在《在土星的标志下》这本文集里的还有一篇《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Syberberg's Hitler,1979)。桑塔格如此安排大有深意。西贝尔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1935-)也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Hitler:A Film from Germany,1977)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桑塔格称赞该片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在庸作频现的20世纪70年代,看到这样的巨制“使我们无法容忍别人的电影”[20]165。桑塔格对里芬斯塔尔的批判出自对纳粹主义在其作品中强烈的蛊惑力的警觉,而在西贝尔西格的电影中,他“所说的希特勒并非仅仅是指真实历史上的那个恶魔,那个造成上千万死难者的恶魔。他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希特勒死后不灭的希特勒物质(Hitler-substance),一种现代文化中出现的幽灵,弥漫于现在并重构过去的一种变化多端的恶之原则”[20]150-151。纳粹的邪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独有的,纳粹之所以能横空出世并带来如此空前的灾难,其背后必然存在着支撑性的力量:被蛊惑的民众释放出了意识深处的恶。希特勒就好比是一部规模巨大的电影的导演,可悲的是的确有人愿意加入他的演出阵营,“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3]102-103。与里芬斯塔尔神化希特勒完全不同,西贝尔西格运用了包括戏仿和科幻在内的各种手法将希特勒世俗化,“用其影片,他也许已经‘击败’了希特勒——驱除希特勒身上的恶魔”[20]160,这正是桑塔格理想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里芬斯塔尔和西贝尔西格虽然同为德国人,但是从其三十三年的年龄差异来看,二者毕竟是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桑塔格如果希望里芬斯塔尔能够超越其时代背景拍摄出类似于西贝尔西格那样的影片,那对于里芬斯塔尔来说未免有失公允——这个与纳粹并肩工作过的女导演虽然才华过人,但也是纳粹时代被“希特勒物质”所掌控和征服的普通的一员。也正是鉴于此,利亚姆·肯尼迪直言不讳地指出,桑塔格未能“向西贝尔贝格提出她向里芬斯塔尔提出的历史和政治问题”[21]85,这种选择性的回避确实是桑塔格论述的一个硬伤。 在电影尚未获得批评界的关注时,桑塔格就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宣告电影绝非仅仅是一种娱乐大众的媒介,相反,“作为严肃艺术的一个新来者,电影处于一个攫取其他艺术并能以层出不穷的新的组合方式来有效地利用那些甚至是比较陈旧的因素的位置。”[2]245她试图通过突出电影的严肃性来彰显其批评价值,从而与其他已被认可的艺术形式处于平等的研究视野之内。在她推崇的布列松和戈达尔的影片里,她都看到了严肃性。比如,布列松的影片是“关于以最严肃的方式获得人性的一种观念”[9]195,而戈达尔的影片“是理智的文本,是对理智的研究;它涉及严肃性”[2]203。既然如此,电影也像小说和戏剧一样兼具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工作者们既有大量来自于小说和戏剧等方面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也有充分发挥创新能力的广阔空间。桑塔格一方面告诫我们要谨防对艺术进行不着边际的破坏性的过度阐释,另一方面又呼吁一种服务于艺术作品而无损其完整性的艺术批评。在此基础上,她建议从形式入手,以精确细致的描述来揭示艺术作品的形式之美。艺术批评的目标是使艺术作品更真实,使人们更关注作品本身。就电影而论,对其形式的关注能够使观众产生一定的批评距离,为自己赢得反思的空间,而桑塔格本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并反思当前文化的艺术家、批评家”[22]155。也正因为一直保持着反思的习惯,所以当她的观点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出现问题时,她会坦然地加以修正,对里芬斯塔尔的态度迥异的评论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在桑塔格眼里,“电影是一场圣战。电影是一种世界观。”[23]118当她觉察到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有可能正在或将会把人们的世界观转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迷恋时,她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笔,以其作为武器,极力捍卫电影这个“严肃艺术的新来者”。桑塔格的言论自然不乏过激之处,但是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颗时刻关注当下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标签:布列松论文; 戈达尔论文; 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电影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反对阐释论文; 苏珊桑塔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