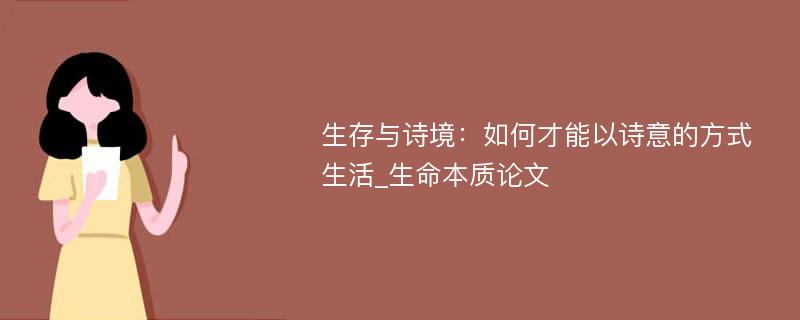
存在与诗境——诗意地安居如何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与论文,诗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1—0016—06
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著名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经过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1889—1976)深刻的哲学诠释,使之“义海宏深,微言浩瀚”,竟为寻求终极觉悟的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粮,这是荷尔德林本人料想不到的。“诗意地安居”是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只能追问“到底如何可能?”而不能问“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不是逻辑上的“某物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它如何被直接理解,达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透彻自明。从前者的立场上看,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现成状态;但从后者的立场看,它却是可以领悟的,因为它是一种缘构成状态,处在“日日新,又日新”的动态之中,这是一种非现成的识度,它既非创造论的,亦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缘起论的。同时,“终极”的问题,其含义亦不像概念哲学家们讲的那样,是最终不变的实体,而是意味着发生着的本源。本源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现成化为认识对象的,而只能在直接的体验中被当场揭示出来,这是一种缘在展现的境界,是存在论解释学的视域。本文试图从这一视域,结合海德格尔的诠释和中国大乘禅宗佛学的识度予以初步的探讨。
一 海德格尔的哲学诠释
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最为推崇的伟大诗人。早在1936年海氏就在罗马作过《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说。1951年海氏干脆以《人诗意地安居》为题,作了一场专门演讲。为什么海氏如此挚爱荷尔德林而不是别的诗人呢?对此海氏解释说:“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的思之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1](P277 )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的诗其实是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别的诗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依海德格尔的诠释,荷尔德林诗中所指的人是一种实存主体,这在海氏那里称为Dasein.即“缘在”(注:Dasein 在学术界有诸如“此在”、“亲在”、“纯在”、“缘在”、“现存在”、“本是”等多种译名,本文依张祥龙先生之说,译为“缘在”,因为Dasein不仅有人的自我觉悟、自我意识、在世界之中的领悟(非反思的方式)的含义,而且还有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含义,即人是一种能够领悟自己和世界的因缘而起的存在。)。所谓实存主体,即是人的主体存在兼摄了人的现实存在与本真存在双重含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实存主体介入社会中的过程就是人异化的过程,这是人必经的阶段,人的生存可能性只能在人的实际生存过程中才能得到显现。然而,一旦人积极展开自己的生存活动时,最终却会发现自己在这种活动中并不是本真存在的展现,而是处在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之中。这种异化的根子就在于人自身的存在结构之中,即“存在于世界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并无“诗意”可言。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艺术性的活动,或是书面艺术或是音视艺术。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2](P463~464)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日益被物化,成了工具化、零件化、技术化的人,整个世界亦越来越成为一架巨大的控制人的机器,生存于其中的“单相度的人”(马尔库塞语)的行为,是一种以功利为目的的“剧场化行为”(哈贝马斯语),这种人就是现实存在的非本真状态的人。这种人处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游离状态中,与世沉浮,没有创造性,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的“在者”(海德格尔语)。在这里海德格尔表达了一种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因为他“看到了存在于每一个特殊状况中的关于人类一般困境的真理。”[3](P237 )他说:“这纯属辛劳的境地中,人被允许抽身而出,透过艰辛,仰望神明。”
在此终极关怀中,缘在处于烦、畏、死的临界状态(雅斯贝尔斯语),把沉沦于世的人唤醒,回归本真存在。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死亡。在这里,死亡不是生理学、心理学和神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存在论意义上本真的死亡。这种死亡的内涵和意义是:第一,死亡是缘在本真的存在,每个人的死亡是不可代替的,本真存在的人是“为死而在”,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根本的有限性,因此死亡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命存在意义上加以领会的现象。在死亡面前,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乃至功名利禄全都失效,对死亡的沉思乃使人探求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由终极意义的探求而有终极意义的体认,而有终极存在的追求,终极意义与终极存在乃是一体之两面。第二,由于本真意义上的死亡,使本真存在在世界深处向我们召唤。死亡开显了人之存在的“空性”,使人的存在面临无底的深渊,顿觉整个生命根基的动摇,存在的晕眩,内心的不安。由此,死亡逼迫人们以时刻牵挂的方式去回答终极生死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回答使本真存在之光透过非本真世界的痛苦和人生烦恼的茫茫迷雾,而不断地绽露自己。第三,人通过死亡而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非本真存在向本真存在回归。非本真存在的人,虽然活着,但却没有意义,他不是他周遭世界的意义承担者,周遭世界也不是他的意义承担者。因此非本真存在的人,既没有终极关怀的呼唤,又没有终极意义的探求,更不用说有终极存在的体认了。而死亡却把这种迷梦惊醒,把这种隔绝打破,使本真世界显现出来,成为诗化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诗人,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是本真的缘在,他们“诗意地安居”乃成为可能。由于这种诗意盎然的澄明境域是我们本真存在的回归和实现,因而对我们来讲就有着最切身的可理解性和感召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非本真存在与本真存在并非是两个不同的存在,而是同一存在发生的不同变化,即从遮蔽的存在状态变成敞开的存在状态,它们是同一缘在的一体之两面。因此,非本真存在与本真存在一样亦具有本源的发生和缘构性,同样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本真存在之所以会从非本真存在中发生,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不甘沉沦的良知呼唤,在于临界状态中人的本心的觉悟,从而自己拯救自己,使非本真的旧的污染的生命系统彻底转变成本真的新的清净的生命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云:“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海氏解释说:“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它的拯救都还无救。用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2](P436)因此, 在死亡中觉悟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现象,危险的世界正是意义境域的来源,痛苦的人生中根植着拯救!
二 “诗境”在于一心之转
死亡的逼迫之所以能使生命有可能进入本真存在的“诗境”,关键在于人能够在死亡中觉悟,故从非本真存在的无诗意进入本真存在的“诗境”,关键在于一心之转,即转迷为悟,前念迷则为非本真,后念悟则为本真。故“诗意地安居”之所以可能,乃是由于在死亡逼迫中觉悟使然,“人之为人,就仅仅在于他始终处于此一跨越之境中。”
死亡的逼迫使人觉悟到自己是先行到死亡中的存在。首先,死亡使人的存在成为不断脱离在者(自在)而单独奔向前方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贯穿着人的一生,只有面对死亡,意识到死亡,才使我们领悟到人是先行到死亡中的存在。随着先行到死亡之中去的可能性的揭示,人便能从多方面领会自己的本真状态,领会到只有它才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死亡之光将人的存在照亮,使人看清楚原来自己就是本真去死的可能性,除了依本真的可能性去展开自己的存在外,其余均不足道!其次,人是先行到死亡中的存在,把人的存在当作整体展示出来,先行的可能性不是退避死亡,而是自由地为死而在,死亡是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把一切向这种可能性伸展出去的可能性一齐展开出来了,这就从本真存在方面预先把当作本身缘在存在全体的可能性囊括进去了。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依海德格尔之意毋宁说:“未知死,焉知生?”唯有当本真存在始终先行进入到死亡这一最终极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之际,本真存在才能先行获得它的全体。最后,人是先行到死亡中的存在,向我们昭示了死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即生命在死亡中存在,必死无疑,因为有生就有死,故难逃一死,这是确定的;而作为死亡来说,又是活着的生命每时每刻具有的可能性,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什么时候死亡,这是偶然的、不确定的。由此为死而在的觉悟,人把沉沦于日常世俗世界的非本真存在召唤到本真存在的状态中,从而使一切的可能性都是为死而在所作出的抉择!
达到诗境一心之转的觉悟,是一种经过死亡震撼而在事上磨炼的大彻大悟,这种彻悟是主客一如、心物一体的高层次生命体验,因而它是超语言(并非违反语言)、超逻辑(并非违反逻辑)、超理性(并非违反理性)的。在这种深切的体验中,生命从语言、逻辑和理性的思维限制中解放出来,自由自在,澄明透脱。人由此心之大悟而“仰视跨越天地”。
由于人的一心之转的觉悟,人才能“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才能在这块大地上历尽艰难而不为其所困,充满劳绩而不为其所苦,“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因为诗意地安居的可能性是在“大地上”展开的,大地上即大地性、人间性、日常性之意,强调的是在大地上、人间里、日常中的觉悟和实践。“诗意性”与“大地性”都是本真觉悟的重要特征。“人的仰视直薄云天,立足之处仍在尘寰。”在本真觉悟存在的方式中,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上,理想在日常奋勉中实现,澄明于时时刻刻的不断缘在,所谓难乎其难或永不可臻的诗境已化入生命存在的超越历程与价值取向,在这里,诗意的理想与安居的现实是既不即不一而又不离不异的。一方面,如果没有诗意的理想在先,就不可能有安居于大地之上的现实奋勉,“天地之距是为人的安居算出的”;而安居于大地之上的现实奋勉也正是为了诗意理想的实现,这是二者的不即不一。另一方面,明知诗意理想永不可臻而又绝不放弃,反将它化入生命实践的现实奋勉,“人通过在神明面前被度测从而跨越此一度”,“上穷碧落,下临大地”,而使诗意理想与现实奋勉转变成安居于大地之上的日常生活之一体两面,这又彰显二者的不离不异乃至相即不二。故海德格尔云:“当荷尔德林倡言人的安居应该是诗意的时候,这一陈述一旦作出,就给人一种与他的本意相反的印象,即:‘诗意的’安居要把人拔离大地。因为‘诗意的’一词作为诗来看待时,通常总被理解为仅属于乌有之乡。诗意的安居似乎自然要虚幻地漂浮在现实的上空。诗人重言诗意的安居是‘在这块大地上’的安居,以此打消这种误会。荷兰德林借此不仅防止了‘诗意的’一词险遭这类可能的错解,而且通过附加‘于这块大地上’造出了诗的本质。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4](P92~93)
由于生命的觉悟,乃使诗意的理想与在大地上的安居奋勉统一起来,时时刻刻自觉化为生命存在,“日日是好日”(唐代云门大师语),永无停止之日,每时每刻都在“诗意地安居”中展开生命的深沉与辉煌。
三 “诗意地安居”是生命存在矛盾的终极解决
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烦恼、痛苦、恶心、畏惧乃至死亡的意识,根源于生命存在的根本矛盾,即心与物(意识与存在)、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和隔阂。人沉沦于世界之中,无法超越和解决这三大矛盾和隔阂,因而在烦恼、痛苦、恶心、畏惧,乃至死亡的临界状态中,发出最深切的终极关怀,要求这种超越的根本实现,要求这种矛盾的彻底解决,要求这种隔阂的完全打通。而一切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实验科学、语言逻辑乃至哲学思辩,都不可能解决这些生命存在的根本矛盾,只有超理性、超逻辑的思诗合一的般若智慧(高层次的生命体验),才能最终将这些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超越、解脱)。
心与物的矛盾和隔阂是生命存在矛盾的核心,因为心与物的矛盾和隔阂蕴含着生命与万物、现象与本体、有与无、一与多等的对立。生命的意识、人的精神是心,不是万物,是自为,不是自在,然而生命本身又想与万物成为一体,达到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因为自为的“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因而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是永远达不到的。与萨特不同,晚年的海德格尔以思诗合一的高层次的生命体验,即“诗意地安居”,化解了心物的矛盾和隔阂,领会了宇宙万物形成于空中,亦消迹于空中;生命亦然,它从空中来,又回到空中去,万物和生命的本来面貌都是空(无)。生命一旦通过深切的体验把握(感觉、证悟、领会)了这个本体和归宿,生命就可以把世间的一切差别,诸如有无、生死、爱憎、善恶、是非、名利、贵贱等以及形成一切差别的各种关系,诸如时空的、因果的等等,都予以全面而彻底的超越。这样一来,生命之外,再也没有歪曲生命、压抑生命、异化生命的外物了。万物有多大,生命就有多大。万物即生命,生命即万物。心即物,物即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二者的关系乃是体用一如,变常不二的。正因此海德格尔说:“安居之诗的特征并不仅仅意味着诗非要千方百计在所有的安居里出现。‘人诗意地安居’更毋宁是说:诗首先使安居成其为安居。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building)。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4](P89)
人之安居是因为诗意活动的存在,而诗意的活动就是度量、建造、创造、想象的活动,人之所以存在,在根本上就是诗意的活动,是建造的活动,人生就是作诗,作诗让安居成为真正的安居,人的存在从诗意中展现。生命的存在,即因诗意的建造(建筑)而安居于大地上。
因此“诗意地安居”,一方面要求诗意的理想,要求把生命存在层层提升以至于空灵、澄明,另一方面还要将此理想落实于现实的建造(建筑)活动,将生命与万物度量和建造出来,这个过程是生命本身存在的展开过程。换言之,“诗意地安居”,就是在诗意的基地上展开生命度量和建造活动,不仅度量和建造万物,而且也对自身作出度量和建造,由此展现一个崭新的天地,辉煌的人生。因此海德格尔说:“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一种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我们由安居的本质来思被称作人的生存这回事; 另一方面,我们将思那作为一种‘让——居’(letting—dwell),即作为一种——也许甚至就是此种——独特种类的建筑的诗的本质。如果我们循此寻求到诗的本质,也就把握到安居的本质。”[4](P89~90)因此所谓建造天地万物,并不是说物质世界都是由主观精神创造出来的,像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那样,而只是说,实存主体在自身意识活动中为自己投射出相应的对象世界,这是诗的意中之境。于诗人而言,就是在运思的想象活动中,将生命与天地万物相互交融,并依据超越层面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进行建造和组合,使天地万物成为心灵化的理想意象,使心灵成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境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此之谓也。海德格尔说:“栽培和照料就是一种建筑。 但是, 人不仅要栽培那些产生于自身的东西; 人还在aedificare(建造)的意义上建筑,即通过建立那不可能倚靠生长而存在并持存的东西来建筑。在这种意义上建立的,不仅有人的居所,还有由人手并通过人的筹划制成的一切作品。”[4](P92)依此,无论人生有多少苦难,从本质上来说,总是充满诗意。人对现实生活无诗意的不满和痛苦,恰恰说明人生在本质上和原始意义上是应当有诗意的,不然人就不会有不满,就不会有痛苦,乃至厌恶。“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人必须本质上是一个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2](P478 )人在世界之中非本真存在是无诗意的,但无诗意的非本真存在并不能否定诗意的本真存在。正如人有眼明,才会有盲者,决不能因为有盲者而否定人有眼明。人本质上是要“作诗”的,诗意般地生活才是人生的价值之所在。
短暂与永恒的矛盾和隔阂,是生命与时间的矛盾与隔阂。从现实存在来说,时间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造成了人的烦恼和痛苦,人们总认为生命的生死与时间的流逝是两件事情,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时间应有分别。本真存在“诗意地安居”的生命体验,彻底破除了这种看法,在诗人—哲学家的思与诗境界中,生命与时间是同步的,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时间原本二而无二。没有瞬间就没有永恒,永恒只能存在于瞬间之中。生命只有在活生生的具体瞬间中才能把握永恒,感觉永恒,从而获得实实在在的永恒,获得完整的生命体验,诗人—哲学家在此整体性的生命体验中,诗化了宇宙,诗化了生命,同时也诗化了时间。于是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的矛盾和隔阂就被化解了、打破了,生死即是涅槃,瞬间即是永恒,“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美好时光,时时乃有诗意无穷。这样一来,一方面把生命从感叹人生短暂与时间无穷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一方面把心态升华到不朽的高度,由是超越生死而任由生死,超越生死是“诗意”,任由生死是“安居”!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和隔阂,是生命与空间的矛盾和隔阂,在现实存在中,二者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是无法超越和克服的。而在诗人—哲学家“诗意地安居”的生命体验中,却能够从具体的、实在的、有意义的有限中,把握(感觉、体会、证悟)到广阔的、整体的、全幅的无限。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抒情诗云:“一粒沙子也可以看到世界,一朵野花也可以看到天堂,从你的手心里能够了解无限,从一瞬间能了解永恒。”[5](P283)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 无限只能存在于有限之中,有限即是无限,舍有限之外无无限,有限与无限相即不二。于是生命便能在一草一木之中体验到自我的无限伟大,心态也可能在一沙一石之内感觉到世界的无限广阔。
生命在“诗意地安居”的彻底觉悟和深切体验中,超越了生命与万物的冲突,克服了心与物的障碍而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庄严境界;超越了生命与时间的隔阂,克服了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的障碍而进入了瞬间即永恒的永恒境界;超越了生命与空间的矛盾,克服了生命有限与宇宙无限的障碍而进入了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的真际境界。在这种超越中,一切平淡无奇,凡俗琐碎的事务都因沐浴了超越的诗意光辉而生命化了、价值化了、诗化了。在这种超越中,生命因克服了三大矛盾障碍,而由伤感孤独升华到体验生命的尊严;由感叹短暂升华到体验生命的不朽;由惋惜渺小升华到体验生命的伟大。在这种生命存在矛盾的终极解决中,生命由外物和时空的奴隶,转化而升华为外物和时空的主人,转化为生命自我的主人,由是生命的本真存在得到充分的呈现,生命的价值得到圆满的肯定,生命的意义得到终极的确认。
四 诗化的生活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
“诗意地安居”是诗化的生活,生活的诗化,是诗境的存在,存在的诗境,这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
“诗意地安居”使本真存在成为一首“存在之诗”,成为澄明的敞开状态,这种澄明的敞开状态的揭示,使人有了诗与思。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真正的语言是从本真存在中自然流出、迸发,语言是存在本身由隐入显的运作和展开,是存在之真理的澄明发生。因此真正的语言必然是诗,诗是对存在的揭示,是澄明之光的普照。而存在则是诗的展现、运行,像大海之涨潮,鲜花之开放,白云之舒卷,江水之东流;似初升的朝阳,长空的明月,山涧的飞瀑;如鹰击长空,高峰入云,百鸟齐鸣,种子吐芽,这既是存在,又是诗。诗乃体道(存在)之作,体道亦是思。诗是诗意地思了存在的真理。思不是概念的、抽象的、超时空的,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表现为“存在的追思”,是存在的显现,思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穿透力直接体察到存在的真义。诗与思合一,二者不一不异。从不一说,诗彰显着神圣的净土,思领悟着存在的真理,前者是显、是动、是升,具有超拔性,后者是隐、是静、是降,具有凝重性。从不异论,诗不是通常文学意义上的那种诗歌,而是展现本真存在之思;思亦不是对象性的主客二分之思,而是深切体验本真存在之诗,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对生命存在之领悟越是深入,越思入存在,就越临近诗;思与语言越诗化也就越临近存在。由此而言,思即诗,诗即思,二者既是本真存在显现的迹象,又是人返本归真的途径。通过生命体验、亲证和实践,二者共同展现不可思议的存在状态。
在“诗意地安居”中,生命与诗在超越的诗境中相会,生命去掉了世俗的污染,自然天成,纯洁无瑕,流泻为美妙的乐章,自由翱翔于诗意的大地上,传达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感动。诗使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价值、终极理想和终极存在显现于天地万物之中。诗性智慧照耀审美人生,审美人生开发诗性智慧,诗意的理想滋润安居于大地的生命,安居于大地的生命护持诗意的理想,真空妙有的诗境由此得到最圆满的彰显。在无欲无愿宁静的诗境中,世间物理世界的成住坏空,心理世界的生住异灭,生理世界的生老病死得到了终极的超克,宇宙人生存在的一切矛盾获得了终极的解决。这时我们的生命是一种真实的、真城的和真切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是清静的、光明的和神圣的世界,这是人之为人的完成,生命之为生命的彰显,世界之为世界的实现——诗化的人生,诗化的生命和诗化的世界!
“诗意地安居”乃是真空妙有的境界,真空的极致为妙有,妙有的背后是真空,唯有达到真空才能彰显妙有,唯有依靠妙有才能体现真空,二者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的。这就是说,要使诗意地安居成为可能,一方面首先要使我们的安居上达到诗意,达到真空,达到超本体论,达到纯审美境界,即在缘在中,从凡夫位层层向上提升,透彻了解现实世界,以至成为觉者、贤者、智者,终而至于成为哲学家—诗人(菩萨、佛)。“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便根据诗意之本质而作诗。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便人性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P480)。 在这里“神性”并不是指“神灵”,而是指神秘而又神圣的天道、终极价值和至真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在上达诗意、真空的同时,又要向下回到大地上,以诗意、真空来点化现实世界(大地),从而拯救它、纠正它、改造它,最后彻底净化它,使之成为诗的世界,成为真正的妙有。这种妙有由是乃依净性而缘起,于是超本体论转化而为本体论,由本体论而开出宇宙论、道德论乃至知识论等等。这种上求下化乃使“诗意地安居”成为可能。因此,“诗意地安居”实际上是向上提升至诗意(真空)与向下落实于大地同时彰显,乃至于宇宙万物不逃于生命诗意照射之外,天地间无有一物遗之以成其为物,这是生命的价值信念和终极关怀的彻底实现,是真正诗境的光辉呈现。在此境界中,我们体验着世界的美满,感受着生命的壮丽,挥写着人生的诗章。宁静、安祥、快乐、光明、自在与本真生命同在!光荣与梦想属于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上的人!生活的诗化,诗化的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
五 结语
在现代工业社会,工具理性膨胀,人文价值丧失,道德意识危机,人日益沉沦为“物化”的存在,陷溺于权、钱、势三毒中而不能自拔。人类社会的一切正在遭受到空前的污染。由是生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紧张、不安、焦虑、抑郁、怀疑、恐惧、疲劳、喜怒无常甚至歇斯底里竟成了生命的常态,人和这个世界毫无诗意可言!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人类迫切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救济,非常渴望回归精神家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深入探讨诗意地安居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如果大树已经生根,它就不会惧怕风吹雨打,电击雷劈。能如此,则能去情欲之惑,蔑钱权之诱,解心知之蔽,破生死之执,在精神解放中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诗意境界。
收稿日期:1999—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