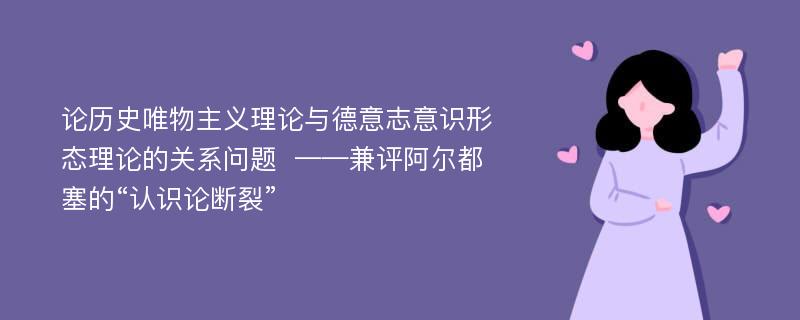
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意义以及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老问题。传统的研究或者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理论上的传承关系,或者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是在一种辩证连续的视域中看待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各种理论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是,马克思是在生产力连续积累的历史进程中看待理论连续进展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上,虽然马克思将后者批判为一种与现实相脱离的、陷入了抽象的理论,但是他仍将他的历史科学看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的承接,把后者看作是对前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克服。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科学;认识论断裂
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意义以及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老问题。以青年黑格尔派为背景的青年马克思思想与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熟马克思思想之间关系的争论,是该问题展开的主要语境。早期的苏联模式是在一种并不充分的形式中来说明两者间的关系,或者以目的论为预设,或者以理论的线性进化为前提。对此,我国已有学者对之作出了批判[1]。相反的极端说法源于阿尔都塞,他认为在两种理论间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即两种理论在问题式上存在根本的异质性。然而,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肯定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之间一定有一种过渡。无论这种过渡是以偶然、断裂的形式展现,还是以渐进的形式展现,它经历了一定的时间。诚然,阿尔都塞强调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绝对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他错误地将理论上的异质性当成了现实上的差异,在现实上他也将历史科学的诞生看作是偶然的。他后期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观点,延续了中前期的看法,将哲学的历史活动比喻为在偶然中“抓住在历史中行进的火车”[2](P189),这正是他中前期“断裂”思想的延续。阿尔都塞遗忘的是,唯有在现实的生产力积累和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可能诞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拟从辩证的思想史考察视角澄清这里的问题,探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
以“爱国、清贫、创造、奉献”为主体的方志敏精神,它凸显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内涵。用方志敏自己概括和倡导的“五种精神”来讲,即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所具有的“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8](P88),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各方面的内容,也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极好教材。
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一般说明
马克思认为,意识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从来都受到所谓的物质性前提的纠缠。人之生命活动的特点就是它要对自身所处的物质世界进行反映,不仅直接反映对象世界,还会把对象世界与它的关系反映出来,甚至可以对这种反映本身进行再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对于人而言,“反思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3](P28)。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发生的悖谬的事情在于,人反映自身与对象间关系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东西(思维)与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的决定关系发生了颠倒,他物、对象决定自我、思维的关系被颠倒。当然,人之所以会无意识地自动委身于意识形态,是因为人已经具备了一种颠倒反映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并没有述诸人的意识本性之类的东西。他认为是人在现实生活所可能身处的历史性位置,在根本性层面上规定着他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马克思将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作为产生意识形态倾向产生的可能起点:“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P30)当然,仅仅拥有可能性,还不等于拥有现实性。只有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才会普遍地倾向于将观念作为统治现实的力量。马克思看到,在理论家中产生这种倾向大量出现是18世纪以来[3](P68)。这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特定的地域中,才会出现观念式的对历史的理解。
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总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现世界本身的颠倒状况则是理论颠倒的根源。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均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社会中,它可能是在对自然界的直观认知中产生;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积累,以及地域和民族间的不平衡发展,它一般都产生于一个民族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情景的理解。于是,在现代历史中,将会存在各种有差异的意识形态理论形式,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一例。因此,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构型是颠倒式的,它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理论则会有不同的表现。
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说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就生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景中。德国的思想家们在构造历史理论时,主动将这种历史现实反映出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便随之产生。马克思将之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反映德国小市民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与英法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然不同。英法两国有着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德国则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试图在向外扩张中、在向外的力量展示中来表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试图通过向内的方式来表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即试图依赖理性在过去的因素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显然,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马克思对这样一种做法持否定的态度。但他同时看到,由特殊的环境所造就的特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却为理论史上的实质性突破,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诞生作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准备——尽管是以否定的方式,并且费尔巴哈在其中的地位尤其特殊。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我们要与三个方向上可能犯下的错误作斗争,尽管它们各自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就1844年左右马克思思想转型的这段时期来看,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便明确表示,在人的社会性问题上,“费尔巴哈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3](P59),而且“……只有他才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加以研究,只有阐明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3](P9)。费尔巴哈真正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使他来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可能达到的最终地步,来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边界。越过它,便是马克思所期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然费尔巴哈仍然陷于意识形态之中,但他的理论服从意识形态理论内部本身的进展运动。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是观念化理论在自身反思中编造扬弃性的历史的运动开始,那么费尔巴哈的理论则在这个运动的最后表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所可能达到的最后界限。这条界限是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它由于受限于颠倒的理论范式,对这种无法克服毫无自觉。此时,构造意识形态理论这样一种脑力分工的劳动再也不能像原先的意识形态理论那样发挥它推动历史的作用,它不再能够为即将到来的历史发挥精神性劳动应该可以发挥的作用。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以观念性存在为出发点而构建的历史理论,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范式有根本性的联系;但他同时希望用这种理论来为不再存在统治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作出论证。因此,意识形态理论反映历史时总是存在一个不可突破的界限,且唯有历史运动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今天,这个界限才会显现出来,以往在意识形态理论下被掩盖的事实才能以矛盾的方式展示出来。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便在于,由于它以往都是统治阶级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中介,只能在观念的样式中来表现历史的进程,因而当历史发展到需要废除阶级的今天时,它便无法再准确地反映历史趋势、正当地引导人们开创未来。在马克思看来,当下的历史趋势是阶级之废除,是一个唯有在唯物论视角下才可能被看清的事实。
对于马克思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存在,是意识形态发展史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这种特殊既有否定的含义,又有肯定的含义。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般只注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否定的一面,马克思某些不留情面的批评也可能使我们只是片面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没有辩证地理解它。辩证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说根据马克思已有的结论,将其抽象地分为好的一方面和坏的一方面,然后只取其好的一方面,而是要从运动的视角出发理解它,将它理解为意识形态理论矛盾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但不是从黑格尔式的宏大的绝对精神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以当时德国本身的历史状况为基础来理解这个民族特殊的自我认识。
在我们家,家务活儿他只管两样:除了开夜床,就是收拾洗脸池子。说来也怪,为什么我洗完脸,池子边上全是水,他洗完了就一滴水都没有。但凡看见水池子边上湿乎乎的,他就又受不了了,赶紧拿抹布左擦右擦,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跑出来质问我:“咱们这是两个人类在共同生活吗?我怎么觉得是一个人类和一个海豹啊?”
三、费尔巴哈理论的特殊地位
栽植方式有穴植法和沟植法2种。栽植的深度应与移植前保持一致或者稍微浅一些,对于出叶的花卉不能栽植过深,以免出现烂根情况,移植过后不能浇水过多,应等到新根长出后再进行浇水。还应确保植株的通风效果。在遮阴条件或者天气较为干燥时,通过植株喷雾或者喷水的方式促进生根。新移植的花卉重新栽植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萎蔫,停止生长,这种情况是一种正常现象,待新的根系长出以后,将会重新生长。折断时期称为缓苗期。通常为保证花卉的长势,以及园林景观的早日形成,缓苗期越短越好。具体在挖苗时可以通过多带土的方式有效避免伤根,降低对花卉根系的影响,从而有效缩短缓苗期。
第一,不能像阿尔都塞那样,单纯地将历史科学和意识形态分割开来,只看到前者相对于后者的飞跃,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连续。两种理论由于视点、方法等一系列差异,确实在范式上有根本区别。
四、结论
意识形态一般是人类历史现实的一般反映,意识形态中的颠倒源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本源地就发生着的颠倒,即人生产的东西反过来成为统治性的力量。同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处于这种一般性的进程中,但它作为理论上对现实的反映,同时是德国特殊的历史现实的反映。在德国思想家试图对现实作出解释时,他们至少碰到两层矛盾,或两层认识现实的障碍。除了处于必然发生的一般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进程,德国当时还处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即相对于英法两国,德国生产力尚且落后。德国思想家探究本国所拥有的矛盾,就不只是看到在本民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会看到自身民族落后与普遍的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不会将自身意识与普遍意识的差异理解为由现实生产力所导致的差异,而是单纯理解为意识形态间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定民族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3](P30-32)因而,双重的经验界限束缚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他们不仅身处一般性的意识颠倒中,同时身处于相对落后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现实中。于是,他们不仅从抽象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还将这种抽象理解为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的实体,将他们所在历史理解为观念发展不完善的阶段。于是,他们试图仅仅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来弥补现实层面上存在的双重矛盾: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二是德国本身与英法两国的现实差距所带来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理论下被掩盖的事实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对历史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根本要素是社会生产中的物质基础。古典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是不愿去发现这个真理,而是他们不能发现,因为物质性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发展到颠倒异化的程度,阶级斗争也没有发展到普遍对立的程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只有在现代才可能出现、才具有“正确性”的理论。
第二,当看到意识形态理论与历史科学之间的连续进展时,我们更要避免这样一种幻觉,即仅仅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连续性,这毋宁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的复活。它的后果是混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界限、意识形态和历史科学之间的界限。我们不能将在所谓逻辑的必然进程中来考察马克思与先前理论的关系。在这点上强调断裂,阿尔都塞又是正确的。
在传统广场设计中,设计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自身的空间组织及景观设计,依靠自身的空间环境保证广场的活力.但过度关注广场自身空间设计,忽略与周边的联系,很容易形成与周边空间相孤立的独立空间.而这种孤立与自身的空间形态有关,如同中山路教堂广场一样,形态上过于独立的广场空间不但弱化了自身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色彩、降低了空间品质,更阻碍了中山路街区的良性发展.因此,广场设计应该注重空间属性的优化与升华,从空间形态和结构出发,通过对自身和周边空间的控制,加强广场空间与传统商业街区之间的联系.
第三,这是最重要又往往被研究者们忽视的一点。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理论和历史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理论范式上的区别,它们之间也不是单纯经由理论上的逻辑反思而获得连续;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源于现实的、每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关系。
五、结语
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是以这样的关系存在着,它们既不是以黑格尔所设想的以观念连续的方式在历史中递进,但也不是在历史中相互分裂。历史中的理论反映了人类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但这种展望也不得不束缚在生产力规定的视界之中,它们在生产力积累运动的基础上展开。表面上看,它们相互反对、相互分裂,但实质上归于统一,并且均基于现实的基础而与之前的理论相互映照。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新理论出现替代旧有的理论,都不仅仅是观念领域发生的变更,唯有生产力积累进步到一定程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变更才会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努力证明,在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两种一般性的历史理论范式,即古典的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范式,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为转换的中介,并且是在现实历史的进展中实现转化的。
参考文献
[1]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哲学的发生史?[J].学术月刊,2005(11):5-8.
[2]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M].New York:VERSO,2006.
[3]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5-0014-03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007
收稿日期:2019-05-0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6SB0089)。
作者简介:张猷(1983—),男,四川乐山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张红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