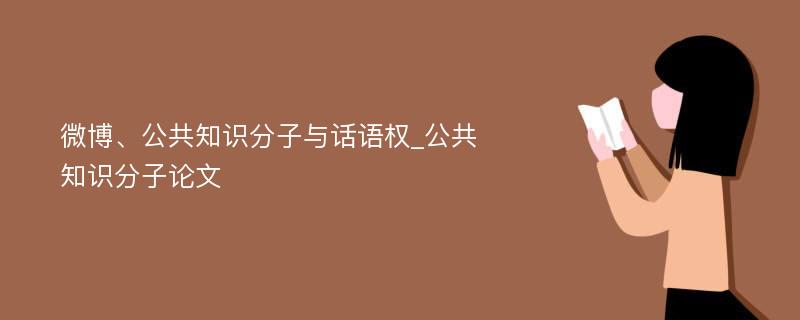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话语论文,权力论文,微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会化网络形式,如论坛、SNS、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2009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社会知识精英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言论,迅速成长为微博空间的新意见领袖。而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包括其公共性表现、影响力、局限性等,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作者的相关研究中,①已经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和前人成果,分析、总结了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和状态;提出并论证了制约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本文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或者说,该如何介入微博,拓展话语空间,彰显中心话语权力,并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建构?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背景
(一)公共知识分子与其公共性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十年来,中外知识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体现出公共良知的一群文化人。显然,知识分子的本义便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②在他看来,现代知识精英的学院化、专业化,正让其“公共”光环面临褪色,因此应强调“公共”两字,借此呼吁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有超越性的批判任务。③
迄今,中国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如陶东风、许纪霖等人,均沿用西方学者的基本界定。④《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也是遵循此标准,即: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⑤当时引发一些争议,甚至招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虚妄的公共性”的批判。质疑关键在于,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谁能未经省察地戴上代表公共利益、具有良知道义的光环?而为便于操作,朱苏力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肯定公共知识分子跨专业的公共事务干涉,强调对媒介的利用;但采用中性价值判断,抽离了褒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意义感。⑥
我认同所谓“公共性”,不仅指面向公众发言、关注公共事务;也蕴含着代表公众利益、批判意识、公共良知和人文精神等多重涵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确实很难有超越阶级、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意识,完全置身于阶层利益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很难苛求公共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纯洁;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普世价值建构及启蒙批判精神,“士志于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环境和传播语境中,我们无法回避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无论中国过去或当代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妨碍我们引用以上界定和标准,来关注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领域的话语权力和公共性身份建构问题。而本文在具体操作上,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指栖身于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人文科学学者;文化媒体人;部分作家、艺术家等。
微博“分享”与“裂变式”传播带来的表达自由,是人们最为赞赏的方面。但有了技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人获得了话语权。在西方政治学研究里,“话语权”(the right to speak)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不受政治干涉的公民享有的自由,是社会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福柯)。而在传播学语境中,话语权是公民自由表达权的一部分,指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空间,隐含着信息知晓权与接近权的前提;更指言语影响他人乃至舆论的“影响力”,即“话语权力”。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成为不同阶层行使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媒介话语权的争夺隐含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话语权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力,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媒介权力。
(二)微博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技术赋权”
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中,“学而优则仕”也是知识分子内在的情愫。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全社会的意识中,一直存有极大的疑问,并非那么习以为常。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作用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开始急剧分化,⑦批判性知识分子⑧处于失声状态;而媒体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二重奏,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虚假繁荣的公共生活。⑨当然,也有一批热衷于公共言说,具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以“公共”加冕,如王小波、陈平原等人。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深远,但人少势弱,而社会对其“虚妄公共性”的嘲讽和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必须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影响和冲击,也会促发社会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我们能够觉察到,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论坛、SNS、博客和微博客等,均是“分权化、去中心化”的媒介形式。它们的兴盛,可称之为一次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意味着公民表达自由权的拓展,大大增加了民主论战和民主干预的可能性和力度。像过去一样简单粗暴的控制信息流动已无可能,这激发了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微博表达便捷、自由与匿名,形成一种随意和不确定性的后台交往模式,刺激了大量原创却是碎片化的内容的产生;借助关注、转发、回复、评论和私信功能等“微型对话”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对话系统。发现与分享的技术理念,形成了微博短小精悍、弥漫式的传播特征。简单来说,全然不同以往的交往技术,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交往场景,进而塑造了相应的交往行为。总之,微博能够促成公众话语表达的“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
从2010年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一个个社会事件借助微博的发酵、蔓延,形成舆论影响力,并最终得到法制和公正的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但民主政治建设仍步履维艰,公民权利仍留于纸面上。而微博的广泛辐射面和深刻影响力,以及调整话语权结构的技术可能性,使人们对其衍生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他们渴望打破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结构,渴望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⑩;期盼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的权利。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领袖化”生存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媒介生存策略和话语权力的彰显,已被置放在微博这种全新的媒介环境当中,进一步接受审视和验证。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目前,微博意见领袖来源多样化,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了它有影响力的主要部分,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综合考察当前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初显。一些具有批判意识、与媒体关系密切的学者,因为与媒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敏感于新媒体科技的力量,自然率先进入,如张鸣、易宪容、贺卫方等人,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和原来传统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网络统计技术所量化的。比如看他的“粉丝”数、跟帖数等指标。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带有多种头衔,如教授、作家、名主持人、主流文化刊物主编等,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
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Baby”在新浪微博上炫富。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达带动了舆论,其专业的解读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再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拥有超过84万粉丝,他在2011年多起公共事件中的言论都受到网友们的关注,“江西抚州爆炸案”、“陈光标慈善注水”、“郭美美”等事件中,他都有转发、评论过千的微博。他在接受《环球日报》(英文版)采访中对“郭美美”事件的评价,被转发19461条、评论4367条,其中网友基本持支持的态度。在现实中,于建嵘是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三农”问题、社会冲突,他非常关注现实中的一些集群事件或公共事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二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不敏感和不熟悉新科技、新领域,回答或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专业知识不够。其次,受到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因害怕“又时时触及讨论红线,只能继续进行‘动态归隐’(mobile privatization)”,“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以儒释为补充的隐逸主导文化下,真正精英型的公共分子的意见领袖很难现身微博。”(11)其三,微博仍是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在微博碎片化和娱乐化的传播机制下,意见抱团和个人崇拜成为常态,而潜在公共知识分子偶尔的见解,极易被淹没在杂碎和娱乐化的信息底层,缺乏广泛的关注;或因不易被理解,而招致误解甚或攻击。因此,不能断言知识分子不关注微博,只是对一件事务的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交锋的产生。公共领域需要文化精英主导,现在看来,微博仍不是一个良好的、能够促成同一知识层面的对话的空间。
三是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目前微博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依托个人和信息的感性魅力,以及他们在诉诸常识中体现出的道德勇气。遗憾的是,当我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微博意见领袖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某种程度上,肤浅的议题设置、对大众极端情绪的迎合、貌似公正公平的观点,是这些意见领袖的传播特点,“伪公共分子”快要成为他们的身份标签。
四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与公众话语主导权的博弈中,可能相互“裹胁”与“绑架”。在一个“平权”、“去权威”、但仍浮躁的言语场域中,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主导权的发挥,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和风险的过程。微博所体现出的自我封闭和集群特征,可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与粉丝群体的相互影响,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或隐忧。
首先,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化”生存,客观上形成了微博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再次中心化”和阶层鸿沟,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草根意愿的表达。其次,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V”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一方面,可能采用迎合性的话语规则和话语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使得意见领袖在公众舆论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感面临考验。另一方面,意见领袖也极可能有意无意地迎合伪公共事件,妥协于集群心理,而成为粉丝的“回音壁”;甚或可能被粉丝群所“绑架”,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从而实际上被削弱了话语主导权。
粉丝个体被群体所“裹胁”,而粉丝群体又与意见领袖相互迎合。这种状态,可能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而对整个微博世界而言,因部落群体的自我封闭,群体间的隔阂与冲突可能会加剧。
三、控制与驱逐:不堪承受之重
公共知识分子受到政商与技术的多重控制,话语空间受制,微博生存环境堪忧。
2011年至2012年初,宋石男、霞葭、连岳、张鸣、于建嵘等五位在网络上人气颇高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先后携带大批忠诚粉丝,出逃新浪微博,转投其他微博网站。张鸣等意见领袖是新浪名人营销战略的重要成果,为新浪微博活跃度做出过重要贡献。对他们的绝然离去,新浪并无挽留之意。从这些意见领袖高调宣称的理由来看,他们主要是不满于新浪的严格审查管理。正如宋石男所言:“新浪微博也与时俱进,它的统治手段富含中国特色的狡黠。”新浪CEO曹国伟曾坦承:“出现敏感话题时,新浪可创造性地限制谈话内容,而不是将其全部删除。”(12)而这种“创造性地限制谈话内容”的手法,无非是在长期审核拖延、劝告等温和手段失效后,采取删帖、屏蔽帖、禁言、删ID等方式。
目前的微博交往,确实有其内在的非合理性,其浮躁交往的种种表现,成为道德主义者攻击的最好口实;而集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冲突,更构成了权力介入微博的极佳理由。从政府对微博的意愿和作为来看(不论其是否热衷于微博施政),都透露出一种强制的权力理性的欲望。如实名制已成为政府机构惰于管理的不二法宝,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屡见不鲜,却难得一见好的效果。虽然,微博实名制在新浪和搜狐等网站中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但北京市于2012年初微博实名的施行,却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不好的先兆。微博等社交媒体是技术经济和商业经济合谋的产物,但媒介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政府定义的“社会效益”。除开外部行政控制,商业控制的“内在化”必然影响着微博自主性及其公共立场。商业力量从来是利润的追逐者,而非建构公共领域的天然支持者,在权力的强力干预外,仅有的支持只能化为无形。
从张鸣等人被迫退出新浪微博等事件来看,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意见领袖仍只能以签约化的方式,遵从权力的意愿,在媒体中讨生活。否则,意见领袖的身份难以确立,影响力难以发挥;更严重的,只能被迫接受违规后的处罚。张鸣等人可以宣称退出新浪微博,进驻其他网站微博,但谁又能保证其他网站会更为开明呢?在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上,公民话语权的获得及话语的分量,只能依靠合理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设计。否则,可以说,作为生活世界的一个新的部分,微博终究如传统媒体一样,逃不掉被系统世界殖民化的命运。而意见领袖仍只能挣扎于传统约束性的媒介评价系统之中,仍只能在半官方性质的媒介旨趣与自我实现的目标之间痛苦博弈。
四、微博凸显“虚妄的公共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如何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有了反省,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得不“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13)。现今的知识界,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激进主义成为生存常态,知识分子对自我公共性的深刻反思,社会对普遍知识分子“虚妄性”的严厉批判,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现实社会中,承受来自多方的攻击和污名,一直是具有公共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的宿命。而微博这一种平权、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更让知识分子所谓“虚妄的公共性”充分暴露。虚妄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的两难境遇:一方面,在开放的网络社会,知识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受制于物质利益、统治权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如采取异常激进的反抗,甚至为了反抗,不惜挑起阶级或阶层对抗,此时,知识分子必然为权力和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极易失去表达自由甚或人身自由。如是,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有意识形态斗争意味的批判。“在统治阶级眼中,知识分子必不可少,却也不可信任;”(14)尤其是批判性知识分子,一贯被斥为消极的空想者和颠覆秩序的破坏者,是虚妄的公共性。(15)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的翅膀被折断,或者寄生在学院体制,或者以签约化的方式在文化企业、媒体中讨生活,甚或直接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时,知识分子确实无颜面对公众对其公共性的质疑和不信任。
除了体制造成的限制外,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使得他们的公共言说常常是畸形的、不成熟的”(16)。而在微博这一众生喧哗的空间中,这种不成熟更为凸显。微博是一种开放空间,内部易形成个体被群体所围观、评论的传播结构,即福柯所提出的“共景监狱”。以意见领袖身份进入微博公共视野的知识分子,只能承受公众的期待、标准、质询、娱乐和愤怒。他们必然暴露自身的稚嫩、脆弱,也注定无法隐藏公共面具背后的一点私利和不纯动机。
公共知识分子正面临公信力质疑,压力成倍放大。有来自网民的恶性情绪宣泄;有对其言说的不理解和误解;更有对其道德、动机和背后利益的揣测。如“专业研究能力不行”;只能“为了名利双收”,而来网上充当“万能知识分子,作秀知识分子”;而“缺乏现实感,理论与实际脱节”、“被利益集团收买”等指责也从未消停。2012年初,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一事,有诽谤之嫌,不仅引发诉讼,更引起双方粉丝在网上的相互漫骂。再如易宪容持之以恒地批判房地产暴利,张鸣一贯批判高校行政化,导致有人做了一些有关他们自身背景的分析及对其道德的质疑。
现在的微博讲坛,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一种磨砺。成也倏忽,败也倏忽。他们可能因某一事件的仗义执言,而一夜间被推上神坛;也可能因其动机被质疑,或者有与体制和权力妥协的苗头,或者有鄙薄底层民众的嫌疑,而一夜间被扯下“公知”的冠冕。2011年底,韩寒连续发出《谈革命》、《谈民主》、《要自由》三篇标题磅礴的博文,引起网络热议,粉丝支持数锐降。三篇短文确实集中暴露了他学养不够、理论不足的短板。至于一些人批判其被“犬儒”了;一些人质疑其文章的立论基础是臭名昭著的国民“素质低下论”等,我认为均值得进一步讨论,也有待观察。
不可否认,有一些意见领袖个体,因在网上发表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也导致意见领袖的网络公信力整体下降。如发表极端言论,挑起个体和阶层冲突;相互粗暴攻击;矫情似的“公共知识分子唠叨”(贺卫方语);甚或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动机险恶地误导公众等。2012年初,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在网络视频上发表对香港人的粗口攻击,损害了北大的声誉,也使公众对网上意见领袖失望感加深。但是,无论如何,个体的不当作为,群体的不成熟,均不应当成为消解意见领袖行使社会责任正当性的借口。
也许,娱乐或其他社会名流可以通过已有身份,获得并保持微博中的光环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这种幸运。他们意见领袖的身份,只能通过其无私的代表公共意愿和利益,才能被公众所赋予;只能凭借其专业与知识,才能被认同;他们的话语权力,只能秉持独立批判精神有所担当,才能获得并维持。反之,已有的光环、自夸的公共性,均只是一种虚妄。
五、坚守传统与推动理性交往
当知识分子因政商的共同压力而被边缘化或主流化,当他们刚刚建立的公共精神和理想信念,被世俗无情地颠覆、嘲弄时,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与人文情怀,已纷纷瓦解。许纪霖曾因此发出一个疑问:“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17)
(一)承接微博技术的赋权
“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8)此时,思考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反思媒体和新技术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传统的西方媒介文化研究无法解决来自非传统媒体的问题,针对西方社会的媒体控制理论也无法解决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讨论媒体文化成为社会启蒙工具的机制,反思新技术赋予和改造人民权力的机制,但不应仅限于此。媒介技术及其创造的公共空间,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质、作用和职责提出了新要求。最基本的,“在当代民主政治中,有效利用技术非常必要。想继续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使用新兴媒体,来参与民主论战、塑造当代社会和未来文化。”(19)
(二)秉承批判精神与道义传统
利益分化、价值多元和思想活跃的时代已不可阻挡的到来;时代需要、并且在呼唤着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中国,各类社会问题极为复杂,非常需要敢于直言、敢于代表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着言论,中国知识分子因此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但我以为,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理应以满怀激情和想象,以知识分子天赋的批判理性的方式,倾情投入这个火热和躁动的时代。承担起启蒙批判的职责,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无法也不能卸下的重担。
微博的技术赋权,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意味着诸多积极的可能性。微博仍是民主政治的新兴推动力量,具有促进民主论战和讨论的潜力,带来了话语权力结构重新布局的可能性。相比传统媒体而言,对微博的权力控制和影响的难度更大。可以肯定的是,微博构成了一个价值多元化表达的空间,用集权制的理想来对待微博及微博时代,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自由表达权终究是时代趋势、人心所向和技术推动。当然,也不能让微博放任自流,去随意消解主流中心性而导致离心混乱;但更不能用专制暴力去消灭多样性来达到一致共同性。
诚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但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绝对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良心和道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良心和道义,这是他们的天性,也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大众的微博交往,正刺激着知识专家走出象牙塔,突破自己的狭小牢笼,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和意愿。
(三)推动公民理性交往
现在看来,微博还远未能构成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在微博空间里,有多元利益的呈现,有相对自由的论争。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领域,但不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社会的理性交往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和培养,有时还需要振聋发聩的警醒。如2012年初方舟子披露韩寒抄袭事件,不论动机是否如方所言,是希望提醒年轻人不要盲目崇拜一个人,事件的客观效果却是我所欣赏的。因为,培养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公民的独立意识、批判与自由意识,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所在。
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无论是代表公共利益、还是天然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感,在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中,一时难以被广泛认同,甚至可能反被污名和指责,这是知识分子必经的磨砺。但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矛盾,自惭于“公共性的虚妄”,而放弃自身的话语权利和职责。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目前最重要的,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交往现实中,交往理性的社会建构仍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
公共知识分子不应以支配者自居,不应恃傲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同样也没有必要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更不能有迎合民粹主义的倾向,将底层民众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抽象地加以美化。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触发议题、引导舆论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微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可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20)也许可以这样说:借助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力量,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进而推动公共领域的发育,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四)身份定位与话语策略的调整
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空间生存的公共知识分子,学科专长、跨领域的博学是必备的素质。仅凭简单的生活常识和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就可以分清是非的时代已过去。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是非观,难以应对异常复杂、人文与技术因素糅杂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纷乱庞杂的微博信息场域中,面对一些维护现存秩序、专业话语背后隐藏私利的技术专家,公共知识分子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支撑,仅拥有一腔浩然正气,是无法与之进行话语论争的,更无法凸显自身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还需要有身份和话语策略的及时调整。
1.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不应放弃普遍知识分子的道义传统,但目前可以作适应社会政治生态和微博场域的身份调整,从普遍知识分子向特殊知识分子的转变,参与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跨过新的千年之后,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尽快适应这种趋势。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面前,把握现实和历史方向感,看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专制政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否则,可能从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会。”(21)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政治视野,正如福柯所言,要求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是作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被压迫者的立场来进行干预。
特殊知识分子“并不预言、承诺某种社会目标,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因而批判、而且是具体的批判,而不是建构尤其是整体的建构成为特殊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方式”(22)。微博技术构成了一种后现代政治的语境,话语权力松散而又具有本土化特征。在这种语境中,微观、中观政治诉求已取代了宏观政治话语。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和空洞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中摆脱出来。因而,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跳出其特定圈子走向微博领域,面向普通大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接受他们的表达赋权;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预社会各领域的活动,多方位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他们的言论和职责可以更具体、更有区域性,可以更设身处地支持边缘性和受压迫群体;在参与民主讨论和辩论中,维护处于具体环境之中的规范观点、价值或原则。当然,也要警惕在国家与市场共谋下,公共知识分子“部落化”之现象,即借口讨论问题的专业化,而放弃或转移问题本身的公共层面剖析及人文关怀。
2.话语表达策略调整
微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赖特·米尔斯,2005)。不仅是社会事务的评议者,也要与优秀的记者一样,充当环境的监视者,拥有触发议题的嗅觉,即能够从纷杂的信息汪洋中,从纷繁的经济社会乱象中,注视到潜在的公共话题,并能够理出头绪。
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从学科专业知识出发引出话题;也可以从现实问题出发,组织思考和言说,但这并不足够;还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知识说得明明白白。在传统的眼光里,无论是张鸣代表的政治学专家,还是易宪容所代表的金融专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阻碍了专家与公众的相互接近和知识对话,阻碍了在微博生存中非常重要的人际吸引力的产生。易宪容一年发表600多篇博客文章,意义并不在于文章的专业精尖,而在于他能够直接面对公众顺畅地交流。
学会使用妥协性的言语技巧。这是由中国民主政治现实决定的。首先需要拥有并维持住一块言说阵地;而正话反说,绵里藏针,打擦边球,是目前环境下言说者必须使用的言语技巧。韩寒发表的《韩三篇》,虽然不大可能经得住严格的学理推敲,但它却把文化界素来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通俗化的表达,由此引发的争议以及是非对错等问题,相对于表达本身,甚至都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也就是说,《韩三篇》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韩寒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改革、民主、自由等重大问题推进到了更广阔的公共话题空间中。
总之,在人类社会内部,权力控制欲与公民怀疑心同等顽强,而表达自由是公民制约权力、控制权力欲膨胀的有效手段,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和保障力量。为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公民中的知识阶层,理应运用包括微博在内的媒介手段,自我赋权,自我救赎。这其实是需要勇气、知识和理性的行为。
六、结语
当今,一批知识精英积极回应媒介技术的赋权,以意见领袖的身份栖身于微博空间中。他们的行为也许并不成熟,动机也并不那么纯洁。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个群体正努力发挥着批判和道义精神,构建自身的公共性,争夺与彰显中心话语权力。在一个“去权威”、“去中心化”、但仍欠缺理性的交往场域中,意见领袖话语主导权的发挥,是一个重新中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的过程。
在形式上,微博有一种外在条件和潜在可能,即成为意见领袖发挥公共精神、引导社会价值共识形成的空间。现在看来,仍存在许多现实阻力。这是因为:微博目前还是一种浮躁的交往空间,其自净机制存在与否,或能否发挥功效,还有待观察;并且,权力体制和商业体制正作为系统性的力量,逐步扩张于此空间。借用台湾时评人张铁志的话说,“知识分子从公共领域撤退出来,是件危险的事情。”(23)也许,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上的表现并不成熟,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个体的不当作为,群体的不成熟,均不应当成为消解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性、批判精神和道义责任感的借口。
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急需公共知识分子的警示和指引。在唾沫横飞的微博世界里,公共知识分子就像是中国言论发展道路上的冉冉新星。他们以自己专业、理性的话语,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公民素质和人们对信息的辨识度,指导了一些公共事件的解决。他们的微博话语虽然零碎,话语价值也达不到振聋发聩的程度,但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了公共话语讨论的空间,引领与推动着公民的理性交往,使得构建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有了可能。
“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24)与体制的妥协、融洽,并非真正知识分子的应当作为。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我们钦佩和赞誉当代知识分子在微博领域作为的方面,不是他们知识的渊博、专业的娴熟,而一定是此时他们表现出的良知与道义担当。
注释:
①李名亮:《现实与隐忧:微博意见的话语权力》,《今传媒》2012年第5期。
②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再如孙立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理想、批判、分析;马立诚认为,他们维系着社会的主要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徐友渔、许纪霖等学者均直接沿用三个层面的内涵。
⑤《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
⑥《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⑦《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是葛兰西(Gramsci)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经典划分,统称普遍知识分子,即相信有一种普遍的真理和知识的存在,并且热衷于扮演先知般的预言家,指导人民往什么方向走,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是福柯所创造的概念,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对应。
⑧《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公共领域与批判性知识分子》,李卉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从对权力迎合、妥协的立场角度,道格拉斯·凯尔纳也将知识分子划分为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和谐性”知识分子。
⑨《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⑩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11)余晓冬:《微博对“公共领域”复兴的解构》,《南风窗》2011年第2期。
(12)宋石男:《我为什么离开新浪微博》,《搜狐评论》2011年7月22日。
(13)蔡翔、许纪霖等:《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
(14)(19)[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公共领域与批判性知识分子》,李卉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5)吉方平:《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5日。
(16)(21)(24)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
(17)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田磊:《微博:新技术的美妙与危险》,《南风窗》2010年第26期。
(20)汪凯:《要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要公共领域》,《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4期。
(22)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张铁志:《台湾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时代周报》2011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