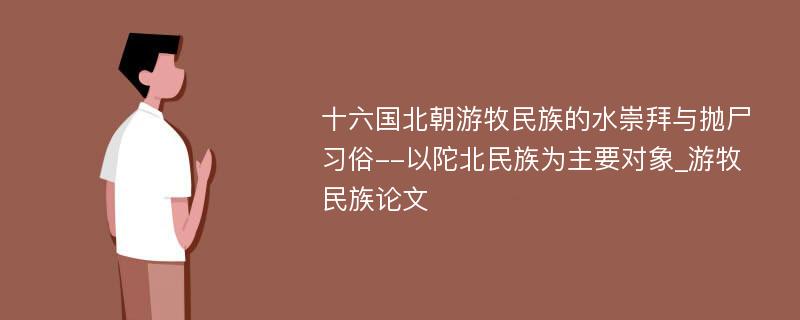
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水崇拜与投尸入河习俗稽释——以拓跋卑族为主要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游牧民族论文,习俗论文,崇拜论文,拓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3-0107-06
十六国、北朝时,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将被杀死者的尸体投入河流中。如《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载,羯族暴君石虎杀死太子石宣的“妻子二十九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在羯族建立的后赵统治时期,出现了荧惑守房的天文现象,大臣赵揽说需要杀姓王的大臣来禳厌。石虎于是选定了中书监王波,“腰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荧惑之变”。《魏书》卷99《乞伏国仁传》鲜卑族的乞伏殊罗与其父乞伏炽磐的左夫人通奸,遭到部落首领乞伏暮末的批评;乞伏殊罗怀恨在心,便与叔父乞伏什寅谋害乞伏暮末,但没有成功。乞伏暮末大怒,将乞伏什寅的肚子刳开,“投尸入河”。
又,《北史》卷39《房法寿传附房豹传》载,慕容鲜卑族的慕容绍宗“自云有水厄,遂于战舰中浴,并自投于水,冀以厌当之”。房豹制止他,慕容绍宗笑道:“不能免俗,为复尔耳。”《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北齐文宣帝高洋末年,猜忌追忿大臣高隆之,于是诛杀高隆之的儿子高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北齐书》卷28《元晖业传》:元晖业,北齐天保二年被文宣帝高洋所杀,高洋命人“凿冰沉其尸”……
从正史中涉及这一现象的部分史实看,所涉民族包括当时的羯族、拓跋鲜卑、慕容鲜卑、秀容胡以及鲜卑化的汉人;所涉习俗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盛行期:后赵中后期、拓跋政权的初期、北魏末期与北齐前期。这种在空间上涉及当时北方几个主要游牧民族、在时间分布上呈现三个盛行期的特点,是否蕴涵着什么?它与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的汉化、胡化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并未加以注意,因此本文选择兴起于今东北嫩江流域、传世文献资料较多的拓跋鲜卑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试着对此做一论述,以求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
一
游牧民族生活的特点之一是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渔猎生活。《魏书·序纪》就称当时的鲜卑族“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称吐谷浑“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另外,如柔然,“无城郭,随水草畜牧"〔1〕。突厥族,“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2〕。游牧民族的这种逐水萆而居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并非易事。以拓跋鲜卑为例,在什翼犍执政时,他曾打算在灅源川建筑城郭,设立宫室,作为鲜卑政权的首都。对此,部落大人们久议不决。为什么呢?太后王氏的话揭示了问题症结所在,她说:“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3〕大意是拓跋鲜卑迁徙惯了,过定居生活尚缺乏必要的物质与心理准备,因此部落大人们才犹豫不决。直到明元帝拓跋嗣时,拓跋鲜卑的迁徙生活才有所改变,《南齐书》卷57《魏虏传》将此概括为:“什翼珪(即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即拓跋嗣)始土著居处。”
在游牧民族的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渔猎是必不可少的。渔猎在拓跋鲜卑早期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鲜卑族在檀石槐执政时期,由于“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4〕。其中所谓的进攻汗国,掠得擅长捕鱼的渔民,《通典·边防十二·北狄三·鲜卑》载为进攻倭国,掠得会用网捕鱼的倭人。考虑到鲜卑的航海技术,杜佑的记载恐怕失真;但他说鲜卑掳掠的是会用网捕鱼的人,应该是对的。因为较之原始的叉鱼,用网捕鱼已是比较先进的了,随着鲜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多,他们捕鱼能力与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应是事实。这还可以从元坦身上得到验证,史称他“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禽兽,春夏捕水族,……器网十余车”〔5〕。“畋渔”、“器网十余车”表明其捕捞自然是网捕。元坦的爱好捕鱼,只是拓跋帝王爱好渔猎的一个例子。前期的拓跋帝王对打鱼捕捞都很感兴趣,《魏书》诸帝纪中记载了不少拓跋帝王观看捕鱼的事例,如天赐五年(408),道武帝拓跋珪到参合陂,“观渔于延水(今源于内蒙古兴和县的东洋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临去畿陂(今河北张北县安固里淖)观渔”;神瑞二年(415),拓跋嗣又“幸去畿陂,观渔”;泰常四年(419),他又“观渔于灅水(今河北遵化县沙河)”;和平三年(462),文成帝拓跋睿“观渔于旋鸿池(今内蒙古丰镇东北)”。这些都可以形象地看出当时渔捕的热闹场面。当时的拓跋鲜卑还将捕捞来的鱼的骨头制成各种装饰品,在被认为是鲜卑遗迹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札赍诺尔墓群的发掘中,即从M29中出土了鱼肋骨制成的骨簪32根、鱼椎骨钻孔的串珠5个。这些装饰品原先摆放在女尸头骨边侧。〔6〕这些出土文物进一步佐证了拓跋鲜卑生活中捕捞活动的存在。
拓跋鲜卑初期所建政权上层政治建筑中存在的“以鸟名官”现象,间接反映了生活于水草丰美之处的游牧民族的渔猎活动。《魏书》卷113《官氏志》对此记载得非常生动,说拓跋初期帝王在官制方面,“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意。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比,咸有比况”。显然,所谓拓跋珪“欲法古纯质”、“不依周汉旧名”,不过是史臣曲笔讳言之辞,其实际情况即是野蛮时代的“以鸟名官”。而拓跋珪之所以会用凫鸭、白鹭等水鸟来作为官号,即在于水草丰美之处不乏此类水鸟,都是他们渔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水禽。这一点还可以从拓跋鲜卑初期帝王出行时用的大驾卤簿的阵势中得到佐证:最初,拓跋帝王出行用的是“鱼丽雁行”阵,即俗称的鱼贯而行和大雁飞行时的“人”字型队形;直到天赐二年(405)年初,拓跋珪才“改大驾鱼雁行,更为方阵卤簿”〔7〕。前后卤簿行阵的不同,既折射出渔猎经历对早期拓跋统治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又体现了其开始步入汉化生活的趋势。
二
当时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所有游牧、渔猎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自然前提——丰美的水、草。水草丰美之地是游牧民族最向往的地方,而失去这样的牧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刻骨铭心的疼痛。汉朝时,河西走廊的祁连山、燕支山,“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长期生活在那里;后来西汉军队占领河西走廊,匈奴痛苦得很,乃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8〕水草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这是汉朝时游牧民族的情况,但在自然条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活动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羯族、氐族、鲜卑族、秀容胡等游牧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他们对于水、草的重视与匈奴族一样,不分伯仲。在水、草二者之中,水更是重中之重,可以说“只有水才是接近干燥地区的中国北部诸人文景观展开的基础条件”〔9〕。没有水,就没有了牧草的生长,自然就没有了游牧民族的畜牧与渔猎,更毋论种族的生息繁衍了。因此,他们对水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我们不妨称之为水崇拜。林惠祥先生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一书的“自然崇拜(Nature Worship)”章中即说:“人类感觉他的周围有种种势力(powers)为他所不能制驭,对之很为害怕,于是设法和他们修好,甚至希望获得其帮助。人类对于这种种势力的观念自然也依环境而异;平坦的原野自然无山神,乏水的地方自然无水神……”;“森林中的居民以林木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尤常以树木为崇拜的对象。”〔10〕同样的道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以水为崇拜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南齐书·魏虏传》即称:“胡俗尚水。”这种水崇拜的烙印深深刻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许多层面上。
(一)春季水上交欢婚配。鲜卑族初期,在繁衍后代的男女结合方面具有浓厚的水崇拜习俗。《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曰:“(鲜卑)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鲜卑族的这个风俗,《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狄三·鲜卑》载为“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然后配合”。尽管两处史料所载鲜卑嬉戏于其中的河流名称小有歧异,但都是讲鲜卑族在春天时,于水滨嬉戏交欢,以繁衍后代。这是毫无疑义的。鲜卑族的这种水滨交欢习俗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他们对水的虔诚与崇拜。
(二)水滨祈祷天神。《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称突厥:“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表明作为游牧民族之一的突厥族有在水滨聚会祭天的习俗。鲜卑族同样有着这样的信仰。如始光四年(427)五月,太武帝拓跋焘西讨赫连昌,“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11〕,体现的也是在水滨祈祷神灵保佑的习俗,与突厥之俗有殊途同归之妙。其他的拓跋族大臣身上也能见到这种习俗的影子:北魏孝文帝患病,彭城王元勰,“密为坛于汝水之滨,……告天地、显祖请命,乞以身代”〔12〕。我们将元勰的做法与有着同样祈祷背景的汉族大臣崔浩的做法比较一下,就几乎可以断定元勰所行的是鲜卑族习俗。史称崔浩的父亲病重,崔浩于是“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13〕。都是祷告神灵,祈求以自己的健康之身来代替尊长的病体,使尊长早日康复。但元、崔二人祈祷地点却是不同的,元勰是在“汝水之滨”设立神坛,祈祷天神以及亡去的先皇保佑;而崔浩则在家中的庭院祈祷北斗。崔浩所用的方法自然是汉族的传统祈求方法,这在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即有记载,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意思是说,南斗神负责人的生,而北斗神则负责人的死;人在投胎前,要先在南斗那儿登记,死后再到北斗那儿注册,等待下一个轮回。活着时有什么请求,都要向北斗星神祈祷。结合拓跋焘在黑水滨祈祷先祖亡灵保佑自己的做法,我们断定元勰所用的祈祷习俗,是不同于汉族传统方式的祈祷,是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祈祷方式。
(三)在心理上,将赖以生存的河流的丰枯同政权的兴衰直接联系起来,视河流的突然干涸为政权衰亡的先兆。《魏书》卷95《徙何慕容廆传》载,慕容鲜卑的慕容德时期,女水干涸,慕容德“闻而恶之,因而寝疾”;他的侄子慕容超建议他向女水祈祷。尽管此事发生时,南燕慕容鲜卑政权已经迁居汉族农耕地区,但慕容鲜卑所曾具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惯性,尤其是水崇拜的惯性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们。
三
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以及基于此而生成的水崇拜,那么在游牧民族中出现投尸人河习俗就并非突兀之事了。《魏书·序纪》追溯鲜卑族的起源时说:“(黄帝的小儿子昌义)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虽然这类追述往往是攀附瞎说,但其中所谓的鲜卑先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却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女魃是旱鬼,《魏书》史臣在追溯拓跋鲜卑祖先时为什么要攀附始均驱逐女魃——旱鬼的事迹,而不去攀附其他的人或事呢?假若我们将此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联系起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旱灾对严重依赖水的游牧民族来说,几乎就是灭顶之灾。①所以,对于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魏书》史臣的这个追溯具有普遍适应性,至于是否确指鲜卑族并无妨大局。下面
-----------------------------------
① 比如汉代的匈奴即曾因为旱灾而饿死大批的牲畜和人口,实力遭受重大打击,见《汉书·匈奴传》;这与定居农耕的汉族有所不同,汉族已经能利用修筑陂坝、漕渠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摆脱或削弱了旱灾的影响。
-----------------------------------
我们就来看一下,《魏书》史臣的这个关于鲜卑族起源的追溯,究竟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投尸入河习俗有什么关系。
首先,《魏书》史臣的这种追溯,表明至少在拓跋鲜卑族中存在鬼魂的观念。其实,各民族中鬼魂观念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各民族常有鬼魂旅行的神话,……鬼魂不一定都到鬼世界去,有时也杂居人世,大都滞留于其生时所住地的附近,或尸体所在的地方。杂居人世的鬼魂常为人所惧怕而恐其作祟”〔14〕。在拓跋鲜卑族中,鬼魂游荡信念是存在的,这可以从拓跋鲜卑的一些祛鬼仪式中得到间接的反映。如为了避免鬼魂游荡作祟,他们同汉族一样,也经常举行“傩”。如《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北魏孝文帝时,“诏罢腊前傩,唯年一傩”。此时傩的次数的减少,反而表明在此之前拓跋鲜卑“傩”的次数是很多的。而“傩”就是驱除游荡于世间的疫鬼的仪式。同书又称北魏“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自然也是驱鬼辟邪的民俗。
其次,可以由此间接明了当时的鲜卑族是接受了将旱鬼——女魃囚溺于水以避免旱灾的信念的。《魏书》虽然毕功于北齐魏收之手,但所用材料多为前人所著,加上北魏前期出现了著名的“国史案”,北方大族多被牵连诛杀,因此著史者轻易不敢“暴扬(鲜卑)国恶”。而这即意味着魏收修《魏书》所采用的前人所撰相关材料——包括对鲜卑族起源的追溯——是曾经得到拓跋政权当局认可与共鸣的,意味着拓跋鲜卑是接受旱鬼的观念的。这是拓跋鲜卑对旱鬼信念的接受,至于将旱鬼——女魃囚溺于水以避免旱灾的信念,在《文选·东京赋》里有这样一段话:“捎魑魅,斮獝狂。斩矮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注云:“耕父、女魃皆旱鬼。恶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为害。”〔15〕这段史料表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将旱鬼囚溺于水中使其不能为害的信念了。而通过本文最初的分析,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生息繁衍与水紧密相关。旱灾自然是最可怕的灾难了,因此将造成干旱的旱鬼囚溺在水中以避免旱灾的信念在他们中应当很有市场。要不,北魏史臣在追溯鲜卑始祖及其事迹时,就不会津津乐道于所谓的鲜卑先祖祛除女魃的故事了,魏收自然也不会照本宣科,予以抄录。
既然鲜卑族有鬼魂游荡观念,有着浓厚的水崇拜习俗,又接受了囚禁旱魃在水中以避免旱灾的信念,那么在历史的发展中,这种囚溺鬼魅于水中的习俗在现实生活中被泛化,成为一种广泛施行的祛除方法,应该不是武断之论。前引慕容绍宗在战舰中沐浴、自投入水的例子即是这种以水祛除不祥习俗的反映,而慕容绍宗称此举为“不能免俗”,则表明此时以水祛除邪气已经是他们所接受的一种习俗了。这是将旱鬼囚溺于水以避免旱灾的习俗泛化的一个例证。另外,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即认为非善终者的鬼魂会作祟,因此他们便将这些非善终者水葬——将其尸体投入河中。如藏族、傣族和独龙族,对于不能善终者,即用水葬。〔16〕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投尸入河的事例如此之多。
总之,以当时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投尸入河习俗,实际上是一种缘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隔绝旱魃的泛化风俗,目的在于隔绝非正常死亡者的魂灵,以保平安。
四
十六国、北朝游牧民族投尸入河习俗的盛衰进程,是一条变化的曲线。在本文开始时归纳了当时游牧民族投尸入河的三个盛行时期。后赵在石勒时期锐意汉化,清定九品,兴办儒学。羯族本身的习俗表露的不多。但到了后赵中后期,原先掌管胡羯六夷事务的石虎在位其间,投尸入河的例子却多起来。显然,这种习俗的盛行似乎与胡化有关。而拓跋鲜卑,从魏孝文帝开始,先是拓跋帝王行幸之滨的活动越来越稀少了,这固然与其生活地域的变迁有关,但在新都洛阳所在的河、洛之滨也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了,这更多的是缘于他们水崇拜的相对减弱。同时,拓跋鲜卑祛除鬼疫的方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南齐书》卷57《魏虏传》记载魏“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由“城门”一词可知他们一定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而由“岁尽”在城门举行祛除仪式可知他们是长年居住在城里的,已非逐水草而居了。一句话,这已经是筑城定居以后的事了。那么拓跋鲜卑的祛除仪式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当时荆楚地区岁末年初的风俗时说:“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可见在岁末年初杀鸡、悬挂苇索桃梗之类来辟邪是汉族的古老风俗,而拓跋鲜卑也采用了这种辟邪习俗,所以《南齐书·魏虏传》才称拓跋鲜卑的这种祛除仪式是“汉仪”。一言以概之,这是北魏孝文帝汉化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此时已经鲜见拓跋鲜卑投尸入河的习俗了,这与拓跋政权初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的拓跋政权保留了较多的本民族特色,投尸入河例子也很多。
与北魏孝文帝时期致力汉化的方向相反,到了北魏末年、北齐前期则是在不停地鲜卑化与西胡化了。鲜卑化的北齐贵族极力反对汉人和汉化的胡人,并在生活上日益“西胡化”,沉湎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已故的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湛的论述,此不为赘。〔17〕而据本文前面胪列事例,北魏末期与北齐前期,恰恰又是投尸入河例子多而且集中的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投尸入河习俗的盛行与淡化又成为汉化与否、汉化程度深浅的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