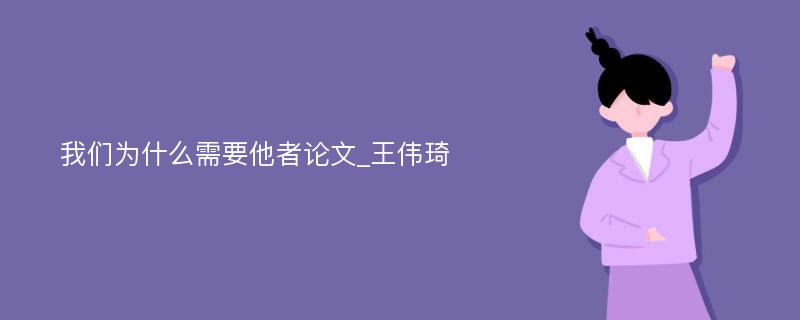
——伦理学视域下人的境况
王伟琦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人是社会性动物,生活于人群之中。从两性生殖,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必须依赖他者的支持。然而,由于人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私本性,使得人在生活实践中经常罔顾他者的利益,对社会群体造成伤害。本文试图从伦理学常识出发,阐述“他者”的重要性,以及应当如何与“他者”和谐相处,收获内心的幸福。
【关键词】:利己 竞争 联合 幸福
引言:人世间有光明和温暖,也有残酷和苦难。从古代到近代,历史的粗线条由暴力书写,在古代,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无数人在战争中喋血;在近代,为了宰割天下,各大强国卷入世界大战,生灵涂炭。嫉妒,是一种恨,它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放出了人性的恶,让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为祸人间。没有和平,就没有幸福安定的生活。
一、竞争的必要性及不足
竞争是必须的,也是正当的。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雄性通过竞争取得与雌性的交配权,胜利的一方拥有更强壮的身体素质和更良好的基因,保证了下一代的健康。森林里的树木为了争夺阳光而奋力向上生长,使得树木挺拔茁壮。良性的竞争环境,使得种属的优良品质得以保存和发展。
从人类社会来说,竞争是人的“自然权利”。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由于资源的相对匮乏,许多人同时想要一样东西,这件东西既无法被共享,也无法被分割,其结果就是通过竞争,由价高者得到。这种竞争是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同一的。竞争机制的存在,是人类强大和有活力的重要保障。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被允许拥有万物及做任何事情。但是,“人拥有这种共同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权利所产生的后果与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是一样的。虽然人可以对某物说“这是我的”,但他并不能享有他,因为他的邻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声称拥有一切。这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对抗”。[1]权利与权利的对抗形成了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中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缺乏信任,互相猜疑,生活不稳定,对未来没有可靠预期。在自然状态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没有是与非,任何事都无所谓公正不公正。正是对争斗的暴力造成的死亡恐惧唤醒了人的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死亡作为公敌,迫使人们达成共识,建立信任,实现联合,使他们为了对付这个公敌,保障尽可能的长治久安”。
二、从物质和精神,与他者联合
休谟的《道德原理探究》中,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中进行考证,论证利己与利他统一的基础。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者。尤其是在商业社会中,社会分工的精细,每个生产者不能仅以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而必须依赖其他生产者。[2]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论述到,由于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每个人只能专职于某一职业,因而人们的绝大部分生活用品需从社会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共同资源中购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3]个体依赖于群体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人只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是天然必然性的。人要生存必须劳动,劳动必须合作,合作创造利益”。“人们在生产中同自然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人所特有的劳动产生了人所特有的社会性”。
社会资源除了极度稀缺的自然资源以外,绝大部分是由无数个他者生产出来的,无数的他者既是消费者,更是社会资源即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离开了无数他者的帮助,个体的人很难生存。个人离不开他者,即是离不开社会,个人的兴旺发达仰仗于社会的繁荣昌盛;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的一份子,亦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不论我以什么为业,社会中若干成员的财富可以有助于增加我的财富;他们消费我所生产的东西,而以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给我作为交换”。(休谟)“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人只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个体依赖于群体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表现。
群体生活要求以合作为基础有序地进行,群体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包括利他性道德在内的行为规范的保证,因此,人的利他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社会性的客观要求”。我们强调利他,不是像圣人那般毫不利己,而是倡导温和的利他。人的交往是以一定的利他心为基础的。温和的利他心可以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使社会和谐融洽。利他心的培养和倡导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形成,因为适时适当地考虑各类人群的利益就不会形成一个严重偏颇的社会。[4]“我们不只重视自己的幸福和福利,同样必须赞扬正义和人道的习俗,因为唯有它们才能维持社会的联盟,每个人才能收获互相保护,互相协助之果”(休谟)人的交往也是以一定的利他心为基础的,所谓“以其无私成其私”,就道出了人与人交往的这一法则。
在精神生活方面,个人同样离不开他者。不可置疑的是,人的精神上,心灵上的需求是在对象化的行为中才能得到满足的。[5]斯宾诺莎用生活经验作为参证来解释人的社会性,说明人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而必然追求社会生活。[6]“人不是一出生就带着镜子的,只有以他人为镜才能照出美丑”(马克思语)社会以及社会中形成的道德准则是个人赖以对照,不可或缺的镜子,是一切情感的来源。当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再多的物质也不一定会增加更多幸福,反而当他的行为能最大程度地带给别人幸福时,他的心灵会得到极大的满足感。所以,人的高级而持久的幸福是在与他人的交往或对社会的行为中才能得到的。人际关系中的交往性是人具有交往需要的体现。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互相帮助,礼尚往来而富有人情味。在交往中各个个体的不同需要交互作用,使人们在思想观念和情感情绪方面的共同性逐渐形成,使个体感到,他的快乐,幸福,荣誉等于自己与他人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7]这种感受的一致性,就是“同情”。同情是人们之间一种情感共鸣,其实质也就是一种同胞感。同情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感应之情。所以借助同情,在自己心中引起痛苦或快乐的情感,对某种行为产生厌恶或爱好的情绪,这种产生于人们之间广泛的情感,就是道德感。同情就成了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即仁爱。[8]如果个人想得到更多的心灵满足和更完全的幸福,得到来自社会的仁爱关照,就要对他者付出仁爱关照。利他心是社会仁爱道德形成的心理基础。
三、自然,一个被遗忘的他者
前面谈论的个人对他者的需要,不管物质还是精神,都是功利的,有所图的。他者,不仅仅是我们利用的对象,更是我们的朋友。他者,既包括人,社会,还包括一草一木,大千世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莫非看起来不能被我们所利用的人和事物,就没有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在这个精神匮乏的当下,这个问题很值得谈谈。我们需要他者,不仅仅是人类的他者,还有自然意义上的他者,即大自然。我们所谈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从功利角度的利用层面,更包含精神境界层面的需要。在《我与你》一书中,奥地利宗教家、哲学家阐述道:“以万物为认识和征服对象的活动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不在于物我隔离的主客关系式,而在于万物一体关系的感悟”。[9]
人所生活的世界,具有双重性,一是“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布伯用“我——它”的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的公式称谓后者。在“我——它”范畴中,“主客间的隔离便建立起来了”。一切他者都只是为维持自身生存的被利用的对象。但是,万物只是我们的对象吗?以万物为认识对象和征服对象的活动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吗?布伯认为:仅仅按照“我——它”公式把一切都看成是“它”(物、对象)而生活的人(我),是只有过去而无真实现在的人,一个人如果满足于把事物当成对象,满足于在经验中认识事物,那么他就只能生活在过去,因为物、对象总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这样的生活是空虚无意义的。斯宾诺莎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财富、荣誉等世俗事物和感官享乐所带来的快乐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把这些作为人生目的,他的心灵就无法达到宁静,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10]它们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不是幸福本身。幸福不能建立在转瞬即逝的东西之上,这样的幸福是不稳固,不牢靠的。幸福不只是一时的感觉,而在于一直持续下去的满足的状态。因此,斯宾诺莎认为,幸福之路存在于理性完善中。人作为他所依赖的同时也是控制他的自然的一部分,要领悟的是永恒必然的自然秩序,是心灵与自然融合一致,人生方能达到至善的幸福境界。唯有对理智进行改进,完善,人才能达到理智与情感,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才能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升华到人的永恒性;才能产生洞明一切,安详深邃的幸福感。唯有这种由理智的完善而产生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那些生活在“我——它”中的人,是将幸福等同于感官享乐,幸福离不开感性需要,但幸福不止于感性的满足,更在于人对必然性的认识和理性力量的充分体现。
人,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理查德昆布兰看来,个人与全体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幸福不能与全体人的幸福分开。整体与结合为整体的各个部分没有本质的区别。同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观点认为,宇宙内只有一个实体,它是“神”,或叫“自然”,是宇宙中唯一无限的存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只不过是“神”的样式,表现为事物的系列和观念的系列。那么,“人”作为“自然”或者说“神”的一部分,理所当然是“神”的感性显现,体现的是“神”的样式。“自然”或“神”作为宇宙唯一的实体,按照自己的本性的绝对必然性存在和动作。这和布伯的宗教观点非常相似。布伯认为,世界万物本来都处于“我——你”的相互关系中,都是相互回应的,就是“一气相通”,是一种“自然的结合”。“我——你”是一个整体,“我——它”是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的形态。“我——你”的世界强调的是“关系”,这“关系”及其“相互性”,就是“仁慈”。布伯的“你”,就是“神”,是“自然”,是“人的理性”。唯有它们才是事物的本真,是永存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无论人还是万物,都在“你”的光照下,作为语言显现。要读懂“你”的语言,需要的是“仁慈”。“仁慈”是钥匙,是通道,透过“仁慈”,万物显现出永恒的本性,通过“仁慈”,可以与“你”相遇。只有在“我——你”中看待世事,事物和世事才不是过去式的,而是“现在的”,指在相互关系中永恒现存的东西。对于在“我——你”关系中生活的人而言,世事或事物是永存的(现在的),人生的意义是充实的。
“我”和“他者”一样,都是神意的显现。通过“仁慈”,我们走进关系的世界,与“神”相遇。能直观到“神”的人,认识自然的永恒必然性,从自然的整体角度看问题,不会被情绪控制,心灵便会变被动为主动状态,因此有自由的精神境界。一个认识一切,看透一切的人,所谓的必然性并不能吓住他。他会敢于面对它。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会用自己的力量竭尽所能,对结果处之泰然,他有超越必然性的力量。
结束语:
我们需要“他者”,不仅仅是出于物质生活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还因为只有超出“我—它”的思维模式,进入“我—你”的思维模式,人生才不是无常的,空虚的,才是有永恒的现实意义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学习和欣赏“他者”,因为万物是一体的,认识“他者”就是“认识你自己”。
注释:
[1]李庆钧《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霍布斯政治学说基础分析[J]
[2]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M]P229
[3]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学思想史》[M]P243
[4]宋慧《利己与利他——从亚当斯密问题入手》[J]
[5]宋慧《利己与利他——从亚当斯密问题入手》[J]
[6]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M]P170
[7]韩昌跃《利己利他双重人性论》[J]
[8]于斌《对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探析——从仁爱到友爱》[J]
[9]张世英《人生与世界的两重性——布伯《我与你》一书的启发》[J]
[10]仰和芝、张德乾《试论斯宾诺莎的幸福观》[J]
作者简介:王伟琦,1990年4月22日出生,女,汉,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硕士,黑龙江大学,西方伦理学
论文作者:王伟琦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7/10/9
标签:社会论文; 幸福论文; 自然论文; 自己的论文; 的人论文; 万物论文; 的是论文; 《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