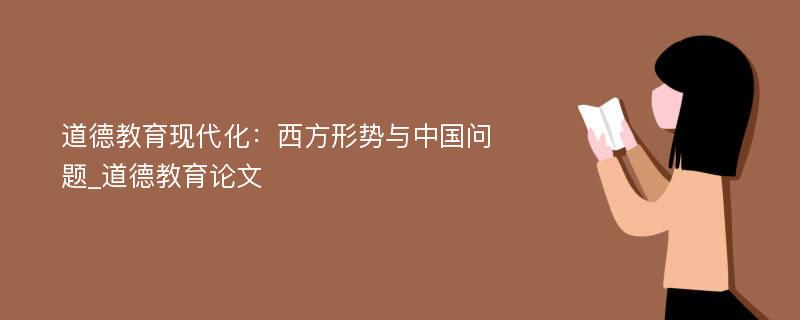
道德教育的现代性:西方的境遇与中国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道德教育论文,境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些人认为,道德教育在当代出现了困境,并把它的原因归结为工具理性或市场时代的多元价值的冲击,归根结底就是,现代性自身的危机给道德教育带来了危机和困境。但是,人们常说的现代道德的危机和困境是比较古代性而言的,道德教育的问题也是就现代性而言的。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道德教育在古代是否存在困境?或者说,道德教育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即,道德是否可经由学校(或社会,这里主要谈学校道德教育)教育获得,在何种意义上它可以获得?如果道德教育在古代不存在困境,那么,现代道德教育的问题就可以在比较中找到解决办法。比如重建道德体系以应对多元价值的冲击。如果道德教育自身存在问题,即在任何时代都有困境,那么,道德教育就需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困境:一种是通常说的道德及其教育的现代性境遇下的困境,一种是背离现代性境遇所产生的困境。
道德教育的困境在古典作家那里就有提出。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过“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究竟是否可教,苏格拉底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是否是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呢?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说过,美德的获得是偶然的。尽管是偶然的,但毕竟需要通过教育而获得,并非指天生就有的。但在《高尔吉亚篇》和《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又怀疑美德的不可教。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国》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哲人的,一种是大众的或政治的;在《高尔吉亚篇》中也有,智者的声音就是代表政治社会的。两种声音的安排体现了柏拉图的写作意图。施特劳斯认为它表现了一种“隐微术”,即柏拉图的写作体现了高贵的谎言与真理,也即显白的教诲与隐微的教诲。[1]按照这种说法,“美德是否可教”就意味着存在一种道德谎言或虚构,即美德或许对大众而言不可教,但又不得不对大众隐藏,并且还要以高贵谎言的手法说美德可教。柏拉图说的“人人可以至善”就是显白的教诲。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隐藏自己的声音,他把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并认为前者可教,后者经由习惯而养成。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明习惯的养成时限问题,事实上习惯的养成总是一个持续而无终结的过程,因而不能用一时的状态表明某种道德品质的具备,因此,他所说的“习惯养成”表明了道德教育的难题。此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德性的养成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说的,他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在哲学上对美德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他是在非哲学层次上(柏拉图的《法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是在这个层次上)探讨政治城邦的德性教育。因而,亚氏的德性(政治德性)教育探讨是针对“贤人”而非大众,大众的德性教育问题不得而知。
道德关涉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古典作家立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现代性作家立足于人的规范下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从美德与规范两个角度看,道德教育都存在自身的难题。一种被召唤的美德总是与人的德行存在差距,人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与人事实上的品性同样存在差距,人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与人的实际道德行为也有差距。因为美德或人性的卓越总是偶然性的表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一种抽象的和静态的要求,且它并不必然总是体现为道德正确,人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普遍的规定,它必然与人的道德行动的偶然性存在背离。所以,道德教育自身的难题总是存在的,而不是因为现时代的变化才出现困境。如果把道德教育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境遇,归因为市场时代和工具理性,必然寻求一种返回前现代或古代的思路,或者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但事实上这种思路拯救不了现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人性往而不返,科学或许带来了人的不幸,但人不可能再回到自然状态。即便科学或哲学不走向大众,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教授邪恶或把真理公布于众,道德教育问题依然存在。恰恰是哲学与洞穴的分隔,表明德性卓越的偶然性,以及大众的道德习俗生活的必要性。
道德教育自身存在的困境与人性假设问题密切相关。道德教育存在着一个人性的假设,即人性有善与恶之分,道德教育就是要抑恶扬善;如果人性无善恶,或者人性无法向善,道德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古典作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但是否走向卓越则只是一种可能,柏拉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样板:霍布斯等人认为人性是恶的,他们放弃了人性卓越的追求,相信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础上的社会更为稳当。不管人性如何假设,人性走向卓越没有普遍的规律,人性的卓越表现是一种偶然。如果把偶然性的东西当成必然性来规划教育,道德教育的困境就出现了。
二、西方道德及其教育的现代性境遇
古典作家从最高的意义上探讨的是一个德性社会。这种探讨与维护哲学事业或哲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柏拉图哲学中的哲人是一个始终追问“何为美好生活”的形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与城邦保持相当的隔绝又站在城邦之内,同时又终身关切什么是“好”的哲人。正是由于他站在城邦之内又以哲学来审视社会,以真理替代洞穴之见,或者说用普罗米修斯之火去照耀洞穴,给“现代”青年带来诱惑,最终难免死在雅典民主社会之下。柏拉图的哲学事业就是要探寻哲人如何在政治社会中获得自身的生存方式,以捍卫崇高的哲学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如何处理哲学(哲人)与政治(大众)的冲突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2]
哲学与政治具有不同的逻辑。哲学始终关切何为“好”或“真理”,而政治和大众社会则关切正义或相对的好。由于大众社会是一个“意见”和信仰的社会,因此它与关切“真理”的哲学是相冲突的。哲学与政治是没有和谐的。[3]政治不可能按照“真理”的逻辑来运行,用哲学来要求政治必然使哲学事业断送。这是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正是由于两者的不和谐,保持它们之间的张力就有必要。所以,在柏拉图那里,哲人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大众的口味,需要与政治社会保持相当的隔绝,但又不能脱离政治社会,或者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大众,否则可能会被大众“意见”和信仰所杀。
在哲学与政治的冲突面前,柏拉图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哲学统率政治而不是归属于政治,即哲人王治理政治,或者哲学与政治的结盟,为此,柏拉图试图描绘了一个哲学生活得以生存的样板城邦:二是采取了古典哲学惯用的“隐微术”,对大众采取了一种显白的说教,或者说是高贵的谎言,把“真理”隐藏起来,让少数“明白人”听懂。但后一点为尼采所反对。尼采认为,哲人不能迎合大众,不能说一些诸如“人人可以至善”之类的道德谎言,否则就会丧失哲人的“求真”意志,但“真理”也不能直说,只能说给有“耳朵”的人听。柏拉图当然知道美德对大众而言难教,但还是在大众之中编造起道德谎言或树立起道德虚构,马基雅维里公然撕破了这种高贵的谎言,把古典哲学的隐微术公布于众,祛除了城邦生活所必需的高贵的幻象与神话,[4]在人性的低处重新构建起一个有别于德性社会的全新社会。
现代性用权利置换德性,这是马基雅维里等现代性思想家建构现代性社会的起点与核心。马基雅维里认为,构建品德高尚的生活及建立一个品德完善的社会是一种幻想,注定要失败,政治生活的目标应当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实际追求的目标,[5]显然,马基雅维里要反对的是柏拉图式的德性社会,他反对把道德问题归属于政治。事实上,柏拉图对德性样板城邦的探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不切实际,并且很累,但亚氏并没有尝试构建一个大众的社会而是一个贤人政治。马基雅维里试图构建政治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针对大多数人的,二是这个社会对道德的要求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道德表现,而不是把它建立在某种偶然性的德性卓越之上。所以,建构这样的社会需要把道德从高处拉向低处,不应关注“应当如何”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人们事实如何的问题。那么,道德的低处在哪里呢?在马基雅维里那里,道德律或自然法则被理解成一种自我保存的权利:根本的道德事实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6]在霍布斯那里,道德只能奠定在人的激情之上,由于人的激情在于虚荣自负和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出于恐惧的动机而采取的自我保存就是自然正确的,[7]所以,霍布斯将道德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用人的权利取代了自然正当,把应当拉回到并使之俯就世俗的存在。[8]因此,道德不应关涉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它只能是一种出乎自我保存需要的权利。卢梭看到了德性在现代性方案中的缺失,在他看来,文明和现代使人类丧失了美好,于是他想构建一个美好社会。而这个美好社会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回到自然状态下的那种美好。但卢梭的自然状态不同于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卢梭同意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他甚至把人性看得更低,[9](并非是指人性更恶,而是指它的动物般原始。)并且认为,对人性恶的限制不能寄望于对人的完满性的普遍要求(或许爱弥尔式的哲人或神学家可以寄望于人性改造得以实现,但公民社会则不可),唯有依赖于普遍的权利。[10]正因为卢梭怀疑启蒙了的自利可以成为公民社会的根基,深知个人自由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于是卢梭既拒绝了古代人的方案,又拒绝了霍布斯式的方案,设想出一种人人同意的“公意”社会,以求得个体自由与共同体的责任之间的和解。然而,“公意”不过是一种普遍的承认,这样的社会也无所谓道德上的绝对好与坏,而只有形式正确。康德进一步完善了卢梭的普遍意志之说,他提出:用形式上的合理性,也即是普遍立法之原则来检验行为准则之善性,而不必要诉诸任何实质内容的考虑。[11]普遍承认的就是正义,就是善性。经过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的现代性建构,古典德性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马基雅维里把德性化约为政治德性,霍布斯把德性化约为社会德性:德性不再是指勇气、节制等,而是指基于权利之上的现代意义上的正义,即不加限制地把德性等同于道德法则。[12]
现代人把道德归属于政治,表明现代人不再相信人性的最高可能性,但现代人相信可以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获得普遍的正义,于是不得不降低道德的目标。[13]柏拉图对“美德是否可教”问题的回答的不同安排或者显白与隐微的两种说教,表明古代人相信德性生活优越于政治生活,相信德性社会与政治社会的鸿沟,相信在政治社会之上还需要有一个德性社会作为样板,相信道德虚构与道德现实的鸿沟,而现代人则不满足于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的鸿沟,完全放弃了道德理想与道德虚构,或者说把道德想象留给了上帝,把道德事实留给了公共领域。为了消除这个鸿沟,现代性思想家设想没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把“应当”设想为同人的最强烈的、最共通的激情相一致,使“应当”俯就“实在”。这就是道德的最为根本的现代性境遇。这种境遇表明,现代性道德已经不再相信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与坏了,一切都以人的权利或普遍的承认作为标准,现代人宁愿相信自我保存就是道德的唯一标准,不愿相信道德崇高,至少是在公共领域放弃了道德想象或道德虚构。因此,以普遍承认或以权利为主的道德规范成为现代性道德的全部内容。
于是,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境遇表现为:
1.现代性道德教育把教育内容从古典德性教育转变为公民教育,做成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好人”成为现代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由于现代性把道德归属于政治,因此,现代性道德已经无法在哲学意义上提出何为正确的问题,而只能在政治上提出对与错的问题,即何种品格是公民社会需要的问题,而诸如尊重、诚信之类的道德品格是以权利为核心或相互的普遍承认为前提作出的,因此,品格教育已经放弃了古典德性教育中的人性卓越的要求。
2.由于现代性降低了道德的目标,道德规范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教人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培养德性成为现代道德教育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诉求。也因此,道德法律化和道德规范教育成为道德教育最后的堡垒,当然这也恰恰是公民道德教育卓有成效的地方。
3.在公共领域,现代道德教育已经放弃了道德虚构,灵魂至善的问题留给了上帝。当然,这并不否认在公共领域还存在人性卓越的道德教育,但至少道德虚构或道德样板并没有确立起来。这意味着,现代道德教育虽然还相信道德崇高,但只是相信它的偶然性获得而非普遍性的获得,因此,现代道德教育并没有把偶然性的道德崇高推及到大众,并把它规划为理性的教育方案。
4.在道德教育模式上,西方在20世纪出现了诸多理论,比如价值观澄清模式、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社会学习模式、品格教育模式、关怀伦理模式等。这些众多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取舍中的产物。价值观澄清派认为,不存在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标准,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价值观教育无法对各种价值进行对与错的判断,它也应当是在不同的价值观立场之间保持中立,着重提高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柯尔柏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试图在承认道德的多元化并回避价值多元问题的基础上解决价值混乱问题。但实际上任何道德思维都涉及具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它仍然还是道德相对主义。品格教育认为应当教导学生一些核心的道德价值,诸如关爱、诚实、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等,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所谓的普遍性的道德品格不过是现代人认同的一套价值体系,它是以权利为基础、以普遍的承认为前提的,因此,品格教育也不再存在古典意义上的对何为对错的寻问,也缺乏绝对的对何为“好”的道德追问,实际上还是缺乏任何实质内容的形式考虑。
三、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性问题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现代性的问题,道德教育如何走同样也绕不过现代性。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西方道德教育现代性的那些问题。事实上,我们道德教育正是由于还不够现代性而显得问题重重。
1.道德虚构不但在私人领域存在,而且还在公共领域(主要是学校和公共舆论空间)确立起来。西方古典德性社会里,柏拉图在处理哲学与政治冲突的问题时,面对大众的美德教育问题采取了“高贵谎言”的手法,即柏拉图明知道大众的道德平庸无企及美德事业而不得不编造了道德虚构,所谓“人人可以至善”。马基雅维里等现代性思想家则把道德从高处往低处拉,完全抛弃了道德虚构。我们道德教育正在走人现代性,但我们没有象西方道德教育那样通过降低道德目标从而放弃道德虚构,而是在公共领域建立起道德虚构,并以道德虚构作为我们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尤其是,道德虚构在我们这里不是哲学上的编造,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意味着道德教育似乎要把道德虚构变为现实。
2.我们的道德教育既没有走入西方的道德教育现代性,也没有真正返回到古典德性社会的德性教育。我们既与西方现代性的道德教育相背离,也与古典德性教育相背离。因为我们的道德教育把针对少数人的德性教育推及到全体大众。在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看来,柏拉图式的教育从最高意义上讲是一种德性教育或哲学教育,也即是基于哲学与政治冲突的考虑对哲学如何在大众“意见”中获得“美好生活”的追问而进行的哲学教育,因此,柏拉图式的教育是针对哲人王的而非大众的,它不同于现代的社会美德教育;这也是所谓古典自由教育的内涵。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则把古典德性教育的德性卓越推及到全体公民。德性卓越的偶然性是为古典作品所承认的,也是为现代性思想家所承认,但现代性思想家为了掌控命运,于是降低道德目标。我们的道德教育似乎没有正视德性卓越的偶然性问题,也没有放弃道德虚构。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道德虚构,而在于把道德虚构留给谁,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开展教育。我们的道德教育当下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把德性教育泛化:把原本属于少数人的德性教育推及到全体大众,把某种偶然性的德性获得当作理性的规划与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的结果必然是道德说教的流行与道德虚伪的产生。我们经常教人道德崇高,但我们很少考虑我们所处的现代性大众社会对道德的要求,这必然产生一种困境。德性社会在道德上肯定要优于商业社会或现代民主社会,这是为亚当·斯密所承认的,但民主政治的生活较之德性生活更适合大众。斯密也知道并想克服民主社会的道德缺陷,所以也没有忘记构建一个与商业社会相适应的伦理框架。我们或许需要保持道德虚构,但如何解决它与道德现实之间在教育上的冲突,是值得思考的。
3.我们在公共领域确立起了道德虚构,但是这种道德虚构又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那种。我们的道德虚构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道德混为一通,没有保持明显的区别——有些道德问题本属于公共领域道德但没有转变为公德,反过来说,有些本属于公德领域问题但又把它归为私人领域,于是在强调公民教育的过程中,渗入了过多的道德传统教育(即个人道德修养教育),从而淡化了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最为明显的是,在“做人”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很多道德规范问题我们通常把它看做是私人事务,或者说我们喜欢把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处事规则应用到工作中去,结果是,本属于公共领域的道德及其教育问题我们把它归结为私域道德以及个体的道德修养。在柏拉图笔下的德性社会或古希腊城邦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不分的,而在现代性社会中两者是相分离的。为此,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建立起道德虚构是值得思考的,即便在公共领域建立起道德虚构,它的内容也应当与私人领域的区别开来,据此,在公共道德领域贯穿个体道德修养式的教育是不太妥帖的。公共领域或许需要道德虚构,但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则需要思考。道德虚构可以是一种谎言,但如果把谎言当成事实来进行教育则会成问题。
了解西方道德教育的现代性境遇,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现代性问题。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发生于现代性,主要是由于还不够现代性,即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步入西方道德教育现代性的前路,从而开始以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为主的德育规划。我们道德教育站在现代性的路口,不想重复西方的老路,但又带着古典德性教育的问题,难免是问题棘手。道德说教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坚持确立公共领域内的道德虚构并依此开展教育,即便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也很难说道德教育就得到根本的改善,因为从美德与规范两个维度看,美德教育或许改变了道德说教的方式,但它的效果还是依赖于一种偶然——完全寄托于周遭世界中的偶然。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或许摆脱了道德说教,但它只不过是转换了道德虚构的教育问题——即把它交给偶然性,从而表面上减少道德虚构与道德现实之间在教育中的冲突,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逃避掉这个冲突问题。所以,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道德说教,这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深层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内的道德虚构的确立,并把德性教育推及到公民大众。道德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只是改变了表面问题而没有触及到并改变深层的问题。
如果在公共领域确实需要道德虚构,那么,也一定不要把德性教育泛化。如果把道德虚构留给私人领域,则似乎可以避免德育中的根本性的问题。为此,则需要重新建构道德教育体系。
标签:道德教育论文; 现代性论文; 柏拉图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道德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人性论文; 理想国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