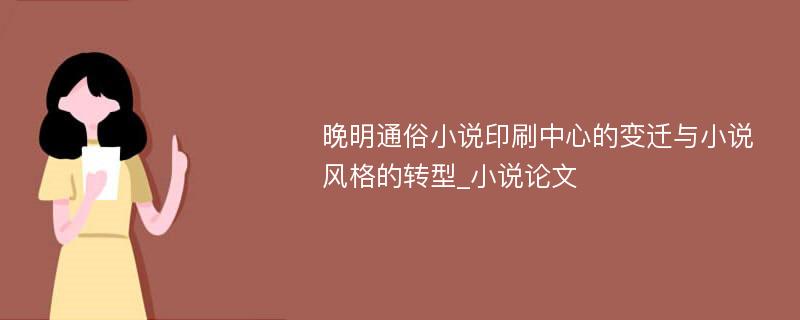
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论文,小说论文,通俗论文,风格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4-0132-07
明代中叶以来,许多书坊竞相刊刻通俗小说作品,直接带来了通俗小说创作、刊刻、评点、阅读的繁荣局面。在书坊的竞争过程中,先后形成了福建建阳、江苏南京和苏州、浙江杭州等刊刻中心。由于不同地区书坊主人的文学素质、经济实力、经营理念和所处地区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书坊刊刻小说的种类也有所区别。同时,图书市场上流行小说的种类也必然对继起的小说作家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书坊主人选择小说的标准,同样影响着作家对小说题材和小说风格的选择。因此,不同地区书坊的先后兴盛与刊刻种类的转换,也导致了小说风格的不断演变。
一、三大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先后形成
自嘉靖年间以来,通俗小说的畅销逐渐引起了众多书坊主人的注意。建阳、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一些书坊刊刻了为数不等的通俗小说作品。尤其是建阳的书坊,不但密切关注读者趣味,紧跟市场,反应迅速,而且所刻小说价格低廉,很快成为当时的通俗小说刊刻中心。但是随着竞争的逐步加剧,仅仅依靠价格优势显然难以保持领先位置。在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苏州、杭州先后取代建阳,成为刊刻通俗小说的中心。
福建建阳地区刻书很早,南宋已经达到极盛,曾与成都、杭州齐名,号称三大刻书中心,所刻书籍分别称为“建本”、“蜀本”与“浙本”。建阳的书坊,集中在麻沙、崇化两个市镇,早期是麻沙占主导地位,所以“建本”又称“麻沙本”。刊刻小说较多的熊大木,其书坊即位于麻沙。而余氏双峰堂与三台馆等书坊,则位于崇化。建阳县既有大量竹木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刻印书籍的黄白纸;又盛产印书墨,据说崇化有“墨坵”。有人说这是一种天然的印书墨汁,有人说这是一种泉水,用它注墨印书,色泽鲜艳,香气淡雅,能防蛀虫。总之,麻沙、崇化一带优异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建阳地区刻书业的发展,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籍刻印中心[1]。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福建一带书坊把握市场的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在通俗小说的刊刻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与金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从他们有能力不停地刊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规模大、成本高以及其他流行作品就可以看出。已经流行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或者模仿这些流行作品而创作的新作品,是建阳地区书坊刻书的主要题材。比如《三国演义》,据统计,明代万历以前的《三国演义》各种刻本,绝大多数都是建阳地区刊刻的,尤其是“CD系统的明刊本都是全像闽本”,而“CD系统趋于通俗化,其版本都是闽本,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趋于历史化、学术化,其版本要么是官本要么是江南本,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2](p.131),仅由《三国演义》版刻的演变,即可看出建阳、苏州先后成为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变迁,及其对小说创作与刊刻风格的影响。
万历四十年前,建阳地区刊刻通俗小说的书坊与出版家很多,占据了通俗小说刊刻队伍的主要成分。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直接带来了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荣局面。建阳余氏的双峰堂、三台馆、文台堂、萃庆堂、建泉堂,熊氏种德堂、诚德堂、忠正堂,杨氏清江堂、清白堂,以及余季岳、刘龙田、郑世容等等,成为刊刻通俗小说的主力军,其总数远远超过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总和。仅就1601-1610年来统计,现存这10年中刊刻的30余种通俗小说,就有21种由建阳书坊所刊刻[3](p.38)。
但是,从万历四十年以后,建阳地区刊刻的通俗小说作品急遽减少,苏州则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刊刻中心。苏州的龚绍山、叶敬池、叶昆池、叶敬溪、袁无涯、袁于令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通俗小说刊刻家,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与商业眼光。他们的参与,带来了新一轮刊刻通俗小说的热潮。与建阳相比,苏州地区的书坊包括天许斋、尚友堂等,不但刊刻小说的工艺水平很高,图像精美,版面精致,且多有名家评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题材选择方面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超前的魄力。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在题材与写作方法上具有创新意义的小说作品,都是由苏州的书坊率先刊刻的(注:沈德符万历三十七年(1609)前后,带《金瓶梅词话》的抄本到苏州的时候,冯梦龙与马仲良“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能够“重价购刻”,可见书坊的眼光与实力。)。这一系列刊刻活动,在通俗小说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据统计,1611-1620年的10年间,苏州地区刊刻的通俗小说至少有11种,占当时小说刊刻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次分别为南京、杭州,而建阳地区只有个别刊本。1621年以后,建阳地区虽然仍有书坊继续刊刻小说,但总数和质量远远不如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其万历四十年以前的兴盛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苏州地区大规模刊刻通俗小说,以袁无涯与冯梦龙等人推出李卓吾评本系列《忠义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为标志(注: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传》,是由袁无涯与冯梦龙修订、校对、刊刻的。今人傅承洲更详加考订,认为《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袁无涯刻本中,征田虎、王庆的内容是冯梦龙加工、改写、增补的。见《冯梦龙与通俗文学》“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紧接其后,新的历史演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新平妖传》等相继刊刻,特别是《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两拍”相继在苏州刊刻,掀起一股创作与刊刻世情小说、白话短篇小说、淫秽小说的热潮。作为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在17世纪20年代,苏州引导着当时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方向。
苏州地区的书坊,集中地大规模刊刻通俗小说的时间并不长,从17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杭州逐渐与苏州并驾齐驱,在30年代后迅速成为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新中心。相比较而言,苏州地区的书坊虽然仍然在不停地刊刻着各种通俗小说,但是与杭州那强大的创作阵容相比,包括陆人龙与陆云龙兄弟、周清原、醉西湖心月主人、西子湖伏雌教主、西湖渔隐主人直到后来的李渔,苏州相形见绌了。于是,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杭州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等方面的地位,又逐渐超过了苏州。
这一时期,杭州地区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高潮。一类是《型世言》、《欢喜冤家》等短篇小说集,另一类是与政治现实同步的时事小说如《辽海丹忠录》、《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这两类作品都是当时特别流行的小说。特别是本时期出现的诸如《西湖二集》这样专门描写与杭州有关的故事的地域小说,充分说明以周清原为代表的杭州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已经有了明确的地域观念。《西湖二集》中所附的《西湖秋色一百韵》,更是明确表现了作者对西湖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地理区域、风土人情的清醒认识和深深留恋。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学者专门提出“西湖小说”的概念[4],并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古代地域小说概念。
二、三大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形成原因
以苏州、杭州、建阳为代表的吴、越、闽三地,本来就是明代并立的三大刻书中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记载:“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但是,就通俗小说的刊刻而言,三地却不是同时并立的刊刻中心,而是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的。
建阳地区成为刊刻通俗小说的中心,以及后来衰落的原因,都与当事人极其强烈的市场意识有关。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现并获得读者的普遍喜爱,建阳地区的书坊迅速翻刻,而且不断重复刊刻,同时自己动手或找人创作,模仿这类畅销题材,及时推出新的小说作品。比如《三国演义》,就是建阳书坊重复刊刻和反复模仿得最多的小说。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福建建阳地区的书坊主人具有精明的生意眼光和文化经营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毕竟只是生意人,他们的文化经营活动往往只能跟着市场走,他们未能主动找到新的小说题材,开拓全新的文化市场。他们也不能引导读者的趣味,虽然他们很能揣摩读者的口味。没有创新,很难永远保持自己的市场优势。
福建建阳地区通俗小说刊刻业的衰落,原因很多。根据现有的相关材料来看,首先是由于它刊刻的图书质量不高,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福建的刻书业,虽然一直很兴盛,影响很大,但质量却总是不高。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说:“宋时刻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按:指徽州)、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这样的论断可从版刻实际得到证实。从现存的建阳地区刊刻的小说版本来看,大多数产品纸质低劣,印刷质量确实很差。更重要的是,一些书坊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将所刊刻作品的故事情节、描写文字偷偷删落,或者将其他书坊刊刻的作品改头换面,说成是新刻、再刻,混淆市场,引起了读者的不满。版本学家在描述版本质量时,很少看到他们说建阳地区书坊刻的哪一部书是版刻精美的。典型的是《三国演义》的系列版刻,建阳地区刊刻了大量的《三国志传》,基本上都是粗制滥造的。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像金陵人瑞堂刊刻的《隋炀帝艳史》以及金陵世德堂刊刻的《西游记》,堪称精美。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作品,其最流行的版本都是苏州及其周围地区刊刻的(如金圣叹评本《水浒传》与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其版本精良、刊刻精美,都是远远超过建阳地区的各种版本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可见福建刻书由于质量低劣,已经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内了。当然,杭州、南京甚至湖州以及江南其他一些地区的书坊,也有许多质量低劣的小说刻本,尤其是与经史诗文的刻本相比较时,缺点更明显,但是相对于建阳地区而言,质量就略胜一筹了。江南地区古代小说刻印之精美,还可以清末人的记载来证明。蛮在《小说小话》中曾记载:“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刻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卷首每回作一图,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可作博古图观,可作彼都士人诗读。”[5](p.268)清初刊刻的小说,到清末给人感觉仍如此精美,可见质量之高。
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保证销路、抢夺市场。从有关数据来看,早年他们显然是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也说明,在通俗小说迅速发展的早期,人们对小说作品、小说书籍的要求,主要还停留于满足填补空白、求新求异的初级阶段。只要题材新、故事新,人们是不太计较版本的精美程度的。同时,这些书本既然主要是作为通俗读物,供应给下层读者做文化消遣的需要,不是作为精致的艺术品来欣赏、保存,那么它的刊刻质量倒在其次了。与此相关,书籍的新奇有趣与实用程度以及成本、定价是购买者关心的主要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对那些读者来说,小说作品的语言、刊刻书籍时的文字是否适合他们,也是影响他们购买心理的因素。很多早期的通俗小说作品,在刊刻时用俗字、异体字、同音字代替那些较难读、难写、难认的字,也是由于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作者的水平,恰恰与读者的水平、期待相一致,所以他们的作品非常畅销。其实不仅仅是通俗小说,就是其他的文学作品与实用型的文字读物,当初也是由建阳地区的书坊主宰市场的。但是,随着苏州、南京、杭州地区的书坊主人开始注意到通俗小说这一领域,以质优价廉的图书商品和快捷便利的流通渠道迅速占领了通俗小说的市场,建阳书坊如不创新,必然走向衰落。这一史实说明,即使是通俗读物,仅仅依靠价格优势,而没有充分的质量保证,也必然没有长久的竞争力。
建阳地区小说刊刻的衰落,还很可能与当地遭受天灾有关。因为如果仅仅是刊刻小说的质量问题,它不会陡然消失。17世纪初建阳余氏还活跃在通俗小说刊刻这一领域,不大可能因为版本不太精美便转眼被淘汰,因为毕竟有不少人还是愿意买价钱特别低廉的产品,哪怕质量稍微差一些也无妨。即使余氏经营不善,不能刊刻新书,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旧版重印,或者将书板抵押给其他书坊,由其他书坊重印。但是,这一时期乃至此后的很长时期竟然就不再出现建阳余氏书坊的消息,这显然是有些问题的。考虑到建阳地区以前的书坊遭遇,陡然急遽衰落最可能的原因是建阳地区的书坊遭受了火灾,烧毁了大量的书板,使余氏以及其他多家书坊的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这才导致他们在后来无法恢复元气,福建建阳的刻书业一蹶不振。当初(特别是宋代)麻沙的刻书规模远远超过崇化,就是因为元代兵火,沦为灰烬,直到明代中叶方才稍有恢复,但已经无法与崇化相提并论。但是,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建阳书坊再次遭受火灾,书籍刻印业又遭重创,只有余氏忠正堂、三台馆与双峰堂以及杨氏清白堂等因为大量刻印通俗小说,找到了新的图书题材,抢占了市场,恢复了生机。由此看来,有着刻书传统且能够屡屡重振的建阳刻书业,如果不是遭受天灾,无法恢复,是不会轻易放弃当地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自动停止刻书业务的。万历四十年以后他们不再大规模刻书,很可能是由于遭受天灾,并被苏州、南京、杭州一带的书坊所挤压,又找不到新的复兴途径,没有合适的图书选题。这样的综合因素,是建阳书坊急遽衰落的主要原因。
随着作为领头羊的建阳余氏家族的淡出,建阳地区通俗小说的刊刻业一落千丈,剩下熊氏、黄氏等家族的少数书坊苦苦支撑。万历后期那些创新型的小说,如世情小说、时事小说、拟话本小说,都没有引起福建书坊主人的注意。或者说,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新兴的题材,但是却无力抢夺该类作品的刊刻权,毕竟这类小说的作者集中在苏浙一带。由于明代政治斗争的中心除了北京就是南京,时事小说所需要的新闻性、时间性,给予了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创作该类小说的极大便利。特别是作为陪都的南京,与北京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呼应。南京的官员与士绅,既关心着北京里的一举一动,又对北京的政治主张与施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因此,就创作时事小说而言,江浙一带在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至于白话短篇小说,它是在说话技艺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说话艺术的繁荣程度,与当地的城市化水平、市民阶层的文化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流行文化,通俗艺术更与城市规模与城市位置有着密切关系。在这方面,江浙一带同样有着地理上的优势。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的市民阶层,都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些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也是当时中国最为领先的。与福建建阳地区相比,其优越性极其明显。何况这些城市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互通有无、相互竞争的局面容易形成,更能促进通俗小说的发展。建阳地区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与江浙一带的城市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因此,在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竞争中,江浙一带的书坊迅速抢占了流行文学的制高点,从此以后整个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只是后来增加了同样位于江浙地区的上海),都是江浙一带的书坊占据着通俗小说刊刻的主要市场。
三、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
苏州、杭州相继成为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既与当地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庞大的市民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文化消费刺激着更多优秀小说的创作与刊刻,更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杭州当地优秀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评点、修订、整理与刊刻过程,提升了通俗小说的品位与档次,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直接带来了通俗小说的兴盛与繁荣。
苏杭一带,是晚明商品经济发展得最充分的地区,也是通俗文化的集散地。早在宋代,杭州的通俗文学艺术就很繁荣,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等著作,都曾经描述过杭州民间说话技艺的繁荣情景与高超水平。明代杭州人对与西湖以及杭州有关的故事仍然极其感兴趣,西湖上也流行着说话等技艺和通俗小说的创作、刊刻与欣赏,这样的地域文化氛围,对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繁荣,显然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就是这种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这一地域特征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从比较早的单行本《西湖三塔记》小说,到17世纪的《西湖二集》、《西湖佳话》,18世纪的《西湖拾遗》、《西湖小史》,以及19世纪的选本《西湖遗事》等,都继续并发展了西湖(杭州)这样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显示出小说界对西湖与小说关系的强烈认同。
17世纪20年代以来,苏州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与刊刻中心,这与冯梦龙、袁无涯、袁于令、吕天成、张无咎等文人的积极参与有关。后来它的核心地位受到了杭州的强劲挑战,呈现出衰落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杭州地区峥霄馆、笔耕山房等书坊主的努力,创作并刊刻了大量的通俗小说作品,另一方面与苏州通俗小说界的灵魂人物冯梦龙的离开有关。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后冯梦龙创作戏曲《双雄记》、编辑出版《山歌》、《挂枝儿》等通俗文学作品后,他就成为苏州通俗文学的核心人物。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曾怂恿书商重价收购刊刻《金瓶梅词话》。袁无涯刊刻的李贽评本《忠义水浒传》,也主要是由冯梦龙怂恿、校勘之后才得以刊刻的。后来他更是亲自动手,创作、改编小说作品,以供出版之用。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修订的《三遂平妖传》刊刻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于17世纪20年代编辑出版《情史类略》、《太平广记钞》、《智囊》以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影响极大。正是由于他的个人努力以及与书商的合作,使苏州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版中心。但是,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成为贡生,进京赴选,然后担任丹徒县学训导(注:冯梦龙担任丹徒县学训导,在崇祯五年(1632)之前。据康熙《丹徒县志》卷二《学校》中就说崇祯五年时知县张文光、训导冯梦龙曾重新修建过龙门、尊经阁等学校建筑。),崇祯七年(1634)则又远赴福建寿宁担任知县,从此远离了通俗文学的搜集、改编、创作、评选、刊刻工作,使苏州地区的通俗小说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从此以后,苏州地区的通俗小说的成就,就一直在杭州之下。
从明末以来杭州地区创作并刊刻的小说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来看,有关小说不但内容、品种丰富多样,而且由于文人的加入,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迎合读者的欣赏口味与阅读期待上,表现出极其敏锐的艺术嗅觉。《喜欢冤家》、《型世言》、《西湖二集》等代表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思想倾向的作品,都诞生于杭州地区;出版《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皇明中兴圣烈传》等引人注目的时事小说和《禅真逸史》、《禅真后史》之类的神魔小说,更能说明杭州地区的书坊对阅读市场的把握是多么地精确。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杭州地区的小说家与书商之间的关系,比苏州地区更为亲密。本来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与书坊主人叶敬池之间,应该是很好的合作典范:文人创作的小说,往往能得到及时的刊刻;市场上流行哪一类小说,书坊主人也能够迅速找到相应的作家进行创作。比如苏州刊刻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以及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其前后过程都显示文人在通俗小说刊刻方面与书坊主紧密合作的关系。可是杭州的峥霄馆,则是文人、小说家自己的书坊,所以创作与刊刻更能同步进行。峥霄馆在17世纪20年代就已经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经过近10年的积累经验,显得更为成熟。该馆主人为陆云龙,字雨侯,号蜕庵,其堂号称翠娱阁,书肆则号峥霄馆,浙江钱塘人,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康熙五年(1666),早年即通诸经子史,工古文诗歌,曾专注于举子业,但功名蹭蹬,后因家贫而放弃,并转而刊刻、创作小说及其他流行作品(注:关于陆云龙的生平事迹与刊刻出版活动,胡莲玉有着极其精确的考证,本处即采纳其说,参见其《型世言研究》第二章第二节《陆云龙生平考述》,南京师范大学2002届博士学位论文。),曾先后刊刻过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以及《禅真后史》等小说作品。他除了刊刻小说外,还刊刻了《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皇明十六家小品》、《钟伯敬先生选注四六云涛》、《翠娱阁近言》、《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近思录集解》、《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以及其他著作多种。从这些刊刻目录可以看出,陆云龙刊刻书籍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因为他都是选取当时最流行的书籍并加以注、评的。不过他又不是一般的惟利是图的书商,他所刊刻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而且以普及性的文学读物为主。比如翠娱阁刊刻的与钟伯敬有关的书籍,就体现出他们紧扣市场的特点。钟伯敬(钟惺)以选评《诗归》系列而著称,由于他署名的选本极其畅销,所以许多书坊纷纷盗用他的名义刻书,这更加抬高了其声誉。翠娱阁刊刻他选注的《四六云涛》与他的作品集,是否得到其授权,尚不可得知,但是这样的行为本身,即已说明陆云龙既对流行关注,也有较高的欣赏标准。其他的作品,比如《行笈必携》,包括《诗最》、《文奇》、《词菁》、《清语》、《格言》、《游记》、《四六俪》、《小品札》等,都是有一定消闲价值和学习模仿、实用价值的文化读物,而《皇明十六家小品》所选取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小品文作品,包括陈继儒、汤显祖、袁宏道、徐渭、屠隆、钟惺、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作品,小品文是当时最流行的文体,这些作家是当时最流行的作家,这样的选择目标,集中体现出翠娱阁的经济与文化兼顾的刊刻倾向。
陆氏兄弟所创作与刊刻的小说作品,也体现出类似的倾向。通俗小说在明代中后期的盛行,尤其是17世纪20年代以来拟话本小说的大量涌现,使通俗小说的刊刻成为经营性的书坊的重要刊刻项目之一。陆云龙因为家贫方才刻书,所以肯定会考虑到当时的读者口味,通俗小说尤其是拟话本小说的刊刻就成为重要的选择。可是,拟话本小说的流行,又是出版界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有了好的小说作品,书坊必然有所竞争。翠娱阁的主人并不是经济实力很强的商人,所以在书坊之间的竞争中并不能抢得先机;不过,陆氏兄弟均是饱学之士,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抢夺合适的小说书稿,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模仿、写作小说,利用自己书坊的刊刻便利,同样可以抢占拟话本小说的市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陆云龙选择了当时人们最关注的九千岁魏忠贤的事迹,创作并刊刻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一举获得了成功。此后,他一方面获得了方汝浩《禅真后史》的刊刻权(《禅真逸史》已经获得了成功,所以可放心刊刻(后史》),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弟弟陆人龙拉入自己的创作队伍,创作了反映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最终以陆氏兄弟合作,创作、评点、刊刻的《型世言》,代表了翠娱阁出版物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与翠娱阁可以相提并论的杭州书坊是笔耕山房。从书坊名称可以看出,这也是一家典型的以写作与刊刻书籍谋生、牟利的书坊。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来看,它在本时期刊刻了《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小说作品,作者分别是醉西湖心月主人和西子湖伏雌教主,这都带有明显的杭州特色。从所刊刻的作品的内容来看,作者与书坊主人都比较大胆,《宜春香质》与《弁而钗》都是描写同性恋的,而《醋葫芦》则是写悍妇的。这两类问题在明末(直到清初)都比较严重,反映这两类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也很多。《醒世姻缘传》、《疗妒羹》、《聊斋志异》等作品中都写到很多悍妇、妒妇的故事,后来到乾隆时期仍有《疗妒缘》之类的小说作品出现。至于同性恋,从明末到清代初中期,表现这一问题的小说作品更多。笔耕山房刊刻的小说作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正说明书坊主人对文化消费市场的把握相当准确。
从所刊刻小说的思想倾向来看,笔耕山房与翠娱阁一样,都是文人的阵地。他们虽然都紧跟市场的动向和读者的喜好刊刻作品,但是这些书坊的主人毕竟是文人,他们即使在创作通俗小说以谋取经济利益时,也不忘记将作品改造成鼓吹道德、实施教化的工具。翠娱阁之名,顾名思义,是以娱乐性作品为主的,可是看他刊刻的小说,则均是以鼓励忠孝为主要目的的。《型世言》“树型当世”的创作目的自不待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作品,更是典型的斥责奸邪、歌颂忠贞的作品,作者从小说的题目即开始明确标明自己的创作喜好,毫不掩饰自己的主观感情。笔耕山房刊刻的《宜春香质》与《弁而钗》,都是写同性恋的,但是小说作者将同性恋中“性”的因素大大降低,将“情”的因素作了很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将同性之恋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情”,还将它纳入道德的规范,比如说《弁而钗》中的李又仙卖身救父,得到匡时的救助,无以为报,只好男扮女装,以身相许,报答匡时,并守节存孤,是典型的知思图报并坚守节操的值得歌颂的人物。作品中许多男子,一旦与他人产生感情或者发生关系,往往按照传统道德中对女子的要求要求自己,成为作者表彰的人物。也就是说,作者着力表彰的往往不是同性恋这一行为本身,而是产生同性恋的原因以及有了恋情或者恋爱关系后的表现。与此相关,一旦男子不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是有其他的目的与其他男子发生恋情,作者往往报以谴责的态度。《宜春香质》中的大多数故事,都是谴责那些利用男色引诱他人、骗取他人钱财的。在这些故事中,引诱他人的同性恋者最后往往不得善终的。这种内容倾向,显然代表了传统文人的观点,不单纯是为了满足市井小民的欣赏趣味。至于《醋葫芦》,更是男性文人维护传统道德、强调男权本位的集中体现,不仅仅是故事新奇有趣,以怕老婆的故事来迎合市井小民的欣赏口味的。
至于《西湖二集》的出现,更体现了杭州地区文人对地域文化本身的重视,以及在通俗文化背景下,他们努力提高白话小说艺术品位的追求。周清原在小说题目中明确标明“西湖”这一地理概念,显示出一种观念上的自觉,这显然具有典型的文人性。而小说作品中所描写的西湖上的故事,只有少数作品迎合了市民趣味,如《天台匠误招乐趣》,其余的基本上都体现了文人的审美追求。《巧书生金銮失对》与《愚郡守玉殿生春》、《寄梅花鬼闹西阁》与《吹玉箫女诱东墙》、《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与《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侠女散财殉节》与《巧妓佐夫成名》等两两相对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了文人阶层的追求与理想,与前期的话本小说相比,明显具有了文人化色彩。
苏州与杭州同属江南水乡,地域既接近,文风亦相似。但是就它们各自刊刻的小说作品的总体风格来看,虽同样显示出文人化、雅化等共同特点,两者仍然有着细微的差别。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石点头》或者是《今古奇观》,苏州刊刻出版的小说,都有比较强烈的教化倾向,而且往往能将作者的倾向性与故事的情节紧密结合起来,作者的说教不显得生硬讨厌,态度也比较和缓。相比之下,杭州地区创作与刊刻的小说,往往比较容易走极端。比如《型世言》之立意,过于追求教化功能,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刻意表现教化意图的痕迹。那些宣泄情欲的作品,也是直言不讳,大肆描写有关色情活动,《欢喜冤家》中大量的性描写,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宜春香质》、《弁而钗》等小说,无论是看作鼓吹教化的小说还是认为是宣扬色欲的作品,总是有走向极端的感觉。这也许与杭州更多地具有市民气而苏州的文化性更浓等地方特色有关。
收稿日期:2003-12-22
标签:小说论文; 杭州南京论文; 南京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杭州经济论文; 金瓶梅论文; 辽海丹忠录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型世言论文; 弁而钗论文; 西湖二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