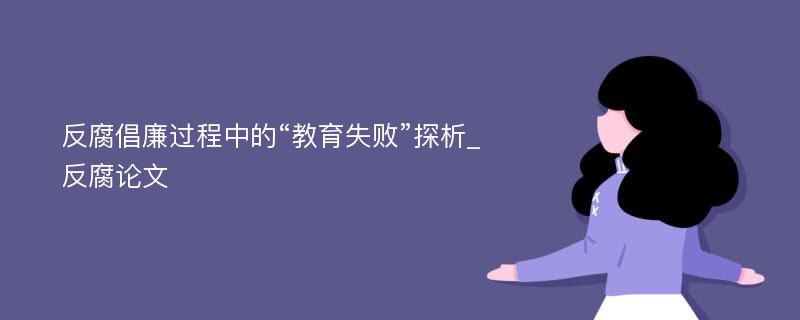
反腐败过程中“教育失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历来注重思想建党,并不断地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这使教育在党的建设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同样强调: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腐败问题会有恶化可能,我们党进行了不间断的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1980年对《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学习开始,二十多年来覆盖全党的重大政治思想教育活动一轮接着一轮。的确,随着教育的开展,涌现了一大批孔繁森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不断地政治思想教育并没有改变“腐败情况继续恶化”的事实[1],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显现的腐败现象更是有力地证明了一个让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教育失灵”。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党内腐败仍然在“滋生蔓延”,腐败案件与涉案人数总是在“经过短暂下降之后迅速反弹”[2],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在广度上并没有真正提高所有官员的思想和增强党性修养。第二,“59岁现象”使得接受党的多年教育的一些领导干部并不一定能经受腐败的考验[3],说明教育在深度上并没有彻底改造所有官员的世界观。第三,腐败官员的“高层化”趋向[4],证明了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教育者本身也并不是真正完成思想上的改造。第四,“群体腐败”不断地推进腐败行为的半透明化[5],使得腐败由原来被人们不齿的行为变成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些人普遍接受的行为,说明了一些人的认识在不断地走向教育目标的反面。
为什么原来我们认为很有优势的思想教育手段现在失灵了?客观而深入地分析,不难发现,并不是教育本身对反腐败没有价值,而是我们的手段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具体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在实施反腐败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的三种偏差,使反腐败教育没有产生它应有的效用。在这里,笔者仅就此三种偏差试加分析。
一、教育对象偏差
在我们对腐败定义进行界定时,必须明确,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的主体只能是掌握着一定权力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可以是某一个体,也可以是由一定数量的权力主体所组成的集团。那么反腐教育的对象应该是谁,就不应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议题。既然腐败只能是权力掌握者的腐败,那么反腐教育的对象也就应该是那些有条件和必将腐败的权力掌握者。这是一个准确而又经济的界定,但是这只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界定,因为在实施教育对象选择时,没有人知道谁是有条件和必将腐败的权力掌握者。所以,教育对象必须扩大到一切有可能腐败的权力掌握者,但是又由于“可能”的不确定性,必然使教育对象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在新中国的第一次反腐高峰——“三反”“五反”时期,对各种人员的改造,使用了思想改造的教育方式。有的人认为这次受了“左”的思想影响的整肃运动是犯了某种程度的扩大化错误,使得一部分无辜党员干部受到了牵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知道在所有权力掌握者中哪一个官员会是必然的腐败者,所以反腐教育就必须是以所有人的腐败假想为前提,这就使反腐败的教育对象必然发生一种扩大化,使其扩大到所有的权力掌握者,这也是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最佳选择。因为在看到扩大化的同时,任何人也不应该忽略这一“扩大化”的结果,为中国廉政建设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反腐败的教育对象在扩大到所有的权力掌握者之后,应不应该停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腐败只能是权力掌握者的腐败,那些非权力主体由于缺少腐败的条件,所以不应该成为反腐败的对象。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反腐败教育,又出现了教育对象的第二次扩大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把教育客体扩大到所有的权力掌握者就停止了,而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全体人们群众都在受着反腐败的教育。
笔者认为,这次才是真正犯“扩大化错误”。其一,扩大化必然导致不经济,虽然在所有层次的部门都没有关于反腐教育经费支出的公开报表,但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是,教育必须使用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对象的扩大化必然造成种教育资源与经费的极大浪费。其二,当教育对象发生了这一程度的扩大时,这时候的教育的客体必然发生了性质上的变换,不再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可能腐败者的教育,而是可能腐败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柳州市检察院把反腐的宣传教育搬上了该市的5路公交车事件[6],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教育对象的性质转变。
二、教育内容偏差
任何人都清楚,反腐败教育只是反腐败的一种手段,而它的真正的目的则是反腐败,或者说是使腐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遏制,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行为的标准:教育是否有意义,那要看教育内容对反腐败的贡献率。大体上说,反腐败教育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四个部分:形势、原因、危害、对策。这是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腐败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四个部分。任何一次教育,在这四个方面的力度分布都不可能是均等的。那么哪一部分应该是反腐教育中的重点?笔者认为,对于前两者的分析,远不如对于后两者的探讨更具有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更能达到反腐教育的目的。
首先,对于腐败严重性与反腐败紧迫性的问题分析,并不有助于腐败形势的好转。面对新世纪党的领导所受的挑战,反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我们所必须要认识的,我们的领导者在各种会议上也是反复强调我国反腐的严峻形势。强调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达成一种对腐败形势的共识,而是建立在这种共识之上的对腐败形势的改变,但是这常常只是表现为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变成自己的知识,成为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要成为一种“大道理”,这一认识仅仅是浮在决定人们行动的意识的表层,并不对人类的行为产生任何的影响;二是理论变为自己的世界观,成为真正的人生指南,真正地实践它,这是人类认识的根本目的。第一层次是第二个层次的准备,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归宿,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但是第一个层次的认识能否转变为第二个层次的认识,以及会转变为哪一种性质的第二个层次的认识是不具有确定性的。在反腐败教育过程中,对腐败形势的过多的分析可能导致另外一个相反的结果,它让人们得到一种结论,腐败是如此的严重,个人是无力改变的。
其次,对于腐败危害性的分析,并不有助于腐败者个体行为的改善。腐败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危害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类似理论,但这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对人们的认识产生任何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君主认识不到腐败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从普遍性来讲,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对腐败性质及危害性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并不需要一个权威的指导。但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之外,人们还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腐败对腐败者个人而言是有益的,它是个人获得权力、财富以及其它一切个人需要的捷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决定腐败者腐败的不是对腐败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而是鉴于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对比[7]。
无论是教育还是查处,反腐败都应当从实处着手。笔者认为,在我们实施反腐败教育的过程中,从实处着手就是要分析原因,找出对策。但是在现实的各级反腐教育中,总是把反腐败教育的重点放在严重性与危害性的分析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的反腐败教育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不能求真务实。
宏观与微观本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宏观目标不能简单地分割为多个微观目标的组合,实现微观目标的手段也不一定有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但是为什么各级各层在实施反腐败教育过程中,总是忽略甚至是回避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呢?不是因为认识原因,而是价值判断的差别。由于“自利性”的存在[8],使各级在反腐败教育过程中,反腐败的标准已经不是该项工作应起什么样的效果,而是该项工作是否做了。当一级组织把学习的着力点放在过程上的时候,它就不再会关心学习的内容是形势、危害、原因还是对策。显然,正是这种价值重心转移,导致了教育内容的偏差。
三、教育目标偏差
反腐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这好像也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在论述这一问题的大多数的理论文章中都有类似的观点:“教育是基础。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坚定干部的政治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国家、政党的本质,国家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明确自己的公仆身份和对人民的职责,从而形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公仆意识,并以这种意识指导、支配自己从事的一切公务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大潮中,不为非分的物欲、权欲所左右,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作到‘拒腐蚀,永不沾’,在灵魂深处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坚固长城。”[9]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但同时又存在着一个值得怀疑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反腐教育的目标就是使广大干部“从事一切(符合要求的、合法的(公务活动”。而这个值得怀疑的思维方式就是一切(符合要求的、合法的)公务活动都必须是以“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坚定干部的政治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识国家、政党的本质,国家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明确自己的公仆身份和对人民的职责,从而形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公仆意识,并以这种意识指导、支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正是由于这一思维方式的作用,使我们在反腐教育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方式而使人们往往忽略真实目标的追求。在反腐败进程中,人们只在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树立起来,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是否已经养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是否已经确立,而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正达到反腐败的目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观点来分析,思想认识问题是腐败产生之根源。的确,当在所有的权力掌握者那里“形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公仆意识,并以这种意识指导、支配自己从事的一切公务活动”的时候,腐败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解决了。同样也不可否认,教育在反腐过程中应该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改变社会认同,提高社会认识,增强对腐败的抵制力度。但是,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疑问:那就是(符合要求的、合法的)公务活动必须要以特定的“公仆意识”作为前提吗?也就是说,把“公仆意识”的形成作为反腐败的根本手段是否是必要的?
首先,使各种公务活动符合社会要求、符合人们的要求是一个低层次的价值目标,它仅要求一种浅层的表面的客观事实,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世界观去指导国家公务人员从事的公务活动则是一个高层次的理想目标,它要求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社会现实的思想觉悟。当人们把公仆意识的确立作为遏制腐败的必要条件时,常常使我们在进行反腐败教育时总是感到力不从心:不是最终目标难以实现,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难以实现;不是奉公守法的行为难以确立,而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难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难以确立”[10]。
其次,观念与行为具有统一性,但是相同的具体的行为却可能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思想目的,无论是对法律惩罚的畏惧还是对人民的忠诚都可以使一个人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腐败行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消灭腐败说到底也就是要消灭这样一种权力的滥用的过程,而无论这一行为是受何种思想的指使。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应该关注的是黑箱之外的输出,而不应该是黑箱内部输出与输入的逻辑规律。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在我们的反腐败教育中,人们总是注重教育的解释功能,而常常忽略了它的改变功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但是正是由于教育过程中这三种偏差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反腐败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只有纠正这三种偏差才能够真正发挥反腐败教育的真正作用。
标签:反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