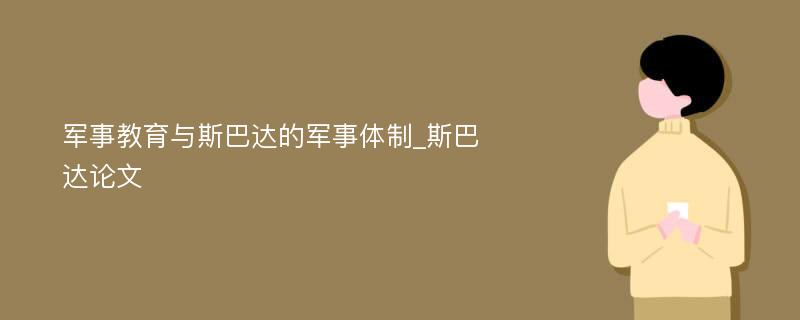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巴达论文,制度论文,军事论文,阿高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通常把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称作阿高盖(agoge)。①关于阿高盖制度人们有三个基本认识:一是“军事化”,旨在培养职业军人。内莫对此有很好的概括,他说:斯巴达的“孩子都被交给城邦,斯巴达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的集体教育(agoge)”②。波默罗伊等人称斯巴达的体制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战士;③卡特里奇也称斯巴达的教育体制可以把孩子培养成战士。④为了这一目的,阿高盖教育体制中文化教育的内容很少,主要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包括各种锻炼能力的生存训练和吃苦耐力训练等。二是“国家化”,意指国家办教育。这种教育针对所有的公民子女,所有的适龄儿童都有权利、有义务接受教育。但对学龄跨度略有不同意见,主流意见认为从7岁到20岁;但斯托巴特、波默罗伊等人认为,孩子一出生就接受阿高盖制度的规约,如接受体检就是这种表现。⑤终止年龄也有不同意见,如内莫认为到24岁为止。⑥三是“永恒化”,永恒化的观点来自古典作家、尤其是罗马作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由斯巴达历史早期的著名改革家莱库古创立,此后其核心内容没有本质变化。现代部分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卡特里奇。⑦
目前,上述观点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批判的重点是第三点,即“永恒化”。阿德金斯认为,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世界几乎没有军事训练,阿高盖教育体制开始于古典时代。⑧皮佩(Piper)、席默荣(Shimron)认为,阿高盖制度起自莱库古时期,但在克里奥墨涅斯三世改革之前曾经一度中断,⑨不过,中断前后没有本质的变化。⑩科奈尔(Kennel)、杜卡特(Ducat)、霍德金森基本赞同皮佩的观点,但认为斯巴达的教育在公元前3世纪曾经发生过巨大变化,后来到罗马时期又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一种娱乐制度。(11)科奈尔、杜卡特还对“永恒化”观点的根源做了分析。科奈尔认为,根源在于史料使用上犯了“同时态”(synchronistic approach)错误,使用史料时不分史料出现和所反映时间的先后;(12)杜卡特认为是人们采用了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具体的制度脱离了其产生的宏观背景。(13)其实,这些批判并没有彻底推翻永恒化的观点。笔者认为,阿高盖制度的三大特征是一个整体,永恒化不仅仅表现在存在时间的长短,还表现为“军事化”“国家化”两大特征没有本质的变化。尽管霍德金森认为这一制度始于古典时代,但没有提到终止时间,如果按一般观点,阿高盖制度终止于罗马征服,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也太长了!(14)至于皮佩等人实际上认为古风、古典乃至希腊化时代的阿高盖制度没有本质变化,(15)这实际上仍然是“翻版”的“永恒化”。科奈尔、杜卡特的批判固然有理论的高度,但缺少对“军事化”和“国家化”的关切,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斯巴达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无意识当中重复着“永恒化”的错误。
教育已经成为古代斯巴达形象的基石,如果认识发生偏差,就会影响到对整个古代斯巴达社会特征的认识。本文与传统观点一样,认为典型的阿高盖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化”“国家化”,不同的是,本文认为这一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应特殊的形势而产生的。笔者还赞同科奈尔、杜卡特的观点,认为具体的史料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认识和使用,防止犯“共时态”的错误。基于上述两点,本文将围绕斯巴达教育中的军事教育成分,长时段地审视斯巴达教育制度的发展,试图恢复古代斯巴达教育发展的本来面貌。
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
如前所述,古典学者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教育在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没有本质的变化。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至少是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教育没有本质的变化,罗马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斯巴达教育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约四百年的时间中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按照历史常识,一种制度历经400年没有变化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斯巴达古风时代的教育与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我们并没有那个时代直接留存下来的资料,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是希腊古典中期之后和罗马时期的作家留下来的。他们宣称,他们所记述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古风时代的著名改革家莱库古,尽管这些作者距离莱库古(约公元前800—前700年)已经数百年。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材料来判断他们所记述的内容是否可信,所以现代学者往往采取“信古”的态度,对这些资料宁信其真,不加质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对古典作家的观点不能证明其真伪,那么因为古典作家在时间上距离古代斯巴达更近,了解的史实一般来说比我们更丰富、更全面,“信古”无疑具有可取性。但是,严谨的研究必须对古典作家的记述慎之又慎。尽管我们缺少充足的史料,但可以借助其他材料和理论对古典作家的观点加以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对不能证伪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信古”的态度。
依据古典作家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与古典时代基本一致,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1.学龄安排集中在7—18岁,7—12岁是第一阶段,13—18岁是第二阶段;2.国家办教育;3.教育军事化,尤其是在第二学龄阶段,其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军人。我们没有材料对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年龄安排做出证实或证伪,因此,姑妄承认之;但对国家办教育我们可以做出某些质疑:斯巴达国家如何办教育?是全部还是部分承办?而对第三点却发现有大量材料足以对其加以证伪。
国家办教育被学者们认为是整个古代斯巴达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国家办教育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物质投入迫使教育服从自己的意志,二是通过规范教育内容体现自己的意志。这里先讨论前一问题。众所周知,国家办教育必须有经费投入。斯巴达国家财政制度一直比较落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也没有强大的财政储备。阿基达玛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宣称,斯巴达没有“公款”,也不准备从私人那里得到捐助。(16)实际上不是不准备而是不可能,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斯巴达公共财政不好,税额不能足额征收,握有土地的公民不肯自觉缴税,国库空虚。(17)斯巴达税收一直采取份地税和公餐税两种形式,公民不向国家财政纳税,只向公餐团纳税。(18)斯巴达对战争收入尽管也设了官员加以管理,但我们在史书上几乎见不到斯巴达的财政安排。这也证实阿基达玛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尽管上述材料来自古典时代,但从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国家体制(包括财政体制)总是呈现为越来越严密、完善。而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古风时代斯巴达国家财政比古典时代更完善;也就是说,至少古风时代的斯巴达国家财政与古典时代一样糟糕。没有财政作支撑,斯巴达的教育投入只能靠斯巴达公民自己解决。实际上,斯巴达的儿童组成的连队类似于公餐团,这个组织的经济来源可能与成年人的公餐团相似,也来自成员(实际是各个家庭)缴纳的“赋税”。霍德金森早已指出,斯巴达公民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绝对平等的,贫富差异在古风时代就存在。既然有贫富差异,就可能有人因为交不起公餐税而失去公民权,也就可能有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个体承担教育经费显示了斯巴达国家教育中的私人成分,表明斯巴达教育并不是彻底的国家教育。
但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称,斯巴达国家设有专门的教育管理人员派迪诺莫斯(paidonomos)。派迪诺莫斯手下还有随从,负责惩罚犯错误的儿童。儿童的日常管理者则是来自国家选任的优秀的erien。(19)斯巴达长老经常到教育场所监督教育过程。(20)这些制度确确实实表明了斯巴达国家对教育存在一定的干预,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办教育的特征。但是,我们不知道上述情况是否反映了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状况,不过,即使反映了古风时代的情形,结合上文对财政基础的考虑,古风时代(乃至整个古代)的斯巴达教育也不是彻底的“国家化”。
教育“军事化”理论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军事化”教育的目的无疑是培养合格军人,教育内容应该包括军人品德和军事技能,尤其是后者。目的和内容、品德和技能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关于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目的的材料主要来自古典时代留下来的文献,但古典文献中同样有不少材料对此给予了证伪,正如下文即将论证的,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等作家认为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合格军人,而是培养军人品德。
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内容与希腊世界基本一致,只不过是对体育更为重视而已。古希腊教育与现代教育不一样。现代教育主要在学校完成,有着完善的组织系统和固定的课程设置;而古风时代的希腊没有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学校组织,生活空间与教育空间高度重叠,因此,公众参与的城邦公共活动以及某些家族内部的私活动本身就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古希腊的公共活动内容丰富,如体育竞技、宗教集会、公民大会、戏剧演出等,私活动中的技艺传授、品德教育、演说能力等也具有国民教育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格里菲斯将家庭、行会组织、宗教合唱团、公餐团都作为教育组织,其中展开的各种技艺、能力和品德培育都是教育的内容。(21)马鲁则指出,古风时代的希腊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其内容包括了体育、艺术、文化等内容,其中体育训练占了重要地位,其次是艺术(包括音乐、诗歌),最后是智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末。当时的哲学家色诺芬(活动盛期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宣称:当时的希腊教育“重视体力甚于重视高尚的智慧”(22)。此后,这种重体育、轻文化的状况才开始改变,先在雅典,然后再到希腊其他地区(斯巴达和克里特除外),这一转变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派兴起才告结束。(23)可见,整个古风时代的希腊教育呈现出“重体育、轻文化”的特征,斯巴达也不例外。现代学者往往错误地将“重体育”等同于军事化。古希腊处于冷兵器时代,士兵的身体素质与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体育确实与军事密切相关。但是,体育竞技毕竟不是军事技能。古风时代的体育主要是掷铁饼、长跑、拳击、格斗等,这些项目与军事技能有着明显的差别。当时希腊世界实行重装步兵制度,列队、布阵、冲锋、撤退、射箭、刺杀、盾牌使用等才是最基本的军事技能,但这些训练并不见于史书记载。当然,古典文献记录了生存训练、战场见习、模拟战争等内容,但我们不能再犯科奈尔、杜卡特所说的“时间错乱”的错误,“张冠李戴”地用来说明古风时代的历史。综合来看,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内容与其他城邦没有本质的差异,也不具有军事化的特征。
现代学者还从其他角度对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军事化”提出佐证。其一是“文化沙漠化”。他们先设定教育军事化必然导致斯巴达“社会不再需要艺术家”(24),进而导致文化教育的缺失和文化领域的“沙漠化”。在古代希腊的众多城邦中,斯巴达的文化生活确实相对平淡,没有出现过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修昔底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但是,这些并不能代表斯巴达的文化生活就“沙漠化”了。古代斯巴达实际上非常重视知识学习。斯巴达儿童与雅典儿童一样,7岁时就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正因为这样,斯巴达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学会了谈话辛辣而优美,言简而意赅。(25)戴玛拉托斯(约公元前515—前491年)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声名。(26)多里欧斯也自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才能应该成为国王。(27)温泉关战役前夕,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曾经收到薛西斯(Xerxes)的劝降信,并回信拒绝,这说明那300位精英勇士至少并不全是文盲。种种事实说明,斯巴达人并不全是一介武夫,正如雅典人并不都是大文豪一样。(28)希罗多德曾经说:“希腊人中除了斯巴达人不爱学习纯粹是希腊人为了自己开心才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29)。
斯巴达的文化生活也不是一潭死水。弗格森说:“公元前580年以前,斯巴达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家乡。”(30)默里也指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曾经出现过文化的繁荣。(31)相传克里特诗人泰拉特斯(Thaletas)帮助斯巴达创立了吉姆诺派迪亚(Gymnopaideia)节,将克里特诗歌传到斯巴达,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32)斯巴达曾经聘请列斯波斯岛的著名音乐家泰尔潘达(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前6世纪初)传授音乐,他可能将东方的八弦琴介绍到斯巴达。(33)吕底亚诗人阿尔克曼与泰尔潘达身处同时期,也曾在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少女之歌》就是他在斯巴达创作的著名作品。吕底亚音乐在斯巴达一直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还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评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提尔泰乌斯又来到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诗人斯特西考鲁斯(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0—前555年)曾经在斯巴达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他把阿伽门农说成是斯巴达的英雄。(34)麦伽拉诗人提奥根尼斯(Theognis,出生于公元前550—前540年,一说出生于约公元前600年)在被流放的时期也曾经到过斯巴达。(35)其他的还有洛克里(Locri)的色诺克里图斯(Xenocritus)、阿尔戈斯的萨卡达斯(Sacadas)、克洛丰(Colophon)的波利姆拉斯图斯(Polymnastus)、库多利亚(Cydonia)的尼姆法乌斯(Nymphaeus)……(36)这些都说明早期的斯巴达文化并没有“沙漠化”。
其二是“公民理想军人化”。通常认为,所有斯巴达公民都是经过严格军事教育培养出来的、温泉关勇士式的士兵,具有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绝对服从上级、彻底献身国家的品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温泉关战役之前,斯巴达决定派两个使节去波斯抵偿被杀死的两个波斯使节,全城发布公告征询人选,多次召开公民大会,颇费了一番周折。(37)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前线各位将领为了转移阵地出现意见不一,互相争吵,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持续了一个夜晚。皮塔纳军团首领阿蒙法列图斯竟然公开违抗战场最高指挥官的指令,甚至搬来大石头扔到最高指挥官的脚前。(38)普拉提亚战役之后,时任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斯巴达将领波桑尼阿斯也没有显示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而是很快“米底化”了。波桑尼阿斯按道理应该接受了阿高盖教育,而且他得以担任年幼国王的摄政,应该顺利通过了教育考核,是坚守斯巴达准则的代表;然而他的迅速蜕变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斯巴达教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阿高盖教育。
其三是“军队超一流”。一般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黑劳士问题成为斯巴达社会的重要问题,斯巴达不得不全面实行军事化教育,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从而建立起一支超级强大的军队,斯巴达凭借这支军队在古风时代后期成为希腊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和霸主。因此,超一流的军队和希腊霸主身份成为斯巴达教育军事化的另一个佐证。实际上这个推论并不成立。首先,黑劳士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39)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则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40)。古风时代后期斯巴达军队的强大另有原因:一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政治上推行了具有民主色彩的改革,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激发了公民的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的领土增加了约一倍,通过分配新征服领土,斯巴达公民总数和军队人数也大为增加。当时斯巴达的公民兵人数约为一万人,出自庇里阿西人的军队数量不少于此数,每个公民兵还有大约7名黑劳士作为辅助士兵,军队总数近十万人。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仅次于斯巴达的城邦是阿尔戈斯。约在公元前490年,阿尔戈斯因为6000名公民兵死于斯巴达远征而无力维持统治,奴隶乘机夺取政权。(41)可以想象,斯巴达军队的数量优势在当时的伯罗奔尼撒乃至整个希腊世界何其庞大。
总而言之,斯巴达作为古希腊城邦之一,古风时代的教育并没有偏离古希腊教育发展的一般进程,与同时代的希腊世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古典时代的斯巴达教育
古典时代中期之后,斯巴达教育与雅典教育(或希腊教育的普遍模式)分道扬镳,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最早的史料来自普鲁塔克,他说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诗人西蒙尼德斯就称斯巴达人是“听话的乖宝宝”,因为他们从小受到比其他城邦更严格的管教,养成了遵纪守法、服从、忍耐的性格。(42)这大概是第一次间接提到斯巴达的教育。然而,普鲁塔克没有转引更多的内容,所以,不知道其他的内容是不是普鲁塔克自己的附会和延伸。第一则明确的史料来自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30年雅典举行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说:“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从孩提时代起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英勇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危险。”(43)这里伯里克利首先把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模式对立起来,显示出两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其次,伯里克利还告诉我们,这个差异的关键是斯巴达实行了严格、残酷的训练,而雅典则是宽松自由的教育。笔者认为,这里的“残酷训练”与早期的竞技体育的艰苦不一样,而应该是因应当时斯巴达的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军事性的训练。
突出军事内容的教育可能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普鲁塔克明确说到公元前399年即位的阿吉西劳斯曾经接受过阿高盖教育。(44)阿吉西劳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44—前360年,如果斯巴达儿童7岁进入学校,那么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最晚应该在公元前440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但最早可能也不会早出太多。因为,据修昔底德的介绍,作为阿高盖制度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内容——裸体训练其实出现得很晚。斯巴达人最早实行裸体竞技运动,在裸体运动之后用橄榄油遍擦全身。但这不是古老的制度,此前就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赛选手也要系一条腰带。就在数年之前,这个习惯才被摒弃。(45)这里的“数年”应该是相对于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而言。修昔底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24年之后开始写作,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参照点。也就是说,全身裸体的竞技最早应该出现在公元前460年前后,那么阿高盖制度也应该出现于这个时期。
在这之后,斯巴达教育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与军事有关的内容更为强调。据公元前5世纪末期希腊知识分子的总结,整个斯巴达国家制度的军事色彩都很浓。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提波戎最早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特征总结为“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目的”,并指出这是斯巴达建立霸业的主要原因。亚里士多德还说,持这一观点的不是提波戎一人,而是许多人。(46)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称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就像一个军营,管理优良,公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它的管理者。(47)所有达到军龄的公民都致力于战争,不从事其他任何职业。(48)他还指出:斯巴达教育强调体育训练,注重培养战争所需的勇敢和团结品德。(49)柏拉图称斯巴达年轻人从小就过军营生活,接受特殊的教育,不仅是好战士,而且适宜管理国家。(50)统治阶级终生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51)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52)斯巴达的立法与克里特一样着眼于战争,(53)其城邦组建得像一支军队,而不像一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54)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斯巴达的政制以战争和克敌制胜、建立霸权、获取财富为目的;(55)同时明确指出,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都是以从事战争为目的,(56)对少年进行严酷的训练。(57)这些作家大多从总体上强调国家制度的军事化,只有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教育以战争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能太过认真,当然,教育制度也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也许从这一点认为斯巴达教育以战争为目的。另外,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赞同柏拉图等人的观点,且没有详细述及教育内容,所以,不能以亚里士多德一人的观点取代其他人的观点。综合考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前460年之后,斯巴达教育中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大大增加了。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知识分子对斯巴达教育的具体内容很少提及。其中内容最丰富、可信度最高的是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古典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年限在7—30岁,分为三个阶段:儿童组(paides,7—12岁)、少年组(paidiskoi,12—18岁)和青年组(hēbōntes,18—30岁),这个年限明显长于雅典。尽管雅典和斯巴达的青年在生理上都是18岁成年,但雅典青年18岁之后就完成了教育,成为合法公民;而斯巴达青年尽管在18岁也完成了教育,但要等到30岁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
在这三个阶段中,在第一阶段,雅典与斯巴达的教育内容其实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斯巴达的体育课程可能更丰富。(58)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二、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伊索克拉底甚至声称他们连字母都不认识,(59)这当然有些夸张;普鲁塔克则总结斯巴达的文化教育时提到:“至于读书识字,仅仅只学到够用而已。”(60)事实上,斯巴达的文化教育并不真如伊索克拉底所言的那么落后,但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确实大大增强了。不过对具体的体育科目古典史料记载较少,色诺芬提到摔跤、奔跑、狩猎(20岁之后),(61)柏拉图提到拳击。(62)其他的训练内容我们无从知晓,只能从当时希腊世界的一般性的体育锻炼去想象,可能包括了赛车、拳击、摔跤、赛跑、投标枪、射箭、角力、跳远、掷铁饼等。当时斯巴达教育中的体育训练可能分量很重,效果也很好。色诺芬称斯巴达要求12—18岁的少年不停地做事,连续地工作,“逃避责任者则将会被褫夺将来可能享有荣誉的权利”(63)。这些训练“使得双腿、双臂和脖颈得到了同样的锻炼”(64)。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在希腊世界首先强化体育训练,后为各国所仿效。他批评当时的希腊各邦在儿童青春期之前就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这种批评理所当然应该包括斯巴达。他还称斯巴达对儿童进行严格甚至野蛮的训练。(65)
生存训练可能是这一时期比较独特的内容,这种训练主要包括光脚走、穿薄衣(每年只有一件衣服)、吃简餐。(66)普鲁塔克还提到“睡草床”(67),这一点可能在色诺芬生活的时代已经实施,只不过为色诺芬所忽视。生存训练中更有名的要算“窃食”。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提到为了解决儿童的果腹问题,斯巴达允许儿童窃取食物,甚至认为窃得的食物越多越好。(68)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还提到,斯巴达贵族从小就练习偷窃,不以为耻,而以偷得法律所不禁止的东西为荣。(69)普鲁塔克则说是趁看护者不注意或睡觉时偷窃。(70)可以看出,这种窃食不是一般的偷窃行为,而是经过人为设计的训练科目,有相关的“法律”作为准则,有“看护者”参与实施。“窃食”表面上看与战争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希腊世界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早出晚归、当天或几天就能结束的,而是要长期在外作战。在当时几乎没有军事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远征在外的将士必须自己解决饮食,偷窃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战场求生的技能之一,色诺芬的远征军就经常靠这种方法解决饮食困难。波尔、科奈尔等人认为,这种窃食(包括独立巡行)实际是成年礼的一种,发生在举行成年礼的阿尔特米斯祭坛旁,在罗易卜丛书的英译本中还特别加上“从阿尔特米斯祭坛”的字样。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混淆了两者不同的“窃食”活动。
第三阶段是斯巴达特有的教育“制度”。这个阶段的斯巴达青年人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受教育任务,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公民,因此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被色诺芬认为仍然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中具有军事色彩的活动主要有“秘密巡行、猎杀黑劳士、模拟战争”等。必须指出,这些活动不是人人都必须接受或参与的“必修课”,而是“选修课”,只是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参与。
“秘密巡行”又称作“库普提亚”制度(Crypteia),是古代斯巴达饱受争议的教育科目,主要记载见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注释家的作品。综合他们的介绍,笔者试图在此勾勒出秘密巡行的轮廓:斯巴达埃伏尔(监察官)每年都要选派部分(通常是最谨慎的)年满18岁的青年,携带最简单的武器和生活装备,甚至不携带任何装备,来到边境、山区,或潜入黑劳士区,独立生活大约一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自己克服饥饿、寒冷和物资短缺等困难,更要注意隐蔽自己,以免被野兽、陌生人、外敌或黑劳士发现甚至杀害。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制度目的的认识不一样,前者认为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道德修为,更强调活动本身;(71)而后者更强调这种制度的统治功能,即通过“猎杀黑劳士”加强对黑劳士的统治,“秘密巡行”只是手段。(72)对这种差异,杜卡特认为此时的希腊世界可能对这种制度有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是亲斯巴达的,忽视了“猎杀黑劳士”这部分内容;另一种是反斯巴达的,强调了这部分内容。(73)
作为“秘密巡行”组成部分的“猎杀黑劳士”既是一种教学项目,更是对黑劳士实施的政治制度,它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实施。这种制度有三个要件:它是对国内黑劳士长期、随意的屠杀。但是这种制度如果要作为长期实施的、“课程化”的制度几乎不可能。正如霍德金森指出黑劳士实际上属于公民私有。(74)对黑劳士长期、随意的杀害势必影响到公民的个人利益,势必遭到其主人的反对,同时也必然加剧国内矛盾,大大增加统治难度和政治成本,因此这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实施。杜卡特提出最可能的实施时间是在公元前360—前330年,(75)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只能是推论。笔者认为更可能的时间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首先,这时候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矛盾极为紧张;其次,战争结束时双方曾经签署和约,斯巴达同意参加起义的黑劳士移民境外,如果留在国内,一旦被发现将被拘为奴隶;(76)最后,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曾经暗杀了2000名黑劳士,(77)普鲁塔克将这一事件作为猎杀的例子。(78)因此,“猎杀黑劳士”更可能是追捕那些逗留或潜伏在国内曾经参加过起义的黑劳士,普鲁塔克正确地指出,这种猎杀只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才实施。(79)从总体看,“猎杀黑劳士”是在特定情况下实施的政治统治,但是执行猎杀的主要是年轻人,这种活动对帮助年轻人获得杀死敌人的技能有一定的帮助,从这个角度看,它也可算作“教育”。
古典作家对“模拟战争”多有记载,但形式彼此不同。根据色诺芬的记载,斯巴达青年年满20岁之后,埃伏尔就在他们中间选出三位队长,每位队长再从中各自选拔100人,分为三组,他们见面之后经常互相格斗,但是他们必须听从在场的长者的劝阻,不得无休止打斗。(80)普鲁塔克则称斯巴达在12—18岁的儿童之间组织模拟战争。(81)波桑尼阿斯曾经介绍斯巴达每年在帕拉塔涅斯塔斯(Platanistas,意为“平坦的小树丛”)举行大规模的模拟战争,他们手脚并用,甚至用牙齿猛烈进攻对方,把对方推入壕沟中。(82)西塞罗认为这简直就是战争。(83)从历史年代来看,色诺芬属于同时代的人,其可信度最高;普鲁塔克的记述颇接近于色诺芬,但没有任何细节;波桑尼阿斯的可信度最低;科奈尔甚至认为波桑尼阿斯描述的这种活动发生在罗马时代。从色诺芬的叙述中可知,参加模拟战争只是部分年满20岁的青年,战斗的激烈程度也不像波桑尼阿斯所说的那样血腥残忍、以死相搏。
总体看,古典时代初期斯巴达教育中确实增加了军事训练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与斯巴达自身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崛起,日渐成为斯巴达的竞争对手。恰在此时,斯巴达自身实力遭到削弱。公元前465年斯巴达遭遇严重的地震,地震给斯巴达国力以严重打击。据史书记载,斯巴达城内住房只剩五间(84),儿童死亡尤重(85),死亡人口达到20000人之多(86)。黑劳士则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乘机发动起义(史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起义加剧了斯巴达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斯巴达的国家力量。雅典乘机在希腊半岛本土发展势力,首先与科林斯发生矛盾,公元前460年,发生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前445年)。尽管斯巴达国力削弱,但也不得不在公元前457年、前449年两次出兵中希腊,阻击雅典的扩张。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雅典,斯巴达并没有获得优势。到公元前446年,雅典控制了麦伽拉、科林斯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抢占了佩盖、厄庇道鲁斯、特洛伊曾等地,雅典海军还在斯巴达海岸线边耀武扬威。在国力下降和公民人数减少、战争威胁日渐加剧、传统霸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斯巴达加强对仅有的公民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为当然又无奈的选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加强了教育活动中的军事色彩。
但是,对这一时期斯巴达教育的军事化程度不可高估。实际上,军事训练并没有占据教育活动的主体,斯巴达教育并没有成为赤裸裸的纯军事化的教育。首先,这一时期的古典作家对斯巴达教育强调的不是军事技能的训练,而是这些训练对提升道德水准和培养特殊品德的价值。例如,色诺芬强调这一教育模式培养了斯巴达公民的吃苦耐劳、谦逊内敛、爱国守法(色诺芬称之为“服从”)的品德。柏拉图称斯巴达的这套制度旨在培养公民崇尚荣誉、吃苦耐劳、节制忍耐的品德。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的观点,但他不欣赏斯巴达的这一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教育出来的斯巴达公民不会忍耐,不会休闲,不会享受和平。尽管他的观点隐含着尚武好战、穷兵黩武的含义,但亚里士多德没有明说。普鲁塔克的观点与色诺芬相似,但更强调爱国守法的品德。
其次,斯巴达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完全停止。古典时代,底比斯诗人品达、开俄斯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都曾经为斯巴达撰写诗作。修昔底德声称伯拉西达绝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87)他的演讲水平绝不亚于雅典的那些演说家,只是其内容更简短、更有说服力。斯巴达也不乏智者派的活动,只不过人数不及雅典那么多,实际上,智者希庇亚曾经在斯巴达获得成功。(88)戎马倥偬的莱山德(?—公元前395年)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而且在临死之前留下来一部构思斯巴达政治改革的作品,(89)国王波桑尼阿斯流亡之际曾经对斯巴达的历史进行总结,这部书成为古代作家了解斯巴达历史的重要著作。前文已述,希罗多德认为所谓“斯巴达人不热心学习”纯属无稽之谈,这个总结不仅适用于古风时代,同样适应于古典时代。他还指出,实际上在希腊人当中只有拉开戴蒙人在与人交谈时是十分谨慎的。(90)其实,“谨慎”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就包括“智慧”的含义。普鲁塔克说:“斯巴达人交谈虽然简短,但确实有力、中肯,能抓住听者的思路;斯巴达人绝不信口乱说,绝不冒失地说出思想苍白或不能引人注意的毫无意义的言辞。”总之,热爱智慧胜过热爱健身运动是斯巴达人与众不同的特点。(91)
斯巴达的音乐、舞蹈在古典时代依然蜚声希腊。据修昔底德记载,曼提尼亚战役时,斯巴达军队按照常规,和着众多长笛手的军乐缓慢前进。(92)普鲁塔克称,在战斗开始,长笛手吹赞赏卡斯托尔的曲调,国王领唱进军凯歌,全体士兵和着长笛的节奏行进。(93)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11年上演的喜剧《利西斯特拉》结尾处告诉我们,雅典青年男女为了感谢神灵,跳起了常在优拉托斯河边表演的歌舞。(94)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研究,斯巴达至少有三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佛里基亚、多利亚和吕底亚音乐。相对而言,佛里基亚音乐更为古老,相传与佩罗普斯一起传入斯巴达。(95)多利亚音乐是在佛里基亚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两种音乐都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赞赏,(96)但吕底亚音乐则受到他们的抨击,认为是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吕底亚音乐据说是由泰尔潘达带来的,他曾经用八弦琴演奏,这说明吕底亚音乐与八弦琴有关系。相传公元前5世纪,克里特音乐家提摩特乌斯还在斯巴达用八弦琴演奏,这说明吕底亚音乐一直在斯巴达流传。公元3世纪的作家雅典尼乌斯称,斯巴达人是希腊人中音乐艺术保存得最好的,他们一直在表演这些节目,并且有许多作家,“这些作品一直保存到现在(即公元三世纪——笔者注),而且还在表演”(97)。
对古典时代希腊作家关于斯巴达政制军事化的记述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冷静。这些作家大多数是雅典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前半期。当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雅典知识分子都希望为雅典复兴寻找灵丹妙药,他们又都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从人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基于此,他们认为雅典失败、斯巴达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国家国民品德、国家制度不同,前者自由奔放,后者谦逊守法,这种品德更类似于“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品德。进而,他们将斯巴达的这一道德状况与斯巴达社会强化军事训练的教育体制联系在一起,将斯巴达制度中的这些成分的意义人为放大。如“窃食”这一仪式在萨摩斯也存在,(98)却未见讨论,但斯巴达的这一“制度”(实际是一种习俗)就被加以追捧。最后,他们将这种被他们人为扭曲的斯巴达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视为雅典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总而言之,古典时代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军事训练的内容。但无论从历史实际看,还是从古典作家的论述看,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一时期的斯巴达教育制度已经蜕变为旨在培养职业军人、专注于军事技能教育的军事教育体制。
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的阿高盖模式
公元前4世纪中期,斯巴达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首先是斯巴达公民队伍瓦解迅速,非公民人数激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玛斯还宣称在重装步兵和人口方面占优势。(99)但到公元前4世纪70年代,斯巴达公民人数骤降为一千人左右(100)。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短缺导致了斯巴达帝国崩溃。(101)但斯巴达人口短缺并不是绝对人口短缺,而是相对短缺,实际上,在有限的公民队伍之外,存在有大量没有公民权的所谓“下等公民”(hypomeiosi、Monthakes)(102)。
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不仅公民贫困化,国家也贫困化了。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之后,斯巴达被迫恢复了城邦自治原则,原先建立在对海外属邦剥削基础上的国家财政开始坍塌。公元前370年,斯巴达在底比斯的打击下,国家一分为二,西部的美塞尼亚独立,斯巴达国家财政几近破产。公元前364年,为了获取钱财缓解国难,年届八旬的国王阿吉西劳斯参与了波斯地方总督反叛活动,(103)公元前361年,他甚至亲自率雇佣军前往埃及,以赚取酬劳,最后虽然赚得200塔兰特,却死于回国途中。(104)积困积弱的国家难以给普通公民提供生活支持,充当雇佣军成为破产公民重要的职业选项。
公元前4世纪,雇佣军已经成为斯巴达国家军队的重要来源。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前315年、前303年,斯巴达国王阿吉西劳斯、阿基达玛斯三世、王子阿克罗塔图斯、王叔克利奥涅姆斯(Cleonymus)先后率军远赴埃及、塔拉斯(位于南意大利)、西西里、塔兰顿(Tarentum)。(105)他们所率军队的主体都是雇佣军。充当雇佣军已经成为贫困的斯巴达公民的主要出路。据狄奥多罗斯记述,当时伯罗奔尼撒聚集了很多人等待雇主,泰纳鲁姆(Taenarum)实际上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雇佣军“超市”。公元前322年,北非昔兰尼的将领提波戎派人前往泰纳鲁姆招募雇佣军,很快就招募到2500名雇佣军(106)。公元前315年,马其顿将领亚里斯特戴姆斯(Aristdemus)到拉科尼亚招募了8000名伯罗奔尼撒人做雇佣军。(107)公元前303年,克利奥涅姆斯前往塔兰顿之前在泰纳鲁姆招募了5000名雇佣军、20000名公民兵(108)。直到公元前255年,迦太基还邀请斯巴达人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担任本国军事指挥官,抗击罗马军队。(109)
公元前4世纪轻装步兵逐步取代重装步兵。希腊军队以前以重装步兵为主,打仗时行动迟缓。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斯进行改革,使用更长的矛和枪、更轻便的盾牌。(110)公元前391年,伊菲克拉特斯凭借这支军队打败了斯巴达,消灭斯巴达重装步兵约600人。(111)轻装步兵开始取代重装步兵。新的兵种带来了新的战术、新的问题,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方阵阵型的保持更难了,战争中时常需要长途奔袭、战略迂回。这些对士兵的战术素养和身体机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也对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轻装步兵、雇佣军成为两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斯巴达教育向比较严格的军事化教育转型。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斯巴达的史料相对短缺,我们对这个转型只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测。可以想象,这时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合格公民,而是培养合格的雇佣军;教育内容方面军事技能的内容势必大大增加。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生存第一,他们也不太可能继续热衷于文化学习,古典时代本已弱化的文化教育势必进一步削弱。如果说斯巴达的教育是一种完全着眼于军人培养,那么最大的可能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期间,传统的“国家办教育”的模式可能遭到进一步冲击。不可否认,在某些强势国王,如阿吉西劳斯统治时期,国家办教育可能得以延续。但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一模式受到较大的冲击。公元前4世纪,主要是因为国力羸弱,国家有心无力,而到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国家办教育的“心”可能也没有了。在这一时期,此前形成的较为严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都被废弃了。据称,阿柔斯一世(Areus I,公元前309—前265年)统治非常强势,他仿效希腊化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国王,铸造货币、在和约上签字、接受荣誉雕像、放弃“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112)他的儿子、继承人阿克罗塔图斯二世(Acrotatus II,公元前265—前262年)与他相似。据菲拉库斯(Phylarchus)描述,阿柔斯和阿克罗塔图斯时期,斯巴达违背了传统的简朴生活方式,追逐波斯的奢华生活,公餐团实际上废止了,居室的装修考究了。(113)普鲁塔克在叙述阿吉斯和克里奥墨涅斯改革的背景时,称所有的公民都过着放荡腐败的生活,置公益于不顾,热衷于私利和享受,传统的政体早已被废止。(114)可以想象,一个一心贪图享受、没有远大志向的统治集团不可能再去接受以前那种艰苦的教育,由国家去操办那种统治集团不愿参加的教育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古典时代的斯巴达教育制度在这时期中止了。但是,笔者认为,由雇佣军头领组织的“民间教育”并没有平息,甚至更加“繁荣”。这套特殊的“教育”就是要培训受训者的战斗技能,获取一技之长。可想而知,这一来自民间的草根“模式”必然会大大增加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对后来斯巴达的教育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元前3世纪后期,阿吉斯四世、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和纳比斯先后实行改革,(115)正是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孕育出典型意义上的阿高盖制度。这场改革名义上是恢复斯巴达历史早期的莱库古制度,但在实际上,“恢复旧制”只是一种口号,制度创新才是这场改革运动的本质特征。(116)纵观前后相续的三次改革,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即“恢复霸权”。三位国王采取的核心措施是组建强大的军队,其他的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一目的,如土地改革、经济改革、释放黑劳士、大力宣传军人品德、加强军事训练等;前三点表面上看与“强兵”没有直接关联,但其真正目的是增加公民人数,增加兵源。教育改革是这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服从于“增强军力,恢复霸权”的改革目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三次改革的史料较少,教育改革方面的史料同样如此。但可以肯定,这种由强势国王推行的教育改革本身使得斯巴达教育重新成为“国家化的”教育。
具体教育改革内容方面,据普鲁塔克介绍,阿吉斯三世(公元前245—前241年在位)恢复了斯巴达古老的法律和传统教育,阿吉斯以身作则,弃绝一切奢华和享乐,带头穿粗布衣服,完全遵守拉科尼亚的饮食、沐浴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拉科尼亚式的“苦行”。普鲁塔克这里直接用agoge来指称斯巴达教育。(117)属于公元前240—前229年的一份昔尼伽派哲学家特勒斯(Teles)的演讲称,当时许多接受斯巴达教育的非斯巴达人都支持阿吉斯的扩大公民权的法案。特勒斯也用“agoge”一词指称斯巴达教育。这表明,这时期斯巴达已经恢复了agoge制度。(118)但是,阿吉斯其他的教育创新不得而知。
相比较而言,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成就更明显,记述也相对多一些。对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这次改革斯多噶色彩很强。斯多噶哲学家塞法鲁斯(Sphaerus)实际是这次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119)斯多噶哲学认为人的根本属性在于道德品性,而人的主要品德是智慧、勇敢、正义、节制,(120)勇敢成为位列第二的品德。这一思想自然会通过塞法鲁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二是克里奥墨涅斯改革的强兵色彩更浓。教育改革必然会服从于这一更高层面的改革要求。在公民队伍几乎荡然无存的形势下,克里奥墨涅斯组建了一支人数达4000人的新军。(121)这支军队大多是在阿吉斯四世之前出身,在阿吉斯改革中重新获得公民权,但他们没有受过阿高盖教育。为了提升战斗力,克里奥墨涅斯必须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据记载,在克里奥墨涅斯的军营中没有戏子、艺人、舞女和歌手,他们远离放荡、淫乱和宴饮,大部分时间用于训练。(122)这种“新军”训练主要针对成年人,但“新军”思想却渗透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尽管普鲁塔克对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一笔带过,但是仅有的叙述恰恰揭示了克里奥墨涅斯教育改革的实质,他说克里奥墨涅斯恢复儿童训练和公餐团、“回归原有的习性和纪律”(123)。这种改革的目的其实是要造就一支具有军人品德和战斗技能的“预备役部队”。
纳比斯改革主要见于波利比乌斯、狄奥多罗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对纳比斯的教育改革记述很少。不过,纳比斯改革的目的仍是“增强军力,恢复霸权”。他曾经在阿尔戈斯取消债务、分配土地,(124)纳比斯还广泛招募流亡人员,组建军队,增强军事力量。(125)通过这些改革,纳比斯大肆扩张,一度占有阿尔戈斯、美塞尼亚、麦伽拉波利斯等地。可见,纳比斯的内政外交与阿吉斯四世、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基本一致。那么,作为克里奥墨涅斯强军主要举措的教育改革也应该有所体现,可惜,古典作家没有留下在这方面的直接记述。
除了上述直接记述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资料窥知这时期斯巴达教育变革的一些内容,这些资料很多来自罗马作家。笔者认为,这些罗马作家的记述,特别是他们宣称亲眼所见的一些内容,主要反映了阿吉斯改革之后的斯巴达教育。因为,如前所述,在阿吉斯改革之前,斯巴达教育曾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改革之后的教育制度虽然在公元前188年被阿卡亚同盟所废止,但很快又恢复了。(126)我们再没有资料证明此后直到罗马征服,斯巴达教育制度发生过重大变化,可见,这一制度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并为罗马人所了解。大多数罗马作家所见所闻的斯巴达教育制度主要是改革之后的制度,只有普鲁塔克等少数作家广泛收集古代史料,其记述可作例外。
从罗马作家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斯巴达教育还有如下新特征。首先,教育的军事化色彩更强了。公元1世纪初期的罗马作家查士丁(Justin)称,卢卡尼亚人(Lucanians)的教育制度与斯巴达相似,其目的都是为了战争。(127)这与提波戎、柏拉图所说“斯巴达国家制度的目的是培养军人品德”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再一次明确指出斯巴达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但他所说的“为了战争的教育”应该属于更晚时期的制度,这从他对库普提亚制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库普提亚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巡行者不带任何东西,而亚里士多德则称携带简单的武器和少量必备物资;二是不带奴仆,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儿童上学有仆人做伴,这种伴侣被称作mothone,当时的莱山德、基利普斯都做过mothone。(128)如此看来,查士丁所说的以战争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应该晚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更可能属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改革时代。
其次,教育计划,尤其是对少年的训练计划更为详细。我们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尼(129)的《论年龄组名称》中看到:色诺芬所称的少年组(paidiskoi)大致上被分成了六组,每个年龄组都有特殊的名称,依次为rhōbidas(14岁)、promikizomenos(15岁)、mikizomenos(16岁)、propais(17岁)、pais(18岁)、meleirēn(19岁)、eirēn(20岁)。(130)这个分组与色诺芬相似又不同,显示了时代特征。阿里斯托芬尼生活在公元前257—前180年,他的这段话反映的应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形。如此细致的命名可以想象很可能每个年龄都有相应的教学内容。但是,这种细致的命名在古典时代从未见过。
最后,罗马作家提到的某些极端的训练科目在此时可能比较普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鞭打比赛。金麦尔(Jeanmaire)、波尔(Boer)和科奈尔(Kennel)等人认为鞭打比赛是斯巴达特殊的成年礼。(131)但是这种观点是从比较人类学的角度,无法说明这一仪式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另外,它是利用其他民族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得不到古典文献的支持,古典作家虽然提到这一现象,却没有人认为它是成年礼。古典作家中色诺芬最先提到“鞭打”,(132)但那是在窃食时对被发现者的惩罚,不是独立的训练项目。柏拉图也提到“鞭打”,称它可以培养忍受身体痛苦的美德。(133)但从上下文看,这种鞭打可能与色诺芬一样,属于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亚里士多德称当时斯巴达的训练比较野蛮,但没有说到这种鞭打。但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西塞罗说:斯巴达的儿童在祭坛上接受鞭打,甚至流血。他甚至听说有人被打致死也没有哭喊或求饶。(134)公元1—2世纪的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约46—120年)也记述了这一事件,普鲁塔克则说他曾经亲眼见过斯巴达青年在阿尔特米斯祭坛被打死。(135)他还解释说,这个仪式是为了纪念普拉提亚战役中在战前占卜时恪守战斗岗位而牺牲的战士。(136)这种“鞭打”与色诺芬、柏拉图所说的鞭打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随意而为,而后者则有了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成为固定的教育科目。这种制度化的“鞭打”可以回溯到改革年代。
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秘密巡行”、“猎杀黑劳士”很可能也恢复了。史料记载克里奥墨涅斯在与阿卡亚同盟作战时库普提亚军队的首领德摩特勒斯(Damoteles)曾经叛变投敌。(137)可见,作为秘密巡行执行者显然存在,那么这一制度当然也应该恢复了。古希腊历史学家米隆指出,斯巴达规定:“如果任何一个黑劳士表现出超越奴隶以上的神情,那就要被处死,而且他的主人也将因为未能阻止他变强壮而受到处罚。”(138)这个材料来自米隆的已经散佚的著作《美塞尼亚史》,因为缺少上下文,我们不知道它实施的范围和时间。但米隆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他所说的这种情况更可能反映公元前3世纪的情形。波利比乌斯对纳比斯的“暴行”的叙述也具有“猎杀”的痕迹,他说,纳比斯不满足于驱逐公民,他对部分被流放者派人跟踪,并于半途杀死他们,另一部分人则在他们流放回来之后杀死他们;他还派人租下与流放者住所紧挨的房子,把克里特人安插到这里,这些家伙打破墙壁,从窗口射箭,将流亡者杀死在自己的家中,不管他在休息还是在劳作。(139)这种行为很可能是被波利比乌斯扭曲的“猎杀黑劳士”的行为。
阿吉斯、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普鲁塔克甚至声称,斯巴达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教育方面的改革取得的成效显著。(140)在以强兵强国为目的的改革中,教育改革实际是军事改革的组成部分,恰恰在两个国王统治时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斯巴达在军事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据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在公元前227年实行改革,公元前225年就恢复了昔日的霸权。(141)公元前192年,纳比斯凭借这支军队一度控制阿尔戈斯、美塞尼亚,多次攻击阿卡亚同盟所在地麦伽拉波利斯,引起罗马和阿卡亚同盟的恐慌。斯巴达的迅速崛起说明,其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是多么成功,而在成功的背后,教育的作用不能忘记。正因为如此,公元前188年,阿卡亚同盟军队在罗马的支持下攻入斯巴达,迫不及待地强制取消了斯巴达的教育制度。(142)这说明,此时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与军事的关系何其紧密,教育制度的军事化程度何其彻底!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所知的比较典型的阿高盖制度应该属于斯巴达历史上的“改革年代”,是阿吉斯、克里奥墨涅斯、纳比斯等政治家增强军力、恢复霸权、振兴斯巴达的措施之一。
纵观斯巴达教育发展史,古风时代的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城邦。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公民人数下降、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斯巴达教育发生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化,加强了对公民的军事化教育。公元前4世纪中期,斯巴达国力下降,公民普遍贫困化,充当雇佣军成为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斯巴达社会生活和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企图重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强化军事训练,造就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成为实力不济的斯巴达的当然选择,斯巴达教育中军事教育超过了文化教育,成为典型的阿高盖教育模式。罗马统治时期,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逐步发展成为与角斗性质相同的公共娱乐项目,(143)失去了公共教育的作用,其形式尚存,但实质已变。总而言之,“军事教育”并不是整个古代斯巴达教育的基本特色。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重视体育”在古代斯巴达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尽管这种重视后来演进为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但“重视体育”对斯巴达军队战斗力和国家实力的提升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梁建东、章颜结合音译和意译,称之为“够格者训练”,卡特里奇著,梁建东、章颜译:《斯巴达人》,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页。
②菲利普·内莫著,张竝译:《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③萨拉·B·波默罗伊等著,傅洁莹、龚萍、周平译:《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2、500页。原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1994年之前,25年的时间内英语世界没有一本新的古希腊史方面的专著,因此,该书民主角度上反映了西方最新学术动态,而书中关于斯巴达教育体制特点的叙述大致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当今的普遍观点。著名的斯巴达史专家卡特里奇也称阿高盖制度由莱库古建立,目的是培养合格的战士。
④卡特里奇著,梁建东、章颜译:《斯巴达人》,第9页。其他还可参考托马斯·R.马丁著,杨静清译:《古希腊简史》,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5页。
⑤J.C.斯托巴特著,王三义译:《光荣属于希腊》,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9页。
⑥菲利普·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第63页。
⑦卡特里奇著,梁建东、章颜译:《斯巴达人》,第9页。
⑧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著,张强等译:《探寻古希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7页。
⑨克里奥墨涅斯三世改革发生在公元前228年至前222年之间。
⑩L.J.皮佩:《斯巴达的衰落》(Linda J.Piper,Spartan Twilight),新罗彻勒1986年版,第54页;本雅明·席默荣:《晚期斯巴达》(Benjamin Shimron,Late Sparta),布法罗1972年版,第26页。
(11)N.M.科奈尔:《美德健身馆》(Nigel M.Kennell,Cymnasium of Virtue),北卡罗里那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页;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Jean Ducat,Spartan Education),斯汪斯2006年版,前言部分;S.霍德金森:《古典时代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Stephen Hodkinson,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伦敦2000年版,第434页。
(12)N.M.科奈尔:《美德健身馆》,第7页。
(13)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多重视角下的斯巴达教育》(“Perspectives on Spartan Education”),S.霍德金森、安顿·帕维尔主编:《斯巴达新视角》(Stephen Hodkinson & Anton Powell eds.,Sparta New Perspectives),伦敦1999年版,第52页。
(14)卡特里奇在《斯巴达式教育》一文中持类似观点,认为古代斯巴达的教育基本不变,特别是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基本相同。P.卡特里奇:《斯巴达式教育》(Paul Cartledge,“A Spartan Educmion”),《斯巴达反思》(Spartan Reflections),伦敦2001年版。
(15)本文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借用了古代希腊史分期的概念,大致上古风时代是约公元前750—约前500年,古典时代是指约公元前500—前338年,希腊化时代是指公元前338年—前30年。斯巴达作为享有实际政治权力的城邦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之后就终止了,所以,笔者认为斯巴达城邦的历史应该止于公元前146年。
(1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69年版,I.80。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32年版,11271b10—17。
(18)祝宏俊:《斯巴达的税收制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9)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Xenophon,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Lacedaemonian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56年版,II.2,5;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莱库古传》(Plutarch,Lives of Lycurgus),洛布古典丛书,伦敦1998年版,XVII.2。
(20)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VI.5;XVII.1。
(21)M.格里菲斯:《早期希腊教育中的公共与私人行为》(Mark Griffith,“Public and Private in Early Greek Education”),Y.L.托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Y.L.Too,ed.,Education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莱顿、波士顿、科隆2001年版,第23—84页。
(22)凯瑟林·弗里曼:《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辅助读物》(Kathleen Freeman,Ancilla to the Pre-Scratic Philosophers),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23)F.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8页。
(24)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25)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IX.1。
(26)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e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VI.70。
(27)希罗多德:《历史》,V.42。多里欧斯是斯巴达著名国王克里奥墨尼斯(约公元前520—前490年在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笔者注
(28)例如,雅典将军阿里斯提德就曾经帮一个连“阿里斯提德”都不会写的文盲填写过选票。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传》,VII。
(29)希罗多德:《历史》,IV.77。
(30)弗格森著,晏绍祥译:《希腊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页。
(31)奥斯温·莫里:《早期希腊》,第163页。
(32)西蒙·霍恩布鲁厄、安东尼·斯泡福斯:《牛津古典辞书》(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页。
(33)雅典尼乌斯:《宴饮中的智者》(Athenenus,The Deipnosophist),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25f。斯巴达的琴原来只有四根弦。——笔者注
(34)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253页。
(35)J.V.A.芬:《古希腊人》(John V.A.Fine,The Ancient Greek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66页。
(36)埃利安:《历史杂集》(Aelian,Historical Miscellan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XII.50;普鲁塔克:《道德论集》(Plutarch,Moralia),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79A。
(37)希罗多德:《历史》,VII.134。
(38)希罗多德:《历史》,IX.53—55。
(39)黑劳士社会地位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详述。读者亦可参考拙文:《“美塞尼亚”问题研究》,《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
(40)祝宏俊:《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41)希罗多德:《历史》,VI.73—83,VII.148.关于阿尔戈斯阵亡人数,波桑尼阿斯的记载是5000人(波桑尼阿斯:《希腊纪事》, III.4.1.),普鲁塔克的记述是7777人(普鲁塔克:《道德论集》245),但此说很可能不准。——笔者注
(42)普鲁塔克:《阿吉西劳斯传》(Plutarch,Lives of Aegsilau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I.2。
(4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39。
(44)普鲁塔克:《阿吉西劳斯传》,I.1。
(4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6。周厄特(Joweet)的译本称裸体竞赛不是古老的传统,是直到最近才开始的。——笔者注
(4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3b10ff。提波戎在史书中记述很少,色诺芬在《希腊史》(III.1.5;IV.8.17;IV.8.18—19)中提到一位同名的军事将领,这两位提波戎很可能是同一人。
(47)伊索克拉底:《阿基达玛斯》(Isocrates,Archidamu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395页。
(48)伊索克拉底:《布西里斯》(Isocrates,Busiri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113页。
(49)伊索克拉底:《泛雅典娜节演讲辞》(Isocrates,Panathenaciu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507页。
(50)柏拉图:《法律篇》(Plato,Law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66e—667a。
(51)柏拉图:《理想国》(Plato,Republic),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547d。
(52)柏拉图:《理想国》,548a。
(53)柏拉图:《法律篇》,628e,633a。
(54)柏拉图:《法律篇》,630d—631a。
(5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365—16。
(5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4b5—9。
(5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8b10。
(58)卡特里奇:《斯巴达式教育》,第85页。
(59)伊索克拉底:《泛雅典娜节演讲辞》,第501—503页。
(60)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VI.6。
(61)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V.9。
(62)柏拉图:《法律篇》,633b。
(63)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II.2—3。
(64)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I.1,3;IV.7。
(6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8b12—39a10。
(66)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I.3,4,5。
(67)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VI.7。
(68)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I.8—9。
(69)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4页。
(70)普鲁塔克:《道德论集》,237E。
(71)柏拉图:《法律篇》,633b。
(72)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XVIII.2。
(73)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第306页。
(74)霍德金森:《古典时代斯巴达的财产和财富》(Stephen Hodkinson,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伦敦2000年版,第114页。
(75)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第304页。
(7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03。
(7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V.80。
(78)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XVIII.3。
(79)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XVIII.。
(80)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V.6。
(81)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VII.2。
(82)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us,Description of Greece),洛布古典丛书,III.14,8—11。
(83)西塞罗:《托斯坎纳论集》(Cicero.Tusculanae Disputationes),V.27.77。
(84)埃利安:《历史杂集》,VI.7.2。
(85)普鲁塔克:《西蒙传》,(Plutarch,Lives of Cimon),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XVI.4—5。
(86)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Diodorus of Sicily,The Library of Histor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XI.63.1,3。
(8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V.84。
(88)柏拉图:《大希庇亚斯篇》,284a—286b。
(89)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90)希罗多德:《历史》,IV.77。
(91)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IX.1,2;XX.5,6。
(9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70。
(93)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XII.3。
(94)优拉托斯河是纵贯拉科尼亚的河流,优拉托斯河边的舞蹈则是指斯巴达表演的舞蹈。这说明当时斯巴达的歌舞在雅典也大受欢迎。——笔者注
(95)雅典尼乌斯:《宴饮中的智者》,625f—626a。
(96)柏拉图:《理想国》,399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42a30。
(97)雅典尼乌斯:《宴饮中的智者》,632f。
(98)希罗多德:《历史》,III.48。
(9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81。但此时斯巴达的公民人数显然少于公元前465年大地震之前,阿基达玛斯之所以宣称不缺人口可能是在此前斯巴达大力鼓励生育,一批青年人开始迅速补充到公民队伍中来。——笔者注
(10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30。
(10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30。
(102)色诺芬:《希腊史》,III.3.6;H.密希尔:《斯巴达》(H.Michell,Sparta),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88—91页。
(103)色诺芬:《希腊史》,VII.1.27ff。
(104)普鲁塔克:《阿吉西劳斯传》,XXXVI—XL;奈波斯:《外族名将传》,第173—175页。
(105)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XX.105—106。
(106)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XVIII.21.1。
(107)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XIX.60。
(108)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XX.105—106。20000名公民兵不一定全是斯巴达公民。
(109)波里比阿:《通史》(Polybius,Historie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23年版,I.32.1。
(110)奈波斯:《外族名将传》,第115页。
(111)色诺芬:《希腊史》,IV.5.11—18。
(112)本雅明·席默荣:《晚期斯巴达》,第6页;P.卡特里奇、A.斯波福斯:《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斯巴达》(Paul Cartledge,Antony Spawforth,Hellenistic and Roman Sparta),伦敦1989年版,第35页。卡特利奇著,梁建东、章颜译:《斯巴达人》,第219页。
(113)雅典尼乌斯:《宴饮中的智者》,142b。
(114)普鲁塔克:《阿吉斯传》,(Plutarch,Lives of Agi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II.6;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Plutarch,Lives of Cleomene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III.1。
(115)阿吉斯四世约在公元前243—前241年实施改革,克里奥墨涅斯三世约在公元前228—前222年实施改革,纳比斯约在公元前207—前192年实施改革。——笔者注
(116)如阿吉斯四世改革中建立的公餐团每团200—400人,而传统只有30人。普鲁塔克:《阿吉斯传》VIII.2;《莱库古传》, XII.1。
(117)普鲁塔克:《阿吉斯传》,IV。
(118)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前言部分;科奈尔:《美德健身馆》,第12页。
(119)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I.2。
(120)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121)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I.2。
(122)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II.3。
(123)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I.2;XVIII.4。
(124)李维:《历史》,XXXII.38。
(125)波利比乌斯:《通史》,XIII.6—8。
(126)大多数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80年就恢复了,但科奈尔认为是在公元前146年斯巴达在罗马支持下获得自由城市身份后恢复的。相关讨论可参考J.杜卡特:《斯巴达教育》,前言部分,第10—11页;科奈尔(Kennell):《美德健身馆》(Gymnasium of Virtue),第9—10、173页注释24。
(127)查士丁:《历史摘要》(Justin,Epitome),XXIII.1。
(128)埃利安:《历史杂集》,XII.43。
(129)拜占庭人,约生活在公元前257—180年,公元前194年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牛津古典辞书》,第165页。
(130)科奈尔:《美德健身馆》,第39页。
(131)W.D.波尔:《拉科尼亚研究》(W.Den.Boer,Laconian Studies),北荷兰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261—274页。
(132)色诺芬:《拉西第梦人政制》,II.9。
(133)柏拉图:《法律篇》,633b。
(134)西塞罗:《托斯卡纳论集》,II.34。
(135)普鲁塔克:《莱库古传》,XVIII.1。
(136)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传》,(Plutarch,Lives of Aristide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XVIII.8。关于普鲁塔克诉说战役的细节,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IX.61。
(137)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XVIII.3。
(138)雅典尼乌斯:《宴饮中的智者》,657c—d。
(139)波利比乌斯:《通史》,XIII.6。
(140)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VIII.4。
(141)普鲁塔克:《克里奥墨涅斯传》,XVIII.4。
(142)普鲁塔克:《菲勒波门传》(Plutarch,Lives of Philopoemon),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6.5;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VIII.51.3;李维:《罗马史》(Livy,The History of Rome),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XXXVIII.34.1—3。
(143)N.M.科奈尔:《美德健身馆》,第6、49页。
标签:斯巴达论文; 色诺芬论文; 雅典论文; 斯巴达教育论文; 军事化管理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希腊化时期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体育训练论文; 教育目的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