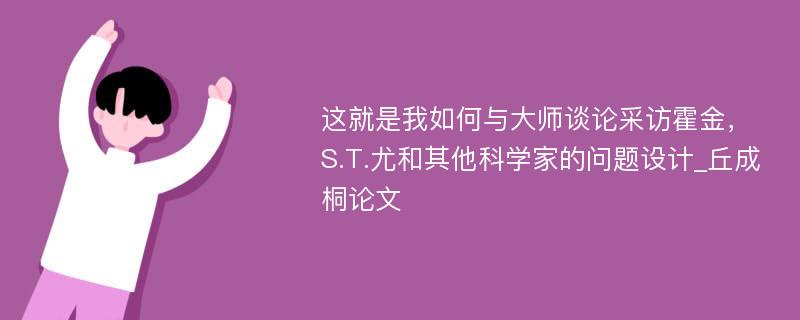
我这样与大师对话——采访霍金、丘成桐等科学家的问题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金论文,科学家论文,采访论文,大师论文,丘成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8月9日至16日,世界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来到杭州,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弦理论国际会议。参加弦理论会议的还有著名华裔科学家、费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威腾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在这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我按照报社领导“尽可能多地向总部发回独家报道”的指令,共向总部发回了16篇专稿,近2万字,另有十几张新闻照片,基本上全部被总部采用,并作了突出处理。文章见报后,受到了报社内外的广泛好评。
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不少同行问我:怎么能写出那么多稿件?又是如何与这些著名科学家对话的?我的答案是:提前准备,认真思考,熟悉对方,提读者想知道的问题。
新闻已经发生
我的准备在霍金到杭州的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7月10日前后,浙江大学新闻办给我发来一份传真,说浙江大学将承办国际数学家大会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面列出了一大批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及会议的大体日程。我发现名单中有霍金、丘成桐、威腾等一大批世界级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在日程安排中有霍金举行公众演讲的内容,并有一次答记者问的机会。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新闻已经发生,即使预告霍金来华,也会成为读者关注的新闻。于是,我立即寻找有关霍金的资料,写了一篇内涵充实、富有可读性的新闻稿《等待霍金》(文汇报见报时将标题改为《霍金要来了》)。
这在全国性大报中是首家披露霍金来华的消息。国内多家媒体转载了文汇报的报道。
霍金乐意回答我的提问
随后,浙江大学新闻办给我打来电话说,考虑到霍金的特殊情况,希望媒体记者将8月11日霍金会见记者时向他提的问题提早交给浙大新闻办,由浙大汇总后交给霍金,并由霍金选定回答哪些问题。
我已经获悉,霍金会见记者的时间是1小时左右,粗粗合计一下,从记者提问到翻译成英文,霍金回答后再翻译成中文,每个问题至少5分钟,1小时内可以回答的问题就是10个左右。霍金的到来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到场采访的记者一定很多。因此,要想争取到向霍金提问,就一定要把问题设计好。
我设计了好几个问题,霍金是如何对理论物理产生兴趣的;他的“黑洞辐射”的灵感是何时产生的;与爱因斯坦和牛顿相比,霍金理论的优势在哪里;他又是如何想到写《时间简史》的,等等。但都被我否定了。因为这些问题我在写《等待霍金》一稿时已经搞清楚,在网上有详尽的资料,属于明知故问。我能够看到的资料,其他人也一定看得到。我于是换了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霍金的疾患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除了三个手指能动,有特强的思考能力,有面部表情外,全身几近瘫痪,连转一下头的能力都没有。而他的科学成就也是超乎常人的,他提出的黑洞辐射理论已经被科学界认同,他写的《时间简史》已经连续13年列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他撰写的《果壳中的宇宙》刚出版就获得安万特科学图书奖,他的演讲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快乐,除了科学上的成功,还有什么能使霍金产生快乐?这个问题是读者关心的,如果霍金回答,可以让读者了解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我于是通过浙大新闻办向霍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霍金先生,您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您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也是超越常人的,除了享受科学研究成功的快乐之外,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8月9日霍金抵达杭州后,我最关心的就是霍金是否乐意回答我的问题。霍金对问题的选择十分慎重。中国的记者向他提出了80多个问题,而他只能回答其中的10个。一直到8月11日下午2时,他才基本选定愿意回答的10个问题。两个小时后,当他面对记者准备答问时,又临时决定对其中的两个问题不予回答。而我的问题他则乐意回答。几乎所有媒体的报道都选用了霍金回答我问题的答案。霍金回答我说: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我从音乐和我的家庭得到巨大的快乐。
霍金与我的答问为我当天的新闻稿增色不少,这是我们的“独家新闻”,也是读者最愿意了解的一个问题,而且富有人情味。此稿受到了报社领导的嘉奖。
网上搜索
稿件见报后,总部很快给我作了反馈:读者希望了解霍金喜欢哪些音乐,他又是如何与人交流的?
其实,第一个问题我在霍金答记者问时就已经提出。在自由提问时,我向霍金夫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主持会议的丘成桐先生表示,霍金太太事先已经与他约定不回答记者的提问。事后,丘成桐先生与我们几位记者一起在西湖边喝茶时告诉我两个细节:霍金不但喜欢音乐,而且还在家中和着音乐的节奏坐着轮椅跳舞;霍金观看了浙江大学安排的文艺晚会,在演奏《黄河协奏曲》时,他流了泪。丘先生的话使我心头一热,双眼一片模糊。我于是再在网上搜索。那段时间,我除了通读《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外,还至少在网上浏览了有关霍金的20万以上的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一个网页中看到了一位英国女记者与霍金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霍金介绍了自己最喜欢的9部音乐曲目。
后来,我在《走近霍金》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位把霍金请到中国来的费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先生)后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对我的问题作了一些补充:霍金很喜欢音乐,甚至在音乐声中摇着自己的轮椅与家人跳舞。他对音乐的熟悉程度绝不比常人低,帕伦克的《格罗里亚》,勃朗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披头士的《请你让我快乐》以及反映中国古代公主悲剧的《图兰多》,是霍金常听不厌的曲目。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大致花去了我三四个小时的网上搜索时间。
在霍金答记者问时,在与丘成桐先生和吴忠超先生(《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的译作者、霍金的中国弟子)聊天时,我已经了解到霍金与人交流的过程。我在《走近霍金》一文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悄悄绕到了主席台的边侧,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霍金的“操作”,面对记者的提问,霍金总会默默地沉思一会儿,然后开始启动他的遥控器。遥控器拿在霍金的右手中,他按动其中的一键,固定在轮椅上的电脑屏幕中便出现了一些英语单词,此刻,霍金的眼特别有神,他的大拇指不断地按动着,词变成了词组,词组又变成了句子,大拇指又一按,声音便从扬声器中发出,我们听到的是典型的美式英语,声音清晰,抑扬顿挫。
我想,有了这样的描述,读者可以如见其人。
曲院风荷话科学
与霍金的对话因为有较大的“提前量”,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选择,更难的是对话时的即兴提问。浙江大学这次为接待霍金、丘成桐等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该校新闻办的同志想我们记者所想,考虑得非常周到,特意安排主流媒体的记者与科学家见了两次面,一次是在湖畔居茶楼与丘成桐先生一起喝茶,一次是在曲院风荷公园内的卓颖舫上与丘成桐等5位著名科学家座谈。前一次喝茶比较宽松,基本上是听丘先生谈。我当天向总部发回了一篇丘成桐先生的专访:《报效祖国是我的最大愿望》,《文汇报》在次日一版倒头条位置刊出,并配发了照片。在卓颖舫上却是让我们提问,请科学家回答。那天参加座谈的除了丘成桐先生外,另4位科学家是: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威腾(E·Witte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D.Gross),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Faddeev),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施维德(A.Stromingen)。
威腾、葛乐思和施维德都不是第一次来华。威腾曾于1998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过庆典活动,并到过北京和上海;葛乐思于1989年来过中国;施维德则已是第四次来到中国,1975年,他曾与另外19位美国青年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参观工厂和农村,到过大寨,并在上海电机厂“体验生活”一个月;法捷耶夫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与来自中国的10多个同学同班共读,数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变化。
座谈自然从霍金的话题开始。几位在场的记者提了诸如“如何与霍金对话”、“与霍金交流是否发生过争论”、“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霍金的黑洞理论”,等等。
我发现,对记者的有关霍金的提问,并非5位科学家都感兴趣,因此,除了丘成桐和施维德(他们是霍金的好朋友)很认真地作答外,其他3位已经“环顾左右而言他”。终于,法捷耶夫说话了:我们都是数学家,能否提一点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而且,对媒体来说,也应该关注“数学”这个话题,毕竟霍金也是来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
我很快进入“绞尽脑汁”之中。数秒钟后,我打破了冷场,向科学家们提出了我当天提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并发明了“勾股定理”等数学公式,这些数学家的发明在世界数学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中国的数学目前在国际数学界所处的地位如何?
丘成桐、葛乐思、威腾和施维德分别就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们表示,中国的数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中国的数学家过于重视应用而忽略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很难对国际数学界产生影响,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太大,不像阿基米德定律那样能持久地得以普及。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太讲求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
我很快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在采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先生时,他打过一个比方:浙江大学已经形成了学科的高原群,现在的任务是要在高原上造峰。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它是孤立的山峰,还是一片高原?它如何与不同的科学相结合?是否会组成新的交叉的学科?
几位科学家对我提出的问题大感兴趣,竞相回答。葛乐思说,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科学的共同语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它与不同学科结合后不会产生新的学科,只会融入到各学科中。法捷耶夫说,基础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预感到其他科学的方向,这种预感带有前瞻性。丘成桐也说,数学与许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如物理学、工程学及现代工业有关学科,吸收各学科的想法。数学不是孤单的一个山头,它融合在群山之中,如果是孤单的山头,数学就不会成功。
在兄弟媒体的记者问及地球爆炸的问题之后,我接着问了第三个问题:当媒体披露“小行星撞击地球”、“地球有可能爆炸”等消息时,身为科学家所持的又是怎样的心态?
科学家们都笑了,他们显然也乐意回答我这个问题。葛乐思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等问题是天文学的范畴,用牛顿力学就可以计算。但据他个人的看法,这种撞击大有可能,这是星球互相追超使然。威腾则表示,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回答,有许多问题他小时候就产生了,到今天依然无法解答。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相反,正是这种好奇心在支撑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科学家们在回答问题时流露出一种对未来中国基础科学的企盼,我于是提出第四个问题:据你们看,哪个年龄段介入基础科学研究为最佳?你们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寄予希望,你们是否愿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
四位科学家回答了我的提问。施维德说,中国的青年会不会成功,还得看他们研究的方向。如果方向对头,他们会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如果方向不对头,一味地讲“应用”,就会进步得很缓慢。丘成桐表示,在浙江大学设立数学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想培养本土化人才。威腾认为,介入基础科学研究年龄越小越好,中国的年轻学生素质不错,他非常乐意与中国学生接触,也乐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跟着名师学,学成后回到中国,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法捷耶夫也表示,他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与10多位中国同学同班学习,他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到俄罗斯去学习,他愿意和中国新一代学者共同研究。
当天晚上,我将我与5位科学家的对话作了详尽整理,并向总部发回了2000余字的专稿。总部几乎一字不删,配照片全文刊出。报社领导就此文给了我第二次嘉奖。
回顾本次对话,我的体会是,你要让对方回答你的问题,就必须让对方对你的问题感兴趣;当对方对所谈的话题稍有不太热情时,必须另选问题。而作为媒体记者,所设计的问题除了是问答双方感兴趣的之外,还应着重考虑两大前提:本报特色和读者口味。当然,这也得益于自己平时的积累。
(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