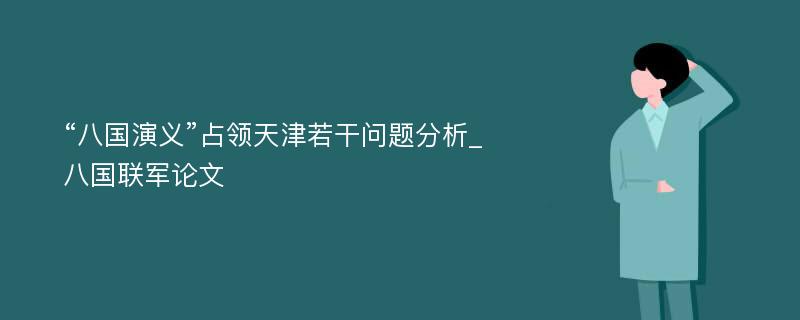
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联军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八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夏季,由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城。7月14日,天津城失守。由此,天津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外国军队占领时期,直到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代表袁世凯接管天津政权为止。这次事件,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被多国军队长时期军事占领的唯一记录,而且还出现了由八国联军组成的占领军政府——都统衙门。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研究,以往因资料的限制,或局限于中外交涉,或仅仅将其视为殖民政权加以批判而已。记录这一时期的权威性史料——《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会议纪要》的出版(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使得我们对这两年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本文主要通过对《会议纪要》的研究,针对这一时期的问题,做一些阐释和考证。
一 都统衙门的建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两天后,也就是7月16日,联军指挥官开会协商恢复城市秩序。俄军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是会议的召集者,他在会上首先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由出兵各国各选派一人组成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对城市事务只有发言权,要另外委任一名总督主持政府工作,掌握行政权。这个方案暴露出俄国人想独揽大权的野心,当即遭到英、日、德3国的反对(注:李德征、苏位智《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8日,召开第二次联军指挥官会议。各国最终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3国委派3名拥有同等权力的军官担任委员,组成临时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则分别由各国派员负责。尽管这一方案获得通过,但是德、法指挥官同时声明,政府的这种组成只是暂时的,随着其来华军队数量的增加,他们保留委派临时政府成员的权利。于是,由俄、英、日3国分别委派沃嘎克上校、鲍尔中校和青木宣纯中佐出任委员组成的“天津城临时政府”成立。
临时政府成立于7月30日,地点设在位于海河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于是,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被称作为“总督衙门”,半个月后确定正式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第10次会议(1900年8月14日)。(以下凡出自此书者,一律简为“第×次会议”。))。在清代,八旗分驻各省,坐镇地方,名为“驻防”,专设将军、都统、城守尉等职官统率。如张家口和热河都统,官阶与将军同样为从一品,其官署称“都统衙门”。统帅八旗的都统同时治理辖地民政,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天津临时政府取“都统衙门”为名,在其发布的中文告谕中,也称临时政府委员为“都统”,表明其为军政府(注:为行文方便,以下称“都统衙门”或“临时政府”,意义相同。)。
按照临时政府建立时公布的“行政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委员应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选举产生”。但是实际上,各国委员均由本国司令官提名,再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成的过程显示出列强之间在政府权力分配上不断发生的矛盾和争斗。8月2日,都统衙门发布第一号中文告谕,宣布临时政府成立,其中提到英、俄、日3国,马上遭到法国司令官的反对。临时政府要求派1名法文秘书,也遭到法国司令官的抵制,提出只有法国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拥有1名委员的前提下才能委派秘书。10月,刚刚抵达天津的德国元帅瓦德西直接通知临时政府,称他要委派1名具有同等权力的德国委员加入临时政府。11月14日,由各国司令官任命、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德国委员法根海少校、法国委员阿拉伯西中校和美国委员福脱少校出席委员会会议,临时政府成员增加到6名(注:第68次会议(1900年11月14日)。)。但是,刚过了10天,意大利海军上将坎迪亚又提出,由于其他6国已经在临时政府拥有代表,意大利理所当然应该派代表参加委员会。1901年4月,卡萨诺瓦海军少校作为意大利委员在临时政府就职。在八国联军中,只有奥匈帝国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当奥军司令官提出派代表参加时,却由于奥国在华军事力量有限,遭到各国的反对而未成。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临时政府,此后临时政府就一直由6名委员组成。
临时政府下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处。各机构为首者,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都是具有专门资格和能力,有的还是久居天津,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外国人,甚至是能讲一口汉语的“中国通”。如担任汉文秘书长的丁家立是久居天津的美国人,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总教习,也曾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卫生局长德博施是一名法国医生,曾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当时正在天津行医。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长期生活在天津,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19世纪末参与海河治理工程。
在都统衙门统治时期,其辖区范围不断扩大。临时政府初建时,管辖区限定在老城以及城外土围墙以内地区。1901年2月,临时政府宣布扩大管辖区,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均纳入其管辖。整个管辖区还被划分为5个行政区。原辖境加上土围墙外25处村庄定为城厢区,其他新扩地区被划分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和塘沽区。除了城厢区以外,临时政府在其他4个区各委任区长1名,并分别由占领该地区的外国军队指派1名尉官担任。区长直接对临时政府委员会负责,没有财政权,但拥有一定限度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权(注:第105次会议(1901年2月8日)。)。
按照清代的行政体制,城市并无专门的政府机构,而是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归属县管辖,政府管理不达县以下。都统衙门按照西方城市行政体制设置,不仅管辖事务远远超出了县衙门,还首次出现了城市行政区的建制。
然而,作为军政府,临时政府并不实行分权或自治体制,而是实行委员会集权制,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根据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以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
从临时政府司法条例以及案件审判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建立的。只是,临时政府不实行司法独立。立法权掌握在联军司令官会议和临时政府委员会手中。司法方面,临时政府设有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但是,各项判决都要经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委员会对法庭的判决有修改权和否决权。按照“行政条例”的规定,临时政府有权判处华人各种刑罚直至死刑,有权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于外国人,则按照治外法权执行,只有权将其逮捕,然后送交其所属国的军事或领事当局审判。
创立警察制度是临时政府法制体系的另外一个方面。临时政府甫一建立,便首先成立巡捕局,着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统。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是由各国军队抽调官兵组成,一部分负责该国军队占领区,一部分组成国际巡捕房负责车站、政府等重要地方。此外由意大利人组成水上巡捕,负责海河等河道的警务。华人巡捕是单独组织,由绅商保举本区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执行警务。城厢地区还被划分为8个治安区,每个区推举6名绅商协助治安管理。“遇有不法情弊”,绅商可以到都统衙门汉文秘书处“禀陈”(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11、23、37、58号。)。临时政府管辖区扩大后,各区每个村庄公举3名绅董充当村正,组织华捕。
传统中国城市秩序的确立和治安的控制,注重依靠社会的力量,衙门在这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当19世纪城市人口大量增长的时候,城市控制方式的滞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陈克《十九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临时政府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这与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强化了。当时,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误认为是监督百姓(注:“明系保民,暗系查看津民动静”(储仁逊《闻见录》,稿本)。),但这却是警察“站岗”维持交通、治安方式的肇始。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巡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地区外,警察最早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同时出现的还有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各国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临时政府制定的税收章程,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注:第32次会议(1900年9月10日)。)。临时政府设置了4处征税的税卡,还将张燕谋的“庆善银号”设为“官银号”,作为政府纳税处。临时政府对各项捐税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实施严格的管理。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税收制度建立后,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公共工程得以实施。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结余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
二 镇压义和团
临时政府成立后,镇压义和团成为首要的任务。当时,仅明确记录在案,经过审判公开处决的义和团就达数十人,各区巡捕抓获并就地处决的义和团还不算在内。各国联军从外地抓获的义和团,有的也交给临时政府处死。杀害义和团民的刑场大都设在义和团活动比较活跃的西门外,而且都是处以斩首的极刑,其至还将砍下的头颅悬挂示众。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在被德国军队从保定擒获后也解到天津,交由都统衙门处决于北门外并悬首北门示众(注:第78次会议(1900年12月5日);“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26号。)。都统衙门还与各国占领军配合,到各村庄清剿义和团。联军清剿义和团的根据地——静海独流镇时,都统衙门还专门发布告谕,威胁其他村庄如果“蹈此复辙,亦照此法办理”(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11、23、37、58号。)。
然而,对联军俘获的女义和团民,临时政府则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有两名义和团女首领被八国联军俘获后关押在都统衙门(注:《俄国人在远东》,第180页;《到北京去》,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1097页。)。临时政府委员会经过专门讨论后,决定将她们押往上海,交由天主教会看管。1901年4月,两名女义和团民被送往上海,交给圣约瑟教会的神父,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看管(注:第133次会议(1901年4月17日)。)。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政府一直向上海天主教会提供她们的抚养费。在天津政权归还之前,临时政府委员会提出由上海天主教会将两名女义和团民交给上海清政府地方当局。
按照其他记载,红灯照首领林黑儿和三仙姑被八国联军俘获并一度关押在都统衙门。关于她们的下落有种种传说,有的说被解往国外(注: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杨家骆《义和团文献汇编》(二),鼎文书局,第56页。),有的称逃到乡下隐居。尽管还没有确切资料证明这两名女义和团就是林黑儿等红灯照首领,但是上述记载为解开这个历史疑案提供了新的线索。
为了防范民间的反抗,都统衙门严禁百姓拥有武器。临时政府一成立便发表告谕,要求百姓限期将持有的军械上缴巡捕局。为此,临时政府委员会还专门做出决议,禁止华人拥有武器和弹药。1900年12月27日,临时政府再次发表告谕,限定5日内将军械交到都统衙门,如逾期不交,一经查出,军械没收,私藏者一律斩首(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11、23、37、58号。)。此后,凡藏有武器或持械犯罪者,无论轻重一律处以斩刑。在都统衙门统治期间,因此而被处死者不下数十人,有的甚至不问罪行轻重,只要持有武器,即被处死。临时政府还将鞭炮列入武器弹药之列,禁止出售和燃放。
与此同时,驻扎天津的各国军官和士兵却可以任意到机器局、军械所拿取清政府储存的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似乎把获得武器视作征服者的标志,有的用作防身武器,有的作为纪念品。都统衙门的餐厅也摆放着来自清政府军械库中的武器,作为所谓的战利品。直至1901年6月,临时政府才对此加以控制。
三 城墙及其他军事设施的拆除
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直至沿海的军事设施一律被摧毁,天津的城墙也被拆毁。都统衙门是这些行动的主要执行者。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提出摧毁华北沿海一带尤其是天津地区的各种军事设施。1901年4月6日,在瓦德西主持下召开的各国联军司令官会议列出了要摧毁的军事设施清单,其中多数位于天津地区(注:刘心显、刘海岩译《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在7月的联军司令官会议上,决定由临时政府负责摧毁天津地区的军事设施(注:刘心显、刘海岩译《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
最早拆毁的是天津东、西机器局和西沽武库。19世纪,天津曾是北方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基地。建于1867年的西机器局,主要生产枪炮,建于1869年的东机器局主要生产弹药,1873年建成的西沽武库则是大型军火库。1901年1月,德国军队首先摧毁了西沽武库,尽管这时联军司令官会议还没有做出决议。东机器局的机器设备被拆除后,连同储存的弹药,一部分被卖给开平矿务局和外国洋行,其余全部被销毁。该地也成为法国占领军的驻防兵营。虽然西机器局没有被列入要摧毁的军事设施清单,但是在联军占领后,机器局中储存的武器以及机器设备、原料和零件等,被分别卖给外国洋行,有的出口到亚洲以外,机器局也成为日本占领军的兵营。从此天津的军火工业不复存在。
在海河两岸,从大沽口到天津城,分布着多处炮台,是清政府军事防御的主要设施,自然也成为八国联军摧毁的对象。由临时政府实施拆毁的炮台,除了黑炮台以外,还有中营、大围子、前营和后营等炮台和兵营,此外还有大沽海河口、北塘、新城等处的炮台和兵营等。
按照列强的要求,天津地区以外的炮台等军事设施要由清政府负责拆除。但是,1901年10月,联军司令官会议又决定将拆除芦台、山海关等处炮台也交由天津临时政府负责。临时政府为拆除这些军事设施投入了17万元。
拆除炮台大都是通过招标由承包商承担。为了拆除山海关炮台,临时政府还专门从天津招募苦力甚至派囚犯前往从事拆除。1902年6月,北方流行霍乱,在山海关拆除炮台的苦力中有霍乱流行,不少苦力逃亡。直至临时政府解散,山海关炮台拆除工作仍未能最后完成。
拆除天津城墙是临时政府委员会首先提出来的。1900年11月,委员会“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提议拆除天津城墙,并很快得到了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注:第84次会议(1900年12月20日)。)。1900年12月,临时政府工程局首先开始从西侧试拆城墙。1901年1月21日,临时政府发布拆除城墙的告谕(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11、23、37、58号。)。拆除工程也采取承包的方式,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注:第146次会议(1901年5月17日);第151次会议(1901年5月31日)。)。临时政府提供1万元和1万袋大米作为拆墙费用,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和地皮归临时政府。
天津是第一个拆除城墙的中国城市。虽然到了19世纪,城墙的传统防御功能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城市发展迅速,城墙成为交通的最大障碍。尽管如此,城墙是城市传统的标志和象征。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没有城墙的城市是人们一时无法接受的。因此,当都统衙门拆除城墙时,天津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待的。城墙被占领者拆除,无疑是城市的耻辱。然而,另外一方面,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4条马路,成为老城区的交通干道,改变了城市交通状况,市民明显感到给交通带来的便利(注: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卷6上、卷6下、卷7上、卷7上。)。当时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边的道路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的变化
西方市政制度与管理的引进,使得这一时期天津城市建设有了一些发展,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一般认为,有轨电车是1906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建成的。事实上,1900年都统衙门刚一成立,就有欧洲人和日本人分别向临时政府提出修筑电车的申请(注:第4次会议(1900年8月6日);第5次会议(1900年8月8日)。)。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优先获得专营权,声称此前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1898年,中日划分日租界的谈判中,清政府曾同意日本在划分给他们的海河码头与南门之间,建造一条马车铁路(注:《天津日本租界条款》,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9页。)。但是,直至1900年,这项计划并没有实施。最终,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获得了有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日本人不得不退出了竞争。
老城区供应自来水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出的。1901年3月,3名中国商人和买办出面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要求给予特许经营权。他们的申请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还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注:第118次会议(1901年3月13日)。)。然而,这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却是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美国人田夏礼以及德商瑞记洋行。公司注册由瑞记洋行出面,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以致该公司开办后实际上成为一家外资公司(注:李绍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在1902年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把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均作为要求清政府必须接受和执行的条件。袁世凯接管政权后,与两家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
此外是城市照明的出现。天津最早的路灯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英租界,老城区的路灯照明则是1900年以后出现的。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要安装一盏路灯(油灯),安装和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注:第72次会议(1900年11月22日)。)。于是,老城区开始有了路灯。“大街小巷各门旁皆要悬灯一盏”,“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注: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卷6上、卷6下、卷7上、卷7上。)。翌年2月,临时政府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筹划由政府安装路灯(注:第293次会议(1902年5月12日)。)。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达成协议时,临时政府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若干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
这一时期,老城区还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电话系统。电话在天津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期,当时一些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了电话。但是,电话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1900年以后的事情。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西文名称为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注:第107次会议(1901年2月13日):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list, 1902, Shanghai, 1902。)。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为临时政府各机构、巡捕房、医院以及主要官员家中安设电话。夏季汛期,临时政府利用电话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清政府接管政权后,由盛宣怀筹建电话局。1905年,官办的天津电话局成立,以白银5万两收买了濮尔生的电报局,濮尔生则被聘为电话局顾问,从此天津的电话改由政府专营。
20世纪初也是天津城市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19世纪,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城市管理的失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天津老城区人口已经超过20万。排污设施的落后、垃圾处理方式的缺失,以及人们法制、道德观念的滞后,使得城市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的随处便溺习惯。
19世纪,天津城没有公共厕所,人们在街上或公共场所习惯于随处便溺。城内外还设有多处粪厂,直接用人粪尿制成肥料,供应乡村。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给数十万人口的城市造成恶劣的环境问题。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2元(注: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卷6上、卷6下、卷7上、卷7上。)。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注: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卷6上、卷6下、卷7上、卷7上。)。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至郊外。这些强制性措施促使了城市环境的改变。
城市垃圾处理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城市生活垃圾几乎就是随处倾倒。1901年3月,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政府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注:《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附录一: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第5、11、23、37、58号。)。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违反这些规定者会被外国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罚(注:储仁逊《闻见录》,卷6上、卷6上、卷6下、卷7上、卷7上。)。与此同时,由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这些,使城市卫生状况发生了改观。在随后的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开始设置卫生局、卫生巡捕等,城市卫生管理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
发生变化的还有城市排水系统。直至19世纪,天津城区排水系统仍然是传统式的结构,技术上一直没有任何改进。加上多年失于维护,缺乏严格的管理,导致多处阻塞,是城区环境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注:《直报》,1895年3月8日。)。城墙拆除后,护城壕和城内污水坑相继填平,城市排水更成为问题。临时政府没有采用政府投资修建下水道系统,而是利用民间集资或投资的方式。他们制定强制性措施,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工程设计要经过临时政府公共工程局审批,如果验收工程质量高,临时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有的私人公司也开始参与城市排水系统的投资与建设。1902年,德国人汉纳根成立的“大广公司”——也称“汉纳根洋行”,提出修建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方案,得到委员会的同意(注:第286次会议(1902年5月2日)。)。该洋行以占用政府土地为条件,承担老城区南部的排水系统建设。按照临时政府同意的方案,他们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被称为“蓄水池”的排污池,老城区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经由专门水道排入海河下游。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才被彻底改造。
1902年6月,天津发生的一次流行性鼠疫,促使了城市防疫制度的建立。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主要在城北区蔓延。临时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冰镇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领取许可证才能掩埋,并由政府专门雇用的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注:第300次会议附件(1902年6月6日);储仁逊《闻见录》。)。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临时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工等严厉处罚。
当时,临时政府还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铺主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
此外,临时政府时期,还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并计划在老城区进行人口普查。不仅组织了专门的机构,拟定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注:第288次会议(1902年5月7日)。),为人口普查做各项准备。只是由于政权很快移交,这次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1902年8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交涉,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了天津政权,都统衙门解散。随后,北洋新政的推行,种种社会变革使得天津城市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都统衙门长达两年的军事殖民统治,使天津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对这段特殊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种种的变化,本文仅仅根据新出版的史料作简单的评述,许多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历史毕竟是连续的,正是在这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新的技术和西方近代市政制度传入天津,对随后而来的北洋新政,对城市的变革与发展,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