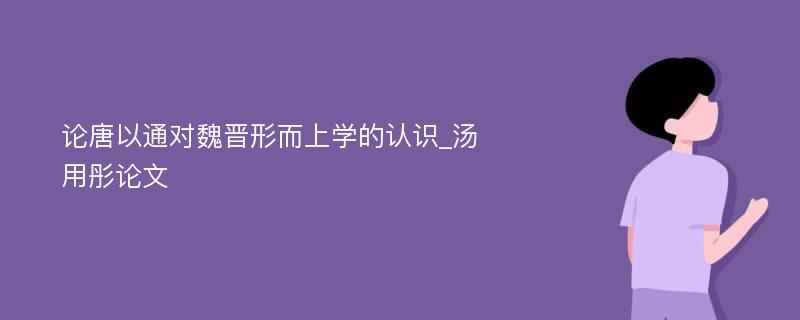
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魏晋论文,论汤用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作者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的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二)理解或解释中的二重矛盾
汤用彤20世纪30至40年代醉心玄学,与他寄心于玄学去关怀国家、民族、文化甚至人生大问题的努力有关(注:参见麻天祥及孙尚扬的汤用彤评传中,对汤先生家学渊源及早年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参与《学衡》杂志社活动、至哈佛师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等的介绍。)。他立志“融合新旧,撷精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由于他自小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60页。),所以,其学说的建树无疑是致力于从哲学上发古哲潜德之幽光,以重体学理之助人驱心至驭身之作用。佛学固然是一种具驭心驭身大作用的玄远之学,但于中国切身的问题解决而言,汤用彤认定,“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注:汤用彤:《理学谵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3页。)理学之形上学特质与佛学有关,而更追溯远一点说,起码中国佛学作为玄远之学的驭心驭身作用,与玄学的影响分不开(注:汤用彤将儒家理学与魏晋玄学关联起来考虑的做法,可在任继愈先生对自己一篇早期论文的写作渊源的追思中,得到旁证。任继愈先生在《理学探源》(刊于《燕园论学集——汤用彤先生九十诞辰纪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一文中,提到文章是在汤用彤的指导下做成的。重刊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使人联想起四十多年前某些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梦想‘学术救国’艰难前进的状况。”(《燕园论学集》第302页)任的论文共分八节,一、绪论,二、理学之渊源,三、汉代中印思想之调和,四、魏晋玄学之建立与本末问题,五、南朝之佛性问题,附夷夏问题及神不灭问题,六、隋唐四宗,七、唐宋之际儒佛之交融,八、理学之兴起。任强调,“本文所论为探研理学之渊源。”(《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302页)任继愈概述说:“宋兴百年儒学复振于五代禅学鼎盛之后。袭魏晋之玄风,承孔孟之余绪,于理气性命心体善恶之问题作一空前之总结束,内之如心性之源,外之如造化之妙,推之为修齐治平,存之为格致诚正,无不尽其极致。两宋以迄清末,八百年来哲学界逐为理学所独擅,岂为偶然?然亦须如此固一种思想之自然演进,非为被动,亦非自葱岭带来也。”(《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307页))。正是为求明有这样一种妙用的学说的真面目,汤用彤开始他对玄学的深悟妙发(注:孙尚扬的评论。在此评论前,他转引了一段贺麟记载的、汤用彤的哲学界定:“真正高明的哲学,自应是唯心哲学。然而唯心之心,应是空灵的心,而不是实物化或与物对待之心。”氏著:《汤用彤》第205页。)。但50年代起他中断了这种研究(注:按麻天祥及孙尚扬二位先生的汤用彤传记,汤用彤原本企图对其40年代以来系统讲授的玄学,作一体系的总结。1947年汤用彤赴美加利福尼亚大学讲课,课程《汉隋中国思想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from Han to Sui Dynasty)中,主要内容也是魏晋玄学。参看麻天祥《汤用彤评传》及孙尚扬《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7卷相关英文讲义。)。他晚年的日子里,佛学研究,并且是考证性的研究,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笔宝贵遗产。他不是个喜记自己心路历程的人,他对玄学研究的中断究竟何因,无从考证。但其魏晋玄学研究中,从不同角度对正始玄学与竹林玄学,还有元康玄学的比较和评论(注:参看汤用彤各种魏晋玄学研究著作中,对竹林玄学一系的评论。),也许对我们理解他的玄学研究中断之原因有所帮助吧。
撇开汤用彤玄学研究中断的原因不说。汤用彤通过其玄学理解,尤其是其对玄学与儒家经典解释关系的理解,仍给儒家经典解释中,解释以致宏志、经世的努力,留下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解释本身的目的与方法之关系的问题。
如果解释的存在,真如狄尔泰所言,具从自由、及普遍之意义开发精神科学研究的功能的话,那么,也就如他提醒的那样,企图从解释对象中发掘或唤起超越个体存在之狭隘性的意义,就不是解释中理性方法,所能力担的重任。他所谓归纳方法中,体现的对解释对象意义的再创造和再体验,可谓与王弼所倡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注:参看[德国]威尔海姆·狄尔泰(W.Dilthey)著,李超杰译:《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选自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5月1版)。)。
但问题是,任何解释,包括经典的解释,对于解释者来说,目的不只是为了发掘对象的意义,尤其是对象在普遍品格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意义。而“得意忘言”的方法,如不是为人文意义寻找的目的作工具的话,也还自有其它的用处。另外,如果太过强调解释中非理性的意会及再创造和再体验,那解释中理性的规范和限制,又如何能保证解释者对对象的解释不是虚,借解释对象而发自己的新义才是实,甚至进一步说,如何保证解释者不是将自己的思想强说是解释对象的新义呢?
第二,从儒家释经的目的来看,述志,无非是为了经世致用。但对经典的“述志”解释尚且不能保证完全克服解释者个人的随意性,那么,与其相附的体用理论,又何尝不是玄远之寄心与行事之实迹矛盾重重?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甚少直接讨论儒士或佛学家对玄学理论的批评。尽管或者这不是汤用彤的有意疏忽,但却与汤用彤先生对哲学的期待相关。如魏晋玄士一般,汤用彤先生企图通过对经典的解释,开发玄学(哲学)救心以至救身的奇妙功用。
毋庸置疑,哲学确与根本问题的认识相关。但根本问题的如何解决,却又相关于具体情境下的具体的人。如果说根本问题的认识,某种意义上,可以是自然、不偏的话,那么,根本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完全是“无为”和“无累”的。过分地强调根本问题的认识与根本问题的具体解决,是可能一致的话,只会导致认识本身及认识作用之期待的自相矛盾。
实际上,从历史中关于魏晋玄学的作用及其定性问题的种种批评里,可以说:1.玄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并不如魏晋玄士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真正克服汉儒的弊端,弘儒家大道。相反,被认为太过玄远,缺乏儒家理想之鲜明的价值立场,缺乏切实地处置人事与物象的具体作为,而与儒不相同(注:作者论文《归本崇无》最后一部分,对此种评论稍作介绍。);2.魏晋玄理的弘发,本就意味着与具体行迹有自觉区分。这种自觉的结果,当然是对人生、社会、文化等之中超越时空限制的终极问题的关注。但这种关注由于没有彻底与对现实政治和人生的关怀分别开来,所以,玄学有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意味,可是不具备宗教意义的终极意味。(王弼的“适变”与郭象的“独化”等都有别于佛家的“顿悟”和“寂静”。)(注:事实上,汤用彤先生在其玄学分期及其汉晋佛教研究中,已触及这个问题。参见《汤用彤全集》第4卷。)
但不管怎样,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仍然给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标签:汤用彤论文; 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玄学论文; 魏晋论文; 庄子论文; 孔子论文; 理学论文; 儒道论文; 道家论文; 佛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