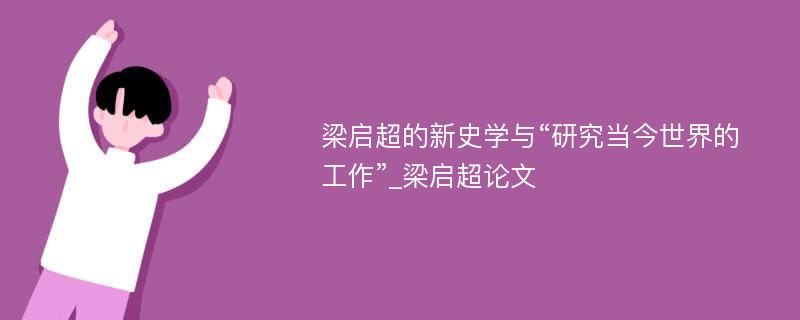
梁启超新史学与“究当世之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世论文,史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因震惊于甲午一役而奋起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曾在多处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①本世纪初他在日本举起了“新史学”大旗:“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②
“不得已”三字,表明了史学革命与救国之间的相互关联,昭示了史学创新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可或缺,说明了一生都在“究当世之务”③,都在摸索中国近代化道路,并在本世纪初一度取得“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④的梁启超,何以矢力追求新型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
基于梁启超既是近代化的先驱又是“新史学的元祖”这一事实,透过梁氏一生活动探讨“究当世之务”与倡导新史学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探讨“究当世之务”如何孕育、催生乃至限定史学创新活动,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工作。
(一)
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国人对外部(西方)世界压力的一种反应而出现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⑤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外部挑战所引起的民族生存危机,来自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比较”。
“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⑥一向唯我独尊的中国,逐渐被打入弱者、贫者、劣者的行列,面临着“为天行大圈所淘汰”⑦的威胁。于是,在中国,就渐渐萌生向被视为强者、富者、优者的西方学习的愿望,产生打破本社会封闭循环传统、变法维新的要求和行动。变法维新的愿望,社会近代化的要求,使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推出的“新史学”在骨子里首先表现为“进化史”,不管后来如何曲折起伏地变化。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⑧
民族危机及“比较”产生了另一个基本的后果:近代民族意识的诞生。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就认为,“民族是历史的主脑”;⑨他把整部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时期(上世史,黄帝至秦之一统)、“亚洲之中国”时期(中世史,秦一统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国”时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华民族之成立发展之迹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贯穿全史的主线。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梁氏继续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⑩
近代国家(国民)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相伴而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致弱的总根源。梁氏一贯认为,在近代世界,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主于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11)
在传统观念中,“国”一般等同于具体的某王朝、某皇室,而“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12)梁氏在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畅快地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13)这样,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就取代了以帝王为主体的传统国家观念。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活动的主体已是国民而不再是帝王将相了。相应地,历史研究和史学服务的主要对象也必须转移,即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国民。早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就发出了对“民史”的频频呼唤;(14)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史叙论》中,梁氏为中国过去不曾写出“国民发达史”而“不胜惭愤”;在《新史学》中,梁氏猛烈抨击以前史家“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批判传统的“正统论”,并明确指出,“统也者,在国非在君,在众人非在一人也”,决心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能普及于国民”;(15)在二十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氏更明确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16)
所以,梁启超提倡历史研究必须包括“民间风俗”,包括传统史学所缺乏甚或“所厌忌”的“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17)必须注意“民间文明的进步”;梁氏努力提倡史家应拥有“社会学的根柢”,运用“社会学者的眼光”,提倡对“无文字”、“无意识”的重视。梁氏很重视“普通人物”和“多数人的活动”,指出“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18)
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维新活动,是前无古人的。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绝的“中央大国”之中。他们努力使这个原先闭关自守的中央大国适应、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潮流之中。对于一个维新者来说,整体历史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梁氏的整体历史观,既包括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念,又包括一国历史不可间断的观念即“通史”的观念。从戊戌时期的“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19)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20)梁氏的这种整体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可贵的是,梁氏的整体历史观还包含了社会(文化)整体历史的观念。
摆脱政治史传统的束缚,打破传统政治史的垄断地位,一直是梁启超的一个基本愿望。本来,康梁一班“国内有心人”闯入历史大舞台是为了改良政治制度。但是,政治改革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限制而至失败。梁启超日益感觉到政治并非孤立,政治改革决不能脱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或变革。民国初年共和政治实践的失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即脱离社会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故对改革家来说,社会(文化)整体的观念具有基本的重要性。这种观念,无疑给梁氏“新史学”留下了深刻烙印。早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就呼吁“广译”、学习包括“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的西方“民史”。(21)一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梁氏继续提出历史“为全社会之业影”,(22)“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23)并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24)这种社会(文化)整体历史观已表现在梁氏的历史分期标准上。梁氏认为“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应“全以社会变迁作标准”划分历史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改换的大势”。(25)
社会(文化)整体历史观是世界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最珍贵财富。梁氏之具有这种观念,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有关,但不能否认,这更是他本人在创建新史学的实践中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成果。
(二)
梁启超已具有社会(文化)整体历史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救亡第一、政治至上的时代氛围中,并缺乏成熟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作支撑,梁氏不可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文化)整体历史的宏愿。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他必然要趋向以政治为中心的史学。
1915年,梁启超带着复杂的感情回顾往事时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灯帷剑,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6)因为要挽救民族危机、改造现实政治,所以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27)认识到政治改造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不能脱离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造,“语政体之良恶”不能离开“‘人’与‘地’与‘时’三者”,(28)所以有必要发挥史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29)也因为民族救亡、政治改造的迫切性,政治问题始终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包括梁启超)的中心关怀,社会其他问题只能退居一旁或隐入“背景”中去,只能作为次要的部分或环境分析的一部分而出现在通史著作中,梁氏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稿说明了这种趋向,其原拟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目录以及文物专史中的分类排列都说明了在梁氏的通史构想中,政治部分一直处于优先甚至核心的地位。
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梁氏心目中的“民族”或“国家”毕竟主要是作为对外竞争的政治实体出现的,其理想中的“国民”毕竟在实质上是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或资格的政治公民,而政治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毕竟只能属于少数人。所以,“英雄”决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故无论何时何国,其宰制一国之气运而祸福之者,恒在极少数人士”;(30)正因为有造时势的英雄,“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31)
这是历史的悖论: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体;救亡需要政治挂帅,政治呼唤英雄登台。但这种悖论并非毫无意义:一种以社会(文化)整体(还有世界整体)为视野、以政治演变(进化)为重心的新通史诞生了,一种立足于“社会心理”之上发挥作用的新型英雄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末,梁启超曾写信给一位友人,谈到不久前创刊发行的《国风报》时说,“《国风》本意原不限于政治问题,但今所出各号,已全毗于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32)这里反映出“本意”与客观结果之间的差距,人毕竟受环境——外部社会环境(时代问题、社会地位、集团归属等)与内部认知环境(兴奋点、经历、学术渊源等)的限制。但是,梁氏所谈论的政治,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已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上属于近代世界的“国民政治”;梁氏所倡导的史学也已与为王朝政治服务的传统史学迥然有异,已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上属于近代世界的“为国民而作”的史学了。
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所进行的以赶超外部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必然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启蒙教育任务。但是,启蒙思想家极易被诱进入“历史唯智论”或“唯智史观”的思想陷井。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外部侵略(“兵战”与“商战”)所引起的民族生存危机,来自对自己国家落后现实的认识,来自对外部世界进步价值首肯,来自对自己民族生存危机的高度觉悟。最先高度觉悟到这种民族危机的是具有较深中学底子而又对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和了解的少数人。他们迫切需要把这种觉悟传导给那些继续生活在旧的模式中、对外部世界还懵懂无知或所知甚少的多数人,以减少近代化的阻力,增加近代化的动力。所以,“开民智”(即梁氏所谓“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33))成为变法维新运动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
梁启超说,“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4)“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35)这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共识,故废科举、兴学校、立学会、倡译书、办报纸等种种活动风行开世。变法终因传统势力的过分强大而告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日日接触西方新思想,“以为欲救今日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36)又因痛感政治改革之不可以独立成功,“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37)于是悍然举起“新民”大旗:“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8)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更使梁“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39)决意离开政治舞台,告别政治生涯,专门从事“社会教育”或“国民教育”,为立宪政治做民间的预备功夫。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贯彻的“开民智”思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此思想指导下从事的大量活动,终于为他赢得了“天才的宣传家”、“近代最卓越的启蒙大师”、“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无可争议的先驱者”、甚至“中国之伏尔泰”等光荣称号。但是,这种“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思想,极易滑向历史观上的唯智论。而在梁启超,确已具有这种民智至上的唯智史观:“吾闻之,春秋三世之因,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40)梁启超认为,“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41)“中国之智,由于民愚也”,(42)与环境物力相比较,“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43)“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44)等等。极端的“惟心”之论也在梁氏言文中屡见不鲜。
唯智史观,说到底是一种唯心史观。它以人类的知识智慧、理性品格等心力因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的历史作用往往只限于初步启蒙,高扬起民族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对于新社会关系的建设往往力不从心,往往缺乏社会关系改造的落脚点和下手处,最终丧失社会改造实践的能力。这有助于解释梁本人为什么在政治实践上到处碰壁,日趋保守,直至最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丧失对新一代青年的感召力。令人悲伤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唯智史观或“国民程度”决定论往往成为顽固守旧派拖延改革(如清末)或复辟(如袁世凯)的借口或理论依据。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清代学术:“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45)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评价梁启超一生学术(包括史学):梁氏一生学术以提倡一“智”字而盛,亦以局限一“智”字而衰。
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历史唯智论是一个致命的诱惑。但是,作为一位过渡时代的思想家,梁启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著作燃起整整一代人的希望”。(46)
(三)
近代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社会的一般生活方式发生不可逆转的质变的时期,用梁启超形象的说法,是“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47)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亡国危险迫在眉睫。这是一个使无数中国志士仁人饱受心灵煎熬的“两头不到岸之时”。(48)要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要说明这个前所未见的时代,要把握本民族的未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渴望了解世界历史的一般潮流,渴望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进行观照、反思。这种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进行整体性观照、了解和说明的工作,非历史学莫属,非新型的历史学莫属。出于对中国近代化的执着,梁启超大声呼唤具有“新范型”意义的史学,吹响了新史学的第一声号角,并在“政治谈”之余,通过长期的史学实践,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新型史学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的“新史学”,尽管具有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同质的复杂、矛盾、多变,具有过渡性、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但已具有中国近代史学的本质性特征:以进化(而非循环)为历史演变模式,以民族(而非王朝或家族)为历史本位,以国民(而非帝王)为历史主体,具有世界(而非华夏民族及其周边地区)、通史(而非断代)、社会或文化(而非政治或王朝政治)的历史视野,以新型的纪事本末体(而非纪传体或编年体)为主要体裁,等等。
梁启超奠立的“新史学”,构成了从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桥梁。假若我们能够借用梁本人在戊戌时期的“君史”、“国史”、“民史”术语并加以适当改造的话,可以这样说: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征是“君史”(王朝史学),近代史学的本质特征是“国史”(国家史学,民族史学,国民史学、或国族史学),现代史学的本质特征是“民史”(生活全史,社会或文化史学,或从下到上的史学)。梁本人虽然模糊地预见到了“民史”的到来,但是在民族救亡、政治改造压倒一切的历史条件下,在唯智史观的指导下,他不能实现“民史”的抱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民史”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民史”的真正实现必须是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全部生活中心的社会里,在经济现代化实践成为社会生活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取得全面胜利的经济基础上。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49)先驱者的忠告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注释: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二第59-60页。
②⑧⑩(49)文集之九,第7页、10页、26-27页、11页。
③1910年,梁启超在致友人信中说:“吾辈所当主者维何,必其在究当世之务,以致用于国家矣。”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称《梁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8页。
④[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⑤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下称《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⑥(19)文集之二,集60页
⑦(11)(13)(26)(28)(30)(35)(36)(37)(38)(39)(44)(47)(48)《梁集》,第356页、302页、124页、643页、470页、614页、72-74页、323页、153页、207页、644页、616页、837页、168页。
⑨文集之六第6页
(12)(46)[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4页、530页。
(14)参见文集之一第70页,文集之二第59-60页《梁集》第62页等
(15)文集之九第3、25、2页。
(16)(17)(20)(2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页、28页、104页、自序、
(18)(23)(25)(29)(31)专集之九十九第64页、10页、35-36页、168页、175页、
(21)(34)(40)(41)文集之一,第70页、14页、14页、122页。
(24)文集之三十八第26页
(27)(32)(33)(42)《梁谱》,第80页、510页、33页、127页
(43)专集之七十二第19页
(45)《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8页。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