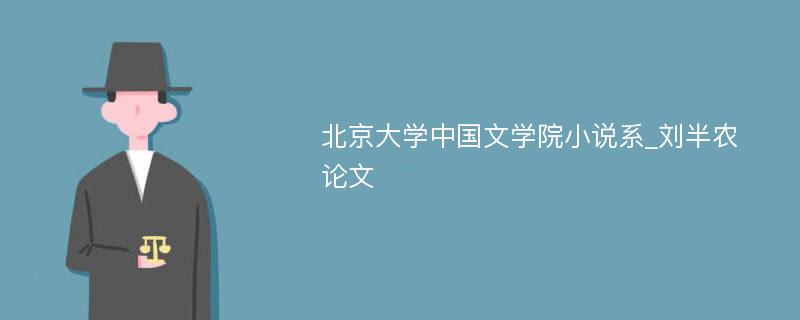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钩沉论文,国文论文,研究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小说进入现代中国的大学课堂,始于1920年。是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接受北大聘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①鲁迅的应聘,促成小说史在中国大学的正式设课,也为北大增添了一门叫好又叫座的课程。不过,在此之前,北大已有开设小说课程的计划,但由于缺少适合的人选而借助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的系列演讲。事实上,在小说正式进入大学课堂以前,小说科作为研究机构,使小说成为学术对象。然而鲁迅的盛名,以及日后出现的引领学术风尚的北大研究所国文门②,使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一直隐而不彰,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本文试图借助相关史料,追怀小说科的历史,并阐释其教育史与学术史意义。 晚清以降,“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大学学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为文学设科。但所谓“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类③,与今天理解的作为常识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次年,由张氏会同荣庆、张之洞共同拟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经学、史学、理学等分别设门,中国文学门始获独立。在其所设的科目中,包括接近文学史的“历代文章流别”;而在研究法上,则强调了小说等诸文类与古文之不同。④应该说,在清政府制定的大学章程中,能够给“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文类一线空间,着实不易。当然,《奏定大学堂章程》对于小说只是顺带提及,并未赋予其独立地位。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小说在中国大学学制中才真正浮出水面。同年年底发表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选修课中增设《宋以后小说》一项。⑤这是第一次出现以小说为讲授对象的大学课程,但当时仅仅列入计划,并未开课。同时,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后,强调以学术研究作为大学的宗旨和使命:“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⑥,并提倡师生开展共同研究:“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⑦。1917年底,北大设立了以文、理、法三科各学门为基础的研究所。⑧ 研究所的组织形式在《研究所总章》第一节《组织》中有详细规定: 第一条 各分科大学中之各门俱得设研究所。例如哲学门研究所及中国文学门研究所之类。 第二条 研究所以各门“各种”之教员组织之,遇有特别需要得加聘专门学者为研究所教员。 第三条 各研究所教员中,由校长推一人为研究所主任。 第四条 每研究所设事务员一人。 第五条 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志愿入研究所,本校高级学生得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 第六条 本校毕业生以外,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入所研究者,经校长及本门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 第七条 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研究所通信员。 此外,研究所各章程还强调教员与教员、教员与研究员、研究员与研究员之间的共同研究。尽管实际入所的研究员以北大本科在学的学生为主,但从章程及后来的实际操作看,各科研究所承担起北大最早的研究生教育之职责,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雏形。 各科各门研究所均设置若干研究科目,由本门教授担任指导教员。其中,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最初公布的研究科目和指导教员名单如下: 陈汉章 田北湖 文字孳乳之研究 特别研究问题 宋元通俗文 科目较少,教员也仅有三人。稍后,《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对研究科目和指导教员的名单有较大规模的修订增补,详情如下: 科目 担任教员 会期次数及时间 音韵 钱玄同 每月一次第一星期(六)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八日 形体 钱玄同 每月一次第四星期(六)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二十九日 形体 马夷初 每月二次第一、三星期(一)三时半至四时半 十二月三、十七日 诂训 陈伯弢(11) 每月一次第二星期(六)二时至三时 十二月十五日 诂训 田湖北(12) 每月一次第一星期(五)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七日 文字孳乳 黄季刚 每月一次第三星期(六)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廿二日 文 黄季刚 每月一次第二星期(六)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十五日 文 刘申叔 每月一次第四星期(四)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二十七日 文学史 朱逷先 每月一次第一星期(三)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五日 文学史 刘申叔 每月一次第二星期(四)三时至四时 十二月十三日 文学史 吴瞿安 文学史 刘叔雅 每月一次第四星期(六)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二十九日 诗 伦哲如 每月一次第一星期(三)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五日 诗 刘农伯 每月一次第二星期(三)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十二日 词 伦哲如 每月一次第三星期(三)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十九日 词 刘农伯 每月一次第四星期(三)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二十六日 曲 吴瞿安 每月二次第一、二星期(四)四时至五时 十二月六、二十日 小说 周启明 每月二次第二、四星期(五)四时半至五时半 十二月十四、二十八(13) 从上表中可知,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在科目设置上涵盖了语言学和文学的诸多分支,语言学领域之音韵、文字(字形字体)、训诂,文学范畴之文学史和诸文类研究,均有所涉及。尤其是在文类研究上,于诗文之外,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类——“曲”和“小说”单独设科,眼光独具,这无疑承载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北大校方和国文门诸君的新文学与新教育理想。而对各科目教员的选择,也注重其术有专攻,所列俱为一时之选,堪称当时北大国文门教师的最强阵容。同时,部分科目采取不同教员分别指导的形式,“文”由黄侃和刘师培(申叔)分授,“文学史”则由朱希祖(逷先)、刘师培、吴梅(瞿安)和刘文典(叔雅)各自完成,“诗”“词”等亦如是。这保证了不同理念和流派的学者都有充分展现其学术观点与特长的舞台,也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各科目中,最值得详细申说的是“小说”一科。与其余诸科目不同的是,小说科由三位教员共同承担,既不像“文学孳乳”和“曲”科之唱独角戏,也不像“文学史”和“文”科之各领风骚,刘半农、周作人(启明)和胡适这“三驾马车”之所以选择同一科目而又能通力协作,与三人兼具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北大国文门之边缘人这“双重身份”不无关联。作为新文学倡导者,这好理解。刘半农、周作人和胡适都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呼唤不遗余力,于诸文类中高扬小说之价值,亦与新文学之主流观念若合符节,借助北大国文门研究所为小说单独设科之契机,传播自家的新文学理想,体现在以三人为中心的小说科历次集会之中。而作为北大国文门的边缘人,导致三人于小说科中聚首,则更值得关注。刘半农最初由于给《新青年》撰稿,于1917年秋经兼任该刊主编和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推荐,担任北大法科预科教授;在此之前,刘氏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译员,创作和翻译过不少言情和侦探小说。(14)这一“鸳鸯蝴蝶派”的身份,成为刘半农屡遭新文化同人责骂的“历史污点”(15);并因难以摆脱旧上海的文人才子气,以其“浅”而被同人批评(16);加之没有留学经历,又常为英美派所嘲笑(17)。胡适由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暴得大名,为蔡元培校长礼聘(其中亦有陈独秀的举荐之功)。(18)不过,同年底《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尚未出版,缺少旧学师承的胡适还没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尽管身兼哲学和国文两门教授,在哲学门尚能开设《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这类主流课程,在国文门的课程表上却不见其名(19);且由于倡导白话文,不断遭到旧派学人辱骂(20)。与刘、胡两位相比,周作人在北大国文门的地位更为独特。身为浙江人和“章门弟子”,周氏在北大的地位本应相当稳固。但周作人却一直有如履薄冰的紧张感。在晚年的回忆中仍强调自家的“附庸”地位:“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凑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21)。周作人最初得同门朱希祖推荐,本拟到北大讲授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22)但抵京后与蔡元培见面时,却被邀请讲授预科国文课程,周氏感到力不能及,对此敬谢不敏,还险些为此辞教南归,后转到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职(23),1917年9月才被聘为国文门教授(24)。查该年北大国文门课程表,周作人承担一年级《欧洲文学史》和二年级《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两门课(25),这在时以“训诂音韵”和“文学考据”为宗尚的北大国文门(26),的确属于边缘课程。可见,前引周作人的晚年回忆,并非自谦。综上可知,刘半农、周作人和胡适在当时的北大国文门都处于边缘地位,却也因此无须放下身段,即可以选择名师宿儒所不屑为之的小说——以边缘人身份研究、讲授小说这一边缘文类,可谓实至名归。加之三人在进入北大之前都曾致力于小说的翻译和创作(27),更使他们成为主持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的不二人选。 从前引《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中不难看出,北大校方对研究所颇为重视,不仅安排了强大的师资,而且各科目集会在时间设置上也堪称细致严密,因此引发学生踊跃报名。在1917年11月22日、25日和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三期刊载《文科研究所国文学门研究员认定科目表》,据此统计报名人数共计152人次(校方允许学生兼任不同科目的研究员)。不过,各科目的报名人数却极不平均,小说科仅唐英、唐伟两人报名(两人还兼任其他科目,而且均未参加小说科此后开展的任何一次集会)。与之相比,音韵报名21人、形体15人、训诂13人、文字孳乳之研究22人、文33人、诗13人,报名人数相对较少的曲科也有7人。(28)日后在小说科研究会中出力甚多的傅斯年,最初报名的科目是注音字母之研究、制定标准韵之研究、文、语典编纂法。报名人数相差悬殊,体现出刘师培、黄侃、钱玄同等知名教授的威望与号召力,也进一步印证了刘半农、周作人和胡适的边缘地位,当然也和作为边缘文类的小说不受重视有关。尽管如此,国文门研究所各科目的实际开展却并非取决于教员声望的高低和研究员人数的多寡。事实上,多数科目没有依照时间表正常开展研究活动,或者即使开展,也没有得到师生的重视,留下相关的文字记录,令后人了解其详情,殊为可惜。独小说科有序进行,而且几乎每次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为今天追怀、重构其过程并阐释其意义积累了宝贵的材料。小说以外的其他科目没有文字记录,并非偶然。除参与者的重视程度外,将前引《国文研究所教员担任科目表》、《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和同年的北大国文门课程表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个中缘由。1917年11月公布的北大《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中国文学门”课程及任课教师有: 中国文学 黄季刚 刘申叔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讫(29)建安) 朱逷先 文字学(音韵之部) 钱玄同 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 哲学概论 陈百年 中国文学 黄季刚 刘申叔 中国古代文学史 朱逷先 刘申叔 文字学(形体之部) 钱玄同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 中国文学 黄季刚 吴瞿安 中国近代文学史(唐宋讫今) 吴瞿安 文字学(训诂之部) 钱玄同(30) 不难发现,上表中的课程及任课教师与国文门研究所各科目及指导教师基本重合(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分别设课,以后者涵盖文、诗、词、曲等各文类,则体现出将“文学史”与“文学”分而治之的教学思路(31))。也就是说,研究所各科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日常教学来完成。在有效完成教学工作的前提下,避免重复性劳动,不重视研究所相关科目的开展,或开展但不予记录,问题不大。但小说在当时未列入课程表。如前文所述,稍后颁布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在国文门选修课程中增设《宋以后小说》。但也是“有目而无文”,由于缺少合适的教师,未能开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曲”本与小说同为边缘性文类,但有吴梅这样的曲学大家位列教席,既得以进入课堂,又得以列为研究科目,受到不少学生的青睐,因而身价倍增(32)。这样看来,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就不仅仅是一项研究科目,而担任着一直未能正式开设的小说课程之角色。国文门研究所为小说文类单独设科,延请刘半农、周作人、胡适这三位新文学倡导者主持其事,从中可见北大校方的良苦用心。这恐怕也正是刘、周、胡三人,尤其是前两人——胡适由于兼任哲学门研究所教员,指导“中国名学钩沉”等科目(33),同时还要在英国文学门开设《英国文学》、《亚洲文学名著(英译本)》等课程(34),分身乏术——对此倾尽全力,从而使小说科在研究所各科目中开展得最为成功、相关材料也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原因之一。 对于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周作人在其晚年中有较为详细的追忆: 北大那时还于文科之外,还早熟的设立研究所,于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公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我于甲种中选择了“改良文字问题”,同人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三人,却是一直也没有开过研究会,乙种则参加了“文章”类第五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刘复二人,规定每月二次,于第二第四的星期五举行开会,照例须有一个人讲演。我们的小说组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一共有十次集会,研究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的崔龙文和英文系三年级的袁振英两人,我记得讲演仅有胡刘二君各讲了一回,是什么题目也已忘记了,只仿佛记得刘半农所讲是什么“下等小说”,到了四月十九日这次轮到应该我讲了,我遂写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那里敷衍的应用。(35) 知堂老人的这段追忆大体无误,特别是以坚持数十年的日记为蓝本,对时间的记录非常准确,但其中仍有部分细节需要订正:集会的数量并未达到十次;研究员除崔袁二君外,还包括后来加入的傅斯年和俞平伯,以及“旁听员”傅缉光一人(仅参加一次);讲演也不限于三回。接下来结合《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相关记录,及《周作人日记》等其他第一手材料,还原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以及期间历次集会之详情。 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917年11月13日,周氏赴北大研究所开会,“认定‘改良文字问题’及‘小说’二项,遇胡适之、刘半农二君”(36)。这是北大研究所成立之前的一次准备会,会议确立了国文和哲学门研究所的研究科目。三日后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号刊载题为《有志研究国文哲学者注意》的通告,介绍研究所的筹备进度:“敬启者:国文哲学门研究所现已组织就绪,内分研究科及特别研究科两项。研究科及特别研究科目已由本门各教授分别担任。……”(37)同月30日,周作人又赴北大开会,并与刘半农拟定小说研究表。(38)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14日,小说科第一次集会按规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员有刘半农和周作人,研究员有袁振英和崔龙文。集会首先由刘半农发表演讲,倡导以科学方法研究小说,提出以“文情并茂”四字为小说界中最美满之评语,进而分析小说不受重视的原因,并结合自家七年来编译小说的经验,探讨如何转变阅读小说的眼光,最后强调研究小说的科学方法应包括历史和进步两方面,后者尤宜以西洋小说为宗尚。周作人在随后的发言中提议研究小说当侧重于进步方面,故研究外国小说当以近代名人著作为主体,19世纪以前的著作可归入历史范围。周作人的发言,明确了小说研究和小说史研究的区别。(39) 同年12月28日,小说科举行第二次集会。与会教员不变,研究员则增加了傅斯年。集会首先由周作人演讲,将小说研究分为过去的小说研究和新小说之发展两大部分,于后者仍大力推举外国小说,强调其“今日所臻之境远非中土所及也”;并将中国小说之演进分为野史、闲书和人生文学三个时代。周氏还介绍了自家拟定的研究课题:“拟就古小说中寻求历史的发展”、“拟研究古小说中之神怪思想”。刘半农随后发言,谈及中文小说之分类(白话之章回小说和短篇之笔记小说)、研究文章之体式(札记或论文),并提出研究所集会不必逐次演讲,宜注重互相讨论、交换研究心得。刘氏也介绍了自家拟定的研究课题:“中国之下等小说此为历史方面者”、“印度近代小说思想之变迁此为进步方面者”。研究员傅斯年则表示愿意先研究小说之原理,指出“小说事就其制作方面言之,则为术;就其原理方面言之,则为学”,并请两位教员推荐相关英文书籍。刘半农还带来英俄法国小说各一种,布置三位研究员分别阅读。(40)较之两周前的第一次集会,第二次集会的内容更加丰富,也具有更为浓厚的研究讨论气氛。 小说科第三次集会于1918年1月18日举行,与会教员和研究员与第一次相同。此次集会改为专题演讲,由刘半农作题为《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这是刘氏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关小说的著名文字,由于有“详细演辞录存(研究)所中”,因此记录稿颇为简略。刘半农演讲后,与会的两位研究员就研究所中已购之中国小说五十余种,各认数种作为研究对象。崔龙文选择《小说丛考》、《顾氏四十家小说》和《晋唐小说六十种》,袁振英选择《留东外史》、《老残游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41)二人就古代与近代、文言与白话的不同选择,是否出于教员的特意安排,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证明。所谓“演辞”与刘半农后来发表的同题文章是否一致,也难以确证。因此无法判断是刘氏事先写好文章,再照章宣讲;还是先草拟初稿,事后再敷衍成文。《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一文不难获取,故不再记述第三次集会演讲的详细内容。 小说科第四次集会于同年2月1日举行,与会教员仍为刘、周两位,研究员则达到四人:傅斯年回归,还新增了俞平伯。集会首先由周作人作题为《俄国之问题小说》的演讲,概括问题小说的定义和条件,与教训小说和社会小说之区别,并分别介绍了俄国小说家赫尔岑《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如之何》(即《怎么办》)、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名著之大意。演讲过后,俞平伯和傅斯年分别认定了自家研究之小说,俞氏为《唐人小说六种》,傅氏为《五代史平话》和《儒林外史》。(42)仍有文言与白话之分。现存周作人公开发表的文字及未刊稿中均无此同题文章。此前几天的《周作人日记》中也没有撰写相关演讲稿的记载。可见,周氏在演讲之前并未成文,事后也未加以整理。不过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讲述日后大行其道的问题小说,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其发现与引领时代风尚之用心,值得关注。 1918年3月1日《周作人日记》有如下记录:“往研究所,胡、袁二君来,未讲演,谈至五时而散。”(43)似乎小说科于当日举行了一次没有演讲的集会。“胡、袁二君”当为教员胡适和研究员袁振英。查《国文研究所报告》,是年3月的两次小说科集会分别安排在15日和29日。可见,这次会谈并非出于北大校方或国文门研究所的安排,而是由小说科同人自行拟定。本月15日的集会恰好由胡适演讲,因此这次会谈很可能是为半个月后的集会做准备,不能算作小说科的第五次集会。 两周后,小说科第五次集会如期举行。出席教员有胡适和周作人,研究员仍为前次四人。《北京大学日刊》误将此次集会算作“第四次”,也导致之后两次集会计数的错误。这是胡适唯一一次参加小说科集会,也是唯一一次发表演讲,题目是《短篇小说》。演讲经傅斯年记录,连载于1918年3月22至23、25至2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十八至一百零一号(24日为星期日,未出刊)。由此可知胡适事先做了准备,但并未成文。记录稿后经胡适本人改定,以《论短篇小说》为题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胡适的修改主要在文字表达,文章结构和主要观点没有明显变化。该文已发表,因此不再记述其内容。胡适演讲后,周作人提出了一些不同见解。两人在彼此的辩驳砥砺中深化了自家对于短篇小说的看法。(44) 小说科第六次集会也于3月29日如期举行,与会教员为刘半农、周作人,研究员四人不变。由刘氏作题为《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45)与《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和消极教训》一样,这也是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关小说的代表性著述。其要点连载于4月16—1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一十二至一百一十三号。定稿则发表于1918年5月21—25、27—31日,6月1、3、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四十二至一百五十四号。小说科第七次集会,也是现有记录的最后一次集会于同年4月19日举行。出席教员与第六次同,研究员中俞平伯未参加,仅剩余下三人,另新增一名旁听员傅缉光。(46)集会由周作人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专题演讲。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事先撰写了详尽的演讲稿(决非纲要)。(47)《文科国文门研究所记事》仅录其要点,全文则发表于1918年5月20—25、27—31日,6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四十一至第一百五十二号,又发表于同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后收入周氏散文集《艺术与生活》。三次收录,除个别标点略有出入外,整体上无大区别。与刘半农的两篇名作相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在当时更为知名,影响也更大,且反复刊载,对其内容亦无须详述。 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的集会,至此中断。虽然5月3日和17日,6月14日和28日的集会已列入计划,并多次公布,但始终未见关乎其详情的文字记录。(48)查这四天的《周作人日记》,也没有赴研究所出席集会,或与刘半农、胡适等人会面的记载。(49)因此,在新史料出现之前,可以认定北大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集会举行至第七次终止。 以上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钩沉辨析,追忆、重构了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以及期间历次集会的详细情况,并阐释了其教育史和学术史意义。北大于1917年底设立各科研究所,最初列入计划的研究科目不下百种,其理想不可谓不高远,气魄不可谓不宏大。但在彼时彼地,相对于开展研究生教育和创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这一系列重大事业而言,此番努力尚属草创,或者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北大各学门研究所,连同其麾下的诸科目,包括本文力图追怀和阐释的小说科,虽做出种种努力,但均难言成功,并很快烟消云散。由刘半农、周作人和胡适的演讲稿改定而成的几篇文章,虽经刊载而闻名于世,但其之于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学术价值。傅斯年、俞平伯等人虽然选定了研究对象,但也均未能落实到文字,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北大研究所没有取得成功,个中缘由,并非经费支绌或人才匮乏,而是未逢其时。尽管有校方制定计划、提供资金,师生认真准备、积极参与,但当时的北大并不具备支撑起如此规模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充足条件。(50)直到四年后的1921年底,蔡元培校长决定改组研究所,经学校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并于次年1月创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51),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光辉岁月。尽管如此,1917年底设立的北大各科研究所仍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特别是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在当时北大小说课程的开设尚未找到适合人选的情况下,举区区数人之力,使小说活跃于大学讲堂近半年之久,其筚路蓝缕之功,惨淡经营之志,依然值得后人珍视与称赏。 ①鲁迅:《日记第九(一九二○年)》,《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②由于1917年底成立的北大各科研究所未能取得预想中的成功,蔡元培决定进行改组,并于1922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有关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目前最详尽的著作是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可参见。 ③《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④《奏定大学堂章程》,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87—588页。 ⑤《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五号,1917年12月2日。 ⑥⑦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 ⑧对此,《申报》曾予以报道:“北京大学设立各科研究所,顷已次第成立。文科研究所于昨日在校长室开第一次研究会,学生志愿研究者约四五十人,蔡鹤卿校长,陈仲甫学长及章行严、胡适之、陶孟和、康心孚、陈伯弢诸教授均莅会。”载《申报》1917年12月8日,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5页。 ⑨《研究所总章》,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八二号,1918年7月16日。 ⑩《国文研究所教员担任科目表》,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号,1917年11月25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将该表与同年11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一号刊出的《文科国文门研究所研究员认定科目表(续前)》合二为一,将学生身份的研究员胡鸣盛、黄芬、王肇详、谢基夏、伍一比、陈建勋等六人误归入教员名单,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二),第1432页。 (11)即前表中之陈汉章。 (12)当作“田北湖”,原文如此。 (13)《国文研究所研究科时间表》,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十六号,1917年12月4日。该表中小说科“会期次数及时间”原缺“日”字。 (14)《刘半农生平年表(1891-1934)》,见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1页。 (15)王森然:《刘复先生评传》,见王氏著:《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五·三沈二马下》,《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1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三·卯字号的名人三》,《知堂回想录》(下),第410页。 (1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5页。 (19)(25)(30)(34)《文科本科现行课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二号,1917年11月29日。 (2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六·北大感旧录二》,《知堂回想录》(下),第546—548页。张中行:《红楼点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2页。 (2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七·琐屑的因缘》,《知堂回想录》(下),第468页。 (2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去乡的途中一》,《知堂回想录》(下),第339—340页。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一○·北京大学》,《知堂回想录》(下),第361—362页。 (24)周作人1917年9月4日的日记中有“得大学聘书”的记载,见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92页。 (2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5—16页。 (27)刘半农于民国初年在上海创作和翻译小说数十种。周作人曾与鲁迅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及哈葛德、柯南道尔等人的小说,并撰写多篇介绍外国小说的文章。胡适早在1906年就曾在上海《竞业旬报》上发表章回小说《真如岛》(未完),在其鼓吹新文学、倡导白话文的著述中也常常以小说为例。 (28)《文科研究所国文学门研究员认定科目表》,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六号,1917年11月22日;《国文研究所研究员认定科目表(续前)》,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号,1917年11月25日;《文科国文门研究所研究员认定科目表(续前)》,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一号,1917年11月28日。 (29)当作“迄”,原文如此,下同。 (31)北京大学《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二十六号,1918年5月2日。标点为引者所加。 (32)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见陈氏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1页。 (33)《哲学门研究所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二号,1917年11月29日。 (3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七·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下),第427—428页。 (36)(38)(43)《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07、710、736页。标点为引者所加。 (37)《有志研究国文哲学者注意》,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号,1917年11月16日。标点为引者所加。 (39)《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三十三号,1917年12月27日。《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14日载:“半农来。四时后同往二道桥文科研究所。袁、崔二君来会,六时散。”《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13页。 (40)《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傅斯年记录),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四十八号,1918年1月17日。《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28日载:“四时往二道桥,半农亦至。六时散。”12月31日载:“傅斯年君函送研究会记事稿。”《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16、717页。 (41)《文科国文研究所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五十一号,1917年1月20日。《周作人日记》1918年1月18日载:“往研究所,五时半出,同半农步行至东安门,乘车回。”《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29页。 (42)《文科国文研究所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六十三号,1917年2月3日。《周作人日记》1918年2月1日载:“同半农至研究所,六时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31页。 (44)《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记录》,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十八号,1918年3月22日;《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记录(续)》,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十九号,1918年3月23日;第一百号,1918年3月25日;第一百零一号,1918年3月26日;第一百零二号,1918年3月27日。《周作人日记》1918年3月15日载:“至研究所,又回至校,与适之谈,七时返寓。”《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38页。 (45)《文科国文门研究所记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一十二号,1918年4月16日;《文科国文门研究所记事》(续),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一十三号,1918年4月17日。《周作人日记》1918年3月29日载:“至法科访半农,同至研究所。”《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41页。 (46)《文科国文门研究所记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一十七号,1918年4月22日。《周作人日记》1918年4月19日载:“又至研究所,六时了。同半农步行至法科,乘车回。”《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45页。 (47)在本月17、18日《周作人日记》中,均有“起讲演稿”的记载。《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45页。 (48)《集会一览表》,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二十五号,1918年5月1日;第一百二十六号,1918年5月2日;第一百二十七号,1918年5月3日;第一百三十七号,1918年5月15日;第一百三十八五号,1918年5月16日;第一百三十九号,1918年5月17日;第一百六十一号,1918年6月12日;第一百六十二号,1918年6月13日;第一百七十二号,1918年6月26日;第一百七十三号,1918年6月27日;《国文研究所课程时间表》,载《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五十一号,1918年5月31日。 (49)《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747、749、755、758页。 (50)陈平原:《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见陈氏著:《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9页。 (51)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标签:刘半农论文; 周作人论文; 大学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北大论文; 研究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