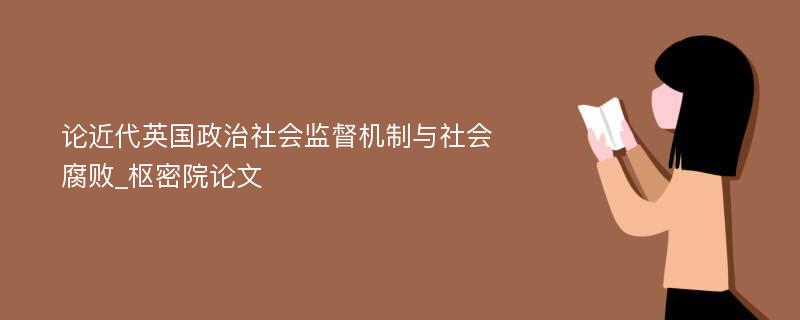
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社会监督机制与社会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英国论文,近代论文,腐败论文,监督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6)04-0090-06
伴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政治权力中央化,君主个人的权力不断加强,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机构不断扩大,因此,中世纪时期的监督机制已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与此同时,新的监督制度远未建立。君主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了这一时期的个人庇护制的盛行,而个人庇护制的确立使得国家制度层面的监督手段无法实施,造成了这一时期监督机制的弱化和缺失。这主要体现在议会和枢密院的政治监督的尴尬和社会监督的两难上。
因此,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政治监督、经济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全面瘫痪。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之下的贵族和官员肆无忌惮,于是,这一时期的英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在具有鲜明特色的海军经营过程中,贵族官员的腐败行为相当普遍,也相当突出[1]。
一 政治监督的尴尬
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的政治监督主要体现为议会监督,也包括枢密院和其他司法行政机构对官员的监督,而前者是最主要途径。议会监督主要是通过议会立法、议员在议会内外发表议论、议会派出专人或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和议会通过对有关当事人的指控等方式来进行。
中世纪时期,英国议会的主要监督对象是君王,议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国王的行为进行监督和限制。与此同时,议会也制订和颁布法令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从中世纪中后期到都铎初期的法令中屡见不鲜。
《大宪章》中就有禁止王室食品采办官敲诈行为的条文。1275年的第一个威斯敏斯特法令禁止郡守和其他王室官员通过职务之便接受国王允许之外的报酬,如若违犯,将付出双倍的代价。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所有的巡回法官及郡守都必须接受关于地方官员滥用行政权力的调查。亨利四世统治初年,法令规定,如果任何郡守对他的人民进行任何敲诈勒索行为,他将会因为敲诈勒索按照国王个人的意愿受到惩处。都铎时期的法令也继续强调对郡守及其以下官员贪污、贿赂行为的惩处,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时的每位君主在位期间都有相应的法令颁布。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强调,郡守、副郡守、郡府职员及其他官员的敲诈勒索行为年年都有发生,法令赋予治安法官考察、指控和逮捕他们的权力。关于同样内容的法令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都曾颁布过。另外对官职的任职资格法令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并对买卖官职行为也有一定的束缚。爱德华五世在1388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所任命的官员必须是“最好的和最有法律知识的人士,必须对他们有足够的考察和认识”,严禁大法官、财政官、掌玺官、王室总管;内务大臣等通过收受礼品或依据个人好恶和偏爱提名任命官员。都铎时期继续实施以前的法令,如 1552年所实施的法令,强调其目的就是“避免在官员和王室大臣中间腐败行为的发生”,这一法令特别针对“行政管理、司法体系和国家财政征收官员”的直接或间接的买卖官职行为,对卖官者要由国王取消其爵位,对买官者要收回其官职。;
由于在都铎晚期到斯图亚特早期君王权力的加强,尤其是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个人统治,加上个人庇护的盛行,有关对腐败行为进行惩罚的法令的实施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君王必须对此类违法事件进行干预和处理,以警世人;另一方面,在庇护制这种潜行政体制下,君王及其政府原本就是依靠个人关系进行统治的,各级官员的职位大都是通过个人庇护网络中的个人关系而获得的。因此,小而言之,对官员的惩治影响被庇护人对庇护人的忠诚和服务;大而言之,这种惩治不利于整个行政系统的稳定和运作。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伊丽莎白女王采用避重就轻、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手段,对官员的腐败行径只能是从严调查,从轻发落。如,在处理税务官威廉·伯德的贪污事件时,枢密院仅仅判定他对属下职员监管不力,以罚款的方式进行惩处而草草收场[2]149。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王在法下”的宪政原则已遭破坏,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国王毫无实施惩处腐败法令的意图,而且,王室政策与相关法令背道而驰,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就是为解决王室财政问题而实施的出售爵位和官职的政策[1]。在此之前英国各朝法令所限定的腐败行为最突出的就是任命官员过程中的行贿受贿行为,而詹姆斯一世将出售官职政策化,因而,通过法令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也就显得多余。
在都铎晚期,对腐败行为进行调查一般都是由国王或大臣派专人进行。如,在1585年,塞西尔和伯利分别派人对海军中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2]187。由于调查是由非议会人员进行的,因此,涉及到与调查者有亲属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时,则调查不了了之。如,伯利勋爵原为海军大臣,当他派人对海军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之时,所涉调查对象大都是其旧部,因此,得出了以下结论:
海军部没有任何官员是舰艇的制造商,也没有任何官员成为任何舰艇制造商的合伙人;没有任何官员是女王陛下海军的物质供应商;没有任何官员单独确定供应品的进货价格,在没有其他相关官员证明的情形下,海军财务官没有进行任何支付行为;所有供应物质都首先进入女王陛下的海军仓库,没有任何截流或盗窃发生,在没有所有相关官员在场证明的情形下,没有任何物质从仓库发出;也没有任何人把用于建造女王陛下的海军舰艇的木材转手给商人。[2]114
而同一年由塞西尔派出的调查人员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从1579年起,官员私下与舰艇制造商签订合同而牟利,在主要物质的供应方面,腐败活动非常活跃。[2]259
这种情况下的对腐败官员的监督只能反映各不同利益派别的斗争,因此,无法进入正常的制度程序。
最直接的监督就是,议会议员和有识之士在议会举行会议期间或会外对贵族官员的腐败行为经常抱怨、控告或进行抨击。大律师爱德华·科克爵士对早期斯图亚特的赏赐制度和行政管理中的腐败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号召议会向国王请愿,要求改变现存的上述制度,他还就海军中的问题进行抨击,“从未听说过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军只会跳宫廷舞,现如今如此众多的官员尸位素餐。海军大臣的职位应该是由最受人信任和经验丰富的人来担当,但是……如果一个职位给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担当,则这一职位就是一个闲职。富有智慧的先人们懂得将一个伟大的人放置于具有伟大头衔的位置,而进入这一位置的人们必须同时具备相关的丰富的经验。在亨利八世时期,管理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就是由商人来担任的,而目前,则是由不能履行这一职责的贵族担任。”[3]399科克还抨击新的官职滥增、王室费用的无度、政府管理的无序以及官场的欺骗行径,强烈要求削减官职数量,降低官员补贴,并列举了庇护制之下的种种劣迹及改善办法:
(1)官员应以自己的职位谋生而不是整天去乞讨赏赐;(2)任何官职之上都不应有主子;(3)任何非官方补助都应取消;(4)廷臣都应得到报酬,但是,国王不应负责他们的津贴和年金;(5)国王应从王室领地中获得最大收入,而不应通过转租方式补贴贵族及官员而减少收入。还有,专利垄断权应予以废除。[3]658
在同一时期,诸如此类不满腐败现象的怨言确实较多。如,罗伯特·希思爵士,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位高权重的白金汉公爵。
议会较为激烈的举动就是对腐败官员提出指控。在1621年的会议召开期间,下院议员对违反法律的腐败行为提出指控,所指控行为包括接受礼品、出售官职和批准使用垄断权等。如,对当时的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的指控不仅是因为他同意批准了大量的垄断许可,而且因为他作为大法官,像其它官职一样,担当着行政和司法的重任,他在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诉讼当事人的礼金,以至于整个大法官法庭都被下院指责为“奢华的权威机构”[4]111。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下院联合上院共同指控培根。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其他的人也受到了指控,如,坎特伯雷特权庭法官约翰·贝内特被指控收取超过标准的司法费用和在检验遗嘱过程中收受贿赂,关于他个人所涉的案件就有30余起[2]187。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受到了议会的指控,如,治安法官弗朗西斯·米歇尔爵士就被指控从伦敦商人那里索要债券和从啤酒馆经营者那里勒索金钱,兰代夫的主教西奥菲勒斯·菲尔德被指控作为培根的经纪人收受贿赂,亚历山大·哈里斯被指控从囚犯那里敲诈大笔费用,另外,下议院还指控两位宗教法庭的法官受贿和出售行政官员任命书[5]31-32。
在斯图亚特早期,议会指控最多的也是最为激烈的对象是白金汉公爵。在1626年,有13篇指控书是针对白金汉公爵的,其中大部分涉及到买卖官职和敲诈勒索等腐败行为,另有12篇指控书涉及到他滥用国家财政收入[4]260-323。约翰·塞尔登认为,由于白金汉拥有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海事专利权,因此通过转让这些特权而获利,并从国内外商人身上敲诈大量财富,仅从东印度公司就敲诈到了 10000镑。约翰·皮姆指控白金汉为他家族的人加官封爵和滥用、私吞王国财富,皮姆认为,白金汉的这种行为激起了民怨。皮姆宣称,在10年中,每年从外国商人的货物价值中每镑征收3便士而获利 3000镑以及从爱尔兰所得7000镑外,共获得 162995镑[6]191-193。
面对议员和其他人士对贵族官员腐败行径的议论和抨击以及对有腐败行为的当事人的指控,早期斯图亚特的国王不仅不进行处置,而且为他们进行辩护。当大法官法庭的大法官受到议会的指控时,詹姆斯一世给当事人提供保护,他要求下院不要捕风捉影,随意谴责犯有小错而实际上并无腐败行为的人[4]111。而面对议会屡次对白金汉公爵的指控,詹姆斯和查理更是极力保护,为对抗议会的指控,甚至不惜解散议会[7]50。
当然,议会以外的其它监督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发挥过作用。如,治安法官不仅受到枢密院的监察、指挥与命令,还受到主教以及更为重要的巡回法官的监督与牵掣。1564年,中央要求地方各主教对包括治安法官在内的地方各级官员的宗教信仰进行调查,不仅要根据治安法官对待国教法案的态度把他们分出等级,还要推荐他们认为适合的人选,指出不称职者;并要咨询教区内已知的支持国教法案的乡绅的意见。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治安法官中,431人被认为是支持国教法案的,264人持中立态度,只有157人反对[8]314。1587年约克大主教爱德文·桑迪斯致信伯利勋爵就约克郡治安法官的现状谈了他的看法,认为在担任治安法官的骑土中相当多的人完全不称职,在绅土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们;他还特意批评了部分治安法官丑陋的个人道德:罗伯特·李,人所共知的通奸者,屡违国法,怙恶不悛,滥用权力;彼得·斯坦利,出名的私通者……[9]69相比主教,巡回法官的监督职能更为突出,自1542年起就被授权审理治安法官失职与滥用职权案件。他们每年巡视地方各郡两次,并向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作汇报;正是根据这些报告,郡的治安委员会定期地被改组,那些不合格的法官将被淘汰,而称职者将会获得入选的荣耀。
但是,像治安法官这样的地方官员,除了与中央有着密切联系外,因其一般都是当地乡绅出身,所以,有明显的地方独立性。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地方主义观念立足于数以千计的面积狭小的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中,村庄、教区、郡、城镇,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相对统一的社会单位,不仅在地理上和行政上具有地方性,而且在社会体系上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共同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语言、风俗、权利与义务塑造出了地方居民强烈的地方归属感,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个人身份认同与对地方的忠诚。这种地方的属性阻碍了中央政府对治安法官及其它地方官员的监督,无论是议会监督还是枢密院以及巡回法官的监督,都在地方主义的氛围中弱化。
综上所述,在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对官员的政治监督形式是存在着的,无论从议会的立法,议会议员或枢密大臣以及中央派出的各类法官对腐败行为的调查,议会议员对贵族官员的抱怨和抨击,还是议会对腐败官员的指控,在这一时期都没有消失。但是,由于王权的加强、个人庇护制的盛行等,这些监督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一方面,议会议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国王阻碍这些监督的实施,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监督陷入了严重的尴尬境地,政治监督因此也就软弱无力,其后果是贵族官员腐败之风盛行,甚至肆无忌惮。
二 社会监督的两难
如何对贵族官员进行社会监督也是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英国君王们颇费周折的事情。在16、 17世纪,英国君王一般是依靠其私人的代理人提供信息特别是提供贵族官员的违法行为的信息。由于缺乏由政府提供薪俸的地方行政官僚体系,君王不得不依赖代理人来执行特别是监督法律的实施。有的代理人是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正式官员,有的是王室的非正式代理人;后者在当时被称作为informers(告密者),“从1530年代末到1624年,告密者是监督实施经济法律的主要群体”[6]143。在1551年以前,告密者主要收集关税官员和外国商人的信息,再向财政法庭报告。1551年以后,利用告密者监督任意提高租金者、欺压穷人者、敲诈勒索者、行贿受贿者和高利贷者成为主要的社会监督手段。早在亨利七世时,告密者就成了国王实施法令和文告的主要群体之一,王室政府对告密者的举报奖赏有加,“告密者也被允许把违法者的情况报告给星室法庭、国王法庭或大会议,如果告密者在以上法庭作证,王室就会奖赏他们。”[10]80亨利七世时期对违法者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一般而言是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而这一时期的文告规定,只要告密者提出违法者的证词,他就可以要求获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10]83。由此可见,当时的都铎君主比较倚重告密者对贵族官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都铎君主对告密者的需要是与都铎时期的行政科层结构的特点相关的。亨利八世时期,由于加强王权的需要,也由于宗教改革后原来由教会对中央和地方管理的部分职能的剥夺,不得不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的功能,于是着手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埃尔顿称之为“政府革命”。这一改革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中央的行政职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把枢密院改造成真正的中央行政机构,并从王室中独立出来;二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这主要是通过由枢密院中选派大臣担任地方最高长官大军政官和以治安法官取代原来由贵族担任的地方行政官员的职能。都铎君主进行第二方面的改革是由于中世纪以来,英国地方贵族在地方的独立性,中央与地方的连接非常松散,中央无法对地方进行统治。改革后,表面上看,似乎中央和地方由于以上官员的派出和委任而连接起来了,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大军政官是由枢密院派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常驻地方,而是委任当地的政治精英担任代理军政官,代行自己在地方的职责。治安法官属中央任命,各地治安法官基本上由当地乡绅担任,治安法官具有两种倾向,即治安法官既赋予了权力,同时又要面临失职后的惩处。下面以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地方官员——治安法官为例,阐释中央对地方官员监督的基本情况。
伊丽莎白社会立法的相关法令赋予了治安法官范围极广的司法职权:可按照举报不经控诉审判较轻的犯罪行为;可传唤有嫌疑的骚动者受审,或在正式审判前将之投入监狱;可监督调查非法领有侍从的行为,并向王室法庭提交违法者名单;甚至有权就针对郡长、副郡长及其属吏的控诉展开调查[8]62-63。许多关于骚乱、毁坏财产、伪造货币、巫术、非法捕猎、不出席教堂仪式等新罪名的设立都要求实施,尽管中央出于削弱治安法官地方大权之需在1590年把听审和判决死刑案件的权力移交给了巡回法官,但这些新罪名以及其他新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如绑架女继承人、毁坏庄稼、破坏篱笆、安息日渎神、酒店骚乱、酗酒、作伪证以及官员的失察行为等仍有待治安法官的调查与审判。
治安法官不仅仅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司法官员,他还享有同样不容忽视的行政职能。在行政事务的管理方面他也是地方社会的“操牛耳者”,且自 15世纪末以来都铎王朝或以法令形式或以行政饬令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其职权范围。以1595年敕令全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近60段详细的指令和对治安法官职权的劝诫;按照这些指令,治安法官被要求调查受灾地区的粮食储备状况,对那些拥有超过家庭生活所需之余粮者要强制其每周携带规定数量的粮食到公开的市场上出售给普通消费者和有经营许可的商人;除商人外,还包括酿酒商、酒店店主、磨房主,面包商的活动、人数及经营许可都要受到治安法官的严格管制;同时治安法官还必须确保穷人受到特殊照顾,如市场上的优先购买权、富人以“慈善的价格”向其售粮、帮助无业者就业、惩罚流浪者;治安法官还必须每月汇报当地市场上的价格以及他们以强制手段实施这些命令的情况[11]32-33。
各项法令在授予治安法官司法、行政权力的同时,也专门规定了对治安法官滥用职权行为的惩处方法。早在1487年,针对治安法官滥用保释权导致许多杀人者和死刑罪犯逃脱法网惩罚的情况,亨利七世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每一次这样的滥用职权行为都将被判处10英镑的罚款。1552年一项法案——授权治安法官对酒店收取保证金以确保酒店营业的有序性以及防止酒店食用非法捕猎的猎物,但同时也规定他必须在下一次四季会议上汇报其执法情况;一旦发现有滥用职权现象每次将被罚款3英镑6先令8便士[12]477。1563年工匠法第十一条也对治安法官的失职行为作出了规定:若治安法官不出席评估工资标准的会议,且未染上任何使其出行有一般危险或是生命危险的疾病,或无其他任何合法正当的理由,将被判处10英镑的罚款;若最终制定公布的工资水准高出或少于会议确定的水平,将被判处5英镑的罚款以及10天监禁的处罚[12]479-480。
如何实施以上惩罚,与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是多层次的,就对治安法官而言,在政府层面,不仅受到枢密院的监察、指挥与命令,还受到主教以及更为重要的巡回法官的监督与牵掣。1616年詹姆斯一世在星室法庭中对即将开始春季巡视的巡回法官发表训令:
记住当你们外出巡视时你们不仅是要去惩罚和阻止犯罪行为,而且也要注意在你们巡视的地区建立良好的政府……你们要向治安法官申明其职责,确保他们无论你们巡视与否都要恰当地行使其职权,并记录下他们的施政情况以在你们返任时向我汇报。[13]219-222
但是,政府层面的监督需要大量有关官员的信息,也就是说,政府层面的监督需要社会层面的信息支撑。而社会信息主要由告密者来提供,不仅枢密院、巡回法官依靠告密者的信息,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法行政机构都以告密者的信息为据。而上文提及的王室赋予告密者的权力及其不菲待遇,刺激了告密者数量的增加,因此,中央所需信息越来越依赖告密者,“在1551~1624年,所需信息的1/4到1/3由他们(告密者)提供,此后,告密者更是占有绝对优势。”[6]144
但是,告密者的社会监督功能是建立在与国王和其它重要官员的私人关系上的,并非制度层面的监督,因此,伴随着告密者成分的变化及其利益的驱动,告密者自身也陷入了腐败的泥潭。都铎早期,告密者群体一般由绅士组成,到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早期,告密者成了大多数社会渣子的专门职业[14]87。大多数告密者“像商人和工匠在自己的职业中赚取利润一样,把掌握信息和举报作为添补自己收入的主要手段,他们的腐败行为是直接的和要求不高的。据1630年代威尔德郡的商人报告,告密者敲诈勒索的金额从5先令到10先令到200镑不等”[15]60。
1552年,就在王室鼓励告密者的行为之时,朝野上下的批评也随之而起,他们认为,告密者的举报行为是出于个人利益,出于私怨,在其监督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腐败行为。尽管不是所有的告密者都是腐败的,但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对告密者腐败的指责是非常普遍的。各级法庭对告密者所提供信息的采纳也是有限的,在伊丽莎白统治的第 13年,一个名叫约翰·克拉普内尔的告密者给国王法庭提供的70条信息中,只有1条被采用[16]239。
面对如此情形,一方面王室政府需要获得地方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这些官员的非法行为的情况,另一方面,报告这些情况的群体又陷入报告不实尤其是自身腐败的境地,中央政府一筹莫展。甚至一直反对利用告密者的爱德华·科克爵士也只能提出折中的办法,他在1621年的议会辩论中提出,“告密者一定不能全部清除,而只能加以规范”[15]64。因此,从都铎后期开始,王室政府通过立法和颁布文告等方式规范告密者的行为,限制告密者权力的滥用。据《王国法令》,在伊丽莎白时期,议会曾3次立法阐释告密者的作用和限制他们权力的滥用。杨格在论述王室如何处理告密者时叙述道:
在我们讨论特殊权力滥用之前,探讨文告对告密者的保护和对其行为的规范是有益的。枢密院提议把他们全部排挤掉而以治安法官委员会取代之,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修改后的方案是保留告密者,但是要严格限制他们的数量,1566年 10月把这一方案通过文告的形式颁布了。[17]137
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因为告密者开始把目标从商人、关税官员和一般地方官员等转移到高级官员身上,严重冲击着现有的行政秩序特别是潜行政体系,詹姆斯也就开始束缚告密者的行为。议会也认为,这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监督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也不利于制度建设,因此也强烈要求立法限制告密者的行为。1604年议会的一份提案就开始要求改革现存的告密者制度,要求限制告密者权力的滥用。枢密院则在1617年采取行动反对告密者之中的腐败行为。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好告密者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了查理一世统治晚期,这一问题还困扰着统治者。我们通过阅读1635年9月6日颁布的王室文告(A Proclamation for prevention of abuses of Informers,Clerkes,and others in their prosecutions upon the Lawes,and Statutes of this Realm)可略见端倪。文告尽管没有单独将告密者列出,但是对文告中所列的人(包括告密者)在实施或执行法律时的种种对权力的滥用行为进行了列举,并提出了防止滥用权力的有关办法,进而指出对滥用权力者进行惩罚的措施[18]472-480。
由此可见,从都铎晚期到斯图亚特早期,由庇护制所决定的社会监督是建立在告密者制度之上的,一方面,由于告密者的举报和提供所需信息,有利于法律、法令和文告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对商人、经济领域的官员、地方官员乃至高级官员的监督;另一方面,有的告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举报失实,甚至告密者自己也陷入了腐败之中。这就使得这一形式的社会监督陷入两难之境,要获取地方和官员的基本信息,必定要依赖非官员的社会群体,而这一群体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之低以及他们自身职能的异化,又使得这一可靠性太差。于是,以告密者制度为主的社会监督就会流于形式,也就缺乏力度。在这一情形下,又怎么能够对贵族官员之腐败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呢!
收稿日期:2006-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