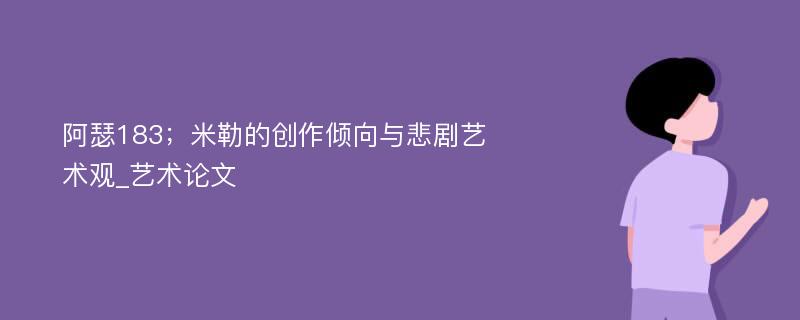
阿瑟#183;米勒的创作倾向和悲剧艺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阿瑟论文,倾向论文,悲剧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阿瑟·米勒一直关注戏剧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谕作用。他把戏剧分成三个等级,认为“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跟国王一样,都是适于作为悲剧描写的对象的”。
关键词 米勒 戏剧 社会功能 悲剧 普通人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阿瑟·米勒认为戏剧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从30年代的《黎明的荣誉》(Honours at Dawm)、《他们也起来了》(They Too Arise)到40年代末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以及50~60年代的《严峻的考验》(The Crucible)、《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和《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等,阿瑟·米勒一直关注戏剧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谕作用。他指出:“不仅现代戏剧,整个文学——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都有一个道德观的问题:是与非、好与坏、高与低。不是简单地提出这些道德观念,而是‘通过表明所谓罪恶的程度来反映。”[①]米勒十分推崇易卜生,并在创作中继承了他的社会剧传统。他甚至改编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人民公敌》。1951年,他在为改编本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必须再次让公众明白,舞台正是进行思想探讨、哲学探讨和最热烈地讨论人类命运的场所。”我们从上面提到的《推销员之死》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刻地解剖社会、反映社会生活,大胆地暴露丑恶,热忱地探讨人生真谛的努力。《黎明的荣誉》是阿瑟·米勒的第一部作品,属于30年代典型的左翼作品。该剧描写了主人公麦克斯的思想觉醒过程。麦克斯无意中被卷入了罢工示威的行列:随着剧情的开展,他逐步认识到,为了根除周围种种腐败和不公正的现象,工人有必要团结起来。从该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勒创作中某些一贯的东西,即将个人品格的正直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道德的背景之下,从而提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他们也起来了》是作者为反映经济大萧条而创作的一部剧本,描写了主人公艾贝·赛蒙在经济大萧条的年月里如何竭尽全力地挣扎,企图使自己的公司免遭倒闭厄运的过程。有人认为该剧是“对生活和现代社会诚实的、人道的反映”。剧中另一重要人物阿尼是个新人的形象,作者突出了他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并通过他使其父亲艾贝·赛蒙获得转变。显然,米勒在《他们也起来了》一剧中树立了他理想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准则。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道德规范上。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这10年,是阿瑟·米勒创作力量旺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对社会的洞察更加深入,对人生的体验更加深刻。当然,这一时期戏剧技巧在他的手里也日臻丰富和自如。他在《桥头眺望》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这一代人的社会剧应该不仅仅是分析并指责各种社会关系网。它必须探讨人存在的本质,以便发现他有哪些需要,从而使这些需要在社会中受到重视,得到满足。”从米勒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所创作的剧本来看,他确实是根据自己的这一认识去做的。《全是我的儿子》首先是一部社会问题剧,但是它对主人公乔·凯勒的描写并不是纯粹谴责性的,而是展开了人性的多层面,表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米勒曾谈到自己如何产生关于该剧创作冲动的过程。一天,米勒家的一位亲戚谈起她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邻居的女儿,因为父亲把质量不合格的零件卖给军队而告发自己的父亲。米勒听后大为感叹,认为这女孩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社会道德感的体现。他说:“自从我开始写剧本以来,我第一次对自己要写的东西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这就是剧本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即对于令人厌恶的危害社会行为的揭露。”[②]主人公乔·凯勒把坏零件卖给空军部队,并将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合伙人,最终造成21名空军战士失事身亡。面对这一滔天罪行,凯勒的儿子大声谴责道:“你究竟凭什么说你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是为了我?你难道没有自己的国家?你难道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该剧留给人们的既有对罪行的控诉,又有对人性、对道德行为准则的思索。《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戏剧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杰作。它向我们揭露了一个只可认可“成功”的社会,而它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恰恰是一个渴望成功却又屡遭挫败的可怜虫。这个极普通的小人物的梦想的幻灭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而这一点正体现了这个标榜美国社会对每个人都提供无限发展可能性、使人人有成功机会的“美国神话”的破产。在指出追求成功的“美国梦”必然破灭的同时,作者又以充满人性的笔调,刻画了威利与比夫父子间的爱与恨,给剧本打上了道德教谕的烙印。《推销员之死》明显地影射了30年代美国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归根结底,米勒用戏剧形式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剧中的俚语、灯笼短裤、史蒂倍克老爷车、哈斯洛斯牌电冰箱以及剧中对成功所下的幼稚的定义,都使人想起三十年代那段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中产阶级环境。”[③]威利的一生“集中体现了带有美国三十年代特征的一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道德纯洁与自我放纵、朴实的自立与多情的交际、自负的乐观与恼人的不安全感。”[④]
1953年1月上演的《严峻的考验》一剧取材于1692年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一起大冤案。阿瑟·米勒通过冤案始末的描写,揭示了罪恶势力的冷酷无情,歌颂了在严刑酷打和死亡面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人性的弱点。阿瑟·米勒为什么要写这段发生在250多年前的历史呢?这显然和本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镇压进步势力,疯狂逮捕、监禁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一现实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阿兰·特拉赫登堡在《战后美国文学的知识背景》一文曾这样写道:“在这一阶段中,一种‘冷战’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着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这样的感情在50年代达到了歇斯底里的顶峰。这时期,专搞政治迫害,列黑名单、做忠诚宣誓、指控颠覆、审判间谍和叛徒、囚禁共产党人和其他被控搞‘阴谋’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生活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恐怖时期的进步作家,米勒对当时那种充满恐怖的压抑气氛有着亲身的体验。他自己不仅被列入黑名单,而且遭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长期审讯。这种令人压抑的现实,使米勒联想起25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著名萨勒姆冤案。米勒仔细阅读了审判的详细记录,核对了当事人的大量证词,力图用艺术手法将这一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重新揭露出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写出并上演这个剧本的重大意义,它本身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和正义感。米勒曾说这是一出硬戏。他希望通过写“一出有针对性的戏”来唤醒人们,激励人们的斗志,这种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作者将萨勒姆冤案与麦卡锡主义的恐怖统治联系起来,使作品带有政治剧色彩,这也是个事实。正如凯瑟琳·休斯所说:“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严峻的考验》是米勒最有‘倾向’性的剧本。”[⑤]但是,“它通过大难临头时人的种种表现——软弱、自私、叛卖、告密、见风使舵、逃避责任以及坚定、隐忍、忠诚、无畏等,向人的良知发出呼吁: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人既不能逃避责任,也不能否认其后果。”[⑥]60年代初,米勒带着《堕落之后》和《维希事件》重返剧坛。在这两部剧中,米勒企图将社会批判和细致的心理分析融为一体,以此来进一步表现人的道德危机,来揭露人性的弱点。作为一位执着的剧作家,米勒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下定决心不逃避现实和责任。
在继承易卜生的社会剧传统的同时,米勒并不一味地模仿。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和易卜生或萧伯纳的时代不同。因此,除了“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外,还应该进一步去探索人的心理。在为1955年瓦尔金版的《桥头眺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说:“新型的剧作家如果想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是比过去更高明的心理学家,必须至少意识到要把人的心理世界封闭起来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否则他就永远写不出悲剧来。”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可以说是将社会剧与心理剧结合得十分完美的典型。这种结合,既保存了社会剧的尖锐性和批判性,又融入了心理剧的细腻和深刻,使作品提高到了现代悲剧的高度。为了更好地认识阿瑟·米勒的创作倾向,我们有必要了解他的艺术观,特别是他的悲剧艺术观。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倾向性和艺术观往往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1949年3月,米勒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悲剧的特性》一文,提出了悲剧的定义,并将戏剧与情节剧、戏剧与悲剧加以区别。他认为,表现人与人之间外在冲突的情节剧虽然也能产生某些紧张动人的效果,但是品位不高,永远不可能上升到真正的正剧或悲剧的高度。只有当剧本不仅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而且也表现人的内心冲突时,它才能突破情节剧的窠臼而走向正剧。至于悲剧,那就不仅需要表现人物灵魂的冲突,而且还要具有令人振奋向上的精神。米勒指出,许多人分不清悲剧性与悲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悲剧和怜悯的根本区别在于悲剧不仅能激起我们的悲伤、同情和怜悯之情,甚至还有恐惧;而且,还能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启迪,使我们的思想得以升华。“悲剧之所以被称作是一种令人意气风发的意识,是因为它使我们觉察到人物原本可以达到却没有达到的境地。因而悲剧和对人类动物抱有某种适当的希望是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闪现出这种较为光明的可能性,才把悲怆中所包含的的哀婉提高到了悲剧的境界。”[⑦]米勒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总之,悲剧是对人类为幸福而斗争的最精确的平衡的描绘。我们最为敬慕悲剧的原因就是因为悲剧以最真实的方式来刻画我们。这也是不应当由于与其他形式混淆而降低悲剧的地位的原因,因为悲剧是我们拥有的最完美的手段——它表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人或我们应当力争做到的那样的人。”[⑧]
关于现代社会能不能产生悲剧,本世纪以来一直成为众多评论家们讨论的中心。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勒奇认为,在一个没有特久的理想、缺乏英雄主义精神的世界里,现代人毫无精神支柱地摸索着;在一个对人、对上帝没有信心的时代里,人是无法从悲剧的高度来肯定生活的。对于克勒奇的这一悲剧观点,持同意态度的人认为,悲剧诞生在英雄崇拜的时代,而在一个以破坏偶像为骄傲的时代里,悲剧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悲剧需要的是振奋、肯定、赞美以及恢复对人的信心。而我们这个人性受到扭曲的时代只能造就平凡、萎琐、低能、歇斯底里或者毫无血气的庸人。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然而,米勒从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身上看到了悲剧的因素。在1949年2月《推销员之死》首演的同一个月里,米勒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代表他悲剧思想的代表作《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我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同样适合于作为最高超的悲剧的题材。从表面上看,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衡量,这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现代精神病学是以古典程式为基础的,例如恋母情结和杀母为父报仇心理,这些都是王族人员的表现,但是在类似的感情状况之下却适用于任何一个人。”[⑨]他强调说,“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种种革命之中,普通人已一再显示了这种属于一切悲剧的内在动力。”[⑩]在米勒看来,那种坚持悲剧人物非有社会地位不可,或必须出身高贵的观点,只是抓住了悲剧的表现和外在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关心的已经不是那些王公贵族的生活了。“可以肯定,一个君主从另一个君主那里夺取领地的行为已经不再能够引起我们的激情了,我们对正义的概念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帝王所想的不同了。”(11)米勒强调普通人生活中同样有悲壮的一面,有着可歌可泣的一面。普通人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最能体会当今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畏惧和灾难,而这些正是传统悲剧所忽视的。米勒认为,无论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有同样的精神变化过程。假如悲剧性行动的高贵气质真正仅仅是身份高贵人物的特有品德,那么大多数人居然会将悲剧置于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之上去珍爱它,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更谈不上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它了。”(12)因此,米勒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推销员、农民、店员、警察、码头工人等一批中下层人民的悲剧形象。他在作品中探索这些普通人的心灵,表现他们与环境的斗争。在《推销员之死》中,米勒为我们刻画了威利·洛曼这一最普通人的悲剧命运。推销员威利·洛曼作为美国社会中最普通的一员,其悲剧命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生道路上的失败者;“美国梦”的受害者;一个失去威信、不称职的父亲;一个被不明智、不理解丈夫的妻子所纵容的牺牲品。(13)作者在1950年2月发表的《推销员的诞辰》一文中指出:“威利·洛曼的悲剧在于他献出了生命,或者说他出卖了生命……,这是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确实相信他本人没有达到那些居住在广播及广告办公室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峰人物为人类所规定的资格。从那些罐头成山堆得高耸入云的地方发出了雷鸣般响亮的命令,叫他去获得成功。这个命令在他居住的城市中那报纸成堆的地方回响着,但他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一股狂风的声音,对此没有人能够以同样的手段作出答复,所以只好直瞪瞪地盯住镜子映出的失败者的面容。”(14)诚然,作者在刻画威利这一悲剧人物时,不仅仅停留在对“美国神话”的揭露和谴责上,不仅仅满足于阐述某种思想。作者显然力图跳出社会剧的框架而使作品升华成为真正的悲剧。同样,米勒还在其他剧中刻画了一系列其他悲剧角色。他们有:《全是我的儿子》中的乔·凯勒,《严峻的考验》中的约翰·普洛克特,《桥头眺望》中的爱迪·卡朋,《堕落之后》中的昆廷和麦琪以及《维希事件》中的冯·伯格等。这些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证实了米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中所写的关于英雄的断言:“我认为,当我们面临一个在必要时候准备牺牲生命来维护个人尊严的人物时,他会唤起我们悲剧的情感。从奥瑞斯特斯到哈姆雷特,从美狄亚到麦克白,潜在的斗争就是个人企图在他的社会中获取‘公正的’地位。”[①⑤]
当然,米勒关于情节剧、正剧和悲剧的划分有其理论上不够严密之处。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确确实实在创作中实现自己的理论。他的作品处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显示出他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前景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注释:
①阿瑟·米勒:《论社会剧》,见《阿瑟·米勒论戏剧散文》P.59。
②Arthur Miller:"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ed Plays."New York,1957.P.17
③ ④伦纳德·莫斯:《阿瑟·米勒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P.62。
⑤凯瑟琳·休斯:《美国当代剧作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P.56。
⑥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107。
⑦ ⑧《悲剧的特性》,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罗伯特·阿·马丁著著 陈瑞兰译。
⑨ ⑩ (11) (12) (15)《悲剧与普通人》,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罗伯特·阿·马丁著、陈瑞兰译。
(13)见拙文《一个最普通人的悲剧》,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4)《推销员的诞辰》,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罗伯特·阿·马丁著、陈瑞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