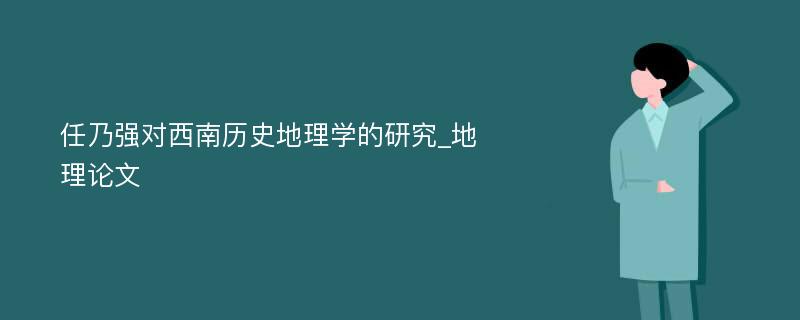
任乃强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论文,历史论文,任乃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3-0056-08 任乃强(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县人,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早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堂,攻读农业经济地理,并由地理学而及历史学、民族学之研究。任乃强国学根底深厚,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在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格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①任乃强一生之治学基本集中在西南地区,学界就任乃强的学术研究概况已多有论述,②然鲜有就其历史地理学之研究做专门探讨,本文兹就其在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略作梳理,疏漏之处尚祈指正。 一、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 任乃强学识渊博,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平生致力于西南及边疆史地的研究,长年奔走于西康地区。③就历史地理学而言,其一生治学大体涉及康藏历史地理、巴蜀及西南史地、历史地图的绘制以及民族、物产等方面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 (一)康藏历史地理研究 1949年以前有关藏区地理的出版物计有十数种之多,在藏区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尤以任乃强为代表,他的《西康图经》之《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④他“弃安适之生活,赴康考察,于是得有长时间与土著各民族接触,研究其语言、历史、情俗以及生产消费、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各个方面。以历史地理学之方法探究康藏民族之社会发展历史,……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⑤“自来言康者,此为最矣”。⑥他勤于考察并时常案之于文献,对康藏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多有考证界定。他认为“多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就‘藏地三区’这一民族地理概念来说,‘多康’指的是卫藏、阿里地区以东,包括青、甘、川、滇藏族地区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就狭义来说,它具体指的是卫藏和多麦之间的这一藏区”。⑦同时,除了对西康江河异名的疏证外,他对康藏名称及其境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也有精辟的见解,针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西译之书的混淆,以讹传讹,以至于对康藏地区的境域和民族都认识模糊这一状况,任先生都一一予以指正。⑧他认为藏人将藏区地形分为塘、捉、冈、陇四类不符合自然地理之原则,不能包举地形之全部。随着其阅历增多,“渐得藏区异地相似之点,于是类别地形得其组织定型”。以三千米为准绳,将西康高原分为高原之部(三千米以上)和峡谷之部(三千米以下),高原之部进一步划分为雪岭、草原(高原草场)、浅谷(高原农地),峡谷之部进一步划分为冈(三千米以下之山巅)和深谷,最后,再根据不同的地形下垫面状况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十一种小类型。⑨任乃强对康藏地形的科学分类,为后进学者的康藏地理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巴蜀及西南史地研究 任乃强对巴蜀及西南史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巴蜀州县地名及建置沿革考释、历史史实的澄清和对巴蜀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上。 他对巴蜀地名的考释主要是针对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以及除大城市以外的温江、绵阳地区、内江、乐山等地地名来历和发展变迁做出疏证。⑩同时对西南地区的史实和交通也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庄硚是顷襄王时入滇,则所取道为溯江溯沅”;(11)“蜀枸酱入番禺路,为剥隘、右江一路,不可能是其它三路,唐蒙所言之牂牁舸江即今之南盘江与西江之称”。(12)在张献忠屠蜀这一历史事件上,任先生认为,明末蜀人大量死亡的原因及责任不能只归咎于农民军,“农民军固恃人肉为粮,明兵实亦相掠而食”,蜀地人口大量损失的原因也有地理方面因素的存在,因为“四川号称天府,历来为人口稠密之区,然对外交通不便,每值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则常以饥荒成浩劫”,史学研究者没有进行缜密的考察就凭主观直觉妄下论断,“徒欲褒扬所谓忠义,记载遂多失实竞以浩劫全案,归罪于献忠一人”。(13) 《华阳国志》是一部关于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任乃强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一鸿篇巨制,又认为地方志几百种莫不推《华阳国志》最为典型。(14)1960年以后,任乃强发愤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他花了30多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巨著。他参阅了30多种版本及大量的文献典籍,拾遗补缺、诠释注解并插图30余幅,由于其谙熟西南史地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自然科学知识,纠正了前人诸多讹误,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著作被称为“西南古代史之百科全书”、“《华阳国志》之定本”。(15) (三)西南历史地图的绘制 任乃强喜欢搜集关于川边之图书,而地图尤备,“十年以来,颇有收获,而地图尤备……属线路图者十种……关于木雅贡嘎之地图四种……市落部分地图五种,地图集两种……单幅泸定县全图三种,共得泸定地图四十四种”。(16)他搜集有川康地质图、川边新图、川边地图、川边土伯坦图、川边各县舆地图等44种有关川边的地图。他不但对这些地图按照地质、交通等内容做出合理的分类,而且还对其底图、着色、印制技术、图纸材料等方面作出科学的评价,为以后的川边地图绘制提供参考。(17)在此基础上,其对康藏地图之绘制亦倾注了大量心血,所绘之地图总是力求科学精确,“近编绘十六区地图,用实测经纬度定点,再依据若干中西探险者与实测者之地图、地记组织填绘,其各部落界线均经绘出,面积数字可按缩尺推求,因尚未借得测面积器,尚不能分别列出”。(18)而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是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为蓝本,参合前人绘制的地图及自己考察绘制的各县地图纂合而成,收集很多处测高点,并绘有等高线等。(19)地图的搜集、编纂成为任乃强有关边疆民族史地著述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自有感于在西康考察中面临的地图匮乏之弊。自1928年起至1936年9月,其共收集相关地图380余种、920余幅,为以后编绘地图的需要,他分总图、部分图、县区图、邻境图四类编号造册,为统一体例撰写了《西康地图谱》,成为其制《康藏标准地图》的基础。任乃强还结合当地政工人员的协助,绘制了县乡镇村图,最后绘成百万分之一的《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分县地图》。(20)这张用现代圆锥投影法、经纬度定位,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绘制成的我国第一张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藏分县地图》填补了我国地图学上的一项重大空白,也为我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起到重要作用。(21) 此外,任乃强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书》是第一部以地图形式记录四川州县建置变迁的专著,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意义,也是其在历史地图绘制方面成就的重要体现。 (四)其他方面的西南历史地理成就 除上述以外,任乃强在西南历史地理学的其它领域也都有自己的建树。关于西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在传统阶段的前期主要以川康及青藏少数民族调查为主。在这方面,解放前任乃强即做出一定成绩,发表许多考察报告与论著。(22)其中以对达布人的分布认识最具代表。他认为当时达布人分布的地面,恰好是在仇池以西、带水以南的地方,他们是坚强保守自己风俗的民族,居住在深山穷谷,汉人足迹难到之地,既未被吐蕃所同化,又未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可以估计其人就是宕昌二百余落之一的后裔,这自然还只是他就历史地理和文献记载作的初步推断。(23)正确解决民族族别,只能注重调查,调查工作又首当注重语言,并需探索各民族历史阶段的地理环境,校订它所可能发生变化的方向,才能够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24)探讨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研究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因为地理因素乃是影响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起着制约或促进民族发展的作用。(25)同时任先生也认为民族的分布受自然地理的影响极为深刻,因为海拔高度影响各地气候,气候又影响到生物的分布。由生物分布的限制影响各地住民的生业和一切有关生活的经济与文化各情形。故如研究十六区的内容,最好是从地理下手,而研究十六区的地理,不必在一山一水上去苦用工夫,只需能明了他山水生成的原因与其结构的公式。(26) 任乃强对康藏地区的交通地理也多有研究,其中对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较为典型,他以实地考察与文献结合证明,“刘元鼎入蕃会盟全部路线、道路距离、沿途情形,皆与今日自西宁经玉树入藏路线吻合,亦与藏史所传文成公主入蕃路线及《唐书》所传文成公主入蕃事皆合,更无可疑之义,世乃谓公主系自打箭炉入藏者,实属荒谬”。(27) 我国金币的使用只有战国末年到东汉初年的三百余年,史籍所载的黄金使用情况很多,但对黄金的产地却没能形成系统记载。任乃强认为,根据记载可以大致推断金矿的地理分布,由于当时冶矿技术原始,大量金币的使用可能需要从西、北两方牧区输入。(28)同时任乃强对四川的物产地理分布也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他将四川一百四十八县依据地势划分为盆内、盆外、盆舷三大部分及若干小区,根据各区自然地形地貌的形成过程来论述矿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分布原因,又根据土壤的性质类型来说明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各种农产品的地区分布差异。基于此,通过各区自然气候条件、地形、交通状况来描述四川省各地区间物产分布的差异及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29)任乃强根据对“临”字的研究,发现秦汉之际的地名带“临”字者,则几无不具食盐之义,(30)以此为据勾勒出了四川地区的盐矿地理分布,可谓见解独到。 二、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学特点 任乃强学贯古今,将学术研究作为人生的不懈追求。自1928年撰著《四川史地》一书起直到其与世长辞,共有专著25部、论文300余篇,学术成果丰硕。其关于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治学特点,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成立了康藏研究社。他的这一举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赞誉。这也是他对当时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积极响应。关于对泸定地区的考察涉及到该区的边界、名胜古迹、人物、风俗观念、交通状况、政区演变、经济发展变迁、民间传说、文化民族分布、宗教信仰、物产、自然气候、金石碑刻、乡土志书等。他对史志后学者谆谆教诲,说治史的经验,总括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历史和地理综合起来研究,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他向贺龙提供很详细的西藏地图,正是史地结合综合研究的结果。(31)以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也证明了文成公主入藏路线与自西宁经玉树入藏路线吻合,纠正了以前的谬误。任乃强以自身的经验得出,从事民族研究需要将历史与地理结合,通俗的理解为文献与实地考察互为辅助,对于康藏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更需与民族地区百姓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32)对于古代遗物更应文献与考察的紧密配合,如在民国三十年,任乃强因纂修《西康通志》特往寻访与高颐阙同艳的芦山樊敏碑,他“辨其石色与砌痕,判为汉魏时物,斥狐妻说荒谬”。又见周凤山所著《芦山县志稿》记载有月亮石,他自往姜维祠访之,并未发现此石,只见到两个石兽。他再查《芦志·古墓门》,疑此石碑是杨巽墓遗物,后经进一步发掘,确实如此。(33)他通过实地勘察还发现“唐宋以来方志书,则无不妄谓邛竹杖为蜀地邛崃山所产,即张骞大夏所见者。一言以蔽之,临邛至邛都间,决不能生产高节实中之山行杖材。我既经踏勘,固未曾有;衡之物理,更不能有;参详文史,自亦不得如此”。(34) 其二、注重地图的大量运用 任乃强对地图的使用相当重视。鉴于当时国内没有关于康藏地区的精确地图,就以自己实测为基础参考古籍,历时十余载,得绘较为完备之康藏全图,后为西藏解放事业也带来了便利。对于边区地图绘制,他都经实地考察后做精确绘制。如对四川边区十六区地图的绘制即是如此,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也就是茂、理、松潘、汶川、懋功、靖化六县地方,号为四川的边区,与四川内部的一切情形不同。相对较高的海拔位置致使地表的生物分布较大差异,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该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情形,因此对该区的研究应先从自然条件入手。任乃强从地貌入手,将该区划分为东南山谷区和西北草原区,进而划分为若干小的流域,并将之绘入地图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任乃强“近编绘十六区地图,用实测经纬度定点,再依据若干中西探测者与实测者之地图、地记,组织填绘。其各部落界限均经绘出,面积数字,可按缩尺推求。大抵,草地面积可三倍于山谷区,而俄洛区面积又约占草地面积三分之二。”(35)他以图来阐释地理、历史,用传统“左图右史”的治史方法来描述地理问题,表现其精湛的制图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古代文献中的地理记载都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郡治在首县与否,都待经过把地名落实到地图上来才分辨得清,望文生义,给地名沿革乱贴标签就会贻误后人”。(36)“旧籍沿革资料完备,但无今地可指,而县志又曲解妄指,与客观条件不合,必须重新探索,就县志资料纠正县志,从地图上的空白处另自找出正确位置来的”。(37) 其三、注重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 任乃强接受了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现代研究方法,注重实地考察,把藏语学习看作研究藏文化的入门工具,在康藏史地研究上打破传统的描述藏区舆地建制沿革的传统模式,根据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宗教学等现代学科的基本理论,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相互渗透、比较归纳研究。(38)他一系列著作论证了德格土司世系及其与萨尔王传的关系。这些论著以中国历史传统研究法为基础,借鉴外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研究德格土司世系,为后人研究德格土司奠定了基础。(39)如他在1949年关于德格世系研究中,与李安宅同游德格,并随身携带德格相关史料进行实地考察,询问土司家臣,回程后与谢国安等先生共同考订出德格土司世系。他运用语言学知识解释了“赞”、“禄”、“阿尼”等藏语的意思,为理清德格世系做称谓的解释工作,用宗教学的视角解释土司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以民俗学的手段来解释土妇转房事件,以历史材料为基础指出康藏行政区划的划分不重地形而在历史之传统,德格境内之飞地与世系关系密切。(40)任乃强用跨学科视角,从多方面论证和梳理了德格世系,为德格土司相关之研究提供依据。因此,可以说,任乃强作为一个胸怀学以致用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边疆民族研究中博采众家之长,经济地理、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均在其视野之中,是一位跨越学科边界、非学科化的学者典范。(41)而自1939年起任乃强撰成《辨王晖石棺浮雕》、《樊敏碑文义集解》等文,对这些文物及其涉及的汉代青衣江流域民族与汉文化的关系详加考证,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42)“三年来,数过芦山,屡审原石,更参诸家,详稽群史,私撰为樊敏墓石图考,樊碑集释樊敏年谱等”。(43)参用了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方法,并用金石学的方法,与文献配合解释汉墓及其随葬物品的真相。此外,任乃强早年专治农学,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植物、矿物的文化分析尤为精辟,这是许多文史学者所不具备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首次运用现代西方地学知识,描述和分析康藏高原的地质、地理、气象和水文。(44)此外,他还对四川省的物产分布作出了科学的研究,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 任乃强并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其治学始终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理念。他这种治学理念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学术视角,也得益于时代环境的推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西南由此成为抗战的重心,然当时西南的现实状况远远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全方位的开发西南,从各方面进行考察,为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依据。而西南民族众多,历史上政权林立,地理状况复杂,从历史地理角度对西南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此时,大批史地学者和教学科研机构云集西南,他们应西南开发的需求,积极开展西南历史地理的教学、科研工作,对西南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45)任乃强在抗战时期的地方志《康藏史地大纲》即为该时的经世之作。 任乃强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的形成也受到其自身所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四川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对其研究理念影响颇为突出。上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1941年李安宅、任乃强等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边疆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藏族的文化、历史和宗教。重点对藏传佛教各派做实地考察,收集大量的藏文资料文物,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得出汉藏互补,相互依存的重要观点。(46)40年代以后,巴蜀研究逐渐成为川大史学系的区域研究课题。在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7)到了8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地理学继续发挥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传统,但主要是对历史地理志进行研究,如刘琳、任乃强对巴蜀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的研究。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传统阶段以巴蜀文化地理研究为主,在现代阶段主要转为巴蜀城市地理及地理环境的研究,如刘琳、任乃强、郭声波等。关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在传统阶段,其前期主要进行川康及青藏等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调查为主,在这方面,民国时期的华西边疆学会等一大批外籍教师及谢国安、任乃强等做出很大成绩,发表了许多考察报告及论著。(48) 任乃强的经世致用理念也来源于自身所饱含的民族大义。到了近代,随着川边开发——改土归流和川边史地之学的兴起,一些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开始了对德格土司的调查研究,研究论著纷纷问世,任乃强用的一系列论著论证了德格土司及其与萨尔王传的关系。(49)用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土司,了解土司。针对西藏地图的绘制问题,任乃强认为“在解放前很少有人对西藏的地理、社会情况做全面的调查研究,英国人为了侵占西藏公然到西藏甚至到川藏边勘察资源,测绘地图,搞社会调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羞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搞调查研究,我才下定决心,利用修志的机会想搞出一份像样的地图来”。(50)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解放西藏,贺龙曾征求任乃强对西藏问题处理的意见,任乃强的倾向是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他还谈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以及进军西藏要注意的一些问题。(51)任乃强在关乎民生的川康交通问题上的态度是“顾国人之为川康交通设计者……皆井蛙之见也,真欲解决川康交通问题,应从川康间地理上实施调查着手,考究所有大小路线,比较文化优劣,相其所宜,因宜设计,从事开发”。(52) 任乃强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以为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变时空之影响也。因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53)他早年欲实现以农兴国的理想因而从事农业地理研究,毕业后又积极从事教育改革,以图实现教育兴国的理想,当边疆出现民族危机时又投身于康藏地区的史地研究意在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引起世人对康藏地区的重视。任乃强对关乎人类生存的人地关系也极为重视,1928年编写《四川史地》一书,发觉四川盆地曾于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发生人烟灭绝之劫三次。而究其原因,皆与人口极度膨胀,地不足以养民有关。以为预防之计,首当开发川边民族地区,消除边腹民族之扦隔及经济发展之差异。(54)在他对四川地名的考释过程中,发现盐亭县“县不产煤,煎盐用木材,残毁山林后,盐业渐衰,成为川北贫困小县”。(55)在对该县地名考释的同时阐明了历史时期以来该县经济衰退的原因,为后来推进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此实皆为当前历史地理学十分重视的人地关系研究之典范。任乃强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在边疆多事之秋,从事民族问题探讨和地图绘制足见其忧国之心。 任乃强在治学上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理念,主张历史书写与社会现实的融通,历史过程与现实格局的关联,要从整体角度上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与区域时空的互动关系。(56)基于此,对康滇间各民族历史宗教、政治、族群源流做出精深探讨,探求其区域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达最终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目的。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言创刊主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任乃强的治学可以说很好地践行了这一主旨。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界对顾颉刚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者的关注较多,对任乃强的历史地理贡献则多强调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一部历史地理古籍文献精品,是研究西南史地的潜心之作,(57)显然,就任乃强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实际研究而言,这一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顾颉刚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那么将任乃强定位为中国现代西南地区特别是康藏历史地理研究的奠基人应是不为过的。随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任乃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会逐渐被学界所认识,其治学思想和理念实亦当为当前及后世史学研究所借鉴。 [收稿日期]2015-04-15 注释: ①任新建:《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序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具体可参见王雨巧《任乃强1894-1989学术及其治学特点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徐振燕《任乃强的西南图景》(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任新建《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杨鸿儒《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强教授》(《西藏研究》2010年第10期)、刘冠群《贺龙与藏学专家(二)》(《民族团结》1997年第2期)、木仕华《试论任乃强先生“开辟康滇间地之四大动力”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等文章对任乃强的经历和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论述:2009年8月成都举行的纪念任乃强专题会议“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亦有众多专家就任乃强及康藏史研究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 ③刘冠群:《贺龙与藏学专家(二)》,《民族团结》1997年第2期。 ④王启龙、邓小咏:《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⑤任新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⑥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序》,见《中国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任乃强、泽旺多吉:《朵甘思考略》,《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⑧任乃强:《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⑨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见《中国藏学文集》上册。 ⑩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170-269页。 (11)任乃强:《庄硚入滇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121页。 (12)任乃强:《蜀枸酱入番禺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134页。 (13)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辩》,《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86-88页。 (14)卜艳军、李新伟:《华阳国志浅论》,《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1期。 (15)杨鸿儒:《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强教授》,《西藏研究》2010年第10期。 (16)任乃强:《泸定考察记》,《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498-505页。 (17)任乃强:《泸定考察记》,《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498-505页。 (18)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19)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遗稿),《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 (20)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21)王雨巧:《任乃强1894-1989学术及其治学特点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22)王小红:《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3)任乃强:《达布人的族源问题》,《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589页。 (24)任乃强:《达布人的族源问题》,《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600页。 (25)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602页。 (26)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27)任乃强:《文成公主下嫁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517页。 (28)任乃强:《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3期。 (29)任乃强:《四川省之自然区划与天产配布》,《地理学报》1925年第4期。 (30)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196页。 (31)刘冠群:《康藏情况报告和几位藏学专家》,《文史杂志》1997年第5期。 (32)王雨巧:《任乃强1894-1989学术及其治学特点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 (33)任乃强:《芦山新出汉石图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33页。 (34)任乃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148页。 (35)任乃强:《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287页。 (36)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207页。 (37)任乃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348页。 (38)罗润苍:《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39)杜永彬:《德格土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40)任乃强:《德格土司世谱》,《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第250-270页。 (41)王建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边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42)魏学峰:《任乃强先生的治学生涯》,《文史杂志》1989年第5期。 (43)任乃强:《芦山新出汉石图考》,《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71页。 (44)徐振燕:《任乃强的西南图景》,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45)肖向龙、袁韵:《抗战时期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46)罗润苍:《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47)王小红:《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王小红:《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序),第7-8页。 (49)杜永彬:《德格土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50)邓寿明:《贺龙为解放西藏请教藏学专家》,《四川党史》2002年第2期。 (51)刘冠群:《贺龙与藏学专家(二)》,《民族团结》1997年第2期。 (52)任乃强:《川康交通考》,《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53)任新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54)任新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序》,第2页。 (55)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川大史学·任乃强卷》,第226页。 (56)木仕华:《试论任乃强先生“开辟康滇间地之四大动力”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 (57)林頫:《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标签:地理论文; 地理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任乃强论文; 西藏建设论文; 华阳国志论文; 民族学论文; 四川大学论文; 西藏研究论文; 历史学论文;
